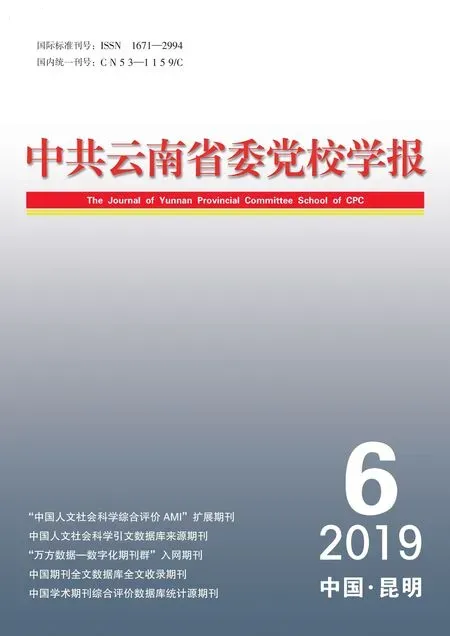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究
杨晓兰
(中共德宏州委党校 科研科,云南 芒市 678400)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民族不分大小、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提高德宏州景颇族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缩小各民族间发展差距,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确保边疆稳定和边境安宁,对于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不能少”意义深远。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德宏州景颇族的跨越发展
(一)景颇族基本概况
景颇族起源于青藏高原北部(今青海省日月山一带),约在1000 多年前,其先民沿金沙江、怒江和恩梅开江南迁至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17 世纪末,大量景颇族逐渐定居在缅甸北部和云南省德宏州一带山区。景颇族分景颇、载瓦、喇期、浪峨、波罗5 个支系,自称为“景颇文蚌”或者“文蚌景颇”(意为“景颇共同体”),常用的文字有景颇文和载瓦文(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德宏州辖区内的景颇族主要分布于全州二市三县37 个乡镇、136 个村委会、1260 个自然村,占聚居区人口总数的47.56%。[1]2018 年末,全州景颇族143586 人,分别占本州总人口数、少数民族人口数和5 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0.91%、22.85%和23.92%,占全国景颇族总人口数的95.86%。陇川、盈江两县景颇族分别占全州景颇族总人口数的33.20%和33.14%。[2]全州景颇族聚居人口20%以上的乡镇有15 个,聚居人口越过50%的乡镇有6个,即陇川县的勐约乡(占75.93%)、清平乡(占57.4%),盈江县的铜壁关乡(占63.66%)、卡场镇(占52.79%),瑞丽市的户育乡(占63.53%)和芒市的西山乡(占92.8%)。西山乡是我国景颇族聚居人口最多和比例最高的乡镇(占全国景颇族人口7.7%),也是景颇族民间传统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国景颇第一乡”之称。
(二)德宏州景颇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跨越
1.社会形态的历史跨越。新中国成立前,景颇族仍处于原始农村公社趋于解体,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云南省委立足边疆实际,批准德宏以景颇族为主的(含傈僳族、德昂族)少数民族山区“不再搞土地改革而通过合作化道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请求,[3]将潞西(今芒市)西山乡列为全省探索民族直过区政策试点乡镇。1954 年5 月“直接过渡”试点开始,西山芒良坝办起了潞西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赵老三合作社,为全省直过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广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政策的实施,解放了生产力,景颇族实现了从原始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跨越。
2.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飞跃。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兴边富民工程、新农村建设及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等惠民政策的叠加,从根本上改变了景颇族村寨刀耕火种、以物易物、刻木(或结绳)记事、缺医少药和封闭落后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级财政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力度更大,边疆民族教育体系更加完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健全,社会保障网更加密实。截至2018 年,德宏州景颇族每万人中已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68 人,高中文化程度人口454 人,有了本民族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景颇族聚居乡村新农合参保率达到10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5%,一幢幢独具特色的民居,使村容村貌有了质的飞跃。景颇族经济社会的巨变,是德宏州发展成就的缩影,更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
3.精准扶贫带动整族脱贫。在德宏州28 个“直过民族”聚居乡镇中,景颇族聚居人口在10%以上的有18 个,占64.29%;在全州8 个建档立卡“直过民族”聚居乡镇和38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景颇族聚居人口在10%以上的有5 个乡镇(占62.5%)、25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占65.79%)。2017 年脱贫攻坚动态管理数据显示,德宏州景颇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7317 人,占全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30.9%。在景颇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陇川县和盈江县,景颇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别占本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的51.99%和31%。
2016 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与德宏州携手制定了景颇族精准脱贫攻坚项目规划,以“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安居房建设、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六大工程45 个项目,全力推进景颇族聚居区精准扶贫。2016—2018年,实施帮扶项目398 项(开工率94.47%,竣工率81.9%),项目覆盖154 个景颇族聚居行政村,景颇族贫困人口5500 户、23600 人直接受益(其中产业帮扶项目覆盖全州37 个乡镇、154 个行政村,近10 万人),项目区贫困人口由2015 年的10821 户、40185 人,减少至2018 年的4040 人,贫困发生率由15%下降至2.83%。2018 年末,全州已有景颇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394 户、18455 人脱贫出列,[4]景颇族整族脱贫目标实现在即,景颇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生存型贫困和素质型贫困交织
1.生存型贫困的消除困难多。第一,深度贫困现象待消除。从县市看,2018 年末,陇川县未脱贫的景颇族人数,占全县未脱贫人数的42.77%;2017年,芒市实现脱贫摘帽,但所辖西山乡未脱贫的建档立卡人数占全市未脱贫建档立卡人数的26.67%,未出列的贫困村占全市未出列贫困村总数的55.56%,贫困发生率为5.81%;瑞丽市户育乡未脱贫户中,景颇族占60.52%。有的景颇族贫困户,虽脱贫出列,但家底薄、抵御各种风险能力弱,因灾、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高。
第二,景颇族聚居乡镇群众收入水平相对偏低。景颇族聚居人口超过50%的6 个乡镇(即陇川的勐约乡、清平乡,盈江的卡场镇、铜壁关乡,瑞丽的户育乡和芒市西山乡),2018 年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0067 元、7816 元、7916元、9417 元、11040 元和8240 元,其中有5 个乡镇(勐约乡除外)均低于本县市平均水平(陇川、盈江、瑞丽、芒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9555 元、10634 元、11940 元、11400 元),5个乡镇(户育乡除外)均低于同期全州平均水平(10325 元)。
第三,贫困家庭缺乏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精准扶贫使建档立卡户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收入来源仍以劳作和国家补贴为主,工资性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甚微,更缺乏持续稳定的产业支撑。致贫原因中,60%以上建档立卡户缺资金。
2.素质型贫困加剧了生存型贫困。贫困乡村学前教育仍较薄弱,少数民族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不到70%;乡村校舍条件改善明显,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但学生厌学弃学现象增加了管理难度。乡村条件使优秀师资难留难引,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适龄儿童持续向城镇聚集,经济较落后乡村的教育教学低水平徘徊的现象,易导致贫困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在景颇族建档立卡贫困群体中,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占41.22%,缺技术占14.50%,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 年,培养新型农民任重道远。
(二)社会治理难度大
从信教群众的分布看:农村信教群众占全州信教总人数的67.86%(尤其是边境、山区村寨较明显),在基督教、天主教信众中,景颇族信众占比较高。例如,芒市芒海镇(景颇族聚居人口占全镇人口总数的36.03%)的7 个景颇族聚居村组,信教人数占本镇景颇族的39.1%。做好信教群众的群众工作,事关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社会稳定。
从人口流动情况看:近几年,在农村务工人员中,缅籍劳工人数不断增多,中缅跨境婚姻在一些经济落后的景颇族聚居乡村更加普遍。例如,陇川县勐约乡的跨境婚姻户,占全乡总户数的11.73%;瑞丽市户育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跨境婚姻家庭占21.47%。大量缅籍人员的流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劳动力的不足,有助于解决贫困青年择偶难,但流入的缅籍人员,多为文化素质偏低者,易使边境乡村智力扶贫任务更艰巨。
从禁毒防艾形势看:德宏州与世界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相毗邻,边境线长且无天然屏障,境外毒源治理难度较大,多种毒品危害并存,给景颇族聚居乡村禁毒防艾工作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三)整族帮扶脱贫有待改进
1.帮扶不够精准。产业帮扶多停留在发放种苗、种畜上,产业发展、乡村规划建设和旅游项目的开发等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有的重基础设施建设,轻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有的帮扶年度实施方案编制不实、帮扶项目储备不够或变更调整大,存在“钱”等项目的问题。
2.帮带机制和减贫机制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偏少,贫困群体对扶持政策依赖性大;乡村集体经济“空壳”的问题解决了,但村集体经济规模小、积累少,带动力弱,贫困户与企业或合作社的利益联动机制运转不理想。例如,2018 年,芒市村集体经济收入在2—5 万元的有52 个,5—10 万元的24个,10 万元以上的仅有4 个,贫困户与企业或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难持续,尤其在培育扶贫龙头企业、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村经纪人等方面困难重重。
3.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一些景颇族聚居在生态功能区(如盈江县铜壁关乡),多数属于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虽然享有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但补助标准偏低(按每年人均1 万元支付生态护林员管护费),生态保护与脱贫发展的矛盾相互交织。
(四)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对民族聚居区的投入
德宏州5 个县市,除瑞丽市外,均属云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梁河县属国家级贫困县),2018 年,德宏州地区生产总值381.1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2.3 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93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25 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04 亿元,经济总量小、税源少,财政自给率不到30%的州情,使其发展举步维艰。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州88%的乡镇无剧场、影院,72%的乡镇无体育场馆,62%的无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66.2%的村无体育健身场所,仍有15.5%的村委会无卫生室、74%的村委会无执行(助理)医师。2018 年末,全州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2351 户、42638 人,脱贫的艰巨与发展的压力,制约了本级财政对“直过区”的专项投入,致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禁毒条例》的落实难以到位。
三、推动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一)围绕高质量发展,抓好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大强调:“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5]“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6]国家“一带一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多项战略覆盖德宏州的机遇,以及多年来德宏州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工作成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各族群众求富思变的强烈愿望与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本州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实难题的破解,更加呼唤高质量发展。
德宏州各县(市)、乡(镇)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加快边疆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高乡村各要素生产率等战略高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统领边疆“三农”工作全局;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推进边疆农村经济社会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加快区域发展,厚植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1.着力打基础、破瓶颈,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发展的重要基础。”[7]要充分发挥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把握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基本特征,加快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和互联网等“五网”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项目落地建成为重点,着力培育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旅游文化、健康产业、高原特色农业等产业,壮大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及时融入“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效循环,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以脱贫攻坚为重点,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深化边疆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更好条件。
2.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把景颇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相结合,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抓实村级扶贫产业规划,在巩固提升优质大米、蔗糖、茶叶、咖啡、坚果等传统产业生产与加工的同时,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产业链长、附加值高、能带动少数民族群众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与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努力实现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的跨越;高标准推进优质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把科技贯通于繁殖育种、种植栽培、田间管理、节水灌溉、农机运用、加工保鲜等环节,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水平,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持续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景颇族贫困群众的生产组织化程度,努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契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整合,注重在质的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引导景颇族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养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行为习惯,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路。
(三)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1.把民族教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能让下一代再过穷日子。”[8]切实抓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的落实,建立健全对民族聚居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营造重学、爱学、助学、奖学的社会氛围。加大景颇族聚居乡镇学前教育投入保障力度,提升乡村寄宿制学校义务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民族小学、初高中学校“民族班”布局和质量,强化定向培养、跟踪培养,为景颇族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多渠道为乡村教师专业技能水平提升搭建平台,进一步改善乡村教师待遇,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稳定,增强职业荣誉感。
2.努力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紧扣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要求,持续实施新型农民培育工程。加强职业教育的普及,完善中等职业教育、高职高专对民族生招生倾斜政策,培养更多景颇族实用人才;依托省州农村干部学院、民族院校、党校,加大对景颇族优秀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村官、致富带头人或专业技术或技能人才、景颇族干部的培训轮训,增强其带动发展的能力;建立健全专技人员定点服务制度,鼓励科技人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到景颇族聚居区发展;优化民族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完善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发展等的扶持政策,吸引退伍军人、大学生及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推广“农村致富带头人示范工程”,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3.强化景颇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团结奋斗的精神,激发景颇族群众的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大普法宣传,培养民族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景颇族群众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引导景颇族在共建共享中缩小与其他民族发展差距;通过吸纳民众参与决策、监督决策、评价决策,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四)发挥政策优势,确保精准扶贫质量
1.用好用足中央、省扶持政策。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预算内资金倾斜扶持“直过民族”聚居区脱贫发展。加大中央、省级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统筹投入力度,抓住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对“直过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机遇,推动金融扶贫与产业扶贫联动发展;建立健全损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现行项目贷款、到户贷款、易地搬迁等金融政策,优先扶持“直过民族”聚居贫困县(市)的贫困乡镇或贫困村实施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旅游、电商扶贫等项目的政策性贷款,鼓励支持“直过民族”聚居的贫困乡村探索走资金互助合作发展之路。结合当前我国减税降费改革,对在“直过民族”聚居区投资兴业的企业或社会团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给予更多税收、信贷、用地等政策优惠;加强与长江三峡集团合作,使各方帮扶的过程,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成为发达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合作发展的过程。
2.完善减贫帮带机制。落实企业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的挂钩奖补政策,对建立减贫带贫机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评估授信,用足扶贫小额信贷和产业扶贫再贷款,对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致富带头人给予创业贷款扶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建档立卡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方式,使每户有劳动能力、有产业发展意愿、有耕地资源的贫困户能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帮带下摆脱贫困;持续推进景颇族聚居区生态工程建设,通过生态公益性岗位、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保护补偿等渠道,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既要创造条件,促进景颇族贫困群体多渠道转移就业,又要防止因大量青壮年劳力的外输,加剧景颇族村寨空心化或人力资源的匮乏;统筹好绝对贫困户的脱贫攻坚和相对贫困户的日常性帮扶,确保景颇族聚居乡村贫困群众持续脱贫。
3.进一步改善景颇族聚居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更好地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加快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多形式提升乡村医疗者素质,促进城乡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发展;推广农村能源替代工程,减少薪柴消耗,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增强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优化景颇族聚居乡村人居环境。
(五)围绕“治理有效”,提高景颇族聚居区社会治理水平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以组织力的提升为重点,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会管理、善沟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为善治乡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以法治乡村建设为抓手,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引导不同国籍人群、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共同发家致富;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口和外籍人员服务管理,努力提升跨境婚姻家庭的文明素养;持之以恒地做好禁毒防艾宣传,强化打防措施,最大限度遏制毒品入境内流,净化社会环境;建立健全联合守边固防常态化机制,巩固德宏州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成果,提升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逐步实现行政村4G 网络和光纤宽带网络全覆盖,以完善的信息化传播平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