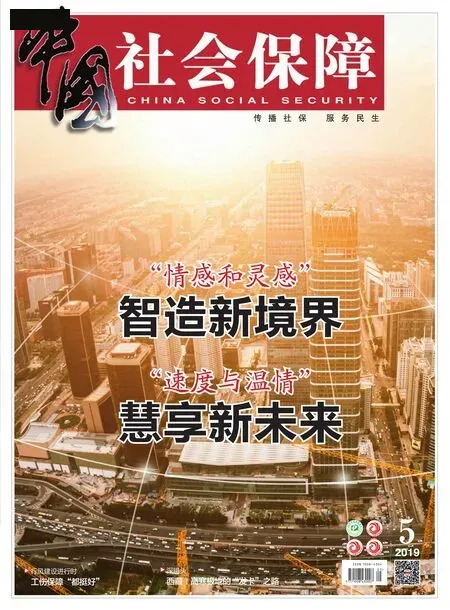阿根廷养老金制度的非公平性
编译/凌文豪 董玉青
阿根廷的养老金覆盖率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分配是不公平的,工作期间和退休期间也是如此。本文通过研究1994—2017年间阿根廷养老金制度准入机会的不公平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演变,并对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等变量如何影响这种不公平进行评估,发现:尽管平均覆盖率水平有所提高,但在1994年改革后的若干年,无论在经济活动人口还是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准入机会不公平情况均显著增加。随着2008年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再次实施,准入机会不公平现象在经济活动人口中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但在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大幅减少。
三个基本维度与两次养老金改革
养老金制度的绩效可以从3个基本维度来评估:覆盖面、福利的充分性和可持续性。除此之外,还须从覆盖面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来考虑制度的分配性能。在横向方面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获得该制度的程度,评估该制度在减少群体之间贫困差距方面的有效性,在纵向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
1994年阿根廷建立私人养老金体系,开始引入个人资本支柱,直到2008年颁布《统一养老金法》重新建立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度。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改革将最低退休年龄提高了5年,并要求满足缴费15年,从而收紧了资格条件,同时取消了省级和市级养老金计划,并将其纳入国家养老金计划。政府希望采用个人资本支柱增加养老金覆盖率,因为个人账户内的存款同其未来的退休联系起来,而这种关联在现收现付制度中是看不到的。但事实上这一改革计划并没有达到此目标,1994—2002年间在职人员的养老金覆盖率减少了15个百分点。
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覆盖率的下降意味着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的覆盖率随后下降。这是2005年实施的养老金纳入计划(以下简称PIP)的主要论点,该计划的目的是使自雇工人能够参加这项计划,因为自雇工人的养老金覆盖率明显低于受雇工人。具体说,在达到最低退休年龄时,PIP计划为自雇工人的缴费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偿还拖欠的缴款和其他款项并获得养老金。
在D·伊利亚的一项研究中,通过1996—2009年养老金受益人群的不均衡指数分析了受益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对收入组内和收入组间养老金可变性的影响。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国家现收现付制度对省级子计划的吸收以及养老金改革引入的更为严格的资格条件,导致1996—2003年间养老金福利方面的不平等加剧。相比之下,通常被称为暂停计划的养老金纳入计划,虽然在目标实现方面效率低下,但在2006—2009年间具有缓解不平等程度的效果。
若干国际组织,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一致认为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全民覆盖。要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放弃缴费筹资计划,就需要有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能够在正规条件下吸收劳动力供应。阿根廷为将老年人纳入养老金体系做出了巨大努力,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2.5%用于为PIP计划提供资金。然而,近年正式就业规模的扩大使得政府并不足以完全为全民保险提供资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之间获得正式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和逃避社会保险缴费似乎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然危害到这一制度的主要缴费设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为例,评估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收入水平为代表)相关的阿根廷养老金制度的不平等程度。同时,研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阿根廷长期住户统计调查的详细版本(1994—2003)和连续版本(2003—2017)的数据,按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将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以十等分法进行划分,并估计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覆盖率。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年龄大于18岁但低于最低退休年龄(女性60岁,男性65岁)。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年龄超过最低退休年龄的人。所涵盖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不论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的、通过扣减工资支付养老金缴费的人;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包括那些享受退休福利或养老金的人。
在本研究所涵盖的19年内选择54个季度的数据,根据公式对家庭人均收入按等分收入群体进行分类,估计养老金的覆盖率每10%的人数,以此计算Wagstaff集中指数。如果这个指数是正值,意味着为社会经济等级较高的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果这个指数是负的,则能够确保社会经济等级较低的个体获得更大的机会。然后构建一个线性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对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进行比较。所选择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4个与教育程度相关的二元变量:中学以下、中学、大专或本科以下、本科或研究生。
阿根廷的养老金制度在历史上曾显示出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覆盖面的差异,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覆盖缺口揭示了养老金制度的各种不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与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之间的差距,显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如何失去了覆盖目标人口的能力:经济活动人口覆盖率的较低程度使预测未来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覆盖率较低成为可能,因为获得养老金福利目前需要30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覆盖率差距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保障体系的再分配潜力未被挖掘,因为它排除了社会经济规模中排名最低的工人。
数据显示,尽管阿根廷养老金覆盖率在平均水平上有所增加,但对在职和非在职人口以及不同指数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的覆盖率差距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虽然在1994年改革前,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覆盖率差距只有6个百分点,但在2008年养老金制度国有化改革时,这一差距已增至11个百分点,且在2017年也是如此。然而,应当澄清的是,这一结果不一定是引入或废除个人资本支柱的结果,而是实施了养老金纳入计划(PIP)。正如结果所示,在2005年第二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期间经济活动人口的养老金覆盖率增加了25个百分点。由于工作期间的养老金覆盖率没有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可以得出“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之间的覆盖率差距增加”的结论。
就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覆盖差距而言,1994年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覆盖率最高的等分收入群体与覆盖率最低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相差约30个百分点。14年之后,较高和较低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增加到71个百分点。根据最新资料,目前最高和最低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已减少到68个百分点。考虑到在工作年龄段内的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的覆盖率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是一个长期的特点,因此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为经济活动人口提供的养老金制度是不公平的。
对于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养老金覆盖率而言,1994年覆盖率最高的等分收入群体与最低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有23个百分点的差距。2008年,覆盖面最高的等分收入群体和覆盖面最低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扩大到27个百分点,然而中间等分收入群体的覆盖率大于两端值。研究发现,2017年覆盖率较大的等分收入群体与较小的等分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缩小至2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倒U型。也就是说,两端等分收入群体的覆盖率仍然低于中间等分收入群体。这表明,虽然最贫穷的个人由于不符合30年缴费的要求而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但最富裕的个人自愿决定继续工作,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权享受的福利水平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情况不同。近几十年,阿根廷没有劳动力大军提前退出的趋势,相反,老年人的就业率有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养老金的不足。
本文还通过1994—2017年间阿根廷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养老金覆盖率及成就指数、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养老金覆盖率及成就指数、积极工作期间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覆盖率的集中指数以及消极工作期间经济活动人口和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覆盖率的集中指数,对养老金制度的非公平性进行分析。
在1994—2017年期间,经济活动人口养老金制度平均覆盖率仅增加7个百分点,最低水平出现在2002年10月。当时阿根廷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下降是1998年进入衰退的结果,2002年失业率高达22%。此外,尽管养老金改革中雇主缴费的减少以及就业政策的实施使雇佣工人无需缴纳强制性社会保险费,旨在减少非正规就业。但非正规就业仍在增加,使社会保险的缴费减少,情况变得更糟。随后的经济复苏并没有实现所有收入群体的平等改善,表现为成就指数始终低于平均覆盖率水平,这表明养老金制度覆盖率偏向于收入较高的人,损害了系统的分配效率。
关于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平均覆盖率,1994—2017年间增加了12个百分点,在实施PIP之前的2005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水平。这种覆盖面的最初下降是对获得养老金福利的要求更加严格的结果,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严重恶化的情况下,要求30年的养老金缴费。反过来,政府的筹资限制导致非缴费福利的筹资减少,从而阻碍了扩大覆盖面。由于执行PIP并没有使所有收入群体得到同样的改善:成就指数高于平均覆盖率,这表明对收入较低的人有更大的分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最后2个季度,以及2016年和2017年最后3个季度的集中指数都低于零。这一结果意味着,在那些年里,PIP使在享受养老金制度方面从有利于富人转为有利于穷人成为可能。
在养老金改革之后的几年里,在职和不在职人员在获得养老金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其最高值,而2005年达到最高值的是那些积极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从2003年5月起,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在一系列高值附近波动,并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记录值。取消个人资本支柱似乎并没有对减少这种准入方面的不平等产生任何影响。相比之下,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减少,这显然是实施了养老金纳入计划的结果。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收入最低的群体也是那些满足30年缴费要求最困难的人,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PIP计划。同样,人们注意到,不平等现象突然减少后又出现了新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反映了在职期间出现的机会不平等,而在没有暂停计划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又转移到非经济活动人口身上。
此外,通过评估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变量与养老金制度不平等的相关性发现,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覆盖面的不平等,因为受教育水平也是影响收入水平分布不均的一个重要变量。受工作不安全感影响最大的显然是那些资历最低的工人。年龄在分配上稍微倾向于富人,因为老年富人更有可能注册公司或拥有正式工作。最后在性别方面,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中男性的相对数量较多。
非正规就业是个挑战
在评价养老金制度的绩效时,必须考虑覆盖面的问题,它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分配情况促成了不同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分析制度的进步性或退步性。如果认为所有工作和不工作的人都必须纳入养老金制度,那么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应影响其获得养老金的机会。相反,人们关注的是获取资源方面的不平等。
通过对集中指数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养老金制度的变化与准入不公平存在关系。尽管在养老金改革后的几年里,无论是对经济活动人口还是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不公平现象都有所增加,但并不足以证明这种不公平程度随着现收现付制的回归而减少。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覆盖面,从2002年经济危机之后到2008年取消个人资本支柱,准入机会的不平等略有减少,但是从未达到1994年改革前的标准。对于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而言,不平等程度的减少只能解释为养老金纳入计划实施的成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已将其GDP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为老年人的养老金全面覆盖提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最需要保障的非就业人口的进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尽管这些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在目标效益方面不是最佳的,但确实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然而,鉴于该系统的资金依然主要来源于受益人,老年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准入条件与在职期间享受的条件正相关显然是不公平的。
本文指出,由于较低收入水平的人获得正式就业的机会也较低,所以在达到退休年龄甚至在更晚的时候其难以满足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这表明阿根廷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尚有足够的空间减少横向不平等。如果正规劳动水平得到提高,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中,使覆盖率独立于缴费者的教育水平、年龄或性别,这将大大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平等。研究还发现,覆盖率存在偏差,这有利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与此同时,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人长寿的可能性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领取养老金制度福利的不公平。最后,按收入水平分列的男性在就业和非就业人群中略微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对集中指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自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不仅在阿根廷,而且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存在着关于养老金制度的主要供款设计和劳动力市场无法确保充分正规就业的争论。如果劳动力市场不能提供充分正规就业,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就不能确保普遍覆盖。同样,非缴费融资来源的增加可能会影响该系统的分配效率,至少人们忽视了与收入有关的税收的累进性或回归性。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养老金制度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养老金制度的风险分担设计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最佳表现才能有效,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如何为全民社会保险筹措资金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