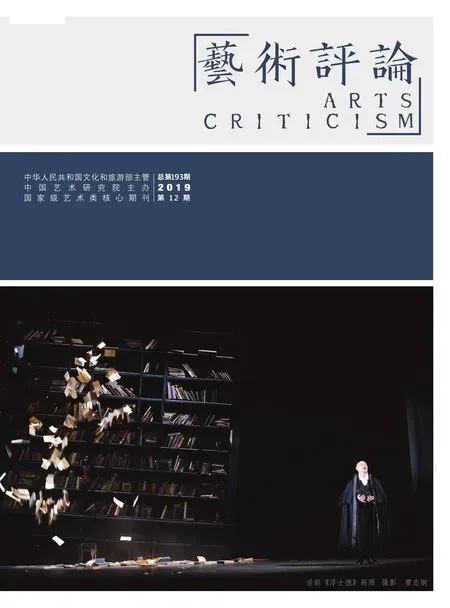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舞蹈文化活体
——透视70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三次勃兴
[内容提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伴随着中国文化进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并且以舞台创作的审美流变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表征。回望历史,70年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有三次重要的勃兴:第一次是激情的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是喷薄的80年代;第三次是多元的世纪之交。三次勃兴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激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喷薄的经济大潮和新世纪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与发展被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命题始终缠绕着。内在的坚持和外来的冲击,使得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混合体”。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在当今舞台上仍然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延续着历史发展中的精彩与争论。在70年的历史节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剧烈和深刻变化的世界,民族民间舞蹈乃至中国舞蹈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再一次勃兴?回望历史,也许能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世界范围内非常独特的舞蹈文化现象,一方面在长期的农耕文化滋养下,中国积淀了无比丰富的多民族传统舞蹈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入专业舞蹈领域,并大规模地登上艺术舞台,成为中国舞蹈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舞台上大量精美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还会看到边远地区鲜活传承的民间舞蹈文化;不仅可以看到校园课堂里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传播,也会看到现代都市广场舞群体中民族民间舞蹈活跃的身影。当代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不再是单纯的舞台舞蹈艺术,抑或是单纯的民间舞蹈文化所能简单归纳的,而是跨越了两个层面,中和了两个领域,成为具有包容性与延展性的中国传统舞蹈的文化活体。
中国文化伴随着中国近现代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复杂的演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也不例外。特别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是舞台创作的审美流变。甚至可以说,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文化现象本身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当代转型的文化缩影。回望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有三次重要的勃兴。
第一次勃兴:激情的50年代与“孔雀舞”的争论
在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进行审视之前,我们必须关注对当代文艺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所确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导向直接引发了“新秧歌”和“边疆舞”运动的兴起。这两个风靡一时、在中国舞蹈史上“舞”下浓重一笔的舞蹈运动,其核心形式与内容恰恰都聚焦于民族民间舞蹈——对传统民间舞蹈样式和内容进行改造,使之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现实。可以说,“新秧歌”和“边疆舞”运动标志着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正式开端,即民俗舞蹈文化从民间层面登上更高的艺术层面,并从政治的和艺术的两个角度设定了对其进行改造和创作的基本发展方向。“新秧歌”和“边疆舞”运动的成功,不仅开辟了文艺工作者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也使民族民间舞蹈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和革命进程中,很自然地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重要来源和基石。这一时期奏响了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勃兴的“序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民族民间舞蹈几乎占据了舞蹈发展的半壁江山,尤其一大批在原有民间舞基础上加工创作的精美作品奠定了5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难以复制的经典性。

《红绸舞》中央歌舞团演出

《鄂尔多斯》贾作光、斯琴塔日哈表演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代表性作品《红绸舞》,以汉族民间秧歌中的舞绸和传统戏曲中的长绸舞作为基础进行发展加工,利用红绸呈现出火炬和火焰的意象。红绸的舞动模拟火的飞腾和迸射,欢快的舞步聚合开散,不仅象征着火红热烈的革命意象,也对应着人民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情绪与炽热期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新秧歌运动路线的延续和坚持,还可以看到舞台艺术创作的因素在加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道具使用是一大传统特色,但舞台作品中红绸已经成为核心要素和象征符号,大大延展了道具的内在意蕴。再例如,贾作光的舞蹈是50年代民族民间舞蹈作品中另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鄂尔多斯舞》曾经在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奖,赢得广泛赞誉。整个舞蹈动作形态极富蒙古族特质,尤其是双手撑腰移动肩部和压动双手手腕的典型动作活泼热情,别具一格。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民间舞蹈,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动作形态并非民间自然传衍,而是贾作光创造性地将蒙古族劳动与生活动作以及宗教等草原传统文化融合并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舞蹈语汇。
20世纪50年代类似的民族民间舞蹈经典作品还有很多,如《快乐的啰嗦》《草笠舞》《丰收歌》等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民间舞创作的“序曲”相比,这个阶段的创作无疑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艺术家响应号召,全面深入到广阔的民间生活中去,对民族民间舞蹈传统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把握,并且在向舞台的提升过程中表现出创新民族民间舞蹈语汇的能力。这一井喷式的发展,显然与学习苏联和东欧舞台民间舞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它实实在在地建构于中国舞蹈艺术家的积淀和创造之上。

《快乐的嗦》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工团演出(1959年)

《孔雀舞》中央歌舞团演出(1956年)
值得关注的是,5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新在当时也曾引起热议甚至争议。1956年的《孔雀舞》是一个焦点。这个作品把民间传统的男性孔雀舞者置换成为女子群舞,并且引入芭蕾舞的元素,改变了动作的审美,引发了对立的观点。肯定的意见认为作品样式创新,反映出幸福与和平的意境;否定的意见认为作品歪曲了生活的真实,走向无内涵的形式主义,甚至给戴上“资产阶级创作道路”的大帽子。撇开时代的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孔雀舞》争议的长久意义在于民族民间舞蹈传统习俗与现时审美趣味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作品在民族民间舞蹈当中加入了外来的芭蕾元素,使其引起的争论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涉及到了创作的走向问题。《孔雀舞》已经沉淀为当下的经典作品,其创新已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范例,所争论的“走向”问题被历史确立。然而“孔雀舞式的争论”在整个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过程中却在不断重复。就如水中激起的涟漪,会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平复,但涟漪本身不会完全隐去——有水的存在,新的涟漪就会存在。
这些创新和争议共同构筑起了20世纪50年代一道绚丽的民族民间舞蹈风景线和永不泯灭的经典性。在延安文艺路线引领下,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走过战火纷飞的苦难岁月,登上了艺术舞台的大雅之堂,迎来了浴火重生。
第二次勃兴:喷薄的80年代与民族精神图腾
“文革”压制了包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舞蹈和其他文艺领域一同开始了复苏。这种复苏首先以喜悦的面貌在民族民间舞蹈作品中呈现出来。
例如《观灯》巧妙赋予了民俗文化中的灯市以象征意味,使热闹的灯市成为社会复苏的缩影,让观灯的人对生活重燃希望。舞蹈吸收了四川花灯的动作形态和川剧变脸技巧,妙趣横生,四个丑类的表演更是充满了讽刺意味。更多的作品例如《燃烧吧节日的火把》《心花怒放》《铜鼓舞》等则直接以热烈欢快的情感抒解为主。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复苏不仅表现在情感的外放上,也通过清新的自然情调之风表现出一种宁静的喜悦与趣味。例如傣族舞蹈《水》选择了一位傣族少女在江边洗头的情景进行细腻描写,使少女的纯真无邪和水的纯净涤荡汇成一种人与水的亲密关系。不起眼的生活细节被赋予了沁人心脾的愉悦和深意,“平淡如水”的生活情调陡然具有了抚慰心灵的意味深长。类似的作品还有《追鱼》《采桑晚归》等,这种细微处见表达的创作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民间舞的创作。可以看到,复苏阶段的民族民间舞创作延续着50年代的优秀传统,“情感”和“自然”成为两个重要主题。
复苏是为了迎接更加沸腾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中苏醒奋发,像一个悸动的青年怀着喷薄的理想和深沉的思索奔向充满未知的未来。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不仅没有缺席,而且以出乎意料的创作激情和艺术追求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例如《奔腾》是一个蒙古族舞蹈的开创性作品,舞如其名,挟着一股无所畏惧的气势奔腾而来。领舞与群舞交织在一起,对应着“一马当先”与“万马奔腾”的意象。舞蹈时疾时徐,既有信马由缰的闲情,也有一骑绝尘的气势,张弛之间表现出高度的自信,潇洒至极。作品之所以对蒙古族舞蹈创作有着重要突破,正是因为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把蒙古族舞蹈艺术化成一种时代的心声和图景。再例如《残春》把朝鲜族民间舞蹈坚韧悠长的身体动律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转折变化中充盈着生命的戏剧感。它如同春天的最后一声呐喊,悲怆中饱含激情,消逝中充满希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舞蹈编导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创造欲望与舞台艺术修养,开始以更高的视野去把握民族民间舞蹈的形态与精神,并将之与个人的情怀追求进行融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趋向,这与新中国专业舞蹈教育的发展紧密相关。北京舞蹈学院自1954年开创和建立中国舞蹈教育体系以来,中国民族民间舞就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舞两个重要的支撑点之一(另一个是中国古典舞),并扩展到全国专业艺术院校中,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专业教学而衍生的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经过了长期的积蓄,不断出现创新的编舞技法和舞蹈美学追求,展露出新的体系发展力量与逻辑。

《奔腾》中央民族大学演出 姜铁红等表演(1996年)摄影:叶进

《黄土黄》北京舞蹈学院演出
民族民间舞蹈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高潮是后期出现的发扬蹈厉的“黄土风”,这与同时期席卷了音乐、影视、文学等文化领域的黄土风潮一脉相承,但是体现出身体叙事的独特性,营造出一个民族脊梁般的精神图腾。大型舞蹈晚会《黄河儿女情》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系列精彩舞蹈合集,质朴的乡土气息与情感引发了舞台的冲击波,迅速传播开来。紧接着,北京舞蹈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推出两台民族民间舞蹈晚会《乡舞乡情》和《献给俺爹娘》,把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其中《俺从黄河来》《黄土黄》和《一个扭秧歌的人》三个作品构成了“一河一土一人”的经典象征符号。《俺从黄河来》以沉稳坚定的山东鼓子秧歌中的跨步和大胆横跨舞台的调度,塑造了一个来自黄河的人物群像。作品的名字与古老的哲学命题不可分割。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作品的身体动态则与答案关联在一起,那踏地留痕的深沉步伐不言而喻。中国人在现代社会急剧的转型时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黄土黄》把这种寻根意识转化为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土地意识。舞台灯光明暗起伏,暗示着白昼黑夜的永恒交替,黄土地上的鼓舞仿佛一个永不停歇的精神仪式,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在几近痴狂的舞动中完成了对土地的坚守。与两个群舞作品相比,独舞作品《一个扭秧歌的人》从描述群像转向了刻画典型个像。一位老艺人在近似于梦呓般的回忆中焕发青春,品尝着舞的永恒与生命的转瞬即逝。这是一个民间秧歌艺人奇异的生命景观:一方面是肉体的有限生命,年华逝去剥夺了舞蹈的身体能力,也即将终结这个个体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是舞蹈不朽的艺术生命,它在不同的肉体生命中流转,在代代相传中延续着舞蹈的生命。“生”与“死”的转换是一种极其浓烈的传统文化的宿命感,以及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以有限的生命去守护和传承民族民间舞蹈,使其得到无限的永生。这一股激荡的黄土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急速社会变化中,既具有一种悲剧气氛,又体现出中华文化坚韧的根性。

《雀之灵》中央民族歌舞团杨丽萍表演

《顶碗舞》新疆自治区歌舞团演出 贾孜拉等表演(2002年)摄影:叶进
与之相反,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另一种追求高度艺术化和形式感的倾向。很有意味的是,大幅的创新再次出现在孔雀舞之上。1986年杨丽萍的《雀之灵》横空出世,风靡剧场也刷遍电视屏幕。杨丽萍以自己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和灵气,独创了自己的舞蹈语汇。傣族舞的三道弯形态特征被演绎到极致,手臂的波浪型揉动和夸张突出的身体曲度成为杨丽萍的标志性的舞蹈形态。这显然不是民族民间舞的传承,而是传承之上的个体突破性创造。在西方《神秘园》电子音乐的空灵意境中,《雀之灵》造就了一个新的民间舞蹈文化的崇拜之物。从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角度去解读这个作品,已经有一些失位。杨丽萍独创的舞蹈形态成为高度个人化的艺术符号,严格意义上很难界定为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杨丽萍的舞蹈形态不断复制衍生,从舞台扩展到民间,产生了极其广泛的传播影响,成为当代舞台与民间互动关系的生动注脚。同时,这也反映出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不可避免的当代化倾向。
第三次勃兴:多元的世纪之交与原生态的回归
随着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不断活跃与积累,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愈来愈明显,在世纪之交形成了一个丰富和繁荣的格局。
当然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在广大地区的自然传衍从未中断,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民间舞专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建立了另一个规范可持续的传承方式。因此在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多元化的创新当中,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演绎依然是主流的现象,只是在创作方式上出现了更加多样的取向与选择。例如维吾尔族舞蹈《顶碗舞》和蒙古族舞蹈《盛装舞》是典型的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舞台雅化作品。作品并没有延伸的艺术表达,只是通过动作的提炼美化和精心编排,对民族民间舞蹈的传统样式进行纯粹而精美的展示,舞蹈的舞台效果与独特的文化韵味令人赏心悦目。彝族舞蹈《阿惹妞》根据彝族古老的婚嫁习俗,营造了一个具有冲突性的戏剧结构,并把舞蹈表演放置其中,使民族民间舞作品充满了人物感和戏剧性。藏族舞蹈《牛背摇篮》和彝族舞蹈《阿嫫惹妞》对民族民间舞蹈动作形态和舞蹈的人体进行了形象化的创造。《牛背摇篮》中男演员以自己的双臂和后背模拟了牦牛那犀利的尖角和坚实的后背,托起和保护了在牛背上玩耍的小姑娘。《阿嫫惹妞》中女演员们前后扶持相连,弯着腰左右摇摆行进,在独特的韵律中蜿蜒出一个大地般深厚朴实的母亲形象。
可以看到,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在创造性地延续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与途径,其中的核心在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表现的视角、思路与方法可以各有不同,但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重要内涵。这样就使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一直维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成为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不可替代的主流。

《碧波孔雀》 中国歌舞团演出(2002年)摄影:叶进

《云南映象》云南映象艺术团演出 杨丽萍等表演(2004年)
另一方面,作为直接从教学层面生发出来的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必然会在舞蹈语汇上受到这样一种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和艺术性影响,在训练层面上对动作风格加以强化,在创作层面上向更艺术、更抽象、更宏观的方向倾斜。这就使民族民间舞蹈远离了民俗文化的随意性与生活性,形成带有舞台典范意义的动作符号体系。例如汉族舞蹈《东方红》选择了冼星海的音乐名作《黄河》钢琴协奏曲,藏族舞蹈《红河谷·序》选择了电影《红河谷》气势恢弘的主题音乐进行创作。两个作品的创作素材分别来自山东秧歌和藏族舞蹈,但宏大的创作主题明显超越了民间层面的舞蹈文化。民间趣味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和民族情怀,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表达出相似的真挚情感与忧患意识。《猎·趔·鬣》与《爬坡上坎》用高度精炼的动作语汇生动模拟出景颇族狩猎和苗族爬坡上坎的生活场景。在错落有致的空间律动中,生活真实的身体动作转化成极具观赏性的舞蹈语言,民间生活也转化为饶有趣味的审美样式。同样取材于胶州秧歌的《扇妞》和《一片绿叶》则走得更远,前者将传统胶州秧歌的动作形态抽离为几乎纯粹的身体样式,剥离了其原有的文化意蕴,将现代艺术的抽象性和民间舞蹈的趣味性糅合得别具韵味;后者使用了雅尼的现代音乐,将最典型的胶州秧歌动作形态在新的连接方式和运动流程中呈现出流畅翻飞的新面貌,一片绿叶的生命和环保主题隐含其中。汉族舞蹈《老伴》别出心裁,其中变形和夸张的动作语汇几乎让汉族民间舞蹈的属性风格不可辨认。尤其是荒诞与“无厘头”风格的浮现让当代的大众审美趣味糅合进入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当中。这些都体现出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在创作追求多元化上的极大差异与灵活性。
世纪之交民族民间舞创作多元发展的极致还体现在两个南辕北辙的向度上。向度之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出现了向市场靠拢的“时尚化”趋向,尤其是注重即时观赏性的大型晚会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很有意味的是,傣族的孔雀舞再度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改造焦点。50年代《孔雀舞》的性别突破和80年代《雀之灵》的审美突破都曾引发巨大的反响,世纪之交的《碧波孔雀》同样令人瞩目、引发热议。作品在市场身体文化的推动下,摒弃了传统孔雀舞模拟孔雀情态的委婉柔美,转而直白地表现女性的婀娜美艳。强化的节奏律动和艳丽的整体审美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孔雀意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商品文化环境的显著影响——孔雀舞中传统的宗教传统和审美习俗让位于市场大潮中娱乐审美的需求。由于《碧波孔雀》的创作关注的是演艺市场的观赏性与传播度,因此民族民间舞“时尚化”争论的焦点也就并不在于传统还是创新的纠葛,而是在于文艺与市场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此前民族民间舞蹈创新而引起的争议不同,文艺与市场怎样契合成为引发关注的命题,这也使民族民间舞创作“时尚化”的争议具有了深层次的理论反思与文化危机感。
然而,在民族民间舞蹈晚会热潮中物极必反的另一个向度随之应运而生。杨丽萍推出大型原生态民族歌舞集《云南映象》,义无反顾地回到最原初的民间歌舞样式。这次回归非常决绝而智慧,歌舞集冠名以“原生态”,从民间征集而来的农民作为舞者直接登上舞台演出。最原生的舞者和当代舞台化审美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结合,云南原生舞蹈文化的神秘感和动人之处被舞台几何级数地放大,不仅增加了演出吸引度,同时引发巨大的文化热度。虽然这场歌舞集演出并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原生态”,但杨丽萍在创作过程中看到并坚守了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从而使《云南映象》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原生意义,与一系列浮华的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相比,爆发出了出乎意料的深沉力量。《云南映象》在原生歌舞舞台演出中获得的成功,实际上恰逢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背景。一大批有识之士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呼吁、传播、实践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前辈们深厚的研究和实践基础逐步推动非遗保护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热点。《云南映象》成为一个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长期积累的舞台爆发点,有意思的是,这次爆发让我们看到不只有服从于商业市场跟风而动的艺术创作,那些特立独行的艺术守护者同样有机会扭转市场的势利之手。
三次勃兴的启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活体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三次勃兴大大推动了中国舞的发展,本文所提及的作品在浩瀚的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只能是挂一漏万,但历史的启示是相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仍然在当今舞台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延续着历史发展中的精彩与争论。那些传统的坚守、创新的突破、商业的冲击、艺术的沉浸与历史中丰富多元的图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长期走过的继承与创新并存的道路呢?
中国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三次勃兴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其根源在于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农耕文化和社会结构。第一次是以20世纪50年代民族民间舞蹈舞台艺术化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通过经济和工业改造传统的农耕社会,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社会现实在憧憬中酝酿并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变的进程中,民族民间舞蹈面临极大的外部环境的冲击。一方面国门的开放使得外来文化大量涌入长期封闭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大潮对高雅艺术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第三次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文化多元化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助力下,无论是速度还是烈度都大大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不再局限于浅层,而是相互渗透与影响到理念与意识层面,在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反思与争议。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伴随着中国历史和社会进程,不仅在形态上发生着更多的变异,在创作的审美和观念上也发生着变化。然而,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根性又始终使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在一种抵触中艰难前行。与别的民族传统文化一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与发展同样被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命题始终缠绕着。内在的坚持和外来的冲击使得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混合体”,成为当代中国极具代表性的独特的舞台舞蹈艺术创作类型。这一类型的独特性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极大的文化价值。它以群体性文化限制了个体性艺术创作,抑制了对传统文化的忘却与抛弃,并阻止了向西方文化的滑落。另一方面又在开放和创新的激励下保持了自我向前发展的活力。于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是一种在多元取向中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活体传承。它没有出现极端割裂历史传统的情况,不是在形式上就是在内容上维系着与传统之根的联系。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与完全不受限制的现代舞蹈创作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艺术的心灵同样飞翔,但这是一颗眷恋大地的心。
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剧烈和深刻变化的世界,当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进步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将给人类社会和文化带来怎样的变化?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能否找到新的定位与起点?民族民间舞蹈乃至中国舞蹈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再一次勃兴?回望历史也许能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早在1987年《舞蹈》杂志发起的针对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讨论中,吴晓邦先生曾说到:“我们今天提倡的民间舞蹈是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的民间舞蹈的继承和发展,对旧有形式加以改造,赋予民间舞以新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舞蹈家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成就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与生命力的当代生存样式,我们需要激情,也需要思索;需要决心,也需要耐心。传统和现代必定成为缠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终极命题。反复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填补文化空洞、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我们依然身处其中。
注释:
[1]吴晓邦.谈中国民间舞蹈的古今异同[J].舞蹈,19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