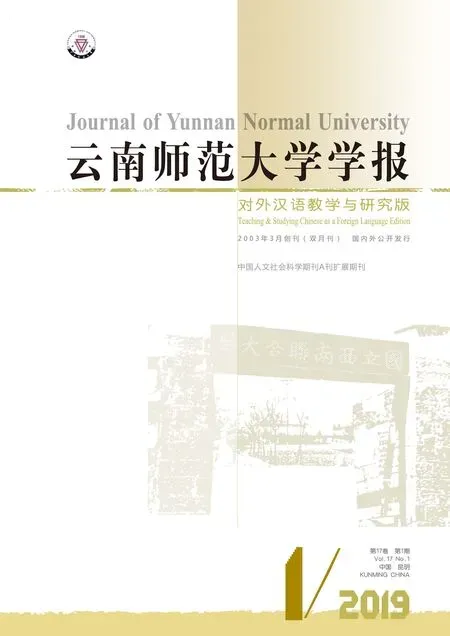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访谈研究
姜有顺, 刘妍芩, 张善超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1;2.西南大学 国际学院,重庆 400715)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近20年来,汉语国际推广的脚步显著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汉语热”。为了满足国际汉语师资的需求,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汉语国际教育(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硕士专业学位(下文简称“汉教硕士”)。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本科专业名称“对外汉语”改为“汉语国际教育”(下文简称“汉教本科”)。2016年,北京语言大学、厦门大学自主增设的“汉语国际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正式开始招生。至此形成了汉语国际教育类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3个培养层次。为方便称说,本文简称之为“汉教专业”,将汉教专业的中国学生群体简称为“汉教生”。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汉教生投身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意愿程度以及专业对口就业率相当低。笔者对就读于西南某重点综合性大学的汉教硕士中外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过问卷调查,发现仅有约23%的受访者将“汉语教师”作为就业第一志愿。许多国内院校的汉教本科的对口就业率不到5%(不含考研);[注]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汉教硕士的对口就业率普遍在10%到20%。[注]赵世举.汉语国际教育类专业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大学教学,2017,(6).即使是就读于一流学府、享受最好教育资源的汉教生也是如此,如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14届汉教硕士毕业生中有半数从事的工作与汉语教学完全无关。[注]徐晶凝.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思考——教师教育的国际化视野[J].海外华文教育,2016,(1).
汉教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表现出脆弱、矛盾的特征。他们往往尚未体认自己作为汉语二语教师的身份,却很快置身于异国异文化语境、接受教师身份的拷问,这导致不少汉教生产生身份认同冲突,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甚至最终放弃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
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有哪些表征?冲突的产生原因是什么?教师培养项目应当如何促进汉教生的身份认同意识?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汉教专业学生的专业成长历程。对于提高二语教师教育质量、推动二语教师的专业社会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考察对象不包含汉教专业的外国学生群体。由于外国学生的教育背景、就业观念、国外本土汉语人才在本国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学生都存在很大差异,导致两个群体各自的身份认同冲突的表征和致因存在较大差别,不宜一概而论。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汉教专业的中国学生的情况。
(一)第二语言教师的身份认同
“身份”,也称为“身份认同”“个体自我”“(个体)自我认同”“同一性”等等,指个人或者群体对其显著区别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特征的认知。[注]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指教师通过专业学习和教学实践对作为教师的自我的认知。是教师关于“我是谁”“我何为”的思索和阐释,是教师对于个人教育实践和职业生涯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身份认同具有个体化、动态建构性、多元性等特征,受到社会文化语境、教师的教育背景、从教经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伴随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不断发展演变。
20世纪90年代至今,第二语言教师的身份认同成为双语教育和教师教育这两个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注]Varghese,M.Morgan,B.Johnston,B.et al.Theorizing Language Teacher Identity:Three Perspectives and Beyond[J].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2005,(1);寻阳,郑新民.十年来中外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述评[J].现代外语,2014,(1);Norton,B.De Costa,P I.Research tasks on identity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J].Language Teaching,2018,(1).二语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按照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路径:
(1)基于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的研究。主要有冲突论(conflict theories)、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和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三种理论模式。一般使用个案或小样本的访谈调查、教育日志文本分析和课堂观察等方法,强调教师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人际互动对身份认同的塑造。[注]Tsui,A B M.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Formation:A Narrative Inquiry of an EFL Teacher[J].TESOL Quarterly,2007,(4);Smit,B.Fritz,E.Mabalane,V.A conversation of teachers:In search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J].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2010,(2);Kanno,Y.& Stuart,C.The development of L2 teacher identity: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11,(95);Xu,H.Imagined community falling apart: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of novice ESOL teachers in China.TESOL Quarterly,2012,(46).
(2)基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理论的研究。主要使用教育思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和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侧重探讨师生种族、性别、阶层地位、母语和二语文化、教育系统权力关系等因素在二语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协商互动机制。[注]Duff,P A.Uchida,Y.The Negotiation of Teachers'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in Postsecondary EFL Classrooms[J].TESOL Quarterly,1997,(3);Johnston,B.The Expatriate Teacher as Postmodern Paladin[J].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1999,(2);Morgan,B.Teacher Identity as Pedagogy:Towards a Field-Internal Conceptualisation in Bilingual and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2004,(2~3);Ilieva,R.Non-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Negotiations of Program Discourses in Their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within a TESOL Program[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10,(3).
以往二语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存在如下两点缺憾:
(1)以往研究的参与者多数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大学或中学在职教师,其中又以英语非本族语者居多。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没有发现针对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发展的专题研究,而这本应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首先,不同语言在习得难度、所承载的文化影响力、语言教育市场的规模等参项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同语言的教师对专业身份的理解及其嬗变也存在差异,需要具体分析。其次,2007年以来,国内大规模培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汉教生的总量持续增长,汉教专业每年毕业人数超过10万。[注]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研究二语教师的身份认同不应忽略这个数量庞大的准教师群体。
(2)以往研究对教师的身份认同冲突基本持批判态度,立场不够客观中立。多数学者侧重考察教师培养项目带给学徒教师的那些符合教师教育者预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学界倾向于将学徒教师的身份认同冲突视为不利于教师发展的、消极病态的表征,针对学徒教师的身份认同冲突的研究数量较少,并且主旨很少超越“预防和处置”的思维定式。
(二)冲突理论视角下的教师身份认同
本文以冲突理论、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Coser)关于冲突的功能主义观点作为理论依据。[注]Coser,Lewis A.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Glencoe,IL:Free Press,1956;Johnson,D P.Conflict and Competition:Analytical Conflict Theories at the Macro Level[A].In: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C].Springer,New York,NY.2008,367~395.冲突是关于信仰和价值观、稀有资源、权力地位的斗争,根源在于有价值物的稀缺性导致的利益对立。科塞认为,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互动形式。社会系统的运转和发展遵循“冲突-发展-再冲突”往复循环的动态平衡规律。冲突兼具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冲突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冲突能够整合各方主体的利益,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催化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和新的制度规范的形成,从而防止社会僵化。
科塞将冲突的根源归结为物质性的原因和非物质性的原因。物质性的原因包括地位和权力的竞争、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非物质性的原因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制度性的歧视、文化差异等。导致冲突的非物质性因素往往比物质性因素更加难以调和。科塞认为,问题的现实性程度与冲突的激烈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引发冲突的问题越是非现实性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就越高。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社会群体正是依赖冲突机制建立和维持该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的。冲突突显了同一群体内部成员的身份,通过强化同一群体的成员关于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性的意识,设定了身份的界限。因此,冲突是专业社会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的一种常态形式。学徒教师不是仅仅被动接受社会他者对自我的干预和塑造,而是在与多元主体的冲突关系中,逐渐掌握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了解教师角色的行为规范,形成教育信念、职业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融入教师共同体并参与行业利益博弈的过程。
汉教专业作为新兴二级学科的建立,意味着对相关学科的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在这个利益调整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汉教生以及其他各方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其权益、实现其主张,难免会围绕价值信念、权力指派、资源分配等焦点展开竞争和博弈。在报考、学习、实习、求职等专业社会化过程中,汉教生难免与其他个人、机构和体制等利益主体产生冲突。学徒教师是整个教育生态链中的弱势群体,更倾向于成为冲突中的妥协者和受害者,因此,这个群体倾向于产生自我生存和发展需求与教师身份之间的冲突,倾向于产生被剥夺感和身份危机。
汉教生的专业学习和实习经历影响他们对汉语二语教师身份的认同程度。他们需要处理自我身份与多种因素(例如教育体制、学校文化、师生关系、教师共同体等)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冲突的处理结果都影响着汉教生对“我是谁”“我何为”的认知。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我们认为以下3个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考察和深入讨论:
1.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具有怎样的表征?
2.该群体产生身份认同冲突的致因是什么?
3.建设该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策略是什么?
本文基于冲突理论,探查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表征以及引发身份认同冲突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者,并提出针对性的身份认同建设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受访者
本研究为小样本的半结构化访谈调查。为了保证取样的代表性,选取受访者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校属性、学校所在地、学历和现从事职业的分布。
受访者共8名,男女各4名。就读或者毕业于北京、广州、上海和重庆的8所“211”或“985”工程重点大学。受访者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下文在直接引用受访者的话语时,均在句末方括号内标记受访者的编号。

表1 本研究的受访者信息
(二)调查问题
通过阅读以往有关教师身份认同、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从研究问题和结论中整理和提炼本研究的访谈问题。通过与在高校从事多年汉语二语教学工作的3位专家型教师进行讨论,发现本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最终形成5个调查问题:
1.你为什么选择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你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优点和缺点有哪些?
3a.[对尚未毕业的受访者]你的就业志愿是汉语二语教师吗?为什么?
3b.[对已经毕业的受访者]如果还有机会让你选择职业,你的就业志愿会是汉语二语教师吗?为什么?
4.你在课程学习和海外实习中,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因为某些事件,使你对自己作为汉语二语教师的身份产生负面消极的情绪(例如忧郁、焦虑、恐惧、愤怒、失望、迷惑、空虚、羞愧等等)?请详细描述这些事件。
5.如果你的一位朋友希望以汉语二语教学作为终身事业,你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三)调查程序
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笔者通过面谈、网络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陆续对受访者进行了一对一访谈。访谈包含指定作答和自由表述两个环节,受访者提供个人基本情况后,首先逐一回答提纲预设的问题,然后自愿就相关话题自由发表意见。面谈和电话访谈全程录音并转写为文字,邮件访谈保留文字记录。
访谈文本由笔者和一位助手分别进行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辨识和标记语篇中显现的影响汉教生的身份认同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者,揭示导致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机制。之后,两人将独立分析的结果进行比较和汇总,争议之处通过两人讨论和回访结果达成一致。
三、结果与讨论
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种子在入学之前就已埋下,课程学习酝酿了身份焦虑,最终在海外实习阶段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下文从3方面冲突的角度阐述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表征与产生机制。
(一)职业身份的焦虑:汉教生的身份需求与行业提供的身份识别资源短缺之间的冲突
1.招生机制:学科属性和项目定位易造成困惑。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汉语国际教育是面向海外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当属于应用语言学学科,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汉教专业在学科发展初期未能与国外通行的学科体系对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的定位也漂移不定。目前汉教本科专业归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学科门类,而汉教硕士专业归属于“教育学”,汉教博士专业则归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滑稽的局面”。[注]崔希亮.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15,(3).专业名称的相似性和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引发了学界长期的学科名实与正名之争,[注]胡范铸,陈佳璇,张虹倩.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J].世界汉语教学,2018,(1).也使得大多数社会人士不明确汉教专业的学科归属,导致汉教专业毕业生有时被不知情的招聘单位拒之门外[注]江浪莎,马凯.两个专业就是同一个呀!专业名称与公告不符 成都一毕业生没了教师公招面试资格[N].成都商报,2014,8,19(12).。
汉语二语师资项目的属性也存在内部矛盾。国外的教师教育可分为继时性教育项目和同时性教育项目两类。继时性教育项目的学制一般为一到两年,要求申请者已经获得特定的本科专业的4年系统训练,入学后主要学习教育学课程。同时性教育项目的学制一般为4年,入学后既学习学科专业课程也学习教育学课程。以汉教硕士为例,学制为两年,这似乎表明它是继时性教育项目;但它对招生对象的专业背景不加任何限制,这又表明它应该是同时性教育项目。[注]徐晶凝.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思考——教师教育的国际化视野[J].海外华文教育,2016,(1).
汉教硕士培养方案企图在两年内兼顾招生的“宽口径”和培养的“厚基础”,实际上困难重重。由于汉教硕士入学筛选标准的宽松,吸引了一些本没有从教意愿的人士出于考取心仪的大学或提升学历等目的来报考,从入学伊始就不甚认同自己作为汉语二语教师的身份。并且,由于许多汉教生是跨专业考研,汉语本体知识和要素教学知识的底子较为薄弱,即使通过一年的专业课学习也未必能补齐短板。生源质量制约了汉教生的专业发展,打击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我是跨专业报考汉教硕士的,一是为了能考进男朋友在读的这所大学;二是为了提升学历,觉得读这个专业既能提高外语水平,又能免费感受异国风情,挺不错的。至于我的工作,家里有点门路,不用特别发愁。没想到入学以后课业负担很重。想想自己其实没有当汉语老师的动机,在熬夜写教案、备课、准备课堂演示时,有时会萌生‘出戏’的感觉。[E2]”
2.培养机制:忽视对汉教生的身份认同教育。
对汉教生而言,最为重要和本源的问题应该是“我为什么要做二语教师,这一职业对我而言有何意义”,而不是“应当如何成为合格的二语教师”。[注]Akkerman,S.F.& Meijer,P.C.A dialogical approach to conceptualizing teacher identity.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1,(2).单纯学习专业知识、操练教学技能和积累经验不能直接促进汉教生对身份的理解,也难以解决汉教生的身份困惑。[注]Kanno,Y.& Stuart,C.Learning to Become a Second Language Teacher:Identities-in-Practice[J].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11,(2);张倩,李子建.职前教师专业身份建构之困境与出路——对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4,(3).然而遗憾地说,无论是汉教生接受的专业教育,还是国家汉办组织的公派汉语教师与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行前培训,都带有重“术”轻“道”、舍“体”求“用”的价值导向。侧重规范性的教学技能操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汉教生的身份认同感的启迪和塑造。汉教生尽管习得了知能,却对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对汉语二语教师职业缺乏共情和认同。
另外,汉教生的实习环境为异国异文化环境,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汉教生由于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加渴求融入专业共同体,得到专业共同体给予的经验和情感支持。本土汉语教师是联系学徒教师与实习机构的教学管理人员的重要他者,起到引领、示范和缓冲的作用,然而,一些海外实习机构却完全不聘用本土汉语教师,没有他们,汉教生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难以得到有效的经验指导和情感支持,极易产生孤独和抑郁情绪:
“那时我一个人在实习的学校,语言不通,学校里连一个汉语老师都没有。后来,我都害怕跟人交流,我害怕本土老师看我的眼光,觉得非常孤独、悲伤。那一段经历不堪回首。[N2]”
3.认证机制:汉语二语教师标准和资格准入体系建设缓慢延宕。
长期以来,汉教专业缺乏健全、科学、规范的教师标准体系,关于汉语二语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缺乏完整、权威的界定。汉语二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一度无法可依、乱象丛生。不少社会人士认为当汉语教师没有什么门槛,凡是普通话说得好的中国人就能教汉语。过去10年间,虽然汉语二语学习者数量剧增,但是相关教师标准、资格认证和核心价值规范体制建设进展缓慢。汉办曾主办“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却从2005年起停考。2007年11月汉办出版发布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直到2014年,汉办才重启了停考10年之久的执业资格认证考试,颁发《国际汉语教师证书》。然而,我国对汉语二语教师的执业资格认证始终未能得到国外教育部门的认可。不能与国外教师资格认证对接,对于申请国外正式教职基本无效。汉教生如想在国外长期任课,还需要通过所在国家、州或省的教师执照考核,最终能在国外长期任教的汉语教师数量很少,海外汉语师资紧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削弱了我国执业资格认证的汉语二语教师身份的合法性和适用度。
“我觉得,国家设立汉教专业,一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外国本土汉语教师,二是为中国人提供必要的师资培训和学历支撑,以便他们出国任教。所以汉教专业最理想的就业出路就是长居在国外教汉语。但是,国外正式教职的门槛很高。国外对国内的教师资格证书甚至专业硕士学历都不怎么认可。我们得设法考取当地的教师资格,外语水平也要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还要克服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不便。光这三点就难倒不少人了。[N1]”
教师标准和资格准入体系建设的延宕,导致社会对汉语二语教师的角色期待比较混乱,对其专业身份产生怀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教生在建构自我身份时,既找不到专业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引领和资源支持,也得不到专家和同侪的知识和经验协同,因此滋生了不同程度的路径困惑和身份迷失。
(二)学科生态的困窘:汉教生的身份特质与大学场域重研轻教的价值导向之间的冲突
1.汉教专业的支撑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冲突,缺少专业学者群落,理论创生能力不足,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较低。
汉教专业的支撑学科主要是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选取三者与语言习得和教学相关的理论模块,组成一个拼盘式的学科理论框架。然而,由于3个支撑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语存在冲突和隔阂,汉语国际教育的跨学科合作程度较低,尚未形成规模性的学者群落,尚未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已有的部分理论还处于碎片化状态,[注]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胡范铸,陈佳璇,张虹倩.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J].世界汉语教学,2018,(1).所以,从事汉语二语教研工作的高校教师所缔结的是一种学科离散、范式分殊、理论话语纷纭驳杂的“想象的共同体”。业内大部分教师教育者的教职和编制虽然在大学的汉语二语教学单位,但是他们实际从事的研究依然是在攻读硕博士学位的老本行,如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领域内开展的,较少从事跨学科的研究,更极少尝试建立汉语国际教育的独立的学术理论。甚至身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不少知名学者也存在“岗位与职责的失配”,他们研究的往往并不是汉语国际教育问题,而是汉语本体问题。[注]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据笔者调查,近七成的汉教硕士毕业于中国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但他们的导师常常来自非语言专业。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教师教育者对汉语二语教学现象的理论阐释和研究范式存在分歧,有时甚至难以调和。汉教生在课堂讨论、选题开题和论文写作时,都可能感受到学科理论话语的隔阂和研究范式的差异所带来的困惑:
“我本科学的中文,导师是在教育学院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的。我跟导师和他在教育学院带的硕士生一起讨论的时候,导师觉得我的理论思考不深入,视野不开阔,我却觉得他们谈的话题大而空,没有紧扣汉语教学。我总插不上话,感觉自己是编外的,缺乏归属感。[E1]”
2.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带有鲜明的工具论和实用主义导向,导致专业口径狭窄,汉教生的研究素养不足,人才培养水平不高。
研究表明,接受研究性教学、具备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对新手教师的身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注]Waller,L.Wethers,K.Costa,P I D.A Critical Praxis: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Identity,Theory,and Practice[J].TESOL Journal,2016,(1).李晓琪调查了15所英美知名大学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发现其中普通语言学及英语语言学类课程约占20%,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教学理论类课程约占28%。[注]李晓琪.英美大学TESOL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考察与思考[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1).可见国外大学相当重视二语教师培养项目的理论学习。
反观国内,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教师教育界近年来推崇的“实践成师”的教师发展模式的影响,汉教专业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强调操练课堂教学技能、减少理论研究知识的讲授,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导向。汉教硕士培养方案对汉教生的汉语知识的要求不甚明确,对其研究能力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汉教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素养不予重视的态度,产生了2个消极后果:
第一,汉教专业的口径狭窄,教学内容未能与相邻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建设紧密结合,也未能与国际二语教育的学术发展前沿保持同步。汉教生接触到的汉语本体和语言教学理论知识比较浅表、陈旧和碎片化。他们很少主动了解学科研究的新进展,也很少参与其他教师的课题研究或开展自主科研,难以得到系统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训练,对二语教育的理解往往囿于具体教学目标的操作经验和感性认识层面。杨薇调查发现2012年京津两所高校的汉教硕士有近69%认为自己最欠缺的是学术研究能力。[注]杨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探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4).理论素养的缺失和创新意识的淡薄阻碍了汉教生的专业发展,他们往往只能充当知识的消费者,止步于照本宣科的“教书匠”的层次,难以成长为“知”“能”兼备、能“教”能“研”的专家型教师。[注]汪国胜.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相关问题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011年12月,我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研讨会’。在会上不少学者认为汉教硕士的培养方针类似于职业培训,对学科发展前景表示忧虑。到了2016年,我又看到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主动要求放弃汉教硕士学位授权的消息[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EB/OL].2016年3月16日.http://www.moe.edu.cn/srcsite/A22/moe_818/moe_820/201603/t20160325_235327.html。我觉得,这两件事似乎说明,行业内外的部分专家对汉教专业的培养质量是不满意的。[S2]”
毋庸讳言,大学的主要职能与核心价值取向是研究学问、创生理论。大学场域内客观存在着重视理论研究、轻视教学实践的风气。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汉教专业强调实践导向的学科价值观,颇有逆潮而动、不随主流的意味,后果是削弱了该专业缔造理论的思辨力以及争取学术资源的吸引力,在高等院校的学科文化评级和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比较低。
第二,汉教专业人才培养的低水平量产模式导致供需脱节,加剧了就业困难。在入读汉教专业之后,学生往往遭遇到自我身份认同与研究型大学对师生的角色期望的冲突。由于所学专业的学科地位偏低、学术资本不足,汉教生往往会对专业的声望和地位感到失望,对汉语二语教师身份和职业前景感到自卑和焦虑:[注]陆俭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定位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2).
“汉教专业的学生是‘样样都通,样样稀松’。汉教硕士搞研究比不过学术型硕士,拼汉语言文学知识比不过中文系学生,拼外语技能比不过外语系学生,当老师教课比不过师范生,考公务员还常常因为专业限制不能报考。选择考博,又暴露了专业硕士在研究功底上的薄弱。越是临近毕业,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就越没有底气。[S1]”
汉教本科和硕士的设立初衷是为了解决海外汉语师资紧缺的问题。然而,汉教生在国内外都面临对口就业的困难。在国外最终只有少数汉教生能够获得国外的教师执业资格长期留任。在国内,由于汉语二语教学单位主要集中在高校,而高校的教学岗位一般要求应聘者具备博士学位,汉教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几乎不可能成为有编制的汉语二语教师。如果选择继续求学,其学术背景不占优势。最终多数毕业生在国内从事非师范性质的工作。这显然违背了设立汉教专业的初衷,也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浪费:
“国内大学都在比拼学科发展和师资建设水平,聘用标准都向学历高、研究能力强、科研成果丰厚的科研型人才倾斜,一般不会考虑学历较低、科研能力较弱的教学型人才。汉教硕士想在大学教汉语,只能做没有编制的外聘老师。去社会上的汉语培训机构和国际学校吧,现在民办教育市场又很不规范。大多数同学只好转行了。[E1]”
“在国外如果只是短期任教,不是长久之计。回国以后还是要从头找工作,从零开始,错过了一生的事业黄金期。年轻人可以自由随性,中年以后怎么办?[N2]”
3.专业角色的异化:汉教生的身份理想与被工具化和边缘化的教师角色之间的冲突
(1)海外汉语教学的现实发展水平低于汉教生的期待,导致汉教生的身份理想与边缘化的角色定位产生冲突。
角色(role)在文献中亦称为“社会自我”“社会或他者的认同”或“被指定的身份(designated identity)”。角色带有社会分工的职能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赋予的和规定性的。教师角色的内涵包括教师职业被配置的社会地位、权利、职责等,突显的是社会制度和组织对教师职业的外在规范、期待和评价。[注]Sfard,A.Prusak,A.Telling Identities:In Search of an Analytic Tool for Investigating Learning as a Culturally Shaped Activity[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5,(4).
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师道尊严思想的影响,汉教生常常为汉语二语教师的身份内涵添加传道、立德和树人等崇高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汉教生缺乏教学经验,不了解海外汉语教学情况,受国内媒体对全球汉语热的渲染的影响,不少汉教生往往对国外任教抱有过度理想化的预期,主观地认为自己将成为国外院校重点延揽的紧缺人才。然而海外汉语教学的现实是:汉语在世界范围内还属于较少教授的语言,尚未正式进入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在外语教育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薄弱,还伴随着少数排华反华势力的干扰阻碍。外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华裔)选择学习汉语多数是出于兴趣动机而非工具型动机。上述因素导致汉语课程课时少,课堂教学效率低,大部分学习者止步于初级水平,教学效果可以说是筚路蓝缕、广种薄收:
“我在T国北部某市的一所中学任教,T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态度与中国学生截然不同,他们在课堂上打闹、聊天、随意走动、化妆是很平常的事。再加上汉语是选修课,除了极个别同学,多数学生只是为了拿学分,学习汉语的热情并不高。有一个班男生人数占三分之二,他们上课不听讲,也不带任何文具。虽然我通过游戏教学法成功调动了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但整个学期这个班平均每人可能只记住了20个词。那时我就想,这样教一辈子汉语,有多少人生价值?[W1]”
也因此,国外教学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学生对汉语二语教师的角色期待往往是相当工具性和边缘化的,一般较少对汉语教学积极给予资源倾斜,或者对汉教生予以特别关照。一位受访者因为身体有恙,在完成了教学任务之后,向学校请假去医院治疗,并获得了学校的批准。但中文组教研组长(外方人员)却发邮件指责他:“完全不适合在实习国家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不配做老师”。这件事让受访者十分愤怒,他提前回了国,从此不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国外教学机构和学习者对汉语二语教师的边缘化的角色定位,一定程度上证伪和瓦解了汉教生对理想教师身份的主观期待。他们难免产生失落和怨怼,怀疑身为汉语二语教师的存在意义。
(2)科层管理制度下的组织对教师的角色定位带有工具性和物化特征,导致汉教生的本体性价值认同与机制的功利性价值认同之间爆发冲突。
汉教生对身份的构建和调适主要受到两个权力与知识系统的影响:一方面是国内培养单位对教师角色的宣教,以大学专业课教师和导师为重要他者,主要通过基于典型范例的(exemplar-based)方式影响学徒教师的身份建构;另一方面是国外实习机构对教师角色的设定,以国外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实习指导教师为重要他者,主要通过基于硬性规则的(rule-based)方式影响学徒教师的身份建构。[注]Xu,H.Imagined community falling apart: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of novice ESOL teachers in China.TESOL Quarterly,2012,(3).
培养单位和实习机构是掌握管理和裁决权力的强势方。它们制定繁复的规章制度,对学徒教师的外在绩效实施规训和惩罚,由上至下地向学徒教师灌输它们对教师角色的设定。体制与学徒教师互动时使用的主要不是对话、协商的“民主话语”,而是以命令、训诫为主的“威权话语”。不少培养单位和实习机构对二语教师的角色认知建立在“学校即工厂”的隐喻基础之上,教师只是功能固着的、可替代的工具,是教学计划的循规蹈矩的执行者,不鼓励教师在既定的教学规范之外施展创意,甚至故意压制教师的创造性。学徒教师是接受培养单位和实习机构的双重支配和监管的弱势方。在专业社会化过程中,学徒教师不得不遵循社会他者对教师角色的规范和期望,缺乏决策权或协商权。面对理想期待与现实体认的冲突,社会化程度较高者易于接受实习机构预设的角色规范和教学评价标准。社会化程度较低者则质疑、抵触甚至对抗机构的教师角色规范和评价标准,被体制斥责为“缺乏能力”或“性格缺陷”,留给他们的现实选择往往只有服从和妥协。
然而,教师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讲好课,还在于示范一种富于创造性和内省智慧的生命状态。教学不是一套测评标准所能量化的,它的内涵还包括教师之为教师的存在方式和介入课堂的方式。科层管理体制将教师从一种有权进行自主决策和反思性实践的专家地位(profession)贬黜为只需服从规范操作的专门技能(expertise),缺乏对教师的创造性和个体性的足够尊重和信任,本质上是将教师身份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sed)了。剥夺了教师的创造性和自由意志,也就扼杀了教师存在的意义:
“我所在的实习基地没有本土汉语教师,汉语教学的管理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她不让我自己上课,而是让本土的汉语实习生上课,只让我在课上示范发音。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发音工具,当实习基地举行汉语教学技能大赛时,我完全不敢上台,我觉得自己不会教汉语了。[W2]”
教育体制对教师主体性的压抑和异化,使得初试啼声的汉教生产生了身份认同焦虑,感到缺乏价值感和获得感。他们可以违心地扮演体制预设的教师角色,权宜地改变外显的教学行为,却难以将之内化。[注]Martel,J.Learning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Pedagogical Progress[J].Foreign Language Annals,2015,(3).“五年级的课程由一位本土的汉语实习生主讲,我主要负责在课堂上示范汉语发音。后来,校方要求实习生上课必须用一种特定的启发式教学法。但是我认为这个方法用在外语教学上弊端很大,因为全程基本用学生的母语教学,汉语输入和输出特别少。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课堂上(作为发音示范)的价值。[S1]”
不少汉教生的教学工作陷入了“过密化”(involution)的窘境:虽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没有带来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的成比例提升,教师劳动的边际收益反而递减,蜕变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究其原因,在于汉教生的身份理想往往遭到体制打压,部分汉教生因此丧失自主成长的勇气和动力,放弃了对教学工作的批判性反思。
四、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建设策略
基于冲突理论,二语教师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专业知识的记忆和教学技能的磨练,本质上也制造了一个安全、可控的冲突语境,得以唤醒、拷问和调适学徒教师的身份认同意识,迫使他们设法处理自身发展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对自我认知图式进行修改和升级。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提出:教师身份认同的养成本身就是教师教育。[注]Morgan,B.Teacher Identity as Pedagogy:Towards a Field-Internal Conceptualisation in Bilingual and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2004,(2).学徒教师对教师身份和从教生涯的价值认同,比显性知识技能的增长更加重要。[注]Martel,J.Learning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Pedagogical Progress[J].Foreign Language Annals,2015,(3).正如受访者所言,“我最大的收获是,认清了自己的内心,找准了人生方向,更坚定了想要做一名教师的信念。[W1]”
因此,汉教专业应重视汉教生的身份认同冲突的积极功能,将塑造和内化汉教生的身份认同作为首要的培养目标。我们提出如下3方面的身份认同建设策略:
1.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宏观层面,学科目前的“准职业教育导向”的人才培养思路值得业内反思。学科应更加重视理论创生,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层次,妥善处理本学科在高校学术圈层的激烈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2.在招生环节,应从严甄别报考者的任教意愿,可考虑增设职业能力倾向测试,结合面试,优先选拔那些有志成为二语教师的报考者。
3.在培养环节,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应该针对汉教生的身份认同给予必要的价值引导和信念感召,增加汉教生的情感带入和主体参与程度。例如组织汉教生对教师生命价值和教学生活的意义等存在论问题开展集体交流和反思性实践。此外,培养单位应积极与国外合作院校和海外实习基地洽谈,共建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或者目的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执照认证项目,这些会有助于汉教生树立更加明确的职业愿景。
总之,“学习做一个合格的老师,就是学习怎么跟学生相处、跟自己相处,让教学生活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2]”汉教生不是先入为主地选择教师身份,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师资项目和实习机构设定的教师角色,在与自我和他者的多种冲突中,他们不断探寻、协商和建构着教师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