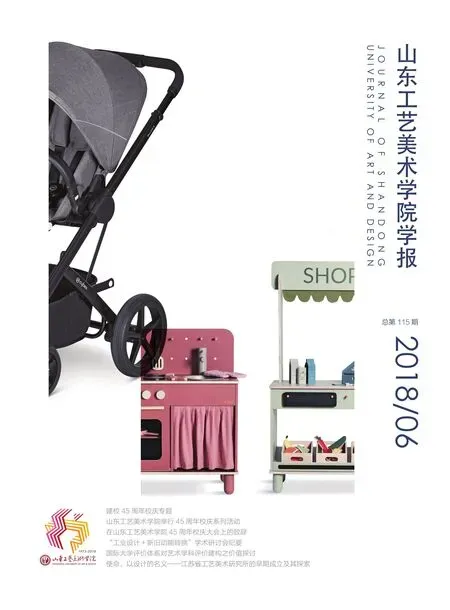中国现代艺术中的“边缘图像”观看辩证法
——国内少数民族题材艺术问题研究
姚绍将 罗霄 张锦华
1.现代艺术的视觉性问题
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有个极有深意的比喻,把人类的进步看作不断沿着梯子往上爬的过程,但是每往上爬几步总是会回头看看。[1]而我们的艺术史的发展也总是处在这样的路上。当“艺术史终结了”“艺术终结”“艺术死亡”被不断提出,我们或许又不约而同地往回“看看”,追寻那与“原始艺术”“先民艺术”“原住民艺术”密切关系的因素,来校正与构想我们未来的路。黑格尔、汉斯·贝尔廷、亚瑟·丹托等批评家都曾涉及艺术(史)终结问题,但是也正如贝尔廷指出艺术只是传统的范式终结了,而新的范式出现。那么艺术就不会消亡,是在不断革新的历史范式中生存。
“原始艺术”在中西方都是一个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纵横关系的词汇,而原始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时而显山露水,时而扑朔迷离。艺术史显示了现代艺术家康定斯基、高更和野兽派、侨社和青骑士、毕加索、蒙德里安、米罗、克利和达利等人都曾取经原始文化艺术;对非欧洲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发掘总是能给西方现代艺术带来一系列新的内容。原始人的艺术扩展了我们有关什么是‘艺术’的观念,使我们明白艺术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原始艺术或少数民族艺术一般来说,并非是纯粹性而是功利性的,也可说是自然主义为其形态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艺术是有着祭祀、巫术,为宗教服务的实用功能,而文艺复兴时期才被称为是“艺术的时期”。造型艺术之图像是直观、明晰和确定的,艺术自律其实也就是直观视觉图像的自律;但是塞尚之后的现代艺术,一反再现与透视法错觉的传统,艺术平面媒介自律追求被提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视觉图像变得难以阐释,不易理解,于是与艺术所面临的困境或转机类似的是直观图像的危机,传统图像再也无法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直观视觉图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时代的例证。而“艺术死亡”的提出暗示直观图像的危机,个人经验的观看替代了传统类型的视觉经验,零散破碎的抽象点线面或图形的现代主义艺术飞速崛起。“直观视觉图像”几乎不见踪影了。
从近百年现代美术史来看,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后发达国家”,我们的现代艺术发展与西方总是保持着一个较大的时间差。19世纪中叶西方现代艺术摆脱某些社会服务产生的时候,中国文人画依然是主流;西方现代艺术自觉发展时,而我们由“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持续的摸索;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家借鉴、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思想主题,形成了以西方18-19世纪现代艺术思潮为基础的艺术习惯,并于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融合发展:或启蒙发新,或救亡图存,或宣传鼓动,或思想解放,或自我表达,或市场盈利。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现代艺术发展历程。时至今日,国内艺术自律到底为何物,或许依然是一种奢望,直观的视觉图像这一基本的形态在很多时候都犹如无解天书,或抛至九霄云外。当现代主义艺术直观图像不见踪影、遭到质疑时候,把从未间断过或从未衰落过的“边缘图像描绘”作为一种反思,因为这种反思描绘的直观视觉图像正好弥补传统美术的单调与当代艺术“无图像”或“无法理解的图像”等视觉性问题。
20世纪初以来,中国主流美术家的创作一直保持着一份边地的情缘,对边地风土人情连绵不断视觉化。庞薰琹描绘的质朴的贵州苗族图像,吴作人笔下高原劳动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景观,董希文看到的独具生命力的高原雪山形象,黄胄以朴实神妙的笔墨塑造的新疆歌舞,杜滋龄大写意下的牦牛与皑皑白雪,吴长江笔下丰富多彩的藏族群众……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在中国美术创作的浩瀚星空。这就是中国现代造型艺术中的“边地描绘”与“边缘图像”。
2.战乱下的田园牧歌式图像叙事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首先是出于战乱,大批艺术家内迁避难;二是国家政府战略需要,沿海很多高校与艺术院校迁移,文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相继从东部撤离,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大致有三条路线:第一是北京—河南—汉口—贵州—云南;第二是南京—汉口—重庆(一部分北上穿过四川—兰州—敦煌);第三是自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云南(或桂林)。进入边疆地区的艺术家自然而然接触到少数民族及民间的生活现实,从而展开了描绘民族性生活画卷的探索,代表人物是庞薰琹、吴作人、常书鸿、司徒乔等人。艺术家们深入大西南、大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避难、考察和创作,成为国内现代美术的首批“边缘图像描绘和制作的拓荒者”。不过他们基本停留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风情的初步接触上,有一定的猎奇心理,画家对民族风俗与生态景观的描绘,仅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关注。著名汉学家迈克尔·苏立文对此是这样描述的:“坚持走到西部的那些人,后来把那些经历视为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值得回忆的岁月。西部省份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原始的美,对于那些来自沿海地区的青年男女来说,有如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他们对中国幅员的辽阔和国土的美丽,以及身为中国人这一事实有了新的觉醒。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改变,使他们的艺术也在发生变化。”[2]贴切可信。
传奇画家沈逸千早在1932年就随国民政府的“陕西实业考察团”进入民族地区,在绥远和蒙古居住数月,用上百幅绘画及素描,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并出版了《蒙边西北画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察绥西蒙写生集》(天津大公报社,1937年)。其传世名作《鄂尔多斯牧游记》《哈萨克牧羊女》中的草原风土人情以透视法的近大远小和国画线性造型来表达。批评家陈锦文认为“他(沈逸千)捕捉到了蒙古广袤无垠的感觉和自由的气氛,以及它的宁静与寂寞。正是边疆的这些特点,使它后来成为受不了沉闷的意识形态,以及国民的官僚政治压抑的艺术家们的避难地。”[3]1941年沈逸千又一次随军队进入大西北写生,因此,沈逸千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领头羊”。1944年6月至1945年2月,吴作人赴青康藏地区旅行作速写、水彩多幅,并开始创作中国画及在康定举行个人画展。他激动地回忆,那雪原上成群的奔牦,把寂静的原野,翻腾得云雾迷蒙,使人看了心潮澎湃。”因此,牦牛、骆驼是吴作人的中国画图像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吴作人经历个人生活的不幸与坎坷及战争的逃难,都无形中为他艺术修养的深沉内涵奠定了感情基础,而40年代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成为其艺术生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漫游青藏高原长达两年,在牧区直接体会边地居民淳朴的民族精神。如1943年8月吴作人参加青海藏民祭海盛典,《祭青海》以壮阔的构图,宏伟的气势勾画了高原辽阔明朗,人民豁达粗放的图像。司徒乔是1945年跟随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前线视察团西北视察组深入到新疆等地,创作了《套马图》《巩哈饮马图》《新疆集市》《蒙族牧民头像》《维吾族歌手》等。他以西方技法与国画理念结合,经常在图像中放置“留白”“虚实”,虽然是水彩与水粉画,却体现了返回文人画传统的情感倾向。对边地风土人情的灵动色调感的图画,引人入胜。
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合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庞薰琹受托于1938年开始搜集古代装饰纹样和考察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翌年他深入黔中民族地区作实地考察工作,深入80多个苗族及其民族部落地区长达数月,收集到600多件民族服饰和刺绣。庞薰琹在苗家人中间生活并创作了一些作品带回昆明,著名的《贵州山民图卷》“表面上是民族学的记录,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些作品将准确性与人情趣味、略带浪漫的格调,以及在巴黎所学得的对形式感的关注结合在一起。”。[4]庞薰琹把此时自己的创作称为“灰色时期”,声称他的《贵州山民图》(20幅)当然不是苗族同胞生活中的真实面目,甚至相去甚远。他指出“真”不在于形,而在于心。叶浅予先生1940年开始贵州苗区写生,在他的很多名画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贵州苗族生活和风情为题材,如《贵州马帮图》《苗家织女图》《苗岭之春》等,他曾说:“我从漫画转向国画,宿愿已久。抗日战争推动了我,苗区之行是个机会。”[5]此番话,道出了叶浅予的国画(尤其是人物国画)与贵州苗家人的密切关系。叶浅予以国画的手法,设色浓厚而不艳俗,以俊朗流畅笔法呈现苗家人生活之美。另外,中国木刻研究会的刘平之,以厚朴手法创作了大量丰富多彩的苗家人生活的版画。1938年常书鸿随国立艺专进入云南,任代理校长,并于1940年在昆明举办个人画展。还有丁聪、郁风等许多艺术家在西部和西南的崇山原野之间旅行。简而言之,此时很多艺术家在逐渐地发现边疆地区,从这些民族地区获得新的视觉素养,耳目一新。在视觉艺术思想中反映出边地生活的文字记录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图像叙事也应受到重视的趋势。
这个时期虽然是国内现代艺术首次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因民族危亡的迫切要求,而形成对边地关注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的“边缘图像”对个人、中国现代艺术、边地艺术贡献很大。这时期的这些艺术家长期居住在国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有一部分还曾留学国外,因突遭战争之苦而避难内地。他们几乎都是初次接触到自己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景观,是颠沛流离、远离亲人状态下的视觉感染,并非基于一种深入理解少数民族文化以图像来进行客观叙事,而是在战略忧患意识中想象构造的一幕幕欢乐温馨的田园牧歌图。艺术家丹青翰墨下的“边缘图像”是一种被动的撤退的视觉休憩。此时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艺术家故乡的战乱,成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虽然这些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但相对于战乱,还是显得宁静,与蒋兆和、潘玉良描绘国内战争的“废墟图像”形成鲜明对比。艺术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新的视觉冲击、新的感情色彩、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形成新的艺术积累。
3.意识形态延伸下的边地视觉经验
20世纪50-70年代,应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国家艺术文化制度体系根基需要全面的整顿,大量民族调查纳入官方文化部门的议程。组织许多艺术家、作家、文艺工作者分期分批跟随工作组、文工团远赴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收集资料。此时,生产建设兵团进入新疆,青藏、康藏公路相继通车,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譬如,“大众化”美术运动,画家下乡下厂“文化上山”运动;在音乐方面,1956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曾派出采访小组到西藏地区歌舞音乐囊玛和堆谢、新疆哈萨克民歌和器乐、海南黎族音乐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
这种以国家文艺政策为基础的美术创作为边地艺术实践奠定了基础,影响了边地人民自己的艺术自觉。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奠定时期,对文艺的总体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是现实的反映”和“无产阶级文艺”等。文艺活动的风雨兼程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纠缠不清。而此时美术创作带有民族团结的重大主题,而实质是也宣传了意识形态之下视觉的宏大叙事。很多艺术家以少数民族题材的图像都或多或少地充当着政治运动的宣传与鼓动角色。此时“中心地带”的优秀的艺术家几乎都被卷入了政治对文艺的大批判中,一定程度上使创作受阻。但实质上,国家倡导的民族大团结政策和民族地区相互交融的便捷推动了民族系列美术创作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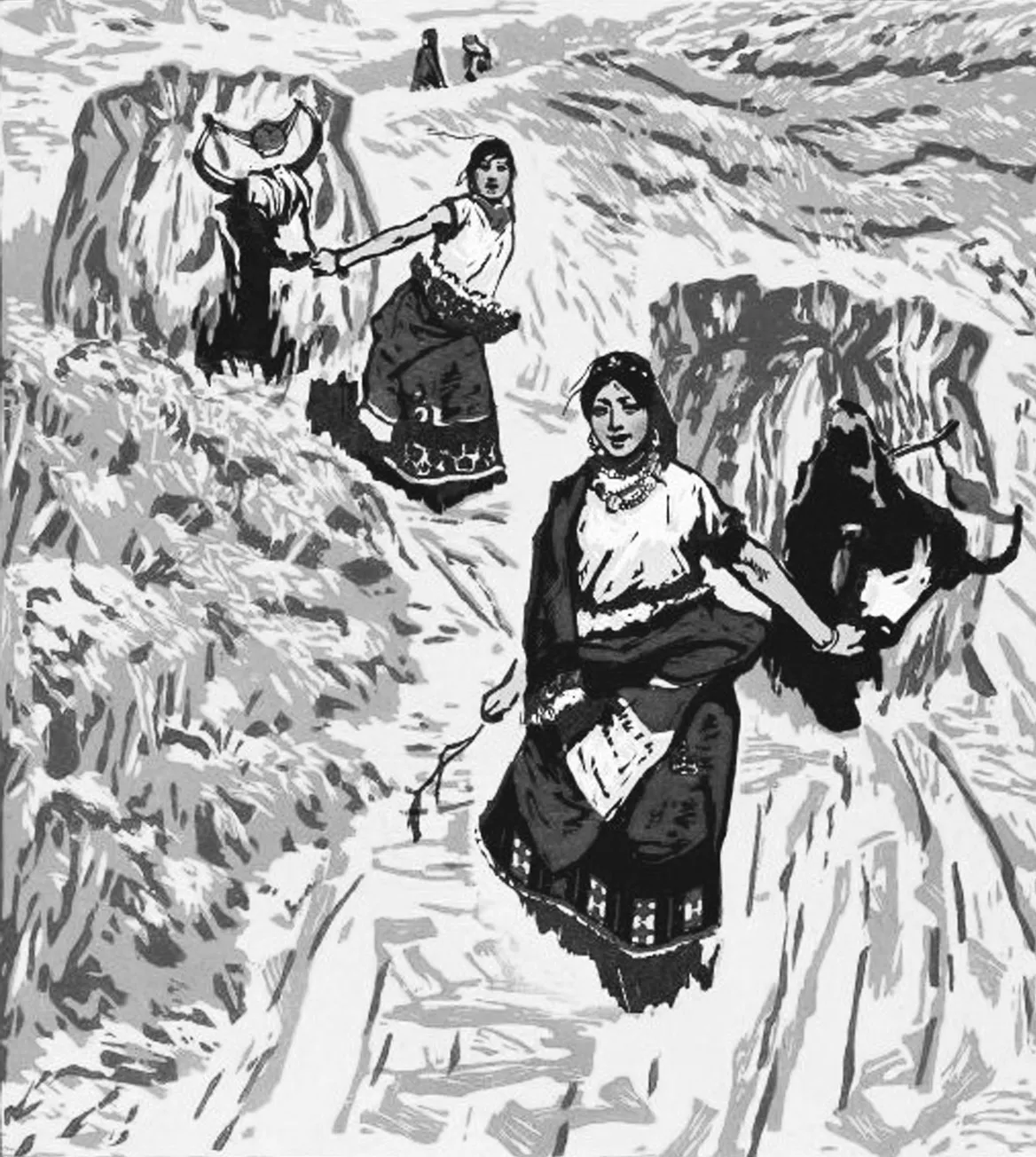
图1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1953年,在四川工作的李焕民把西藏、甘孜、阿坝等民族地区作为创作基地,以版画为主,木刻版画《藏族女孩》有机糅合靠在门框、靠在帐篷或躲在妈妈身后看陌生来客的藏族女孩的视知觉而完成,情感真实细腻。《初踏黄金路》(图1)呈现西藏民主改革后,藏族人民用歌舞来表达丰收喜悦的画面。金黄色粮食般的画面,喜笑颜开的藏族姑娘手牵着载驼粮食的牛走在金色路上,以富有想象力而不乏生动地表达新中国藏民的生活,隐含着与国家宏大叙事的视觉趣味。“而政治文化中心的一些艺术家为了暂时忘掉政治压力与党务要求,一起旅行,逃离北京沉闷的气氛。如1961年,吴冠中和董希文去西藏作画;郁风跑到大西北;吴作人时常去边疆与藏族人、牦牛呆在一起,而不是与首都的文化官员。”欢快的乐观主义情绪充溢在董希文充满阳光和鲜花的田园般的西藏和边疆地区的风景画以及农民们和牧民们的笑脸中。其《千年的土地翻了身》以少数民族题材寓意新世界的到来。他的画风也显示出谢洛夫和以撒·列维坦的影响。此时川地风格的雕塑开始发展起来。1963年,郭其祥用石头雕刻出一位西藏妇女,与后来的油画家罗中立那样,创造出了一种宏伟厚重的形式与生动自然的效果。吴冠中写意油画《扎什伦布寺》(1961),潘世勋《潘世勋西藏画册》,民族画家哈孜·艾买提《罪恶的审判》,周昌谷以水墨为主充满诗意的《两只羔羊》,以新疆少数民族为题材的黄胄的《日夜想念毛主席》《庆丰收》《洪荒风雪》等作品,虽然以平民化审美意识礼赞少数民族地区风格与劳动生活的作品,但并没有隐退一种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的视觉宏大叙事。再有就是从小就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刘大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他的作品有着一种装饰效果的宏大构图,但也有饱满的文化含量。如《马背上的民族》《巴扎归来》《雪山》等。“藏地美术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几代艺术家不惜辛劳,呕心沥血,在藏族聚集区挥洒热血与汗水。
此时的“边地描绘”出现两个特点:一是在新中国民族团结主题的宏大叙事中民族题材的创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与高度政治化的“文革”文艺的“高大全”“红光亮”图像形成对照;二是自由艺术家因避开压抑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进入民族地区进行的创作,延续着到边地自由创作的视觉方式。但是二者都是在意识形态延伸之下对少数民族边地描绘的视觉经验。相对于不能描绘“悲剧”“苦痛”的“文革”主流艺术而言,边地描绘更显示出一种艺术真实:视觉图像直观地自然而然发生的内在要求。很多这类艺术作品生命在接下来的时间获得了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4.都市与边地之间自由的观看之道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批青年像朝圣者一样源源不断地奔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对边疆审美想象的激情,被真正踏上了这些地方后的饥寒交迫、冷暖交加等各种伤痛所取代;对边疆真实生活的热恋转为对亲人的无比想念。70年代后期的返城浪潮中,暂时消解了对民族地区的神往。
但是随着现代工业与城市的快速发展,引起人情冷漠、信仰丢失等等状况,文学家艺术家又通过边地的字符领域和图像叙事寻找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淡漠与流失的信仰体现,进而重构“边地故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保存人和自然的原初状态。向着边地的朝圣之旅,就是对俗世的怀疑和逃离,是游荡的现代人或都市人的梦想。“闲逛者”“波西米亚人”“拾垃圾者”,与其说是现代人或都市人的“绰号”,不如说是他们灵魂的徽章。他们在人群之中游走,寻找远走他乡的机遇,要认“他乡”作故乡。边地残存着信仰,仿佛是现代人信仰体系崩溃的最后救星;尚未污染的自然之中,仿佛埋藏着获救的秘密。经历上山下乡返回中心地带的作家,对边疆生态系统“二度叙事”,目的在于寄托那一份拥挤的心灵与压抑的情绪。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贵州山地吊脚楼里的姑娘,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等等都充满了巨大诱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作家通过文学作品的想象建构了大量边疆神话。作家把自己在边疆少数民族体验转化为了一部部的文学作品。王蒙的《在伊犁》、张贤亮的《绿化树》、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的《蹉跎岁月》、先锋派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的《心灵史》《黑骏马》等,还有新世纪以来阿莱的《尘埃落定》、杨志军的《伏藏》《藏獒》,冉平的《蒙古往事》、姜戎的《狼图腾》等,在很大程度上以字符领域的想象带动视觉艺术家走向少数民族边地。与之前几个时期相比较,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缘图像”是画家主动出击,以寻找灵感艺术,提高艺术领悟,自由重构民族图像叙事为己任。
陈丹青与黄素宁以艰苦卓绝经历在藏族地区找到了少数民族这一特殊题材,史诗般的构思、充分的写实技巧,还原了艺术的真实。陈丹青《西藏组画》笔下的藏族人民不再是前两个时期的初触民族地区的自我田园牧歌式图像与50-70年意识形态大叙事下载歌载舞的宣传符号,而是一种有着生命厚重与深沉的文化载体。同期去藏族地区的还有艾轩、吴长江、莫测等。陈丹青与艾轩的作品相比较:陈丹青视野中的图像是英雄般的西藏人,辛勤劳作、拥抱接吻、脱衣沐浴,他们如此强烈的身体的在场,使我们几乎能闻到他们的气味,能听到他们的大笑或喋喋细语。艾轩呈现的图像是西藏人生活在一个荒凉、寒冷、空旷的世界里,唯一打破静寂的声音只是那永不停息的风的呜咽。李忠良和“伤痕美术”代表之一的张红年创作了《土地的深情》(1980年),描绘了沉重的西藏人,而苏立文认为,事实上却没有传达出任何情感。

图2 《苗岭踏青》 叶浅予
城市、工业、“拜金主义”等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西方五花八门的艺术手法相继进入国内。而也是相对自由的环境使得“1980年代那些拒绝西方影响的雕塑家,正在更靠近自己家乡的地方——所幸的是,不是在云冈和龙门的佛教雕塑里,而是在本土文化的深处以及少数民族的艺术之中寻求灵感。”[7]徐匡表现西藏人和牧民的有力黑白形象,与罗中立、陈丹青和艾轩创造的油画藏民形象形成对比;董克俊是五月木刻研究会成员,后定居贵阳,他从黔地苗家人的信仰、巫术、面具、舞蹈、斗牛和祭祀中寻找主题,以黑白色(早期)与原色创作,传递苗族人野性而活力的视觉图像。张克瑞《冬季草原》(1980年)、佚名《珠海姑娘》都是扎根于对少数民族的视觉经验。叶浅予创作了有名的《苗岭踏青》(图2),云南版画家李忠翔、郑旭、曾晓峰深受佤族等少数民族风情启发,发展出色彩强烈的视觉风格。吴长江对藏人的研究显示在对于木刻优美线条的巧妙拥有。袁运生在首都机场装饰壁画《生命之歌》,用复杂的构图、动作与事件,以一种设计感描绘了西双版纳傣族人过泼水节的情景。云贵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艺术家们的向往之地,人们被那里繁茂的热带风、风景如画的村寨以及美丽的妇女所吸引。泼水中的两个裸体引起了风暴,西双版纳的党的官员宣称,傣族人反对这种形象表达,墙上的裸体部分先后被帘子和镶饰板遮盖了起来。而袁运生曾是同丁绍光一起到西双版纳的,丁绍光也描绘了大量傣族人生活的图像。如《西双版纳的村庄》(1970,墨笔),为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壁画《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当然,丁绍光后来又成为“云南画派”昆明艺术家成员,以描绘西南少数民族为特色的“申社”成员,此组织还包括刘自鸣、姚钟华等。他们是“中国重彩画家”,以坚韧的高丽纸的正反两面施以厚重的笔墨,大大增加了色彩的深度与亮度。特立独行的罗尔纯长期呆在西双版纳作画,赞赏高更和梵高,置身于主流之外,但是画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常常对中国艺术家产生解放性的影响。而同时,刘秉江和周菱也为北京饭店创作了壁画《创造·收获·欢乐》。“四川画派”艺术家刘国枢呈现了名作《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罗中立在大巴山的生活成就了《父亲》(1980,油画)图式。黄永玉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腹地凤凰的那些风景画属于他最优秀的作品,另有阿诗玛插图《妈妈的好女儿》。他更乐于悉心审视家乡河岸、人民、房屋与田园,与大文学家沈从文共同构建了一个美丽而温馨的边地神话。这一时期另有不少民族题材的作品在文化部举办的第六届、第七届美展获奖,如韩书力的连环画《邦锦美朵》、韦尔申的《吉祥蒙古》、陈逸青的《走出青海》等。
90年代以来,刘秉江追随导师董希文深入民族地区以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路子,1962年—1999年先后到云南、四川、广西、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西藏等傣族、彝族、侗族、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黎族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写生。而值得斟酌的是80—90年代创作成为名作的《塔吉克族少女》(图3)《塔吉克族新娘》《新疆喀什妇女》《维吾尔族老人》《蒙面的喀什女人》《塔吉克族新娘》等,皆是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题材的人物画。詹建俊是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的弟子,在新疆地区写生,以强烈的色彩与坚实造型的油画展现了新疆人民的形态。雕塑家王济达和他的妻子金高在蒙古美术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品主要以表现蒙古族普通劳动人民形象和生活为内容,在人物塑造上,突出“力”与“运动”的表现。造型概括、简练,生动并富有气势;风格写实、质朴。如《驯马》《月亮花》《线》《母亲》《套马》《草原女民兵》等。吴长江几乎每年都去藏族地区写生,写生就是他的创作,对写生的重视、对学生的教诲,以及他对藏族题材的固守,都体现了一种对人性本真本我、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追求。他的绘画刻画出了少数民族生活的质朴与艰难,画出了他们与自然接近的原始的美。他出版了影响后世的《吴长江西藏速写画集》和《吴长江的世界·西藏人和生活素描集》。此时的董克俊依然以贵州少数民族的风俗为基础创造图像,只是在早期黑白色中加入丰富的色彩,作品增添欢乐的情调。另外,还有女艺术家王平和刘雍。王平从贵州苗族的艺术、宗教信仰和风情习俗中寻找主题,用陶土和木头创作出有力的、自由的艺术形式,如作品《圣柱》等。本土工艺大师刘雍的雕刻艺术将黔地民族民间文化融入现代艺术创作,很具创造性。当然,在当下国际蜡染工艺热潮中,苗家人千年历史的蜡染技术成为当代新艺术的重要媒介材质。

图3 《塔吉克少女》 刘秉江

图4 《塔吉克新娘》 靳尚谊
此外,靳尚谊、“草原画派”组织者之一妥木斯、黄胄等老一辈优秀艺术家都会时常深入他们曾经去过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创作,创作了《塔吉克新娘》(图4)、《垛草的妇女》、《欢腾的草原》等作品。即使新世纪的今天,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成为艺术家采风写生、艺术教育调研获取灵感的基地。全国艺术院校学生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验,“边地图像”也出现在电影、广告设计、都市建筑中,多元地呈现了现代都市与边地之间自由的观看之道。
5.结语
显而易见,从未间断过的“边缘描绘”并非一个简单的艺术采风调研与写生的问题。艺术史发展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暂时地走入带有人类浓重原始韵味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中徘徊,艺术家也经常从“边缘描绘”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美术图像或造型所建构的边地描绘,既可以采取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也能够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都有意无意地蕴育着某种艺术生命力的活力因素,直观的视觉图像始终为核心。中国现代美术的“边地描述”,也是这样一种辩证的逻辑:自由的“田园牧歌式”的图像叙事是一种“喜剧模式”,而同存反面的或是战乱背井离乡,或因意识形态与城市荒漠而逃避中心的“悲剧模式”,那也就毋庸置疑地隐含着对纯粹的和绝对的自律艺术的理想主义嗜好的批判。边地并非真正的边缘,少数民族艺术与少数民族题材的艺术经常会引导人类“回头看看”。
注释:
[1]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博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2]迈克尔·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M]:陈卫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72
[3]陈锦云.美术大记事[J].天下月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7):207-208
[4]同[2],175
[5]余岛.大画家叶浅予与贵州苗族[J].中国民族,1993(10):41
[6]同[2],250
[7]同[2],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