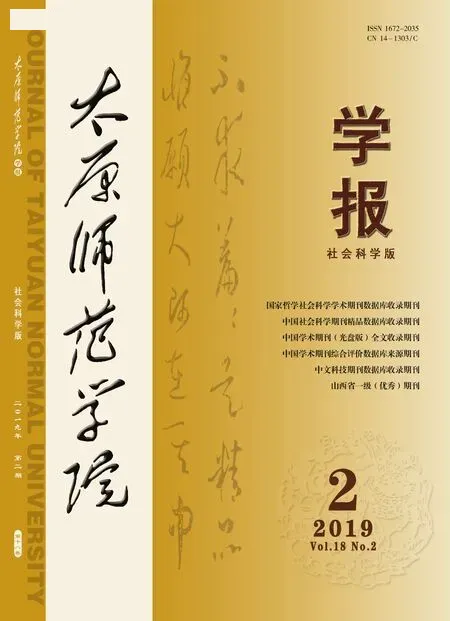从死亡言说看贾宝玉对《庄子》的接受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与很多著作避谈死亡不同,《庄子》和《红楼梦》用较大篇幅书写“死亡”。根据笔者统计,《庄子》里“死”字一共出现了209次,涉及各种各样的死亡现象和复杂的死亡观念。这说明死亡意识是庄子生存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探究庄子生命观念的重要视角。《红楼梦》也描写了大量的死亡现象,充斥着大量的死亡言说,这也与该书整体所呈现出的悲剧感、幻灭感相契合。贾宝玉作为小说中思想意识最为丰富的灵魂人物,他不仅阅读《南华经》,还结合自身的经历去阐发和领悟。贾宝玉的死亡意识渗透进其怪诞行为和动人的情感世界中,形成了其生命形态的审美气质,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492
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贾宝玉的精神世界有对《庄子》思想的接受。《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无材”“自适”“齐物”“人道”的观点皆源自庄子,是建构主人公贾宝玉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也是《红楼梦》全书的思想旨归。[2]《庄子》“道”“气”的内涵为“虚”“无”,而贾宝玉的“情”则为“有”,但“物化于情”和“物化于道”之间存在承袭关系。[3]笔者认为,庄子对贾宝玉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二者在死亡意识上相契合的表征,其实质是二者的行为模式与生命哲学都深受死亡焦虑的驱动,这是二者承续性的根本表现。但是,在深刻的死亡感知与哲学思索后,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贾宝玉关于生存意义的追溯更具主动性。
一、言说死亡
《庄子》和《红楼梦》都对“死亡”格外青睐,庄子和贾宝玉不仅言说死亡,还形成了深刻的死亡观念。庄子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必然性,这也是庄子死亡观得以构建的前提。《庄子》恢诡谲怪、自由散漫的语言背后是一个超脱哀乐、飘逸出尘的人物形象,世间一切对于庄子来说本该是无差别的存在,但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庄子却如常人一般在意。他反复叹息时光的流逝,不厌其烦地言说着大量的死亡现象。如: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4]241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4]584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4]630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4]746
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讬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4]1000
和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不同,庄子将最惨淡的事实摆在人类面前,毫不避讳地说着死亡必然来临的残酷性。《红楼梦》也是如此,故事开端就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高唱死亡之歌。此外,“悼红轩”[5]5“薄命司”[5]52等词句在开头便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死亡氛围。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虽然成长于脂粉富贵堆,但“似这般生死劫谁能躲”的道理却时时警醒着他们。曹雪芹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人必然会死的观点。
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口气没了,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5]384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以强求的![5]487
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5]807
况且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5]845
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5]921
不仅如此,大量的死亡现象也贯穿于庄子的哲学表述和《红楼梦》的叙事发展中。庄子笔下的死亡现象纷繁复杂,涉及的死亡对象有狸狌、子桑户、孟孙才母、老聃、子来、庄子妻、髑髅、鸟、单豹、张毅、彘、山中之木、主人之雁、老龙、狙執、龙逢、比干、箕子、恶来、桀、纣、伍员、苌弘、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庄子等,这些生命的死亡情境各有差异,死亡原因不尽相同,庄子的评论也具有差异。同样,在《红楼梦》中,一百二十回的叙事内容被认为是金陵的录鬼簿,充斥着大量的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从《红楼梦》第一回开始,贾雨村发妻、林如海儿子、贾敏、贾珠、冯渊、贾瑞、秦可卿、瑞珠、林如海、金哥、守备之子、秦业、秦钟、金钏儿、鲍二媳妇、老太妃、菂官、贾敬、尤三姐、尤二姐、晴雯、贾元春、林黛玉、夏金桂、贾母、贾迎春、王熙凤等人相继去世,死亡现象贯穿并推动了《红楼梦》所有的叙事结构。生命的丧失和繁华的凋零,营造了最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情景。《庄子》和《红楼梦》中大量的死亡言说,体现了作者对“死亡”命题的青睐。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死亡感知最丰富和深刻的两个人物。林黛玉长期在死亡准备中神伤,贾宝玉不仅经常把死亡挂在嘴边,还时时陷入对死亡的遐想中。本是翩翩公子的贾宝玉却最为真切地见证了死亡和衰败,频繁的死亡体验造就了贾宝玉的哲人气质和特殊风貌。和林黛玉喜散不喜聚的死亡准备不同,痴痴傻傻的宝玉极度留恋相聚的美好时光。他曾在欢乐气氛中笑着说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5]807这看似通达的话语,却渗透出对生离死别必然到来的忧伤。人必然会死的观念是庄子和贾宝玉生存哲学思考的基础,也驱使两人在显性层面上对死亡产生焦虑。在这种强烈的惧死动机下,庄子和贾宝玉在死亡准备中展开了自身的生命哲学逻辑,具体表现为“无为”与“无材”。
庄子和贾宝玉都留恋着生命的存在状态,他们的死亡言说建立在自己对“生”的痴迷与“死”的无奈之上,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生命形态的选择和对待死亡的态度。如何生存才得以保全自身,是庄子和贾宝玉思索存在的前提。在应对和解决死亡焦虑时,与儒家对生存价值的功利追求、宗教对死亡的美好遐想不同,庄子和贾宝玉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庄子非常注重养生,书中有大量关于如何保存生命的议论。在《达生》篇中,谈论了单豹养神、张毅养形的事迹,两人都没能达到保全自身之目的。庄子保全生命时主张将养神和养形结合起来,而“无为”思想是养神与养生相结合的根本途径,也是庄子生命形态的最大特征。庄子的“无为”体现在主张去智巧机便、去知识、去名利、去富贵、去仁义、去崇高、去权术,反对执着外物而“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庄子列举了大量因俗欲而走向死亡的例子,呈现了他死亡思想的倾向性。狸狌“卑身而伏、不避高下”,最终“中于机辟,死于罔罟”;浑沌因有了“七窍”而死,最终“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伯夷、盗跖为了名利而“残生伤性”;烈士为天下善,却“未足以活身”;一只狙因敏捷巧便而被吴王射死;关龙逢、比干、箕子、恶来忠心耿耿,却都死得凄惨;圣贤如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忠烈如鲍焦抱木而死,忠傲如申徒狄负石而死,忠义如介子推抱木燔死,坚信如尾生抱梁柱而死,等等。死亡焦虑是庄子认识世界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在庄子心中,这些因外物而殉身的人都不足以称赞,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保全生命。由此逻辑可知,庄子形成了“无为”的生命哲学观念,其实质是消解道德、消解崇高,绝圣弃智,摒弃一切可能会妨碍寿命的凡俗欲望。
庄子这种惧死动机下的生命哲学逻辑深深地影响到贾宝玉的人生选择,具体体现为贾宝玉的“无材”。贾宝玉就像是《庄子》笔下那棵因“无材”而得以保身的神社栎树,较之栎树,他的选择更加具有叛逆的性质。他满腹经纶、气质出众,本是被贾家寄予厚望的后辈,却选择成为“无用之人”,坚持一种与社会主流相对抗的姿态。偈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被甲戌侧批为“书之本旨”,这体现了“无材”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凝聚在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中。贾宝玉含玉而生,却视金钱名利为粪土,对学问和仕途经济都嗤之以鼻,这是典型的道家态度,故贾宝玉排斥混迹于名利场的贾雨村,把那些规劝他立身扬名的话语称为“混账话”,并认为自己此番态度认识和超凡脱俗的林黛玉心心相印。贾宝玉从没在意过功名、富贵,长期以来在大观园中过着不为正统所接受的生活。他批评薛宝钗:“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5]378由此可见,贾宝玉绝不是懵懂乖张之人,他的反正统、反世俗实质是一种超越性的死亡观念引领下的清醒状态。虽然贾宝玉因不爱读书、不求上进、不理俗物而有着“无事忙”“富贵闲人”的雅号,但他却不是薛蟠那样的纨绔子弟。贾宝玉含着青埂峰下的补天石而生,在他的身体里,人和石的秉性融为一体,故贾宝玉的生命形态自然体现为“无材可去补苍天”。不仅如此,和庄子一样,贾宝玉的死亡观念也体现出了对“崇高死”“伦理死”的消解和对“顺应而为”的追求。贾宝玉在讨论死亡时说:
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窝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也断断不把这万机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5]384-385
《庄子》中所列举的如伯夷、叔齐式的人物正是贾宝玉口中那些为了沽名钓誉而死的人,他们逞勇为名,白白伤害了自家性命。贾宝玉像庄子一样鄙视主流所认可的“崇高”,反对名重于命,自然也消解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价值论。而贾宝玉的“无材”也如庄子之“无为”一样,没有走向自我毁灭,反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存在形态。这是因为二者的本质都是惧死动机下所选择的生命应对机制。
二、思考死亡
贾宝玉和庄子陷入深深的死亡焦虑后,用“无为”和“无材”构建了自身的生命哲学。因为选择忘怀事功得失、弃绝执着,所以他们都能够回归本真,最终趋向于“真人”,都活出了超越尘俗的人生。虽然他们都在惧死动机下展开了关于生命的哲学思考,但死亡的焦虑仍会萦绕心间,进而损害形体,在此情形下,一切养生方式都是无效的。所以,如何认知死亡成为解决死亡焦虑的核心内容。庄子的“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4]262正是沿着这个逻辑出发,只有超越对死亡的普通认知才能够真正有克服死亡焦虑的可能。庄子对待死亡的认知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死生昼夜,生死一体。“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4]616,生和死的关系就像白天和黑夜,是自然的变化。死和生一样,是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4]733“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4]615可见,生和死是一体的,对死如生。其二,生劳死乐,死生如梦。庄子认为世人悦生恶死的想法过于狭隘,提出“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4]103的疑问。庄周梦蝶体现了庄子天马行空的诡谲思维,但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庄子同样追问过“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4]104,谁能确定生为梦、死为觉呢?其三,不死不生,不知生死。“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4]229“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4]274庄子克服死亡焦虑的最高层次是消除生死观念,进入到彻底的虚静状态。这三点是庄子死亡观念的三个层次,具体到方法论上,庄子追求“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4]128的“悬解”状态。老聃去世时,秦失作为朋友却“三号而出”;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孟孙才母亲去世时“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4]274。庄子的“悬解”状态消解了死亡的伦理意义和情感影响,进入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79的自由境地,这也是超越死亡的动机下庄子的应对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贾宝玉。
贾宝玉在女儿堆里受到冷落以后,“说不得横了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5]217。贾宝玉在认识到人必然会死的前提下,自觉地追求庄子“哀乐而不能入”的状态。在惧死动机下选择消解生存情感以求得宁静,这是贾宝玉的策略。这也说明贾宝玉在死亡焦虑下生存应对方式和庄子是一致的。后来贾宝玉阅读《庄子》中表达“绝圣弃智”思想的《胠箧》一则,有感于此,不禁提笔续曰: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5]218
薛宝钗的“仙姿”、林黛玉的“灵窍”是贾宝玉被“迷惑缠陷”的主要原因,所以贾宝玉想“绝圣弃智”,将这些影响他思绪的东西一一摒弃,最终使得自己能够进入“忘天下”的逍遥境界。这是贾宝玉死亡意识深受庄子思想浸润的重要体现。
庄子真正能够超脱生死吗?贾宝玉又是否从庄子的思想中获得了解救自身的方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质上钱钟书先生早就发现庄子的超脱有欲盖弥彰之嫌疑,其云:“庄生所谓‘悬解’……皆尚多此一举。非脑中横梗生死之见。何必作达。非意中系念生死之苦,何必解脱。破生死之执矣,然未并破而亦破也;忘生死之别矣,然未即忘而亦忘也。宋儒所谓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6]235-236将庄子视为真正的超脱之人,是颠倒了庄子生命哲学的逻辑思路。但是,庄子反复言说的生死观念体现出他对死亡的强烈焦虑,而“悬解”是他构建克服死亡焦虑的方法体系,故惧死动机和生存焦虑才是他生命哲学的真正起点。贾宝玉也是这样,他主动汲取庄子“绝圣弃智”思想浸润的根本原因是他过于在乎自己与林、薛等女儿们相处的情感体验,脑中横梗,所以苦闷难解。当他像庄子那样,早早理解到这些惹人烦忧的女子终为尘土,那么她们的喜怒哀乐便显得不那么重要。贾宝玉受到庄子的影响,主张摒弃人类在情感和气质上的独特性,使自己不因外物而心动,进入到庄子所营造的精神境界。散人贾宝玉,正是由于过度沉浸于薛宝钗、林黛玉、袭人、麝月等女子的灵性美好之中而不能自拔,所以妄想从《庄子》中找到解闷之法。而这种逻辑思路也决定了贾宝玉无法得到真正的超脱,无法达到佛家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后来,贾宝玉“续毕(《南华经》),掷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诸意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5]218。可见,这位怡红院的多情公子在求助庄子后又继续用全部心思爱恋着这些令他迷惑缠陷的女子。贾宝玉寄希望于用庄子消解情感、智识的方法回归忘我的境界,保全自身的形体,但最终都陷入了“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的境界。
三、应对死亡
贾宝玉虽然在死亡与存在的问题上受到了庄子的影响,但是他对死亡焦虑的应对途径和意义追溯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貌。庄子是通过“心斋”“坐忘”的抽象心理状态来实现对生死的超越,在对待自己的死亡时采取自然的态度。庄子有云:“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4]1063天人合一,体现出一种不困于死的大境界。庄子甚至想象自己死后“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4]1063,本为万物,归于万物。庄子为深受“死苦”的众生提供了一条“保身”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实质不仅消解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还消解了人类存在的伦理意义、情感体验,这虽类似于佛家的“空”,但庄子又没能真正走到林黛玉所说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状态。和庄子自觉排斥伦理情感,以审美和形而上的方式对抗死亡不同,贾宝玉以最真挚的“情”来应对深深的死亡焦虑,同时用这种人与人之间炽热的情感联结来建构出死亡之于人生的意义。贾宝玉在见证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死亡体验以后,他恐惧于美的死亡,极度迷恋暂时的美好: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人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5]290
虽然贾宝玉也曾在庄子思想中找寻忘怀牵挂的方法,但庄子本身的心理机制先天“未心放”,贾宝玉探寻之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失败之后,贾宝玉继续在大观园中悲女儿之悲、乐女儿之乐,用一片痴傻之心无差别地对待终归尘土的女子。贾宝玉也曾对庄子的应对方式感到绝望,与其无休止地寻求克服死亡焦虑之道,不如让死亡早点来临,尽早解脱痛苦。这更进一步体现出贾宝玉的死亡焦虑: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5]201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的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5]633
平时的贾宝玉无正形,但他思考存在时的“疯话”却极其敏锐和深刻。贾宝玉的死亡言说虽然透露出他对于死亡的耿耿于怀,但他并没有形成及时行乐的世俗思想,他选择用最为深刻和复杂的“情”主导自身的生存状态,过上自己所认同的快意人生,由此来应对自身深深的死亡焦虑。虽然贾宝玉也会对自己无法摆脱和女儿们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结而苦闷,但贾宝玉的“情”却一直都是他人生的主旋律。贾宝玉不仅以“情”来克服死亡,还在“情”中找到了死亡之于人类存在的意义。贾宝玉不止一次对自己的死亡进行遐思:
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敬可怜。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5]356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5]385
庄子认为死亡情境中生者的态度为“安时处顺,哀乐不入”,而“虚静无为”才是他所说的“死得其时”。贾宝玉对自己的死亡想象则呈现出与庄子完全不同的面貌,女儿们的“怜惜悲感”与“眼泪”是贾宝玉的“死得其时”,他者对贾宝玉存在的依恋则构成了贾宝玉对死亡的意义追溯。贾宝玉不仅没有否定情感哀乐,反而在众人对自己的情感爆发中获得了满足,死亡的悲感被生存的满足感所消解,这正是贾宝玉对庄子死亡观念的超越。
在应对死亡焦虑上,庄子虽然创设了一种形而上的死亡美学,心心念念于超脱困境之道却暴露了自身的“有所待”。贾宝玉的死亡言说也呈现出深深的死亡焦虑,但他却用所有心血守护存在的美好,结果却在情感的极度张扬中获得了关于死亡愉悦的遐思,这使得贾宝玉的生命形态除了是惧死动机下的应对机制外,还获得了死亡之于存在的意义。林黛玉和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对生死思考得最深入的人,林黛玉的死亡准备让贾宝玉产生爱怜,贾宝玉的“无材”与重情使林黛玉视其为知音,这也是二人爱情萌蘖的基础。阅读《庄子》可以让读者获得有限的超脱之感,而观贾宝玉的人生,方能感知人类在死亡乌云萦绕下生命存在的伟大而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