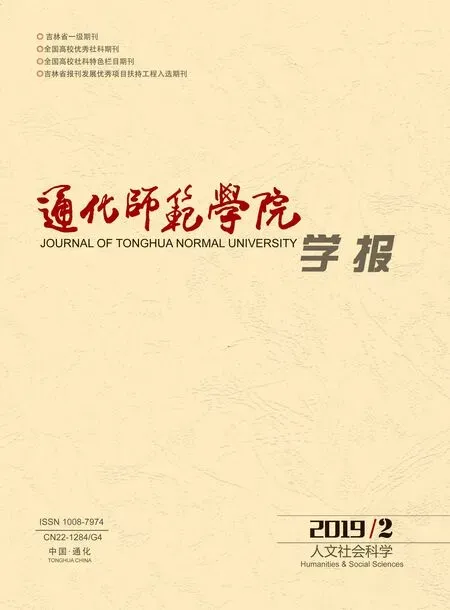“推”出来的中国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的动态性特征及其当代意义
沈玉梅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自提出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学界几乎没有被提起,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末期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开始关注,新千年伊始,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迅速升温,至今热度不减。①截至2017年12月12日,在中国知网,以“差序格局”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1945篇论文:1958年1篇,此后一直到1987年才有2篇;1987-1998年共21篇,1999年开始升温,每年均呈上升趋势。1999年16篇,2005年54篇。此后研究热度骤升,每年论文数均在100篇以上,2010年最多,达183篇。至今热度不减,2017年153篇。由于费孝通没有给“差序格局”一个明确的界定,因此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见仁见智。陈占江将这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是在自我主义层面理解差序格局并对之进行了延伸性解读;二是将自我主义作为费孝通的思想局限予以批评性解读。[1]徐前权、刘小锋把对“差序格局”的研究归纳为三种维度:一是描述性的;二是建构性的;三是理解性的。[2]不过,纵览这些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哪种诠释和解读,学者们大都在静态的视域中对“差序格局”概念进行解读,却常常忽视了这一概念的最重要特征——动态性。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提到过,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3]本文即是对“差序格局”概念的动态性特征进行解读,以期学界指正。
一、“私”的问题产生之根源:“差序格局”概念提出的原初语境
要说清楚“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动态性特征,还需回到这一概念提出的原初语境。我们知道,1947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论文集出版,其中第四篇“差序格局”和第五篇“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即是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着重阐述。回归文本,“差序格局”篇首费孝通即指出,“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同时他也认为这个“毛病”不仅限于“中国乡下佬”,就是所谓城里人同样也有:“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4]24
对于中国人“私”的问题,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应缘于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对中国文化、民族性的批判,比如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梁启超《论公德》中的“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之说,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缺乏公共精神”之判断,等等。知识分子们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旨在为当时命运多舛的中国开辟出一条新思想新文化的光明之路,以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20世纪30年代左右晏阳初提出的“民族再造理论”即是为根治农民的四大病根——愚、贫、弱、私——之实践努力的重要表现。费孝通研究“乡土中国”的目的也是意在探寻出一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之富裕之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志在富民”。
费孝通认为,既然“私”是中国乡下佬乃至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好好讨论一下。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就是群己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而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划法和西方社会又根本不同,所以就必须要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先讨论,然后才能讨论“私”这一问题。[4]25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费孝通提出来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
二、“推”出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动态性特征
为了更好地说清楚群己界限如何划分,即“私”的问题,费孝通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比较法,以“西洋”社会之“捆柴”式“团体格局”为镜像,形象地刻画出了“推”出来的中国社会结构之“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26-27。
这里,费孝通用到了一个动感很强的“推”字。事实上,在讨论儒家文化与中国社会结构时,用到“推”字的学者并非费孝通一人。比如潘光旦1936年在谈到中国社会的个人与群体关系时就用到了这个“推”字,他指出,个人和群体之间是一种‘推广’与‘扩充’的关系,也就是从修身始,经过齐家治国,而后达于平治天下。[5]339再如,余英时谈论中国儒家文化特点时同样用到了“推”字,他认为,儒家文化具有两个层次,即“为仁由己”和“人伦秩序”,它们是一以贯之的。仁伦秩序并非外力强加于人,它是从个人这一中心自然地推扩出来的。而“礼”就是和这一推扩程序相对应的原则。[6]29应该说,这个“推”字在儒家文化传统的人伦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
既然“差序格局”是“推”出来的,那么,它是如何“推”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什么“推”动了那颗“石子”形成了一圈圈的愈远愈薄的“水波纹”式的中国社会结构?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它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以及由“‘血缘关系的投影’形成的地缘关系”[7],对此我们并不苟同。因为,费孝通说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传统社会里,人和人之间关系形成的纲纪是“伦”,这也是社会结构的架格,这个架格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4]28比如血缘和地缘,既因人而异,也因人之势力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背后的那个“伦”是不变的。《中庸》里之所以把五伦作为下之达道,是因为社会结构里的“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也就是从己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的一条通路。[4]28因此,我们认为真正“推”动那颗“石子”的是“伦常”。
也正是在“己”之“伦常”的“推”动中,“差序格局”呈现出了最重要的动态性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由于差序格局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己”作中心,而“己”之中心势力的强弱变化也随时随地地推动着“己”之社会圈子的大小自如伸缩。比如血缘上,既可以如贾府辉煌时的“一表三千里”,也能够如潦倒归来时的苏秦之“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地缘上,街坊既可以小到比邻的两三家,也可以大到整个村庄。
二是“公”“私”关系的二重性。一重是以“己”为中心向“内”推所产生的“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4]29另一重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所产生的“公”。“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4]33“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修、齐、治、平”的层层外推,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8]
三是价值标准的相对性。由于差序格局是以“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克己复礼”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基于这个出发点,社会范围从“己”向外推,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比如亲属,与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悌;再如朋友,与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信;等等。于是,在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里,就形成很多条私人关系的网络,而每一条关系网络都对应着一种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因此而有差异。[4]33-36
正是由于差序格局具有以上的动态性特征,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其社会结构并非固定不变,它总会因以“己”之“伦常”的向内或向外“推”而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换言之,“己”之“伦常”的动态性“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也处在动态性的变化之中。于是,当我们基于这种动态性视角,运用动力理论来理解差序格局概念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扩张与伸缩、公私关系的二重性、差序界限的模糊性以及价值标准的相对性等问题,而不再局限于对差序格局本身的定义及其涵盖性的解读。[9]
也正是在这样的动态性视角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私的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自我主义之儒家文化传统:“私的问题”产生的根源
上文已述,费孝通“差序格局”一文的根本目的在于“讨论私的问题”,即追溯中国人“私”之毛病产生的根源。对于这一问题,费孝通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的比较分析中找到了答案。
在费孝通看来,这两种社会结构根本的不同点在于: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这种格局是由一个一个的团体构成,每一个团体皆由若干人组成,不同团体之间有着非常清楚的界限,模糊不得。每一个团体都是一个组织,他们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即使同一团体中存在不同的分组和级别,那也是预先规定的。因此团体格局群己界限清晰分明。[4]25而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则因“己”之“伦常”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界限搞成了相对性,因而群己界限模糊不清。[4]30换言之,西方社会的公私关系清清楚楚,而中国社会则公私关系不清不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种社会结构截然不同?费孝通认为是它们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不同导致的。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平等观念,这既保证了每个人地位平等,又使大家的权利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它规定了团体不能抹煞个人。而中国社会则以“自我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一切价值皆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4]28
那为什么这两种社会的道德基础又不同呢?费孝通认为是这两种社会存在的文化基础不同导致的:在西洋社会,文化基础是基督教。上帝作为团体的象征物,不仅保障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而且将这种平等体现在世俗生活中,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中国社会,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最讲究的是“伦”与“仁”。“伦”重在分别,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是从“己”一个一个推出的,社会范围则是由一个一个“己”之联系所构成的私人联系的网络。[4]33这种人伦又是通过“仁”体现出来的,“克己复礼为仁”。
由上可以看出,在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团体格局社会里,爱不分差序,同一团体的人是“兼爱”的,即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找不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这样的社会里,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基础,实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价值原则,因而群己界限清楚明白,公私关系确定分明。而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社会中,爱有等差,每根以“己”为中心的私人联系都被一种不同的道德要素维持着,也就是说,社会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在这样的社会里,以自我主义为道德基础,实行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则,故而群己界限不清不楚,公私关系模糊不清。由此,中国人“私”之毛病产生的根源便不言自明,那就是以自我主义为道德基础的儒家文化传统。
四、“克私奉公”:“差序格局”的当代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大致逻辑:先从中国人“私的毛病”问题切入,运用比较法,在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镜像中,通过西洋的“捆柴”式之“团体格局”刻画出中国的“水波纹”式之“差序格局”;接着阐述以“己”之“伦常”“推”出来的“差序格局”之伸缩性与相对性的动态性特征;最后回到中西比较的镜像中,通过基督教文化之“个人主义”与儒家文化之“自我主义”的对照,找到中国人“私的毛病”之根源在于以“自我主义”为道德基础的儒家文化传统。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公”与“私”相互纠缠之“差序格局”之所以呈现出伸缩性与相对性的动态性特征,是源于“自我主义”的儒家文化传统。就如费孝通所言,“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这种价值原则中,“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4]28-29由此,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是由“自我主义”这一内隐的思维结构外化而形成的,这二者互为表里地构成了这一社会结构的公私关系之意义[10]。就此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差序格局衍生了自我主义,[11]这显然是对费孝通这一概念的误读。而且,当我们在自我主义之思维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审视差序格局概念时,学界关于它的诸多争论似乎也就自然消解了。
既然以自我主义为道德基础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私”之毛病产生的根源,是导致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那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私德盛行、公德没落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任何社会里,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12]8。它都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约定俗成,并在潜移默化中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凝聚在一起。换言之,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主义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启以及市场经济的实行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早已内嵌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中,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如此,许多学者指出的当下中国公共性建设遭遇巨大困境的原因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逻辑无限放大了“自我主义”内推之“私”的一度时,我们尤其不要忘记,“自我主义”还有外推之“公”的另一度,而恰恰是这一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理想。也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使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能够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敢于担当,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勇于献身,无私奉献。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荣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101。
因此,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逻辑无限放大了“自我主义”之“私”的一度而消解了“公”的另一度时,新时代的中国应该着重于塑造并弘扬克“私”奉“公”的时代精神,培养当代“中国的脊梁”。这里,克“私”指的是限制“自我主义”之内收倾向,奉“公”指的是发扬“自我主义”之外推精神。正是这一原因,晚年费孝通在谈论中国社会结构之“差序格局”时,不再讲以“己”为中心的内收之“私”,而是着重于强调以“己”为中心的外推之“公”:“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种“差序格局”“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14]也是在此基础上,晚年费孝通提出了“场”的概念:“‘场’就是从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限,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15]158-159并把这个概念作为对“差序格局”概念的补充。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新时代的中国,“自我主义”逻辑给中国带来的重要影响或许并不是广大民众囿于“自我主义”的内收之“私”以至于整个社会公共性的空场,而是更大程度上在于能够发扬“自我主义”之外推精神并进而引领整个社会推行公共事业之“中国的脊梁”式精英人物的缺失。换言之,当下中国危险的并不是私德盛行、公德没落,而是承载着能够推行公德之载体的缺失。在传统中国,这样的载体是士绅阶层。中国转型现代社会发展后,士绅阶层已经解体。因此,当下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到士绅角色的替代性力量。而承担着“三个代表”重任的广大党员干部应该而且必须就是这样的重要替代性力量之一,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当下中国的新士绅阶层之一。但是,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自我主义”逻辑以及由其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腐化销蚀着这一阶层。
对于这一问题,党中央不仅非常清楚,而且尤为重视,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一个明证。从“四个意识”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到“中央八项规定”之严整“四风”与反对特权;从巡视利剑的高扬到“打虎”“拍蝇”与“猎狐”之重拳反腐;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在自我主义基础上衍生的各种“主义”和“文化”均列入反对的视野之内,并上升到党的政治建设的高度予以强调:“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16]63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扬儒家的“外推”精神,克私奉公,真正担当起“三个代表”,成为当下中国的新士绅阶层,引领中国广大民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惟其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