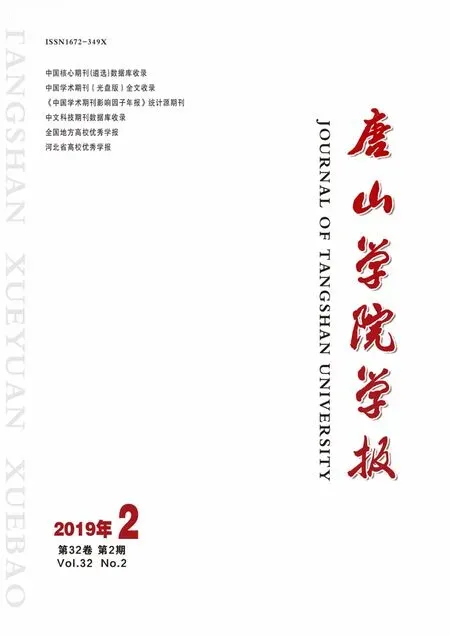屏障畿疆
——清末边疆民族整合进程中的绥远
许 珅
(1.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2.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 政法教研室,北京 100010)
绥远在现代中国行政地理中已不复存在,但清代、民国时期的绥远地区却在国家边防和民族整合进程中充当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晚清时期面对俄国在北部边境的步步紧逼,绥远的作用已由监督、稳定蒙古诸部族转变为抵御外敌入侵;到民国时期,日本的入侵更使西北咽喉绥远被国人认定为“国防前线”。与此同时,绥远广袤的土地也为人地矛盾凸显的内地省份提供了生存的资源,晚清大规模的屯垦更为孱弱的清政府作出了巨大的财政贡献,而移民的涌入和土地的开垦也为绥远地区统合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社会基础。纵观晚清至民国,近代边疆民族整合进程以实现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权力内卷为主要目标,以建省而直接统治为整合手段,新疆、台湾、东三省、西康、热、察、绥建省都遵循了这样了历史逻辑,位于内蒙古地区的绥远也在此进程中,并突出反映了其由边地向边疆整合中心地带的转变。
一、清代绥远地域特征及传统建制
(一)近代绥远的地域特征
绥远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处于中国的第二阶梯,平均海拔在2 000米以上。阴山山脉中部的大青山横卧于绥远中部,将绥远地区分为山前和山后两个区域,也将其分割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两侧,这决定了该地区处在游牧与农业的交汇地带。大青山南部的河套地区和土默川平原在自然环境上适宜农耕,并在清代得到开垦。绥远社会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以外的山北地区则不具备农耕条件,然而在晚清、民国时期,为增加财政收入、促进该地区发展,山北地区也被大量开垦。就地理位置而言,绥远处于亚洲腹地、中国的西北边疆,属于内蒙古地区。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再加上清代以来的“蒙汉分治”政策,使得绥远地区相对闭塞,与外界联系很少,社会现代化进程滞后且缓慢,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边缘型[1]4。由此可见,无论地理位置、社会发展还是受关注程度,绥远无疑是边疆地区。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利范围,尤其是属地范围不明确。清代以盟旗制度统治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严格划分牧场、属民,以皇权的权威将蒙古各部统合于中央,再加上“蒙汉分治”政策,禁止蒙汉之间进行经济文化往来,这使得内蒙古地区一直处于闭塞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绥远处于游牧、农耕交汇地带,自古农牧分界线北移是普遍现象,随着晋陕移民的不断增多,蒙地被逐步开垦。清中后期,为继续实行“蒙汉分治”政策,清政府在绥远建立了管理内地汉族移民事务的口外七厅[注]土默特旗设置了归化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和林格尔厅、丰镇厅、宁远厅。,内蒙古旧有的社会秩序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始,开放蒙禁打破了蒙汉藩篱,使这一变化更加剧烈。与此同时,近代民族危机加深,蒙古地区的统治秩序受到挑战。从此,绥远这个门户地区进入晚清统治者的视野,开始作为移民实边、巩固国防的主角而成为边疆整合的中心。
(二)绥远的传统建制与特性
清代绥远地区共有两盟十九旗。清太祖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克林丹汗,制土默特二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后者包括察哈尔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至顺治十年,有乌兰察布盟六旗,分别为四子部落旗、茂明安旗、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喀尔喀右翼旗;至乾隆元年(1736年),有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七旗,分别为鄂尔多斯左翼前、中、后旗,鄂尔多斯右翼前、中、后旗,以及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乾隆二年置绥远将军主持绥远蒙古军政事务,对土默特二旗、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七旗和乌兰察布盟六旗监督负责[2]。
绥远将军辖区与清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土默特二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作为内属蒙古的一部分,是最早归顺清朝的部落,直接受朝廷统辖。前者受绥远将军管辖,后者为察哈尔都统管辖,编入八旗作为拱卫朝廷的主要军事力量。这部分蒙古部落是清王朝确立伊始的同盟者。西北部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采用札萨克制度统辖,共十三旗,均为外藩蒙古中的内札萨克旗,是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的过渡地带。总体而言,绥远在清代是通往漠北和漠西地区的必经之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绥远将军除主持地方军政事务之外,最主要的责任即为防范藩外民族入侵以拱卫中央。
同时,处于蒙汉交界地带的绥远在统辖方式和社会形态上又别具特色。绥远是长城以南汉人移民的首选地区,虽然清王朝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但为维持生计,自17世纪中期[3]117,山西等省内地破产流民便开始“走西口”移民谋生于此。随着移民规模的逐步扩大,清政府在绥远地区建立了有别于盟旗制度的理事厅,管理移民事务,隶属归绥道,属山西管辖。自雍正元年始,至清末开放蒙地之前共建立归化、萨拉齐、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丰镇、宁远、神木共八厅。这样,盟旗制与厅县制长期共存,在地域和权力方面错杂纠葛,这是清代绥远地区行政制度的特点。
二、绥远传统建制的打破及防御功能的凸显
(一)移民屯垦的增加和厅县的增多
清前中期,绥远地区的发展是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缓慢进行的。由于移民和放垦的增加,农业的发展和牧业的萎缩是一大趋势。康、雍时期清政府组织移民在归化城一带建立粮庄,农业经济开始在绥远地区发展。雍正时期,土默特地区已成为重要粮食产区,并能保障北疆军粮供应;乾、嘉时期绥远粮食已贩入内地,并在嘉庆初年作为赈灾粮运往山西、河东、安邑一带。随着农业的发展,绥远一带形成了众多粮食集散地,丰镇、宁远、张皋、包头均以粮食贸易形成商业中心[4]93-96。这一时期,绥远与山西之间也随着移民往来和粮食贸易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农业、商业的日趋发展使绥远地区不再是传统的游牧社会,而更凸显了农牧交融的地域特点。在蒙汉隔离政策下,绥远地区是禁止内地汉民迁入、开垦的,康、雍、乾时期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多为军屯军垦,但在生计压力下已有内地移民来此谋生。乾、嘉以后中国社会弊病丛生,晋陕迁至口外的移民数量与日俱增。正如民国时期的学者所说:“晋地山脉连亘,耕地较少,凡可种之区无不人烟稠密,鸡鸣犬吠相闻。其人口之增加,虽不甚速,然亦有可观。毗连之临省,又皆为文化较高、人口过剩之区,惟有北邻之绥远,原为一未尽开辟之地,虽天然环境稍逊,要亦无碍晋人刻苦之经营,于是,绥远一变而为山西人口倾泻地,遂由此发生种种不可分之关系。”[5]在农业移民纷至沓来的同时,绥远南北连接晋陕外蒙、东西连接宁甘京津的优越地理位置,也吸引着晋商来此发展商业。山西商帮大盛魁就是绥远商贸的代表,其经营商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6]。
与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相反,牧业则处于持续萎缩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放垦的日渐增加使畜牧业赖以存在的牧场大范围缩小。光绪二十八年全面开放蒙地后,至宣统三年,仅伊克昭盟共报垦45 356.9顷,放垦35 532.2顷[4]22。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农业既能解决粮食和饲草料困难,又可以获得租金,这使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王公更倾向于选择农业。虽然牧民存在严重的抗垦情绪,在鄂尔多斯地区甚至多次发生武装抗垦的“独贵龙”运动,但是并不能阻止畜牧业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与之相适应,清政府开始改变绥远地区的统治秩序,由起初严格禁止移民到默许移民,再由取消部分禁令到光绪三十三年全面开放蒙疆。牛敬忠教授对近代绥远社会状况有深入的研究,据他考证,乾隆年间绥远地区蒙古人口在30万左右,宣统年间民政部户口调查显示为248 979人,而1937年绥远省盟旗人口为20万左右。由于在清中前期汉族农民在绥远地区属“非法”,因此无法统计具体人数。在光绪年间口外七厅汉人有1 940 312人。据贺扬灵1935年调查,在《察绥蒙民经济解剖》中提到绥远地区乌兰察布盟、伊克盟及归化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共202 619人,绥远省总人口2 123 768人,粗略估计汉民十倍于蒙民[1]60-63。在“蒙汉分治”的原则下,清廷设立与内地相同的厅县来管理绥远汉民事务,并解决蒙汉纠纷。与盟旗制度相对,形成了蒙汉分开管理的双轨制。随着近代绥远厅县逐渐增加,其性质也逐步变化。起初,绥远地区设有口外七厅,具体为:乾隆时期,在土默特二旗境内分别设立了隶属归绥道的归化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和林格尔厅(也称口外五厅),在察哈尔右翼四旗境内设立隶属大同府的丰镇厅,以及隶属朔平府的宁远厅。以上道、厅均隶属于山西省,作为理事厅负责司法行政上的管理。光绪十年(1884年),理事厅改为抚民厅,开始为民众编立民籍。这表明以前被视为违禁私垦的内地移民,成为朝廷承认的编户齐民。蒙汉之间虽仍有界限,但融合发展的趋势已然不可扭转。自此,内地的封建制度较为完整地延伸到绥远地区。这一时期厅的设置具有相对合理性,厅管汉民、旗管蒙民有利于缓解大批移民到来所引发的蒙汉民族矛盾,并能够保障农业、畜牧业生产的相安并行。
1902年1月5日,慈禧和光绪帝在由西安返京途中正式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往绥远推行垦务。为巩固边防、开发边疆地区,“移民实边”“放垦蒙荒”与有清以来封禁蒙古的政策完全相反,蒙汉隔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还增加了武川、五原、陶林、兴和、东胜五厅。相比较而言,此时厅县的设置是以开垦蒙疆为宗旨,与“蒙汉分治”“蒙汉隔离”政策下以清晰蒙汉界限为目的的厅县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以“新政”为转折,清王朝对绥远地区的统治原则和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绥远再也不是封禁之地,成为了解决内地人地矛盾和缓解财政困难的新地,由此吸引着统治者的眼球。
(二)绥远防御功能的变化
满族统治者与内蒙古诸部的合作关系自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建立,清朝建立之后,内蒙古作为北部屏障肩负着边防重要使命。绥远将军的设置也反映了清政府对绥远地区边防重要性的重视。起初绥远将军以防范漠北蒙古部族、回疆地区自西北方向的侵扰为主。康乾盛世之后边疆动乱鲜有发生,直至清晚期国门开放,列强对内蒙古地区的觊觎使得绥远地区防御功能的重要性凸显,所不同的是此时绥远的防御对象不再是国内部族而是日俄等侵略国,绥远由边防重镇转变为国防要地,“屏藩”之地转而成为国防之中心。
俄国对蒙古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并没有抑制住俄国人的野心。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制定其吞并蒙古地区的“穆拉维约夫计划”,以期通过贸易,首先从经济上来控制蒙古地区,然后逐步达到从政治上加以全面控制蒙古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通过《北京条约》《陆路通商章程》,获得“两国边境贸易在百里之内,均不纳税”“俄商小本营生,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如该商欲前往贸易,中国亦断不拦阻”[7]等贸易特权。从而使内外蒙古和新疆厄鲁特蒙古地区成为沙俄独占的无税贸易区。之后又通过《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和《陆路通商改定章程》,全面扩大其在蒙古地区的贸易侵略,致使十九世纪末,“南起张家口,北抵恰克图,东自呼伦贝尔,西迄伊犁等,整个蒙古地区物产集散的城镇贸易市场上的牲畜、皮毛、野兽裘皮和土特产等,基本上被沙俄等外国资本势力所控制。蒙古地区已成为沙俄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和掠夺牲畜、毛皮等畜产资源的基地”[3]194。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归化城对整个蒙古、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对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地区,甚至对我国(沙俄)的土耳其斯坦地区和西西伯利亚来说都是一个转运站的时候,它在贸易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8]。这使得绥远在清末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肩负着反侵略的重任。
当时的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清楚地描述了绥远地区有清一代防御性质的转变:“前代以阴山大漠为塞,我朝以兴安山阿尔泰山为塞,前代以匈奴突厥回纥鞑靼为敌国,我朝则以俄罗斯为敌国,驾驭并远防范益难,溯自天聪崇德以来,臣服蒙古洎于康熙之世准部披猖,同治之年西会俶懮而京辅仁宴然无烽燧之警者,以蒙古为藩垣也,蒙部二百年来,奉朝贡、听征调、供役使,趋上之急惟力是视者以朝廷加之勤恤也,近则俄人之势日益盛强,蒙古之众日就贫弱。”[9]400可见,内蒙古在为清朝守土固疆方面有重要的功劳,然而近代以来面对强敌俄罗斯的威胁,防御责任重大但防御能力极弱。“我边备不修兵窳器钝,科城七部乌库四盟虚弱无人,倘出非常何堪设想”[9]403,如此以来邻近京畿的绥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责任之大不言而喻。
与绥远紧邻的山西对绥远地区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最为深切,管理归绥道并与蒙古各盟旗往来密切也使得山西对绥远地区视为己域、密不可分,山西省对绥远地区发展巩固必要性的认识尤为突出,清末历任山西巡抚对绥远边防重要性都做出过精辟的描述。光绪十五年,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指出,“蒙古强则我之候遮也,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出入之间,利害不可以道里计矣”[10],直言应增强蒙古各盟旗的力量,以抵御沙俄蚕食蒙疆。光绪十二年(1886年),山西巡抚刚毅认为:“伊克昭盟所属地方,地近塞城,远拱京畿,形势所关,不独为晋省紧要边防,实亦中外吃重关键,诚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固吾边圉,免为逋逃渊薮,有事则防敌伺隙,便于控制事机。”[11]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在《电垦晋边折》中还说:“晋边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地,川原饶沃,迩来互市日增,强邻所逼,形胜所在,亟宜预之为防。”[12]他还具体提出了设局、筹费、定租、驻兵等各项措施。
国防任务的加重使朝廷对加强绥远地区边防的认识愈加深刻,作为京畿的屏障,绥远俨然已成为边防中心。清末“新政”“精武备”“裕度支”的目标在绥远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边防重镇与建省之议
行政建制是国家统御地方的直接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是地方发展变革的重要指向因素,与内地的一体化一直是晚清直至民国统御边疆的主体思路,其中以省制建设为代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行省制,刺激了蒙、疆、热、察、绥改省呼声的高涨,并在朝中引发激烈讨论[注]李细珠在《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中详细讨论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及绥远建省的意义。,蒙古建省之议的提出是晚清统治阶层视角西移的典型代表。绥远作为蒙汉交接之要冲,农牧交界、蒙汉交融又是边防重镇,晚清以来以移民实边、广置厅县为主的整合方式,已经将西北边疆置于国家整合的视野中心,置省的提出更将此推向一个新高度。
外国入侵、边疆危机以致巩固边防刻不容缓;边防废弛、蒙地贫困急需财力支持要求发展蒙地;蒙地发展以开垦土地为基础,应视蒙情形建立行省。这是贻谷、岑春煊等人奏折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以置省加强统御蒙地的逻辑表达。如“今则边禁已弛矣,向所恃为藩篱之固者,此日实毫无可恃,及今设法布置犹恐后时,若有惮烦难因循守旧,辙后患何堪设想。奴才待罪晋边审察情势,忧临氛之日逼,叹蒙族之式微,深维疆索之空虚,熟虑边防之预备,是以上年奏程德全广开蒙垦,摺内详陈边蒙情形,以建置为不可缓。为兴蒙计实为备边计也。”[9]324同时,清末改革家们认为,筹饷上上之策即为开垦蒙地,而绥远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放垦的首选:“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蒙长皆欲自练其兵而苦于无力。是则欲练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练费非开蒙土不可。今蒙地接晋边者东则为察哈尔右翼四旗,西则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土饶沃,水草丰衍,乌拉特、鄂尔多斯两部依阻大河,形势雄盛,灌溉之利甲于天下,臣诹之寮属考之案牍,准格尔有招垦救灾之案,达拉特有兴屯收租之议,是蒙之便于开地可知绍祺奏土达二部争地租可至十万。”[9]401“我边备不修兵窳器钝……备之之策莫若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练蒙之兵,边实兵强,防密盗靖计无先于此者是有数便。”[9]402
蒙古地区设立行省的议论出现于清末“新政”之后,最早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提出。日俄战争后,从边防角度出发的蒙古设省议论再起,这时的建省主要指包括绥远在内的内蒙古地区。时任军政使副使的姚锡光于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在考察心得《筹蒙刍议》中提到:“封建与郡县二者不能并存,而封建之制尤不宜于今日之世界,势力分薄,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侮,其势不能久存,而非易封建而郡县不能为治。”[13]3蒙古建省为“监制奉吉,屏障畿疆而设”[13]30,并详细陈述了蒙疆设省的具体方案:内蒙古分为东、西2省,以直隶边外承德、朝阳2府6州县及口北3厅、东4盟蒙古、察哈尔左半部为东省;以山西、陕西、甘肃边外诸部、察哈尔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设口外各厅、阿拉善厄鲁特蒙古为西省。外蒙古分为东、西、北3省,车臣、土谢图2部为东省;赛因诺颜、札萨克图2部为西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北省[14]。给事中左绍佐以“西北空虚,边备重要”请“热河、绥远城皆列为行省”[15]。岑春煊的《统筹西北全局折》详陈了开发与经营西北的措施,对蒙疆、西藏等边地疆域区划提出系统的建议,从充实边防角度论述蒙古设省的重要性,并从热、察、绥入手,提出以承德、朝阳2府及卓索图、昭乌达2盟各旗为热河省;以直隶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3厅,山西丰镇、宁远、兴和、陶林4厅,原管察哈尔左右旗地段及附近寺庙、马牛羊牧厂、王公各厂并锡勒郭林盟地为开平省;以山西归绥道之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5厅,新设武川、五原、东胜3厅,合乌兰察布、伊克昭2盟及阿拉善1旗,并陕晋向理蒙务各边州县为绥远省,统称北三省[16]。随后,清廷将岑春煊奏折发下,谕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袁世凯、陕甘总督升允、四川总督赵尔巽、绥远城将军贻穀、热河都统廷杰、察哈尔都统诚勋等边疆重臣各抒己见,对此议题,贻穀、廷杰、诚勋均表示肯定。
可见以蒙疆在内的边疆设制问题已成为清廷加强边防统御的重要课题,而近畿地区的热、察、绥地区更是首当其冲。虽然朝中热议不断,但是直到清王朝灭亡,热、察、绥建省之议也并未付诸实践,面对包括《辛丑条约》在内的搜刮,仅财政一项就成为阻碍以上省制的重要原因,在绥远地区的放垦反而成了清末“新政”筹饷的重要来源。时人议论:“蒙古地方非不可立为行省,设巡统治,然蒙古各旗贫困殊甚,一切经营何能自办?当此国帑支绌之际,政府亦断无可移之款。故此事当俟他日再议。”[17]
四、余论
晚清的绥远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展着一体化与民族融合进程,随着移民的增多,绥远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断发生着变化。在“蒙汉分治”的宗旨下,汉族移民管辖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光绪十年(1884年),已建立的管理口外汉民的口外七厅,由理事厅改为抚民厅,在管理汉民事务的基础上增加了编立民籍的权力,从而将口外移民固定下来,不再以流民看待,使其从法律上融入绥远社会。与此同时,清王朝在西方侵略势力的打击下日渐衰落、财政拮据。鸦片战争后,沙俄和日本对蒙古地区加紧吞并、瓜分殖民活动,使蒙古社会危机日益加重。清朝统治者从保全其统治利益和保护边疆安全出发,提出改变治蒙政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宣布取消蒙禁,实行“移民实边”和开垦蒙地的“新政”,也是在此时,绥远建省的声音首次出现。绥远,在社会发展和外来冲击下开始了新的发展。
晚清的这种进程将绥远从封禁之地转为边疆民族整合之中心,仅仅是近代边疆地区整合的序曲。民国建立之后,随着省制逐步推进,绥远地区军阀势力的介入,省方与盟旗在地权、事权上的纷争,日本侵略势力的冲击等使得该地区的管理与整合更加复杂与艰难。大变革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显得格外敏感,抽离了旧有封建秩序之后,如何以新的方式将民族地区统合于国家之中,是近代中国所面临诸多问题中的难点也是重点。近代统治阶层视野向绥远地区的转移和由此导致的绥远功能定位的变化,只不过是我国近代边疆民族地区整合的一个缩影。尽管探讨清末绥远之边疆整合不能反映近代民族国家整合的全貌,但也足以看到边疆民族地区以新的方式统合于中华民族之中的曲折进程,并将边疆带入国人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