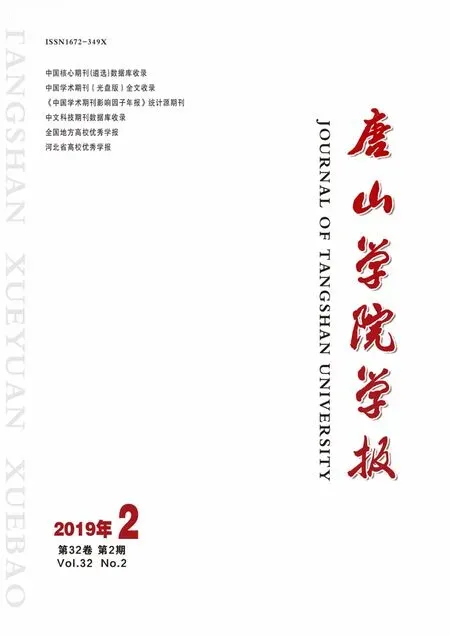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冀志强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阳 550025)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发生了一场以评价表现主义为开端的文艺论争。这里所说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理论氛围。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研究重点由经济、政治转移到了文化与艺术[1]。这个观点是符合实情的。冯宪光则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与1930年代在德语学界发生的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直接相关[2]。这场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表现主义文艺与现实主义文艺的不同观点。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这场论争中的主要观点,来表明一种更为积极地对待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态度。
一、从表现主义到人民性问题
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位表现主义的性质。齐格勒(Bernhard Ziegler)在《现在这份遗产终结了……》一文中说:“首先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表现主义是哪种思想的产物,不折不扣地遵循这一思想,会引向何方呢?——引向法西斯主义。”[3]12齐格勒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指向的观点引发了关于表现主义性质的论争。
齐格勒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对待表现主义的一种普遍态度,即认为表现主义本身就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但问题是,希特勒政权并不喜欢表现主义,而是把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艺术定性为“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就在论争开始前不久,希特勒政权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关于现代艺术的“颓废艺术展”,以引发公众对现代艺术的厌恶之情,而当时德国的现代主义主流就是表现主义。所以,尽管有个别的表现主义作家转向了希特勒政权,但我们并不能把表现主义本身定性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艺术类型。
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肯定了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与进步倾向。正如彼得·菲歇尔(Peter Fischer)在《我们如何评价表现主义》一文中所说,当时的表现主义讨论主要还是局限于文学领域,而要想对表现主义有较为客观的理解,还要将这一辩论追溯到绘画领域。他肯定了表现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抵抗,并认为表现主义打破了一切艺术形式的传统,也是一场艺术形式的革命。他说:“在今天,离开表现主义就无法理解和评价世界艺术;同样,没有表现主义,我们的现代建筑艺术以及今天最杰出的文化成就也是不能想象的。”[3]98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种洞见。
在菲歇尔看来,正是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才导致了纳粹对于表现主义的摈弃。他说:“表现主义的主要功绩,如前所述,就在于使平面、色彩、线条这些绘画手段获得了独立性。”[3]99由此不难看出,他对表现主义的推崇,是从艺术形式的维度来看的。从内容方面,他认为,尽管表现主义作品并不具有直接的进步意义,但是它并不因此而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不过,菲歇尔也批评了表现主义的个性主义与其所影响下的新宗教热。
阿尔弗雷德·杜鲁斯(Alfred Durus)在《抽象,较抽象,最抽象》一文中也批评了表现主义的神秘主义与新宗教性,但是他也指出不能因为表现主义者高特弗利特·贝恩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就认为表现主义必然要汇入法西斯主义。他指出:“表现主义在政治和思想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运动,既有可能向左转,也有可能向右转。”[3]107克劳斯·贝尔格(Klaus Berger)也指出,表现主义可以导向法西斯主义,但也可以导向共产主义,表现主义与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论断还是比较公允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较为合理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种辩证的评价。
在这次论争中,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布洛赫(Ernst Bloch)与卢卡奇(也译为卢卡契,Georg Lukacs)这两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他们二人的观点主要也是就表现主义的本质展开的。
就表现主义而言,布洛赫的视野显然要比卢卡奇广阔得多。关于表现主义所涉及的艺术领域,布洛赫与菲歇尔的看法是一样的。表现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但是,就像布洛赫所批评的那样,卢卡奇的文章里从未出现表现主义的画家,以及像勋伯格那样的音乐家。这样,他就很难客观地评价表现主义的地位,因为对于表现主义来说,绘画比文学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在这次论争的最后,齐格勒也改变了他在开始时对表现主义的态度。齐格勒对自己的这个立论提出了自我批评,认为这个观点在修辞上与内容上都是错误的。进而,他也认为表现主义是用来瓦解清规戒律和经院主义的。他在《关于表现主义讨论的总结》一文中公正地肯定了布洛赫等人的观点:“表现主义是在绘画艺术中形成的。可是在这次讨论中,恰巧对绘画艺术谈得很少。”[3]190他指出,在讨论中只有杜鲁斯系统地研究了绘画艺术中的表现主义。他也认为:“最有道理的是那些指出了表现主义二重性,或确切地说,多重性的人,指出了在表现主义中蕴藏着多种发展可能性的人。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确实是表现主义突出的特征。”[3]194但是,齐格勒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理解表现主义绘画,他认为表现主义绘画中丑化的、肢解的人物肖像是违背人道主义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中,还涉及到了人民性的问题。齐格勒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人民性的问题,而布洛赫也想在表现主义那里挽救人民性。那么他是如何思考的呢?布洛赫认为,表现主义是与虚假的新古典主义针锋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他们完全回复到人民艺术,喜爱和尊重并在绘画上首先发现了民间艺术。”[3]149也就是说,他将现代主义对于民间传统的吸收与借鉴看作其人民性的特点。
但是卢卡奇认为,在表现人民性上,先锋文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认为,布洛赫的解释只是混淆了人民性的概念。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先锋艺术当然会从民众那里吸收一些东西,但这并没有保证先锋艺术实现了人民性。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先锋艺术具有了人民性,它也就很难成为先锋艺术。我们当然不是说先锋艺术的反动性,而只是说先锋艺术总会与人民性保持着一段距离。
正由于这样,卢卡奇批评布洛赫说:“真正的人民性,同所有这一切毫无共同之处。否则,任何一个收集玻璃绘画或黑人雕塑的狂妄之徒,任何一个在疯狂之中把人们从机械的理智的桎梏中的一次解放加以庆贺的势利小人,都会成为人民性的先驱了。”[3]175尽管卢卡奇对于表现主义并没有达到深刻的认识,但是他这个批评也确实指到了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某些现代主义艺术被人所诟病的地方。
卢卡奇从两个方面诠释了人民性的涵义。其一是艺术与遗产的关系。在他看来,具有人民性的大众艺术与人民的历史遗产保持着活跃的关系,这种作品的内容都产生于人民的生活和历史;而先锋艺术却是要割断同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之间的联系。其二就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具有人民性的大众艺术总是现实主义的。他还认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通向先锋文学的道路只有一道非常窄小的柴门。他要求文学再现社会现实,而不是表现内心的主观情感,所以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都停留在了直觉的水平。所以他把表现主义称作“抽掉现实的抽象”(Wegabstrahieren von der Wirklichkeit)。这样的论断可能就失之偏颇了,而他认为先锋文学缺乏真实、缺乏生活就有武断的嫌疑了。
由表现主义而涉及的人民性问题,也说明了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所以,在这次表现主义论争的最后,《发言》编辑部总结说:“我们的大讨论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争论的典型的德国反映。”[3]91这样,在梳理了关于表现主义的主要观点后,我们再来分析关于现实主义的两种代表性的态度。
二、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观点
陈学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中认为,由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观点主要产生于他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故而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个观点尽管有其道理所在,但是卢卡奇对于现实主义的阐发与他早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着深刻的关联。再者,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也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定。
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中,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卢卡奇在《现实主义辩》[注]卢卡奇此文标题在《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中英译为“Realism in the Balance”。“现实主义辩”是《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的译名;它在董学文等编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中被译为“争论不休的现实主义”,在《表现主义论争》中被译为“问题在于现实主义”。中说:“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古典文学反对现代文学的问题,而在于究竟哪些作家和哪些文艺流派在现代文学中代表着进步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现实主义。”[4]3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论阐发,卢卡奇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人;而除卢卡奇之外,布莱希特也提出了自己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他们二人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支脉。
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观点体现为他所说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他的这个提法来自于恩格斯的表述。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一信中认为,巴尔扎克的创作违反了他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卢卡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的。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的“总体性”(totality)观念是紧密相关的。
在《现实主义辩》中,他说,“总体性”概念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并且,他还以原始经济的分散性来说明这种整体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他说:“真实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动的、发展的,是产生罪恶和美德、繁荣和不幸的一个整体。”[5]322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反映这个整体。但是,布洛赫则把矛头指向了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整体的体系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卢卡奇这边的。资本主义使得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且,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这个观点也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这个世界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紧密结合成一个大的整体。
不过,社会整体性是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整体观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关于人的整体。他说:“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会当作完整的实体来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他们的某一个方面。”[4]48但是,整体性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一个方面;如果也要把人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表现,这可能就有问题了。我们之所以把他的“总体性”观念分成人与社会两个方面,是由于这涉及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中处理对象的不同。
首先,卢卡奇要求现实主义反映社会这个整体。我们承认,这样的文学主张的确可以产生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是必须要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整体呢?如果只反映局部的真实,就不是现实主义吗?所以,反映这样一个整体,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有限的个体,即使忠实于现实主义方法,如何能够客观地描写那个社会的整体?通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全体,但事实上却只是看到了社会的一隅;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真实,但事实上也许只是看到了表象。譬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real”在这里主要表示的是“真实”的意思,而不是“现实”的意思。因为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根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那里,“本我”是更加真实的人格,但它并不意味着现实,表现为“现实”的人格是“自我”。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对某些自诩为现实主义的倾向提出质疑。也就是说,作家认为自己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观察现实并反映现实,但是不是必然“真实”地反映了真的“现实”。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说,在资本具有控制力量的社会中,人却很难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社会中的人本身就无法成为一个生存的整体,那么文学如何去反映人的整体呢?卢卡奇在讨论经济所导致的世界整体性的时候,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环境中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境况与经济现实并不具有同样的特点。甚至,社会与人的两种情况正是相反的。
我们也可通过卢卡奇比较的两种经济环境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原始经济环境中,当然没有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但是正因为生产不是一个整体,或者说生产者都是孤立的,所以他们就要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生产。事实上,卢卡奇也看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样,尽管社会没有成为一个总体,倒有可能让人有条件成为一个整体。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也正由于生产关系是一个整体,并且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却导致了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人根本无法达到这种生产的整体性。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生产的整体性之中体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当然,这种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与个体生存的碎片化之间也不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它们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本质。
卢卡奇主张文学反映一种整体性,并不能否定现代艺术表现人的生存的碎片化这种追求。当卢卡奇批评古典经济学家只是看到了物而看不到人时,他的辩证法也只是看到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没有看到这个整体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当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组成一个整体时,却成为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碎片。现代主义所做的可以说是:我们就以碎片化的方式描写我们体验到的碎片式的感觉。这难道不是客观地描写了一种现实吗?
其实,卢卡奇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被肢解现象。他说:“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些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7]79他也指出,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合理化原则,对于统一性有一种破坏作用;合理化就是专门化。他说:“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7]174这样,也就有了人的个体生存的碎片化。每一个生产中的部分、环节都是整个总体的有机部分,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的分裂却无法还原为一个整体,人性的碎片却无法实现为一个整体。既然这样,在以资本控制为主的社会中,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反映人的整体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卢卡奇的某些观点却也表现出一种广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他说:“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的原则正是我们在前面强调的:对人的完整性的关心。”[5]300从现实主义对于人的完整性来看,说“关心”比“描写”要合适一些。因为“描写”是对现实的再现,所以它需要一个前提,即人在现实上是完整的。但在资本控制的社会中,这显然是很难成为现实的。“关心”则不需要这样的前提,它是一种诉求,而不要求对现实的再现。
三、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观点
在卢卡奇发表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时,布莱希特也写了一些文章来阐述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以此批驳卢卡奇。但是,布莱希特考虑到反法西斯文化阵营的团结问题,因而没有公开发表他的这些文章。所以,学界所谓的卢布之争并没有公开的形成,而只是一个隐性的存在。
在《反驳卢卡契的笔记》中,布莱希特表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他将卢卡奇那种只以几位经典作家作为样板的现实主义观点视为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他说:“现实主义不是形式问题。我们不能只接受单独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或者人数有限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形式,并把这称为现实主义的形式。这是非现实主义的。”[3]287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是建立在少数几个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的形式基础之上;其二,只是建立在小说的某种特定形式之上。
布莱希特对于卢卡奇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他说:“把现实主义视为形式问题,把它同一种(而且是老的一种)形式联系在一起,这便是给现实主义做绝育手术。现实主义的写作不是形式问题。一切妨害我们揭示社会因果关系的根源的形式必须弃掷,一切帮助我们揭示社会因果关系的根源的形式必须拿来。”[8]16不难看出,布莱希特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并认为文学家可以用多种方式揭示这种因果关系。他甚至指出,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也有可能歪曲现实;而不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也有可能真正反映了现实。当然,他这里说的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就是一种简单的“反映”。
布莱希特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界定是:认识现实、干预现实。他说:“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越能认得清其中所包含的现实,这件艺术作品就越现实主义。”[8]27认得清现实,就是要揭示出社会现实中的因果关系。他还说:“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习惯的看法是,一部艺术作品,它的现实越容易辨认,便越是现实主义的。我的定义与它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它的现实被驾驭得越容易辨认,便越是现实主义的。”[3]342他这里的“驾驭”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不是从表面上的摹写,而是在挖掘一种深层规律,并使之明朗起来。只要作品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它就是现实主义的,而不管它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方法。
他以雪莱的《“虐政”的假面游行》为例,说明运用幻想、象征的手法揭示现实,这就是现实主义。所以,在他看来,雪莱是比巴尔扎克更加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还认为,对于剪辑法、陌生化、内心独白这样的叙事技巧,不能从现实主义出发提出指责。这意思是说,这些叙事技巧可能会走向形式主义,但也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他说:“不要太肆无忌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谈论纯形式问题,这样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3]301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布莱希特这里,现实主义不只是某种特定方法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黄应全将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二人的现实主义分别描述为“封闭式”的与“开放式”的。当然他强调这两个描述性的概念不具有任何褒贬色彩[9]。应该说,这种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戴维·莱恩(Dave Laing)说:“实际上,布莱希特作品的实质在于,它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艺术领域里第一次真正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10]布莱希特以自己的创作,表现出了现实主义方法的多样性。
布莱希特也谈到了“人民性”的概念,但是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否定了通常的那种认为人民性与现实主义有着本然联系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忠于现实的生活摹写,这种摹写符合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这种文学就是人民性的。但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联系并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他说:“‘人民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大是人民的。相信它是人民的,那是非现实主义的。”[3]309他指出,词语“das Volk”(民族,人民)加上词尾变成“das Volkstum”(民族性)后有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味道,而又由这个词变化出来的另一种形式“das Volkstümlichkeit”(人民性)自然也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就使得这个概念具有了一种迷惑性。这在现实中的重要表现就是,法西斯非常喜欢标榜自己的“人民性”,而这种歪曲就是由“das Volkstum”开始的。这样,“人民”就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标榜“人民性”并不等于真正的现实主义。
所以,布莱希特强调:“我们心目中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人民,是改变世界和改变他们自己的人民。我们心目中的人民,是进行战斗的人民,因而我们心目中的‘人民的’是一个战斗的概念。”[3]311他对于“人民性”的理解包括诸多方面的内涵,其中与文学艺术具有紧密关系的是:它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通俗易懂的;它吸收并且丰富群众的表达形式;它以传统为出发点,并进一步发展传统。针对他的这些表述,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推论:其一,布莱希特把“人民”与“人民性”的概念具体化了,使它们不再是一种类似卢梭的“公义”那样具有永恒正义的抽象概念。它们作为一个群体,也是需要不断改变自身的。其二,在对“人民性”的阐释中,他其实已经给现代主义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合理性的论证,因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目的就是丰富文学的表达形式,也就是丰富人民群众的表达形式。
由于布莱希特认为人民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战斗并改变现实的群体,所以现实主义就不应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叙事规则与美学规律,即使它们属于某些文学经典与典范。用某些经典与典范来规定现实主义,就是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他说:“我们不能从特定的现存作品中推出现实主义的结论,而应当使用一切手段,以便使人民能够驾驭现实,不管这些手段是旧的还是新的,是行之有效的还是未经考验的,是来自艺术的还是来自其他别的方面的。”[3]311他强调,从现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去推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这样得到的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标准。由此看来,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更近似是一种精神,而不是某一种叙事模式。他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为先锋派铺垫了一条进入现实主义的通道。
四、结语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表现主义论争”,启发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它本身不具有政治倾向性,而是有着多种的发展可能性。但是,表现主义本身的先锋性,使得它与人民性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对于现实主义,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卢卡奇的狭隘理解上,而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现实主义不单是再现现实、反映现实,它更是指反映与再现的真实。因为我们看到的所谓现实不一定是真实。在这种意义上,优秀的表现主义同样也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
所以,与其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风格,不如将它理解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的精神,就是达到真实。所谓真实,不仅有外在世界的真实,也有内心世界的真实。我们不能要求文学必须描写外在世界的真实,它也可以描写内心世界的真实。如果表现主义表述了内心世界的真实,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了。现代主义文学中,有对于人的碎片化生存的刻画。由于这也是对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现实的挖掘,所以也就具有了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