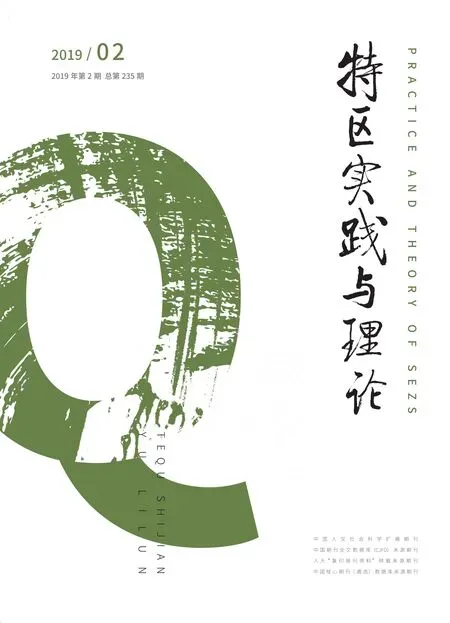转型期我国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分析
唐 斌
政治信任作为民众对政府的可信度进行评价后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包含着四个方面的结构要素:主体——谁信任、客体——信任谁、介体——政治信任的认知来源、环体——政治信任产生的环境。在政治信任的这四个结构性要素中,政治信任的主体和客体是两个能动性的人化要素,政治信任的介体是一个联接性的物化要素。“要研究评价,就不能不研究评价情景在评价中的作用。”①冯平:《评价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政治信任的环体是一个背景性的要素,决定着政治信任主体对客体评价的考量基础。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政治信任水平是这四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的流失正是由于这四个结构性要素的变化所致。
一、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
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一国的民众是对该国政府进行政治可信度高低评价的主体,而民众对政府可信度的评价总是与其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大小密切相关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社会渗透,全体社会成员被整合到了各种类型的政治组织及其延伸组织之中,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社会利益的唯一源泉,其他的利益来源都被严厉禁止,我国社会呈现出一种高度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就造成了民众对作为公有制的代表者——政府的高度依赖,个人的自主性被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过去所极力推崇的计划经济,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没有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作为基础,实际上只是传统社会的整体主义的一种强化状态而已”。①白春阳:《现代社会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88页。政治信任是一国民众对政府实现其利益可能性大小的一种政治评价,理性政治评价形成的前提是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相对于客体而言必须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而不是完全依附于作为政治信任评价对象的政府而存在,如果主体完全依附于客体而存在,那么主体对客体的信任就成了一种不得不信而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换言之,如果民众的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或者政府的代理机构手中,并且对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都缺乏自主选择权的话,那实际上政治信任的主体就缺失了评价客体是否可信的资格与动力:(1)政治不信任资格的缺失。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国家通过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每一个个体都牢牢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单位或公社内,个体劳动者不能够自由流动。民众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政府以计划的形式通过城市中的单位或农村中的公社定额分配给职工或社员,离开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个人将失去生存的必要条件。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体制将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机会等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公民任何政治不信任的表达都意味着生活资料和工作机会的丧失。(2)政治不信任动力的缺失。改革开放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崇的是集体主义的指导思想,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服务于集体的利益,忽视个体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事实,分配上实行的则是平均主义的原则,自身收入与贡献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政治信任作为民众对政府实现其利益可能性大小的一种政治评价,在一个利益分配极度平均而普遍贫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依照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利益分配逻辑,也缺少产生政治不信任的动力。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民众对政府依附性的地位加上高度的平均主义使得民众的政治不信任缺少产生的土壤。此外,政府为了实现公共舆论上的整齐划一,对民众不同的政治声音实行高压管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制度化信任,使得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众的政治信任至少是表面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信任是一种暗含利益基础之上的预期,政治信任主体的地位决定了其对政治信任客体可信度评价的标准,在民众从依附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其对政府可信度的评价也必然会植根于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而更具能动性和自觉性。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基础是从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不再垄断资源与机会的供给,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在资金来源、经营领域、运作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人们的就业形式和收入来源方式也越来越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社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资源和机会供给的源泉,而这些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调节来实现的。市场经济促使了整体性社会开始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化,个体从对政府及单位或公社等政府延伸组织的高度束缚中逐步解放了出来,集体主义的话语霸权开始遭到了个人主义现实的不断消解,公民相对于政府逐步确立起了较大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本身具有趋利性的特点,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在对利益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上,市场经济体制也带来了人们对利益看法的改变,各种利益的主体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个体对合法私人利益的追求不仅不再被视为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而且被社会广泛推崇。利益是政治评价中的关键性因素,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在民众的生活方式由缺乏独立人格的依附型生活方式向重视自我的自主型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交换成为了民众处理与政府关系的主要法则,民众会越来越基于自身利益的损益去对政府的可信度进行评价,评价中所包含的批判性色彩会越来越强烈,而盲目性的成分会越来越弱。由此,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资源配置的格局进入到全面积聚阶段以来,虽然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民众对政府可信度评价自主性程度的提高,其政治信任仍呈现出流失的态势。
二、政府官员腐败程度的扩大
腐败是政治系统的一种顽疾,指的是政府公务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实现私人目的的权力异化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性使用。腐败的产生一方面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另一方面也和特定社会的制度完善程度紧密相关。腐败产生的人性基础在于人性的贪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正是看到了人性中无止境的贪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条公理,于是提出对掌握公权力的个人来说,必须对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制约。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官员腐败的人性之基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刺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标准成了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的主导标准,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其是否忠实地履行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要求,而在于其获得财富的多少,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之下,公务员人性中追逐私利的本性也被极大调动起来,政治廉洁的观念被严重侵蚀。就时代背景而言,一个国家特定时段制度的完善程度也对腐败有着最重大的影响,因为制度设计出来是用来规范人的,制度决定着人的行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在转型过程中,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旧制度由于其滞后性不能起到规范的作用,新制度的建立又是一个较长过程,而且新建立起来的制度中存在着的制度漏洞也需要逐步去完善,这样就会留下大量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这些缝隙和漏洞为公共权力的寻租提供了空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曾吸取历史上政府官员腐败的教训,针对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腐败的形势在我国有所遏制。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廉政建设失去了客观基础,廉政制度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利益驱动下,部分政府公务员开始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腐败现象开始滋长蔓延。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腐败在我国进入泛滥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如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46150人。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02 -11 -1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234852.htm,2016年4月27日。总的来说,腐败在我国社会社会转型期呈高发的态势,并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腐败人数增加。据《新京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与前五年相比,2008年至2012年查处的受贿官员的人数增长了19.5%。③宋识径、邢世伟:《5年立案侦查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新京报》2013年10月23日(A07)。2013年至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百万元以上贪污贿赂案件10986件,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5900件,较前三年分别上升120%和40%。查办涉嫌犯罪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11478人,其中原省部级78人、原厅局级1527人,比前三年分别上升47%、79%和170%。④戴佳:《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交出满意答卷——“打虎”“拍蝇”给力 反腐打出声威》,《检察日报》2016年5月17日(A05)。上述数字仅仅是官方正式公布的已经被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的数量和涉及的官员人数,由于腐败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于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和报案成案率低等原因存在着“犯罪黑数”较高的问题,所以实际有贪污贿赂行径的官员人数必定大大超过这个数量。二是腐败层面的扩散。在十八大以来对腐败保持持续高压态势之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基层蔓延的不良态势。在有的基层干部中甚至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政治生态,腐败在他们看来不再是一件有违纪律和官德的可耻行为,而是对腐败行为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政治道德良知的约束力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关涉腐败犯罪的政府官员的级别也有上升的趋势,不仅县处级以下的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的数量较大,而且市厅、甚至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被查处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如1997年到2002年五年间,中纪委共查处省(部)级干部98人,平均每年受到惩处的省部级干部人数占一线工作省部级干部人数的1%—2%。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02 -11 -1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234852.htm,2016年4月27日。三是腐败规模的扩大。腐败按照腐败主体的人数来分可以分为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两种形式,社会转型期我国公务员的群体腐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掌握公权力的一部分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抱成团伙,结成一个相互之间有利益勾结关系的共同体,利用职权协同性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塌方式的群体腐败,这是我国现阶段最具典型性的群体腐败形式。第二种是由于某一政府机关主要领导人的腐败起到了消极的带头作用,导致该政府机关各公职人员在腐败的问题上虽无直接的利益勾连,但构成了上行下效式的群体腐败。第三种是担任同一职位的政府公职人员前赴后继式的腐败,即使他们的腐败行为事实上并无内在的关联,但在外界看起来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廉洁是现代政府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中民众对政府最期待的基本价值,而“腐败是执政信任的最大的敌人”。②白春阳:《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官员腐败的高发态势也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在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的“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中,采用0—10分的量表测量公民对九种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看法,结果显示民众对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打分为7.24分,严重性程度高居各种问题的首位。③严洁:《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5页。2005年起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就“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展开了调查,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尔后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 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又进行了此项调查。在这十一次调查中,只有腐败问题从未跌出民众关注度的前十名。Espinal和Hartlyn认为安全和腐败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处理安全和腐败问题的好的政治表现也普遍地和信任的上升相联系。④[美] 佩里·K.布兰登:《在21世纪建立政府信任——就相关文献及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由对政府能力的信任和对政府责任意识的两个维度构成,政府能力的高低只是民众在评价政府是否值得赋予信任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即使政府的能力再强,但如果政府的权力被用来作为与民争利而不是为民谋利的工具,那必然会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产生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从微观的层面进一步而言,政治信任的客体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公务员是政府构成的基本单位,民众对政府责任意识的判断正是建立在对政府的“守门人”——公务员这一政治角色可信性判断的基础上,倘若一国政府公务员腐败的数量大量增加,那该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必然会趋于下降,因为此时在大部分民众的意识里,政府这一政治机构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而成为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正是在此意义上,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增加会降低公民对于政府的尊重程度,⑤[美] 乔恩·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刘霞、张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戴蒙德则更进一步指出:“腐败(和其他形式的滥用权力)相比,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其他问题会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民主的支持造成更大的腐蚀作用。”⑥[美] 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三、网络对政府负面形象的放大
政府形象是民众对政府的总体感觉,而政府官员形象指的是政府官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向民众展示的形象的总和。政府官员的形象是政府形象的直观体现和具体化,民众对政府官员形象的认知是判断政府形象的窗口。廉洁程度是民众评价政府官员可信度的首要标准,但并不是全部,民众对政府官员可信度的评价还包括政府官员形象诸多的其他方面,“政府官员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抄袭造假、奢侈消费、言语举止、生活腐化、非正常死亡、亲属问题等都构成了影响政府官员形象的主要风险源”。①唐钧:《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新形势下群众工作(2010—2011)》,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4—98页。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被各种信息包围着,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与判断,大都是以他们看到、听到的媒介现实作为依据。民众对政府形象的判断也是建立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正是媒体报道中包含的各种政治信息,构成了人们认识和评价政府的主要凭藉。我国社会转型期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先后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更替,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是报纸和广播,20世纪90年代是电视,进入到21世纪后互联网则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近二十年来,网络普及率在我国不断提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历次统计报告显示,1997年10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数仅为62万;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10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5/P020120709345374625930.pdf,2018年3月5日。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数已达2.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16%;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8年1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index_4.htm,2018年3月5日。而到2018年6月,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8/P020180820630889299840.pdf,2018年8月20日。我国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网络成为政府形象展示的主要平台。
在我国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享有对政治信息的独占权,政府对政治信息的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一方面政府对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实行严格的管控,各种新闻机构对公共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和反馈都在政府信息管理的范围之内,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对信息进行剪裁和取舍,对可能影响自己形象的负面信息实行封锁,仅将有利于树立自己正面形象的信息通过官方媒体传递出去。在这种单向灌输模式的传播体制下,政府是公众舆论的主导者,民众完全处于缺乏对信息选择的被动地位,面对的是来自于各种媒体高度一致的政治信息。媒体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却能决定受众想什么,在这种单向灌输传播模式带来的“雪球效应”的作用下,塑造出来的必然是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政府形象。
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比较起来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上具有传播主体的匿名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和传播形式的综合性等特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传播的这些特点一方面为我国政府正面形象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网络将有关的公共信息及时地传递给民众,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那就能够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成为展示政府形象的窗口,进而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正面形象;但另一方面,网络也有可能充当政府负面形象放大镜的角色。网络新媒体在我国的出现和普及率的不断上升打破了这种单向的灌输模式,网络传播的特点让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完全把控变得不再可能,政府也因此丧失了对公众舆论的绝对话语权。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仅仅是作为传播过程中被动的受众而存在,公共信息单一的从政府流向民众,两者处于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而在网络时代,民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发布到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有的网民出于吸引网友关注的意图,故意夸大一些个别政治事件中的负面成分,而部分网络媒体在求新求快的市场竞争中未经核实就发布了一些有关政府和公务员事件的失实报道。“信任属于与知识相关联的认知范畴。说‘我信任你’意味着我知道或者我认为我知道你的有关情况。”①[美] 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载自[美] 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2页。政治信任的形成过程以一定的政治认知为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讲,网络新媒体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窗口效应”更加明显,网民很容易将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的个别事件上升为影响整个政府整体形象的问题,这使得有关政府负面形象被放大的机会大大增加,客观上影响了民众对政府可信任度判断的认知基础,对民众的政治信任无疑会起到削弱的作用。
四、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
环体作为政治信任主体对客体可信度评价的背景性要素,其本身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国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一种成分对主体政治信任形成的影响尤为突出。社会信任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的信任,主要是指一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同时也包括熟人之间的信任两种形式。齐美尔认为社会信任能够起到社会关系粘合剂的作用,“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②G.Simmel:《The Sociology of Simmel》,New York:Free Press,1950:326.社会信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由信任、网络和社会规范三个部分构成,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部分。社会信任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的政治信任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同时,两者又是相互支持、相互建构的:一方面,政治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一个国家民众之间社会信任度的增加。社会信任度的增加有赖于社会个体可信度的增加,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可信度主要是来自于外在约束机制对信任客体可信度的保障,对政府公正、有效处理失信行为的信任正是从反向上强化了社会中个体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社会信任是政治信任产生的社会基础。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够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从整体上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在社会信任上形成了一种易于信任的民族特质,那这种民族特质也会扩展到政治领域。从个体的角度来讲,容易相信他人的个体也更加容易将信任的对象扩展到政府的工作人员;相反,如果个体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政府公务员必然也很难得到他的信任。因而,一个社会信任贫瘠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低水平政治信任的社会。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信任呈现出社会整体信任水平较低、不信任主体的普遍化和不信任客体的扩大化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较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从2011年起连续发布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该调查将社会总体信任界定为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上信任状况的基本印象和判断。信任得分对应的信任程度为:80分以上为“高度信任”,70—79分为“中度信任”,60—69分为“低度信任”,50—59分为“基本不信任”,0—50分为“高度不信任”。③2012——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该标准被进一步修正为81—100之间为“高度信任”,71—80分为“基本信任”,61—70分为“可以信任”,51—60分为“不信任”,0—50分为“高度不信任”。2011年课题组首次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仅有57.1%的被访者对社会信任的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34.8%的受访者勉强认可,经过进一步的赋值分析,我国社会总体信任度的得分为62.9分,处于低度信任中的较低端水平。④杜军峰、饶印莎、杨宜音:《2010年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的调查》,载自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5—146页。2012—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总体信任度为59.7分,属于“不信任”的水平,进入了社会信任的警戒水平。⑤饶印莎等:《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载自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2—73页。在201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对象的信任水平处在“低度信任”的低端水平。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杨明教授等人以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认为在1990年到2002年期间,我国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从60.3%下降到了43.7%,下降幅度达16.6%。⑥杨明、孟天广、方然:《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第二,不信任主体的普遍化。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信任主体付出其信任可能性的大小是和其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的,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主体的灾难线较高,而相对易损性较低,在一次信任关系中付出信任后即使遭遇到了信任客体的背叛,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对信任主体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而那些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社会群体,由于其手中掌握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十分有限,相对易损性较高,一次较大的信任背叛可能就意味着对其生活会产生致命的打击,因此他们在决定是否选择信任时表现得更加谨慎。而现阶段,我国社会信任的衰落已经超越了收入、地位等因素的限制,成为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第三,不信任客体的扩大化。社会信任包括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和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两种类型,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阐释了宗教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他认为欧美国家的普遍信任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国民的社会信任属于特殊信任,信任的半径很小。①[德]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福山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程度和该国的社会信任程度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信任的程度决定了该国私营企业能够发展到的规模。美国社会属于高信任度的社会,中国社会属于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对外人的不信任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导致华人企业无法做大做强。②[美]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73—74页。如果按照韦伯和福山的说法将我国的社会信任归结为特殊信任,那至少社会个体对熟人的信任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对熟人的信任是我国社会信任的最后一个堡垒。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即便是熟人很多时候也不能够成为信任的对象,郑也夫认为在我国“杀熟”——欺骗熟人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事实,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③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是民众信任的两种具体形态,如前文所述,两者在构建上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促关系,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形成的保障,对政府的信任能够激发起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基础,为政治信任的产生提供社会土壤,个体社会信任度的增加也同样增加了政府官员赢得信任的机会,而社会信任度的下降又反过来会破坏政治信任形成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当下中国,政治信任的缺失,影响社会信任的建构,而社会信任的不足和秩序失范,又加重政治信任的流失”。④丁香桃:《变化社会中的信任与秩序——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