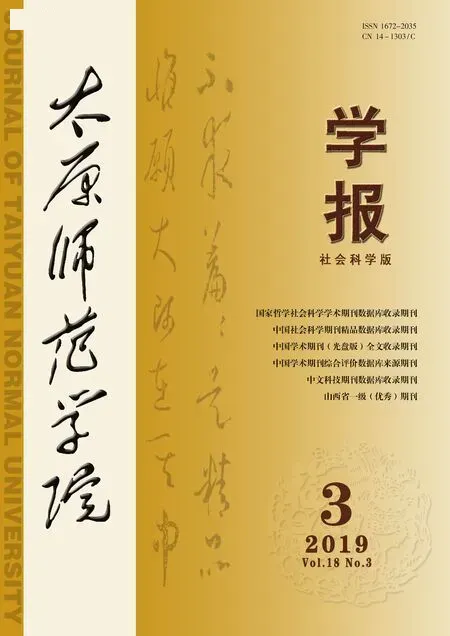论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后现代性
王桃花,程彤歆
(1.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后现代主义是近代西方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它源自现代主义,但并不是对现代主义的直接继承或绝对批判,它既吸收了传统的内容,又融合了现代的形式,它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接受了传统,并赋予自身更多表达自由。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世上一切都是虚幻的、无规则的、不确定的,任何企图给事物制定单一原则的观念都应该被抵制,一切宏大叙事都值得被怀疑,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尔甚至直接指出:“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4。
后现代主义小说承载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它不再像现实主义小说般以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目的,也不再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揭示人物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实际上,人物与故事情节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心中,现实是由虚假语言创造的虚假现实。文字在后现代世界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表达,所以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更倾向于主动告诉读者文本是如何被虚构的。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时间通常紊乱无序,人物的真实身份被隐藏,对人物本身和对事件的描述大多都是不真实、不确定的,且“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2]5。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是一个擅于运用后现代写作手法对社会、民族和历史进行书写、探讨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众所周知,记忆书写贯穿于石黑一雄的所有作品之中,他从不刻画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乐于书写各个时代里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他总是赋予作品一种淡淡的、朦胧的忧伤感,并以平淡、优雅的文字为读者讲述某个特殊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透露出石黑一雄对后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在《远山淡影》(APaleViewofHills)中,石黑一雄以切换叙事视角的方式不断干扰叙事者的回忆,让叙事者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往返中虚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以此使读者难以看到真实的历史事件,给读者造成极大的阅读障碍。其实,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对石黑一雄的早期作品进行过研究。在国外,帕兹曼尼·彼得天主教大学文学院博士伊娃在研究石黑一雄的早期作品时曾指出:“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主人公对现实的思考、回避和扭曲以及他们对事实的沉默、不充分或过度解释,都显露出叙事者的不安”[3]5。马莱特认为石黑一雄在早期作品中大量运用的日本元素源自其日裔身份:“石黑一雄循序渐进描写人物的这种方式受到了日本文化中温和、克制特征的影响,并且这也是他作品的总体特征”[4]19。郑朱雀教授认为,美国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是一个介于英国和日本之间的话语中枢:“石黑一雄战略性地运用美国这一他者身份来展现他与日本和英国之间保持的临界距离”[5] 242。胡铁生指出:“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石黑一雄小说的上述风格和特征集中起来,可以归结为创作手法的多元性和文学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而这两点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6]145。陈娟将《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相结合,论述了石黑一雄小说的不可靠叙述[7]。滕爱云则从伦理角度出发,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了《远山淡影》中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并得出结论:“石黑一雄还是希望在每个人物承担伦理身份责任的同时也能好好照顾自我的生命意识,这就是他在小说中传达的崇高和温暖”[8]199。综上,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写作手法、语言特色、伦理问题而且还涉及作家的民族身份,但对其后现代性的分析稍有欠缺。截至目前,石黑一雄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从《远山淡影》到《被掩埋的巨人》(TheBuriedGiant),他由对日本和英国文化的描写,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直到后期他不再满足于描写现实世界,转而对科幻、神话等领域进行了大胆尝试,他开始借幻想的未来世界和奇幻的史诗神话来聚焦于当下克隆人问题和人类民族恩怨问题,表达出他对当下社会中各种潜在危机的担忧。尽管石黑一雄的写作视角在他已出版的七部长篇小说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他作品中特有的后现代性却始终存在。笔者认为,后现代性在《远山淡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为石黑一雄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确立了其跨文化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特殊定位,也为他终获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现代性在《远山淡影》中具体表现为后现代不可靠叙事、对权威的怀疑与消解以及对后现代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关注,这三点恰好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所在。在大众悲鸣文学“已死”的时代,别具一格的石黑式后现代写作为文学摆脱“已死”的僵局提供了新思路。
一、后现代叙事策略之不可靠叙事
在后现代文本中,语言与现实并非一一对应。陈世丹教授曾经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本文具有不同于现代主义精心编撰的严谨解构,它的创作和接受的惟一原则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决定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规则,去寻找意义是既无可能又无必要,阅读行为和写作行为的‘不确定性’本身即‘意义’”[9]65-66。后现代解构主义同样认为:“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既定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因为所有的语言体系在本质上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不可靠的”[10]3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历史在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用虚构文字堆砌的虚构文本,回忆在后现代文本中往往也被看作是由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精心构造的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虚假呈现。
在《远山淡影》中,石黑一雄将这种不可靠叙事运用得恰到好处。该小说采用双重叙事法,一方面是叙事者悦子的近况,当初随悦子一起从日本移民英国的大女儿景子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变得抑郁、孤僻,在独居的公寓中上吊自杀几天后才被房东发现,她的死亡给悦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另一方面,在与现任英国丈夫生下的小女儿妮基回家看望自己的短短六天中,悦子断断续续地回忆了曾在长崎生活的日子,其中包括与前任丈夫二郎、公公绪方先生、邻居佐知子等人的过往经历。该小说在现实与回忆的交替叙述中展开,但作者并未将这些叙述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推进,而是把它们看似随意地分散在六天中的各个时间段,打破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让读者难以把握历史真相,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如梦似幻、捉摸不透的神秘感。
自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事,该理论就被大量运用于文本分析之中。在布思对“‘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11]75的定义上,查特曼对“隐含作者”作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隐含作者不是一个人,没有实质,不是物体,而是文中的规范”[12]87。在查特曼看来,隐含作者可以被用来评判文本叙述者话语是否可靠:“叙述者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是由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思想规范存在很大分歧;也就是说,叙述者的描述与作品其他部分的叙述有着较大冲突,从而让我们怀疑叙述者是否诚实或者对他讲述‘事实’的能力存疑。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有着本质冲突;否则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也就难以形成”[13]149。在《远山淡影》中,悦子是文本的“叙述者”,她负责站在当下时间点用当下身份来讲述历史事件。而佐知子是一个始终只存在于悦子回忆中的人物。根据悦子的描述,自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而佐知子则完全相反,她固执、自私、任性,似乎在她心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够随美国人弗兰克一起移民美国。悦子总能清楚地回忆起佐知子称赞自己的话语“你真好心。我肯定你会是一位好母亲”[14]10。类似这样的称赞,小说中出现了不下十次。面对佐知子坚持带女儿移民,悦子害怕年龄尚小的万里子无法适应环境变化而出现心理问题,于是她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叙述者通过对以上往事的回忆在读者心中建构出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但叙述者一旦脱离回忆进入当下时间线,读者则立即感受到叙述者话语的不可靠。若悦子真如回忆所言,自己永远以孩子的利益为重,且她也曾劝阻佐知子不要移民,那么她在当下时间线里就不会以移民者身份出现在英国。而且小说在开篇就提到悦子的大女儿景子由于不适应移民环境而抑郁自杀,这一事件也明显与悦子回忆中那个担心朋友的女儿出现移民心理问题的好母亲形象不符。作为后现代流散文学,对一代移民者给二代移民者造成伤害的批判是该作品想竭力表达的主题之一,但根据以上文本对比分析,叙述者行为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叙述者话语的真实性必然遭到读者怀疑。
布斯认为读者在阅读不可靠叙事文本时需要对文本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15]134。在阅读《远山淡影》时,欲发掘文本的不可靠性,就要对文本的前后差异进行对比分析。首先,悦子曾提到佐知子为了能够去美国,狠心淹死了万里子心爱的小猫们。在悦子的回忆里,佐知子便是这样一个任性冷血、只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女儿意愿的母亲。但另一方面,悦子又时常想起佐知子说的“对我来说,女儿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悦子。我不会做出有损她未来的决定”[14]50。其次,悦子对佐知子淹死小猫画面的描述与前文佐知子对战后一个女人亲手淹死自己婴儿的描述相差无几,这让读者不禁怀疑那个淹死婴儿的女人是否和佐知子、悦子是同一个人。接着,当悦子试图说服万里子随佐知子移民美国时,悦子的身份开始变得混淆、模糊:“他很喜欢你,他会像个新爸爸。……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就马上回来”[14]224。最后,当悦子回忆起曾经陪佐知子母女去长崎港口游玩的一次经历时,她说“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14]237,但根据悦子之前的描述,去港口游玩时她正怀着景子,那天玩得很高兴的实际上是万里子。从整个文本来看,悦子作为叙述者,总能一字不差地复述过去与佐知子的对话,可她往往在回忆与景子和万里子的往事时三缄其口、含糊不清。例如在回忆到万里子失踪事件时,悦子自顾自地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14]46。很明显,文本叙述者的回忆是选择性的回忆,也是虚实相生的回忆。叙述者试图依靠不可靠的话语为自己建构良好的自我形象、掩饰过去的罪责、逃避现实责任。
申丹指出:“不可靠叙述产生于作者编码与读者解码的过程之中”[16]36。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好似设置了一个游戏,让小说充满了不确定,小说不论是对人物身份还是历史事件的描述都前后不一、矛盾重重,读者需要亲自参与游戏过程,并对文本进行双重解码,只有设身处地地解读、脱离或超越叙事者话语才能解开一切谜团:悦子即佐知子,景子即万里子,悦子回忆的佐知子母女的往事其实就是自己和景子的往事。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游戏中,后现代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消解权威”和“怀疑一切”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我们不信任任何权威,至少我们不依赖任何权威,不永久地依赖任何权威:我们对任何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17]24在后现代社会,曾被视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真理都陷入被怀疑的危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向心人物也逐步失去他们的可信度,人们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反对一切自我标榜为核心、原则、规律的事物,不承认所谓的逻辑、公式、本质,强调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追求个体的开放性和世界的多元性。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是一种后现代式叛逆。
在《远山淡影》中,绪方先生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人物,是权威的象征。和老同事远藤一样,绪方先生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用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14]79教育着日本的年轻一代,纪律、忠诚是这套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具体内容为“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14]80等意识形态概念。对于绪方和远藤等众多老教师来说,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有义务让年轻人时刻保持为国牺牲的热情:“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14]189。同时,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对年轻人有恩,曾经的学生必然会一直尊敬、爱戴他们:“你不知道我们多么辛勤地工作,……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14]189。赖艳指出:“绪方先生所指的教育体系,显然基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以及1937年3月出版的《国体之本义》。这些文件为教师与有权力的人使用,使人们相信天皇是神,是世界的中心,牺牲自我服从天皇的意志不仅是责任,更是人生的目标。”[18]47二战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影响了一大批日本青年,对于在传统教育体制下成长的绪方一辈来说,西方文明带来的平等、自由等观念显然是对日本传统教育体系的毁灭性破坏,在绪方先生眼里,洗衣机和洋裙的出现让日本女性丧失了妇德,妻子不随丈夫投票给同一政党这种事更是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战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年轻一代早已不再追随传统思想的脚步,他们不认同父辈坚守的传统思想,而是追求自由、多元、平等,曾经的爱国教育者在他们眼里都成了导致国家受苦难的罪人。儿子二郎试着反驳绪方:“旧的教育体系里也有一些缺点,其他体系也是。”[14]80绪方先生以前的学生松田重夫甚至认为正是老一辈的传统思想让日本承受了战争伤害,他曾发表文章,指出绪方和远藤早就应该退出教师行业。当绪方先生前去质问时,他严肃地指出:“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我不怀疑您的真诚和辛勤工作。……可是您的精力用在了不对的地方,罪恶的地方”[14]188-89。
如今,年轻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一股脑地追随权威、信奉传统,而是有了自己的思考,敢于怀疑真理,勇于向权威挑战。同样,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后现代特征,他们不再像传统小说一样书写宏大叙事,也不再通过刻画自带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角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与石黑一雄一样,“后现代作家不再相信世界上任何普遍存在的绝对真理,一切真理都只能是带有主体视角的‘局部知识’,是带有个人色彩的、对现实的某种理解和描述,而非对唯一事实的准确再现”[19]7。正如伊哈布·哈桑所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消解’文化中的一部分”[20]92。后现代社会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宣布与传统和现代性决裂,瓦解整体、消解权威、怀疑一切,他们不害怕矛盾和摩擦,相反,他们身上有一种后现代式叛逆,敢于正视过去并利用过去,在过去经验的帮助下产生新的未来。
三、后现代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问题》中对后现代社会人类主体身份作出阐释:“后现代主体是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或者永恒的身份主体。身份变成了一个‘可移动的宴席’,……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并不是以连贯的自我为中心而整化的。在我们的内部存在矛盾的身份,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引拉,因为我们的身份总是摇摆不定”[21] 277。后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产生于个人与不同文化的摩擦碰撞之中,它不仅是寻找个人定位的漫长心理过程,也是寻求社会、民族归属感的文化融合过程。作为流散作家,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借用悦子和绪方先生的经历,书写出了人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焦虑是后现代身份认同困境的最初表征。二战过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让许多普通民众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于是日本社会逐渐兴起一股移民热潮。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文化的进入让日本人感受到了民主和自由,这自然让当时的普通民众对西方国家趋之若鹜,移民面临的文化差异问题在战败的失落、重建的无望面前显然不值一提。在那个特殊年代,无人知晓移民西方和重建国家哪一个才是正确选择,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指导建议,当下和未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对于悦子这样没有特殊社会身份的家庭主妇来说,移民或许是最能带来希望的选择。移民者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身份群体,他们通常还未脱离自己的原文化,也未完全融入新文化,他们“既归属于母国,同样也归属于他国”[22]222,长时间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这种不确定感和零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给移民者带来了身份焦虑。悦子作为移民者,她的身份诉求明显呈现出“动态的流散认同”特征,即“主体不再持守给定的文化身份,而是在动态移位的过程中解构或重构身份;不再执着于‘寻根’,更重要的乃是身份建构的‘过程’;流动在种族文化和移居地文化之间,并未显出对后者的敌意,而是在两个文化的旅行互动中建立起一种流散的视野,从而克服离乡失根的忧愁”[23]27。
悦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她努力融入英国文化,拒斥与日本文化相联系:“我们最终给小女儿取名叫妮基。这不是缩写,这是我和她父亲达成的妥协。真奇怪,是他想取一个日本名字,而我——或许是出于不愿想起过去的私心——反而坚持要英文名”[14]3。对于悦子来说,一切日本性事物都是她成为真正英国人道路上的障碍,她拒斥英国丈夫对日本文化的好奇与向往,并对他所写的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章表现出强烈厌恶。但悦子总是言行矛盾,她一面反感自己身上的日本标签,一面又不断地为日本文化作辩护:“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的文化,更不理解二郎这样的人。……二郎努力为家庭尽到他的本分,他也希望我尽到我的本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称职的丈夫”[14]114。在这里,悦子对日本文化又爱又恨,她害怕日本文化阻碍自己成为英国人,又反感英国人诋毁日本文化,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悦子身份焦虑的表现。除此之外,悦子虽已移民英国,但她却没有融入英国。“你父亲刚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妮基,我记得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像英国。原野啊,房子啊。正是我一直以来想象中的英国的样子,我高兴极了”[14]238。实际上,悦子始终只在自己认为的安全范围内移动,她“一直没敢到英国北部的农业区去”[14]55,她不愿走出舒适区,因为她害怕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不被英国人接受。“日本人”三个字是悦子身份的象征,不论她接受与否,这个身份注定伴随悦子一生。但悦子心中最大的伤痛——大女儿景子的自杀,却被英国媒体以最刺眼的方式报道了出来:“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14]5。这一刻,悦子的移民幻想被彻底打破,她清楚地看到了英国人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也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是怎样被排斥在外,可她早已无法回到过去,她已然成为新社会环境中的边缘人。
如果说悦子是由特殊流散经历而陷入文化身份认同困境,那么绪方先生的身份问题则是出于对新旧社会文化价值观转变的无所适从。对于绪方先生这类肩负教育使命的老一辈教师来说,在战争年代他们应该做的就是配合国家和政府的战争政策,为国家培养勇于牺牲的青年。绪方先生在战前给学生们传授“日本中心论”,要求他们把政治性课本一字一句背下来,让他们坚信日本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在战时他大力鼓吹军国主义,给年轻人灌输日本理应向外扩张、要勇于为国牺牲的观念。在那个年代,绪方先生是一个配合战争政策、维护政府统治、为国家培养优良战争人力储备的爱国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自身身份要求,而且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认可。然而,日本战败后,曾经受人爱戴的爱国主义教师一夜之间竟成了受人唾弃的国家罪人,其他像绪方先生一样在战时鼓吹军国主义的人也都遭到了社会大众的批判。“现在很多事都变了。而且还在变。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过去您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时不一样了”[14]188。松田重夫的一番话让绪方先生对自己在当下社会中的身份定位感到困惑,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家更强大,他绝不曾想过自己的教育理念会给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带来毁灭性伤害,他更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要把战败的罪责推卸到自己身上。多年来习惯于被人追捧的绪方先生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背负一个人人喊打的罪名生存于当下社会,于是他也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之中。
石黑一雄曾指出:“我们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具备任何广阔的洞察力。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感受到自己被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24]136。显然,悦子和绪方先生都是石黑一雄所说的这种缺乏洞察力的人,他们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向过程中的牺牲者。作为旁观者,他们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仿佛是一个必然结果,而对于身处乱世之中的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作为流散作家,石黑一雄的双重文化背景让他的作品能够站在国际化视角进行思考,他既不以日本作为唯一文学灵感来源,也不局限于在英国历史中挖掘素材,就像悦子游离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绪方先生摇摆于传统与当下一样,他也将自己悬置于多元文化之中,以永远的第三者视角审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对历史还是对当下,石黑一雄的文字总是呈现出若即若离、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隐藏在那朦胧虚幻文字背后的,实则是石黑一雄对后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对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关怀。
四、结语
身为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注入了大量日本元素,因此许多评论家都习惯从日本性出发研究该作品,仿佛石黑一雄在这部作品中充当了一个日英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的确,在《远山淡影》中,不论是对地理环境的描写,还是在语言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充斥着鲜明的日本性。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绝不是一个只会拿民族身份作卖点的作家。他因“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揭示出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擅长在作品中进行各种后现代风格写作,尤其在《远山淡影》中,他通过典型的不可靠叙事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通过描写年轻一辈身上的后现代式叛逆突出后现代社会消解权威、怀疑一切的思想特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后现代身份问题表现出极大关心,通过对悦子移民经历和绪方先生身份转变的讲述,书写出了人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也凸显了他厚重的时代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