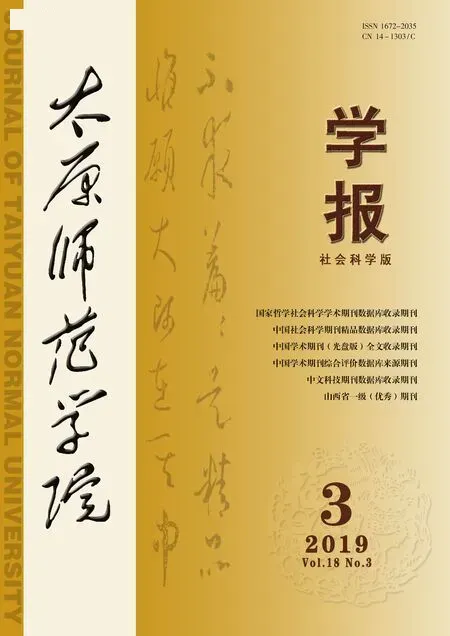深渊还是故乡:徐玉诺诗歌的空间幻象
陈 琳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1915年,以陈独秀等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振兴民族、改造旧秩序与个性解放的激进使命,给青年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在河南省第一师范读书的徐玉诺,也是这群兴奋的年轻人中的一个。随后河南开封学联被反动当局镇压,气愤的徐玉诺竟意图以卧轨自杀的极端方式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反抗。诗人饱满的热情和看似冲动的自戕行为之间构成了一种戏剧张力,也是他此后人生中不断上演怪诞、矛盾行为的预示。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的徐家营村,此后辗转多地、颠沛流离。和其他现代诗人不同,徐玉诺似乎从来都没有表达过对城市的惊诧艳羡,却不断地在诗歌里呼唤着故乡。正如周作人所说,徐玉诺是一个正在寻路的“永远的旅人”[1]91。这样的评价所浸透着的苦楚,是徐玉诺其人及其创作最鲜明的情感基调。李丹梦将徐玉诺的写作与河南的地方性精神结合起来,展示了“文学河南”与个体命运的纠缠。[2]而在诗歌当中,徐玉诺不断以空间的想象重新组织记忆,返回童年创伤性的现场,在塑造“将来之花园”的幻象中驶向诗歌的纵深之处,常如临深渊,在现实与幻灭之间游走徘徊。“空间”在这里指的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也是诗人在文本中创造的“物质和场所或空间的幻象”[3]28。
一、空间形变:裂开的大地
徐玉诺从小生长在充满匪乱之灾的河南鲁山县。1900年,义和团运动波及豫西,徐玉诺的家乡也被卷入其中。诗人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感受到了动荡不安。其后徐玉诺考取了鲁山县立高等小学而得以离开家乡,然而就在这段离家不远的路途中,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的叔父徐海在给他送面返回的途中遭遇匪乱,不幸中流弹而死,尸体还被野狗撕咬,待被发现时,诗人只看到叔父剩下的一只鞋子。这样残酷的经历被徐玉诺写入了小说《一只破鞋》中。归乡的路途埋下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恐惧与哀伤,而类似的创伤性事件在战乱和匪灾中频频发生。在这些痛苦的回忆中,诗人唯一的守护者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在故乡“叫着我的小乳名”(《梦》),而故乡却常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徐玉诺的小说《在摇篮里(其一)》就是对故乡这种复杂经历的讲述。故事开头就是一个噩耗,“乓啦啦”这“使人心都要寒死的声音”警示着大难即将来临,人物的情绪掉入了焦虑不安的黑洞中。这时陪伴着“我”的是母亲,尽管她已经“慌张得颤抖得连气都喘不出来”。母亲的守护是“我”可以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而父亲在整个匪乱之灾中是不在场的角色。有着母亲的家才是诗人从小依恋的庇护之地,在描写到母亲的作品中,诗人充满惨痛的、强烈的不安才能暂时平息。母亲在梦中发出的呜咽让“我”感到沉重的悲哀。诗人对母亲极为细腻的感情和爱戴,也促使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女性化的温柔气质。在叶绍钧根据徐玉诺亲身经历所创作的小说《火灾》里,徐玉诺也就是言信君的原型——“他怀抱着我那爱啼哭的七个月大的女儿,甜蜜地说‘我们抱持她,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这让我觉得他身上含着女性的美”[4]316。这些隐藏在诗人身上的柔性特质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母亲的效仿。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与对故乡苦难的忧惧,以一种复杂、矛盾的混合方式浸入到诗人对生命的深层感知中来。
因此,在徐玉诺的诗歌里,母亲、故乡、死亡的隐喻不断交替、扭结在一起,这使诗人的感情能够得到最大释放。这种非理性的恣意幻觉,也是象征主义所关注的问题。自胡适推行白话诗以来,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越过了语言的牢笼,但仍旧停留在对物的直观描摹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思潮在中国形成较大影响,随着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象征派诗人的出现,新诗才得以冲破阻隔诗人心灵与万物相“契合”的障壁。[5]614在这样的创作趋势下,新诗开始抵达主客观相容的隐秘精神世界,如波德莱尔的诗中所言,“具有一种无限物的扩展力量”[6]233。中国新诗的空间随着想象力的释放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周作人《小河》那样的寓言式象征,坠入了李金发等缔造的诸如“深谷”般的纵深空间意象。这就意味着象征派诗人可以不囿于刻写真实,而“执其如椽之笔,写阴灵之小照,和星斗之运行”[7]41。徐玉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创作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现代性特质,并且实现了进一步的空间变形。他的新诗创作通过想象力的驰骋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审美空间。于是,徐玉诺在《燃烧的眼泪》中写道:
我哭到沉醉没知觉的时候,忽然大地从我脚下裂开;我同时也坠落在里面。
一位白发的母亲,正在张着两臂迎接我。
可怜的孩子,你也来了!她说着,我仿佛沉在温泉里。
那些眼泪即时在秋后草根一般的枯骨上燃烧起来了。渐渐烧起墓上枯草。[8]97
“忽然大地从我脚下裂开”一句开启了诗人的奇诡幻象。大地本是生命之家园,万物存在之根本,此时竟随着诗人的心胸一同撕裂。“下坠”是滑入黑暗深渊的体验,沉重的肉身在可感的状态下趋于湮没,诗人的心理感受幻化成为了一种实在的身体感受。濒临深渊而无家可归之时,另一个幻象出现了,那便是儿时的守护神——母亲的形象。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家屋感与母亲的身影和呼唤无法分离”[9]28。母亲出现在这个可怕的变形空间里,向“我”张开双臂,带领“我”回到家乡。这本应该是温情脉脉的幻象,可母亲却是带领“我”归入深渊,此时“我”竟感到沉入“温泉”一般奇异的温暖。诗人在出生时与母体分割的创伤,似乎在这次充满着死亡隐喻的空间裂变中终于愈合。[10]诗歌在这里埋藏了巨大的矛盾张力,在获得归属感的同时也加剧了炽烈的生命苦痛。最终,眼泪在“枯骨上燃烧起来了”,“我”与挚爱的亲人一同沉入生命的“温泉”里。诗人敏锐的感受力使得他所直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形,在故乡、深渊、母亲的怀抱和死之温泉里不断翻转,这是现代诗歌里对死亡的一次极为特别的抒情,也是新诗采用散文化文体的一次实验,而诗人以空间的奇特形变实现了诗歌的情感张力。
“裂开”的大地制造了一个幽暗深邃的空间,仿佛俯瞰深渊,诗人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空间坐标,并且多次在诗歌中呈现这带着死亡恐惧的诡谲想象,譬如:“人生如同悬崖上边的一枝枯草/被风吹折,颤颤连连的坠落下来了”(《枯草》),“将堕落到底的时候、嗅得污泥的香气了”(《杂诗》之十),“深深地沉入渊的最深处了”(《杂诗》之三),“他也深深的沉在污泥里”(《没意义的人生》),“将要重重落下的黑暗哟”(《黑暗》)。诗人在诗歌中多次使用“坠落”“堕落”这样的动词,让自己的身体承负重量,处在下滑及濒死的失控状态中,将自己从现实空间中一次次抽离。而充满“污泥”的水底、“渊的最深处”,这些封闭、黑暗的空间营造都带有令人压抑的死亡隐喻。这些空间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完全消灭捕捉光线的可能,视觉被彻底压制,人的主体处于混乱失序的黑暗之中。巴什拉曾将这种黑暗的空间想象与“地窖”联系起来,地窖作为“暗部”存在,“分担了隐藏在地下的力量。当我们在地窖里做梦时,我们跟深渊里的非理性相互呼应协调”[9]44,“在地窖里面的恐惧不再是那么明晰可辨的”[8]45,当诗人把所缔造的黑暗深渊与地面之上的故乡共同置于非理性的死亡想象中时,这种纵向上的空间整体便形成了奇诡的比例变化,超出了直接的现实摹写而进入了一个混沌的梦境。
二、空间错置:返回记忆现场
在写作《燃烧的眼泪》的同一年(1922年),诗人写下了《夜声》,延续着他对黑暗空间的捕捉。“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听觉反而显得异常灵敏,“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这首诗歌的声音营造很有特点,“杀杀杀”三个短促的平声字连在一起,本身就会产生奇特的音效。朱光潜在《诗论》里讨论诗歌的声音节奏时,引《元和韵谱》点出了平声的特点乃“平声者哀而安”,又引“四声歌诀”的“平声平者莫低昂”[11]197,由此可知,使用平声字本来可以舒缓情绪,但三个“杀”字相连在一起,则形成了短促急切的节奏,营造出紧张的效果。诗人“循着五四新文化所闪耀出的光明而投身时代洪流,却又很快受到压抑,这又使得他更加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际涯的黑暗”[12]34。在学联运动被镇压时诗人采取极端的自杀行为,虽然怀有一定的警醒沉睡者的意图,但更像是诗人受到长久以来的灾难经历刺激,迫使他在创作中反复咀嚼死亡主题,并采取了一次对死亡的实证行动。[2]诗人对时代的感知更多来自于个体的创伤性经验,“徐玉诺闯进了一个似乎不属于他的时代氛围之中,没有任何功利心的既非社会改良者又不是新的文化秩序的重建者,他只肩负着一个弱小诗人的使命痛苦并挣扎着”[13]2。
诗人依靠这些深刻的惨痛的记忆,将亲历的或是梦境中的事件生动地再现出来,这其中就包括对声音的精确捕捉。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就有诗人注意到诗歌中声音的作用,只不过这种声音的营造只是服务于描写现实的目的。康白情说,“写声就要如听其声,写色就要如见其色”[14]221-222,其诗论比较倾向写实主义。在徐玉诺这里,写声也是为了营造现场感,但这声音是想象的、穿越时空的声音,目的是将记忆中的时空拉回现场,呈现不同层面的空间并置。“记忆”是诗人进行时空穿梭的重要驱动力。诗人一面不断咀嚼、召回记忆,一面又在这些苦难的回忆中备受煎熬。“假设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杂诗》)。确实,诗人总是对发生在故乡的经历有着太过清晰的回忆,他可以非常生动地向别人讲述这些血与泪的苦难。诗人曾经对叶绍钧说:
在我的家乡里,公认为疯子的与老人孩子的一样的众多。我的姑母就是个疯子。还有我的一个同学,他眼看着父母妻被土匪杀了,自己肩上受了三刀,却没有死;从医院医好了刀伤出来,早已成为一个疯子。我可以作一个譬喻:一个人受到猛烈的火烙,在身体留下个可怕的瘢痕;以后只要抚摸到或看到这个瘢痕,当时一切被烙的惨状就完全涌现于心目中了。这怎能叫人不成为疯子![3]99
诗人在《火灾》里又再次将这“被烙的惨状”呈现了出来:
没有恐怖——没有哭声——
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死在火焰中了……[8]177
在这首诗里同样有生动的声音效果,如“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破碎着”,增强了诗歌的现场感,声音的渲染突破了线性的时空维度,而实现了身临其境的空间错置。又如,“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在黑影中》),细微精确的声音使得记忆又穿透了时间返回到当下。在此二例中,“声音破碎着”“拍着”都是当下进行的声音,并且使用了动词后加“着”字的结构。“在空间位置系统中,‘着’句表示某一位置点上留存有持续动作的物体,表示一种未完成的,正在进行的动作。”[15]175在诗人另外一些情绪比较轻松的写景状物的诗歌里,也还是常见这样的结构。在福州仓前山时,诗人陶醉于自然风光所写的《一步曲》:“小鸟总是那样的唱着,细风总是那样的吹着,我总是一步一步的走着。”诗中连用“着”字句,营造了一种轻盈的在场感。 穆木天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立体的,运动的,在空间的音乐的曲线”,而且应该是“一个有统一性有持续性的时空间的律动”[16]。当然,诗人可能是无意识地造成了这种空间的绵延感而并非出自刻意雕琢,这更可以看作是诗人主体的一种时空感知。
诗人在儿童时期与母亲共同经历的创伤性回忆,也以时空错置的方式无比生动地不断再现。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法,导致创伤性的回忆会经常复现,而那种儿童时期遭遇的焦虑和恐惧则会蔓延到往后的人生中。[8]徐玉诺反复从苦难中汲取写作资源,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小说《一只破鞋》《到何处去》都浸透着对创伤的精准记忆。但是诗人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很少写作,逐渐隐没于文坛。连对徐玉诺作品表达过关注的鲁迅,都曾表示无法得知徐玉诺的踪迹,“不知道哪里去了”[3]3。诗人自己的解释是“一直沉湎在苦难没落的生活里,几与知友绝缘,更不写作了”[17]。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徐玉诺在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上“缺乏相对稳定的求索方向”,囿于中原农民的保守性格,浪漫主义而自由散漫导致了其创作力的衰竭[注]刘济献、刘忱在《徐玉诺和他的创作》中分析诗人创作消沉的原因时指出:“(徐玉诺)无论是在社会思想上还是在文艺思想上,都表现出了既缺乏相对稳定的求索方向,也缺乏开放式的多方面吸收营养的素质。”参见刘济献、刘忱所编的《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22页。。诗人的好友周仿溪则认为徐玉诺的创作消沉是受了叶绍钧的影响[18]。叶绍钧在《诗的源泉》一文中写道:“只要是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关系”。周仿溪认为此观点对徐玉诺影响颇深,再加之诗人崇奉道家思想,安于无为。当然,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外因,但还应注意到诗人自我的内部原因,即诗人终于在辗转的人生中主动地将这些记忆封存起来了。
1933年徐玉诺送给张默生一副奇怪的图画,画中有一副棺材,并对友人解释说:“我创作这个棺材的意思就是盖棺定论”,并宣告“徐玉诺在烟台已死也”[12]53,对阶段性人生作出一种刻意的告别。诗人曾在诗歌中赞叹过海鸥:“愚笨的,没有尝过记忆的味道的海鸥呵!你是宇宙间最自由不过的了。”(《海鸥》)诗人对记忆的重负早就有过深刻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过分依赖记忆,也限制了诗人写作的视野),所以,他常常有意识地去摆脱记忆。在拜访叶绍钧的日子里,他常流连于江南风景,常觉得“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一步曲》)有时候诗人则表现得十分坚决,“我们将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记忆”(《宣言》)。这种渴望摆脱记忆的欲望与对死亡的追求相互交织,造成了诗人对死亡独特的认识,即有时甚至希望将记忆的永久封存寄托于死亡。
据徐玉诺的学生景中天回忆,徐先生于茫茫大雪中立于一片荒冢之上,竟致晕倒在雪地,被家人找寻到带回家,抢救一番,诗人苏醒后写下了《生命》:
但我记得,
医生用针刺入我心房的时候,
我的灵魂是平安的;
在另一个地方,
得到极浓厚极甜蜜的安慰。[8]36
诗人迫切希望以断裂的方式分割自己的生命,企图“盖棺定论”,是否也意味着这种幻想的死亡和浸润着血泪记忆的诗歌时代已经终结。如果说五四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所要求的“为人生”的写作,还能与诗人达成某种契合,使诗人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当文学日益向意识形态靠拢,从“为人生”到“为国家”,诗人显然已无法从记忆中获取更多的写作资源了。 从诗人建国后写的诗歌诸如《小打瓜》《好汉要当志愿兵》等中,再也看不到其对困苦人生的抒写,而融合于大众的通俗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诗人主体性与民族国家的召唤最终达成了一致。而在这种变化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在每一次人生的断裂之后,试图重新构建新质“自我”的努力。这个新质“自我”的想象,和诗人投身于抗战及建国后的歌谣写作所代表的国家想象是同时进行、互相渗透的,他的创作转向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幻想的“花园”
在鲁山县文化局工作的乔书明收到诗人痖弦来信询问“鲁山诗人徐玉诺故里的老房子是否还在”后,便去寻访徐玉诺的故居,并将这次探访的经历写成《故居“梦幻花园”》[19]274-281。诗人故居所在的徐营村背靠凤凰山,两间土墙瓦房便是徐玉诺的家了。“院子西南角还残留一棵老树,树旁尚存一口枯井,苍苔斑驳的井口上,盖着一块厚厚的、仿佛是岁月冻结成的石板”[18]。面对此番景色,乔书明感受到了“一种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的苍凉”[18]。“诗人享誉大洋两岸的盛名和眼前这破败冷落之家实在有着天壤般的落差”[18]。而诗人就在这泥土的房子里写下了《将来之花园》:
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慢慢地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这就是我的工作呵!……[6]122
这座“花园”是诗人亲手为孩子们搭建的幻想乌托邦。这个充满天真、安宁的梦境与诗人颠沛的人生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首诗在众多残酷甚至血腥的灾难书写中显得格外平静。事实上,这种冲突感在诗人身上常有所体现,除去新文化运动事件中的自杀事件,还有很多例证。比如诗人有着写作的抱负却又能从热闹的文坛彻底隐退,随遇而安。[注]这可以从诗人解释自己当年为什么拒绝鲁迅出版其作品的建议看出,“自以为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头喱”,认为这是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可见诗人的写作抱负。参见刘济献、刘忱所编的《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21页。1945年宛西陷落后(在此之前,诗人在宛西乡村联合师范教书),诗人来到新野县的徐庄,又过上了隐士生活,常在清风月明之际与老友谈天、兴办私塾,到日本投降以后才返回故乡。[注]据刘涛在《徐玉诺史料掇拾》一文中发现的史料:叶红在《中国时报·先锋报》“徐玉诺专号”中所刊载文章《先进诗人现教古书——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中提及“这位被时代遗弃了的既往诗人,现在已经变成‘隐逸之士’了。原来他在新野西北隅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安了家。”该文见《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5年第12期。对于故乡,诗人经常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似乎任何一间“湖起坯”[注]乔书明所写《故居“梦幻花园”》一文中提及“湖起坯”是诗人家乡人用“河边、湖畔的硬泥划成坯块,晒凉而成”的一种当地建筑。该文见刘振军所编《徐玉诺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都可以安顿下来。但另一面,诗人却很少有安定感,常做出一些被人当作怪癖和“发神经”的举动。据诗人在省立第三师范授课时的学生陈孑英回忆,徐先生夜晚常到山野去生活。“在幽静的花园里”忽然会出现一只“黑豆一般的小枪口”对准“你的眼睛”(《永在的真实》),就连幻想的花园里也充满不安,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平安,宁静都是幻影”(《永在的真实》)。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与河南地方性战乱破坏了诗人居住场所的稳定感,从而导致了其“无法建立使其存在得以立足的感觉结构”[20]82。同时,这又显示出了诗人对现有秩序的拒斥态度,常对其所生活的空间进行逃离,流露出不能循规蹈矩的反抗因子。
诗人在《小诗》里表达了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空间感受,并幻想出一个充满着不安气氛的房间:
我这屋里有了黑斑的蛇吗?
为什么我不敢进我这屋子
进来就要急着跑出去呢?[8]238
这间可能会有“黑斑的蛇”的房间,可以折射出诗人怀疑与恐惧的自我意识空间。“空间不仅是客观的填充物体的容器,同时也是人类意识的居所”[9]11。因此,这个空间幻象可以非常自然地与“我”的心理活动融为一体。诗人接下来写道:
我想了这是我的好机会,
我所久待久待的,
我快变成一个有翅,
空虚而且空虚,
一切都没有,
而极自由的人了。
诗人这里所谈及的“自由”更富有意味,这“自由”是一种自主选择的权利,诗人在随后的诗里,将这种思想进一步阐释:“‘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我一点也不反对;因为当历史用各种圈套来罩我的时候,我脱然的跑了”。徐玉诺的诗歌充满自我本真的表露,诗中经常出现“孩子”这个人物形象,孩子不具备严密的理性和伪装自我的能力。“不稳定”就是试图寻求在稳定的本质中不断遭遇的虚无与不安,这也构筑了徐玉诺诗歌的怀疑精神。但“我”不会永远停留在虚无之中,这种“跑出去”“跑了”是对新的意义的渴望,也可以理解为对现状的彻底放弃。诗人在诗里借助有“蛇”的房间这一幻象,完成了一次文学意味上的空间逃逸。
与精神空间逃逸相反的则是主体意识的圈禁。如《他的现在》一诗:
我现在心爱黑暗,
这是不易捉摸的心理;
我在房内走着,
只有一个可以瞧见光明的小窗,
我心心念念地想把它关起来。
可怜的心理呵!
他怕觉着了他的存在。[8]317
从诗命名为《他的现在》也可以看出诗人返回自身与当下的思考。而与《小诗》中的“跑出去”不同,诗中的“我”如此惧怕光明而“心爱黑暗”,要将窗户——这个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关起来,将自己关在紧闭的空间从而打造了一个自我的囚牢。空间性是主体性的重要构成,黑暗的房间也是诗人遭遇虚无的隐喻,在这种精神与客观空间的并置中,“他怕觉着了他的存在”。诗人对存在的领悟激发了生命形而上的意义探寻,加之不断发生的现实苦难发酵,致使诗人的很多作品常弥漫着遁逃人生的虚无感:“他挥着死的病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和希望”(《命运》),“人生充满着没意义,他也气馁而且疲倦了”(《没意义的人生》)。
严峻的思考也形成了诗人对梦境书写的依赖,因为梦可以制造现实人生逃逸的幻象。梦境在徐玉诺的诗歌中频频出现,诗人常将自己的梦非常细致地记录下来。在《梦》一诗中,“我”听见母亲叫我的乳名,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空间场所切换,“我”走过“繁市的街”,“跑进了一个医院”,像一个游走的灵魂,因为看到已死去的医生躺在病床上而吓得“昏倒在地”。这样的梦境还原还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里所崇尚的“梦”书写存在着很大差异,并没有像后者一样连通天堂与地狱而抵达一个超验的精神世界。徐玉诺的“梦幻”更多的只是生活逃逸的出口,有时诗人并不愿意承认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而用一种不确定的、迷惘的口吻喊出:“不一定是真实!”(《不一定是真实》)诗人似乎认为梦境会延伸到现实中来。而“梦”的作用是“在这里,必须离开那里”。这样的“梦”书写亦不同于鲁迅的《野草》或是何其芳的《画梦录》中诡谲绮丽的想象和复杂的思辨,更多的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味与逃离。
废名认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21]诗人在《记忆》中也写道:“等到晚上卧在圈牢里,再一一反嚼出来,为什么我在寂寞中反刍。”这来自于“反刍”生活的梦境书写,构成了中国新诗中象征主义发端中的另一面相。而在《将来之花园》中,那如“破布”一般展开的梦境,何尝不是诗人在咀嚼生活的酸楚之下,对未来的一种乌托邦幻想。
四、结语
在现实与幻想的模糊边界行走,诗人既希望沉溺于梦境,又常常希望走出咀嚼着沉重过往的想象与幻梦。作为一个在五四文坛上曾与众多大家同行的作家却选择迅速归隐,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强烈关注,却在刻意为之的记忆逃离中停止了对艺术更加纵深的探索;严肃与怪诞、现实与幻想、隐遁与妥协,这些矛盾促成了徐玉诺人生和创作极具张力的表现。诗人在诗中经常使用“截断”这个词,正如其主观上截断自己的记忆上演“盖棺定论”一样,在归乡路上,徐玉诺也“截断了故乡的情思”(《故乡》)。故乡与死亡边界的模糊,那块充满着母亲召唤的“血地”始终是他要逃逸却又向往的一个幻象。正如克朗(Crang Mike)所言,文学中的重返家园之途往往都是以故乡的永久失落为起点。[22]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地方性苦难的裹挟下,诗人向内的幻想与向外的逃逸大概也都是无路可寻。诗人的诗歌里对于灾难的“反刍”、想象中的变形、在现实或虚构的空间逃逸,也是一场自救的文学想象。诗人看到“故乡的影片一片一片地,都飞散在不可知的海上”(《故乡》),似乎预言了诗人寻求回乡之路,仍旧是个未完成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