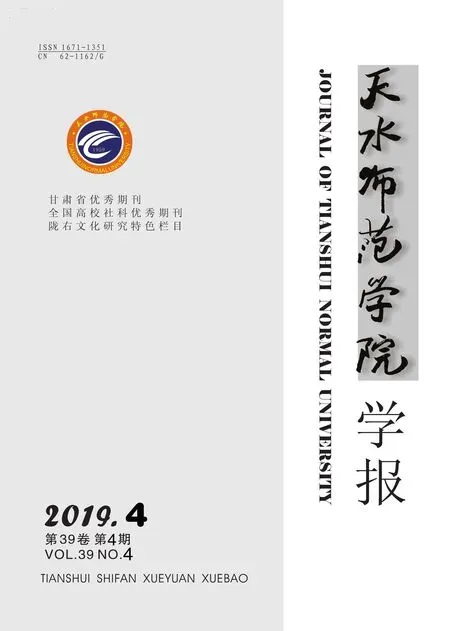冯友兰通论佛学对敦煌哲学研究可能的启示
范 鹏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冯友兰的佛学研究与敦煌哲学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理论关联?如果存在,这一关联的结合点是什么?冯友兰的佛学研究能否为敦煌哲学的研究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启示?由于冯友兰对佛学的研究是佛教研究者对冯友兰颇有微词的方面,至少是争论较多的地方。而敦煌哲学更是一个名已经立了但题并没有真正破的有待证明的领域。基于这样的现实,本文只能用“可能”说启示,不知道是不是能实质性地得到管用的启发。
一、冯友兰通论佛学要旨:主要观点与基本方法
冯友兰对佛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时期和《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期,可以简称为“大史期”与“新史期”,如果细分,中间还可以加一个“小史期”。关于“大史期”与“新史期”的区别,冯友兰自己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我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30 年代发表以后,我总觉得其中的玄学和佛学部分比较薄弱,篇幅不够长,材料不够多,分析不够深。”“在《新编》这一册中,我改写了玄学和佛学部分。经过改写的章节与两卷本的有关内容比较起来,材料没有加多,篇幅没有加长,但是分析加深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因为我抓住了玄学和佛学的主题,顺着它们的主题,说明它们的发展。”[1]311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对佛学的分析说明分为五章,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十四至四十八章,这五章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形成了冯友兰通论中国佛学之要旨,也有学者称之为冯友兰的佛学观。[2]其中,重点是第四十四章《通论佛学》,本文所谓冯友兰通论佛学主要是依据这五章特别是第四十四章的观点。依据这五章里对冯友兰对中国佛学研究作出的贡献的研究,我所见到的主要是1990年冯友兰先生逝世之后召开的纪念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许抗生的文章《冯友兰先生论中国佛学的特点和发展阶段》,该文收入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友兰先生纪念论文集》,同时收入的还有美国学者郑学礼的文章《冯友兰与禅宗哲学》。1997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冯友兰研究(第一辑)》收录的台湾学者黄俊盛的文章《冯友兰与中国佛教哲学——以“格义”“教门”“宗门”三阶段说为中心》(由于他是台湾第一所由佛教创办的大学研究所华梵人文科技学院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专门承担梵文及佛学方面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我对其观点特别重视)。柴文华主编的《冯友兰思想研究》共十九节,其中第十六节专门讨论冯友兰的“佛学观”,得出在佛学研究方面“冯友兰的特点是关注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佛学与中国人的关系,这实质上是关注中西文化的碰撞,此一点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格义’‘宗门’‘教门’的划分具有原创性”[2]392的结论,对这一结论我十分认同。柴文华还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作过这方面的研究。
(一)一个主题两种表达:以生死轮回为主要特点的神不灭论及其“表诠”与“遮诠”
1.一切宗教都是神不灭论,有些宗教的教义是哲学。“佛教的教义是哲学,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507佛教的思想理论根基是以生死轮回为主要特点的神不灭论,这就是佛教与佛学的主题。佛教把不死作为人的命运和“苦”的根源,以“空”为人不死的根据,让“涅槃”成为摆脱“苦海”的期望。佛学为佛教教义进行哲学的论证,使“生死”“形神”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继玄学“一般”与“特殊”主题之后新的哲学主题。
2.佛教由于基于“个体之不死”形成以生死轮回为主要特点的神不灭信仰,被冯友兰断定为“多神论”。
3.中国佛学表达佛教教义与佛学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以道生“涅槃学”为代表的“表诠”即以“是什么”正面表达思想的方式,另一种是以僧肇“般若学”为代表的“遮诠”即以“不是什么”反面表达思想的方式。冯友兰在《新知言》中称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二)一个对子两个“心”: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分析“个体的心”与“宇宙的心”
1.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历史曾经在前苏联和中国哲学界被滥用,时称“两个对子”,冯友兰在分析佛教哲学即佛学思想时正确深入地运用了其中的“一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将唯心主义进一步以讲“心”的范畴的不同分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用“一个对子”分析佛学中事实上存在的“个体的心”与“宇宙的心”。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冯友兰哲学思想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在他建构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过程中就有过论述。
2.冯友兰认为“佛教和佛学主张一切都是唯心所现,但是,这个心是个体的或是宇宙的心,各宗派的主张则有不同。如果认为是个体的心,那就必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它自己的世界,不可能有公共的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认为是宇宙的心,那它所现的世界就是公共的世界,各个个体所公有的世界。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1]513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从《大乘起信论》开始到慧能的禅宗顿悟派都明确这个心为宇宙的心。这事实上更是一种“格义”即用外来的一套分析工具讲同样是外来的佛教哲学。
3.我个人认为冯友兰运用“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个对子讲佛教哲学,分析“个体的心”与“宇宙的心”是有道理并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的。佛教哲学可能是这个对子除去西方哲学史的某些阶段能够准确运用的不多的几个对象之一。
(三)一个方法三个阶段:以“止观”认识宇宙人生和“格义”“教门”“宗门”
“止观”确实是佛教认识和修行的一种方法,但冯友兰的解释似乎并不是佛教的原意,而是自己特殊的理解。在冯友兰看来“止观是从生死轮回的问题出发的,是围绕这个问题发展的”。“止”就是停止对虚幻不实的世界的错误认识,“观”就是看透世界虚幻不实的本质。佛教这种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这就是所谓“格义”“教门”“宗门”。
什么是格义呢?冯友兰解释说:“佛教初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听到佛教的哲学,首先把它翻译成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然后才觉得可以理解。宣扬佛教哲学的人也必须把佛教哲学的思想,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说出来,然后中国人才能够理解,这种办法当时称为‘连类’或‘格义’。”冯友兰举了《高僧传》卷六记载的慧远讲“实相义”时听众费了很多时间都搞不清楚,甚至越来越糊涂,后来他用庄子的道理一讲,听众就理解了的例子来说明这就是引“庄子义为连类”。冯友兰又举《高僧传》卷四记录的另一个大佛学家法雅用中国原有的思想讲佛教,学生容易理解被称为“格义”的例子说明这个概念。我想,后来我们讲西方哲学的人用规律、逻辑解释“逻格斯”(Logos)大概也就是所谓“格义”的方法吧。这种讲法作为普及性质的传播大体是可以的,但作为专业的学问大概就不足为据了。在对“格义”阶段的具体说明过程中,冯友兰举了僧肇的《肇论》(由作为总论的《宗本义》和《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四个分论构成)、慧远的“神不灭论”和《三报论》、道生的“辩佛性义”“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以及谢灵运的《辩宗论》来论证了他们是如何用中国的术语讲佛教的哲学的。应该说这些人物的选择很有“哲学的代表性”,而且冯友兰注重的是这些思想家个人有创见的方面。比如,僧肇除去《肇论》这篇大论文之外,还有《维摩诘经注》,可是冯友兰只是提到了这个注却没有把它作为僧肇的佛教哲学思想去认真深入地分析,就我所知《维摩诘经》的哲学思辨色彩非常浓厚,这个注当然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哲学著作,文字优美、思想深刻、意境玄远。冯友兰在论“教门”的章节时引用过这个注中僧肇讲“默”的一个故事。[1]535
所谓“教门”按照冯友兰的解释就是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了一个宗派尊崇一个佛教经典从而使同一种宗教有了不同的思想观点的现象。在分论“教门”的章节,冯友兰主要讲解了尊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三论宗、假托印度马鸣菩萨所作陈真谛翻译实际上很可能是陈真谛本人写作的《大乘起信论》、玄奘的《成唯识论》和华严宗的三个“义”。冯友兰对这些也有人称为相宗(唯识)、空宗(三论)、性宗(华严)哲学思想的分析是以他所立的主题、方法和阶段划分进行的。在我看来,这是真正把佛教哲学纳入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无论佛教史和佛学理论家们怎样评价,就哲学史的视角来说,冯友兰至少是打通了佛教哲学这个“关节”,使其与前前后后的中国哲学史有机关联了起来。
所谓“宗门”专门指禅宗,据冯友兰说是禅宗自称。冯友兰对禅宗不仅是情有独钟,而且体悟独到,不少专门研究禅宗的学者都大加赞许。在冯友兰看来,禅宗自认为是超越了“教门”是“有根据的”。[1]552“禅宗并不仅只是佛教和佛学中的一个宗派,而且是中国佛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阶段。”[1]553这一阶段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开启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推动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佛教说,禅宗认为以前的佛教都是在“教”的范围内说事,而禅宗自己是“教外别传”,它所重视的不是任何一部经典,而是超越经典的“以心传心”“密意”或“心法”。“从佛教和佛学的发展看,禅宗的兴起,也是对于佛学的烦琐哲学的一种否定。”[1]554过去天堂的门票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太昂贵了,禅宗有点天堂的门票降价了的意味。就中国哲学来说,禅宗的出现进一步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3]109“禅宗中的人,……大概都主张下列五点:(1)第一义不可说,(2)道不可修,(3)究竟无得,(4)‘佛法无多子’,(5)‘担水砍柴,无非妙道’。”[3]102在冯友兰看来,禅宗的好处就在于敢于把十分复杂的佛教思想简单化。“禅宗的主要意思,说穿点破,实是明白简单。”[3]107除去讲意义派别,冯友兰其实只讲了禅宗的八个字:“不道之道”“无修之修”。其实,他最欣赏的还有八个字:“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在两个派别中冯友兰理所当然地推崇慧能的顿悟一说。为什么我说是“理所当然”呢?因为冯友兰作为一个新式的理学家,他自己的哲学就是简单明了、主张顿悟的。他得益于禅宗的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这十六个字。
二、冯友兰通论佛学的主要观点、基本方法与敦煌哲学研究的联系域与对接点
讨论冯友兰通论佛学对敦煌哲学研究可能的启示,必须交待一下我倡导并正在推进的敦煌哲学,同时也必须寻找冯友兰佛学观与敦煌哲学研究共同指向的领域和可能发生联系的学术理论对接点。
(一)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和敦煌学研究新动向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敦煌哲学?简单地说,我所理解的敦煌哲学,就是以中古时期(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丝绸之路(汉代开通繁荣六百多年的从中国长安到欧洲罗马等地的古代陆路文化商贸通道)上在中国西北形成发展的敦煌文化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成果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宇宙观、认识观、规律观、价值观、历史观、人生观、心性观)问题,进而探索敦煌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其主要思想内容是大盛融通之道。敦煌哲学的对象就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敦煌,作为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敦煌文化。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发现于敦煌的文献、出现在敦煌的文物和有关敦煌的文字。凡与敦煌直接相关的能反映出敦煌作为文化符号价值具有敦煌性的敦煌经卷、敦煌文书、敦煌壁画、敦煌洞窟、敦煌雕塑、敦煌社会、敦煌人物、敦煌史迹均可视为敦煌文化的内容,也都是敦煌哲学直接或间接的研究对象。
敦煌哲学大体包括敦煌文化哲学、敦煌宗教哲学、敦煌艺术哲学(敦煌美学)、敦煌人生哲学、敦煌历史哲学、敦煌社会哲学、敦煌政治哲学、敦煌教育哲学等,敦煌哲学既是哲学的三级学科或中国哲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或动向。“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敦煌学研究的新动向”这个说法,对敦煌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认识,因为我过去的说法注重的是哲学思想,所谓“宇宙人生根本大道”,而这个新的提法注重点转向了“哲学精神”。关于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正是冯友兰本人立过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
(二)中国化的佛教是冯友兰通论佛学与敦煌哲学研究的联系域
说到敦煌文化我自己常常用“三个5”说其主要的内容,即5百个洞窟、5万平方米壁画、5万卷文献(一般称为敦煌卷子)。我对敦煌文化的理解与过去很多人的理解略有不同,主要在三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表达形态。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使敦煌在一千年左右(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以敦煌莫高窟在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始开佛教洞窟为起点,也可以藏经洞发现年代最早的文献公元393年即后凉麟嘉五年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为起点,到1368年元朝灭亡敦煌莫高窟停止营造为止)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史上成为人类文明几个主要形态广泛接触交流的大都会,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明交流道路造就了敦煌文化特殊的表达形态。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4]因此,敦煌文化更多的是在与其他文明形态与宗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相较于先秦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类型或阶段而言,敦煌文化是直接在开放的前沿与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波斯文化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世界性,是一种更具国际比较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敦煌文化骨子里还是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占据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过去,不少学者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敦煌文化时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敦煌文化排除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我看来,敦煌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而这一典范在当今世界无论从学术还是政治上来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二,敦煌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因、以佛教文化为基本内容、以形象化的宗教题材为主要表现方式、以多文明多宗教交融创新为基本特点、以“通而不统”为其主要精神的综合性文化形态。甘肃社会科学院颜廷亮指出,“敦煌文化指的是以4~14 世纪为存在时限、以那一千年间敦煌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状况为存在背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全体居民具有鲜明特点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主要内容、文化定位、文化特征、主要精神等方面理解敦煌文化。就主要内容而言,敦煌文化是由敦煌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体敦煌地区居民创造的、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和主导、以宗教文化为主要表现方式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就文化定位而言,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化》一书中将敦煌文化定位为“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汉文化圈的西陲硕果”,即敦煌文化是专属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文化特征而言,敦煌文化是一种去中心主义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中华文化中心论,也不是佛教中心论,而是追求一种开放性、兼容性的“无中心而有重心”的多元文化交融体;就主要精神而言,敦煌文化既有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汇通追求融合,又有多层多样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并盛,既保持了各个文化类型自身的独立性,又兼容了不同文化类型各自的合理性,这就是敦煌文化“通而不统”的精神内涵。[5]
第三,敦煌文化的核心精神“通而不统”是“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精神的特殊表达。“和而不同”意味着承认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反对无差别的同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和而不同”的精神提倡多元文化在相互交流和想互融合中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这一精神已经被世人所公认,达成基本共识。具体来说,“和而不同”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文化传统内部各种思想流派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以此论儒墨道法释之间的关系就十分恰当。面对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有宏大视野的学术史家已经看到,其实诸子百家在理论上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只是理论建构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方法有所不同,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推而广之,“和而不同”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学术派别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是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文明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敦煌文化所体现的“和而不同”的国际间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通而不统”的精神,更深刻、更广泛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和精深思想,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精神作为哲学底蕴,才造就了千年辉煌的敦煌文化,而这一精神与“和而不同”一起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资源。“和而不同”主要表明的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态度和体现文明平等性的交往交流原则,而“通而不统”则主要表达的是文明交流交融的行为准则和实现文明互联互通而又不消解文明丰富性的文明理想。尊重文明多样性只是一种态度,而打通文明多样性则是一种实践。态度固然重要,但愿景成为现实才是尊重和交流的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识体为前提,“通而不统”的敦煌精神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粒“定心丸”,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识体的思想基础,当今世界需要“通而不统”的文化精神。与“和而不同”得出的过程有所不同,“通而不统”不是依据什么文献的一些概念而总结出来的,而是通过研究敦煌文化的众多表现形态,从各种文化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这也许就是敦煌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传统研究方式有所区别的地方。
从我对敦煌哲学的界定和敦煌文化的理解中就可以看到冯友兰的佛学观与敦煌哲学的联系域了,那就是“中国佛教”“中国佛学”或者叫佛教的中国化。冯友兰的佛学观是研究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敦煌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文化标本。更为重要的是敦煌文化这个标本不仅为研究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本,一些内地已经失传的佛教经典在敦煌保存了下来,同样存在的一些经典,敦煌的译本往往是最古老的;而且敦煌还保存了大量当地民众开展佛教活动的原始材料。既有大量的写经,还有不少通俗的说唱文本;既有闻名全球的敦煌壁画,还有鲜为人知的敦煌人的僧俗混合生活方式;既有传统哲学可以借助的文献,也有敦煌哲学特别注重的活态的哲学研究对象。就敦煌所藏的佛教经典说,姜亮夫指出“敦煌所藏佛经可能是最早的译本,因为它把原文录上了”。[6]47不仅有最早的译本,更有最早的写本,比如,杨学勇就提出:“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中论》写卷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论》手抄本。”[7]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三)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及其表现方式是冯友兰通论佛学与敦煌哲学研究的对接点
冯友兰通论佛学的佛学观与敦煌哲学的联系域是“中国佛教”“中国佛学”或者叫佛教的中国化。具体说其对接点还可以说得更加具体一点,这就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及其表现方式。冯友兰注重的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及其表现的哲学方式,敦煌文化则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及其表现的世俗宗教方式和艺术方式。用冯友兰通论佛学的佛学观去理解敦煌文化中的佛教、佛学及其表现方式,可以大大加深对敦煌佛教文化解释的力度和理解的程度;反过来,用敦煌文化中的佛教、佛学及其多种表现方式,丰富发展完善冯友兰的佛学观,接着冯友兰往下讲,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佛学思想及其发展阶段必将产生重要作用。敦煌卷子大约有5万卷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佛经,大部分是手写本,“卷子内容以《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为最多,因为这两部经在佛经里面,宗教意味最深,不是哲理意味最深”。[6]122敦煌写经绝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因祈求自己或亲人生活安康、病痛痊愈、路途平安而请人抄写的,写经人则多为寺院年青和尚,也有个别很有名望的高僧,如唐代的悟真(约公元811~895年)等。从这些对接点入手,探究冯友兰佛学观对敦煌哲学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而推进敦煌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化佛学思想的研究,对学术界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当然也是一件多多少少有点意义的事。
三、冯友兰通论佛学对敦煌哲学研究可能的启示:阶段明主题、分析有框架、表达无定式
(一)对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敦煌佛教文化的哲学研究应该明确自身的思想主题
冯友兰对中国化佛学思想主题的确认是经过将其纳入中国哲学演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之后逐步明确起来的。这起源于“大史期”的朦胧猜想、“小史期”初步推定而定论在“新史期”的重新思考之中。冯友兰自称对中国化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新史期”分析加深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因为我抓住了玄学和佛学的主题,顺着它们的主题,说明它们的发展。”这启示我们:敦煌哲学的研究如果欲对其思想主题有一个初步的确认,就必须将敦煌哲学对敦煌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纳入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全部进程乃至整个佛教思想史的大视野之中。就研究敦煌哲学的多数学者的现状看,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连敦煌佛教自身的全部面目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敦煌佛教与敦煌艺术研究成果的运用还处于生吞活剥阶段,有时甚至吞都没有吞下去。只有把敦煌佛教思想文化中的哲学意味把握准并将其纳入中国化佛教思想进程中去,才能划定其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的定位。同时,冯友兰的佛学观还启示我们,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要纳入中国化佛学思想的进程中,而且作为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还应该纳入中国哲学思想的进程之中去考察,只有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才可能找到敦煌哲学的历史定位与思想主题。“通而不统”只不过是我们在初步研究敦煌哲学的过程中大胆假设的一个思想主题与精神现象,还没有得到什么理论的论证,更谈不上什么“充分论证”了。明确敦煌哲学在中国化佛教思想过程中的地位,从而把握其思想主题,这是冯友兰佛学观对敦煌哲学研究的首要启示;这一启示同时也要求我们将敦煌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中去,这两个方面过去我们不仅没有做到,而且也没有想到,正是冯友兰的佛学观,是他通论佛学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
(二)对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敦煌佛教文化的哲学研究能够运用“表诠”与“遮诠”的方法
冯友兰通论佛学对佛教思想的表达方式有所谓“表诠”与“遮诠”的区分,在其他地方他也称之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就其自身说,他在构造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时候主要运用的是“正的方法”,而在《新原人》中讲四境界时,似乎更喜欢所谓“负的方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禅宗的理解。这些方法运用到敦煌哲学的研究中来,对敦煌文化进行哲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表诠”与“遮诠”的方式在敦煌地方表达佛教思想时同样是存在的。大量的佛经主要都是通过写、讲、说、唱、画的“表诠”方式来表达的,而“遮诠”的方式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大量的壁画只能用直白的方式讲释迦牟尼成佛的佛传故事和成佛前的本生故事,而作为表达思想的经变画要讲佛经故事中表达的思想内容大概只有用隐喻方式即所谓“遮诠”的方法了。在敦煌壁画中表达佛经思想的经变画最多的是《东方药师经变》,大约有百幅以上,因其思想倾向于消灾延寿功能的阐述,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现实需求,所以不仅在敦煌,在全国其他著名石窟也同样存在,但迄今为止在敦煌是保存得最多的。在敦煌“唐代以后,经变画成为壁画最重要的内容,往往在洞窟的南北两壁画及东壁整壁画经变画,如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法华经变等,虽然在隋朝已经出现,但所表现的情节故事大大增加。另有不少新出现的经变,如观无量寿经变、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劳度叉斗圣经变、十轮经变等等。”[8]144经变画并不是一般地展示佛教传播的宏大场面,而是通过佛经中不同的故事表达一种特定的观念甚至思想。因此,经变画成为敦煌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以《法华经变》为例,在敦煌唐代的法华经变画中,不仅有序品表现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的宏大场面的壁画,而且还有包括见宝塔品、观音普门品、药草喻品、譬喻品、信解品等十多品,该经共十八品,至少有一半以上在敦煌壁画中有专门的画面。这些经变画通过描绘佛经故事宣传佛教思想,启发信众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形象的画面,加深对佛经的理解。比如信解品讲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与父亲走失,沦为乞丐,而其父则成为一个大富豪。一日,儿子行乞食来到父亲家门口,却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父亲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却并不马上认他,而是先让人把他高价雇佣到自己家里干活,经过二十多年之后才逐步让他管理账目,一直到儿子对家中事务了如指掌时,才召集家族中人说明真相。这个故事,一方面表达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共同思想,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表达了其忍耐成大事的主张,可以说表达佛教的一般道理用的是普通人都能看明白的“表诠”方式,而更深入的思想则用的是譬喻性质的“遮诠”方式。用这样的思路来解读经变画似乎比我们以往的说明要更加通达一点。这是冯友兰佛学观给我的重要启示之一。我曾经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研究《维摩诘经变》故事画中的“不二”“不思议”思想,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共同的困惑是画面究竟能不能表达如此深奥的宗教哲学思想?如果可能,那么在《问疾品》这幅画中又是如何通过形象生动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我们能想到的只是我们的解释。其实,现在看来,佛教经变画自身是有一套冯友兰称为“表诠”与“遮诠”的方式的,只不过我们对手印、喻意、象征、刻画、物象、线条等等的表达还不深入掌握罢了。如果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其表达方式,“形象哲学”与形象史学一样是可以讲的。比如,手印就是佛教表达思想的一种独特的创造,最常见的有说法印、施无畏印、与愿印、降魔印、禅定印等所谓释迦五印,多一些的还有十二手印,据说密宗的手印有几百种。手印是非常明确的肢体语言与立体平面艺术可以共用的艺术语言,在我们理解佛教雕塑与壁画过程中发挥着其他解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许是敦煌哲学“观其迹思其所以迹”的重要入手处。
(三)对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敦煌佛教文化的研究可以纳入“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进行解释
我们可能受益于冯友兰佛学观的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他最有创见的“格义”“教门”“宗门”三阶段说,这是逻辑的分析框架,与历史的真实演进结合起来说也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敦煌哲学研究的敦煌文化最兴盛的时期大约是一千年左右即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这其中应该包括冯友兰所谓“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但是,这三个阶段在敦煌佛教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敦煌哲学与敦煌学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段文杰先生有《佛在敦煌》一书,在分析敦煌佛教艺术的同时,对佛教在敦煌的传播发展也有涉猎。
敦煌佛教的兴起与传播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从逻辑上推论,由于敦煌地处西域与中原之间偏向西域的地界,从西来的佛教应该在敦煌比中原传播早一些,但事实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是十分充足。敦煌所在的整个河西走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已经比较兴盛了。随着北魏在敦煌设立军镇,河西走廊西端的军政中心转移到了敦煌,这一转移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敦煌的传播。特别是丝绸之路在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和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天下称富庶”的富裕地方,佛教也随之有了新的气象,大量宫廷写经传到敦煌,东来弘道、西去求法的频繁往来,使敦煌成为佛教双向强化的重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敦煌文化的中原基因至关重要,不少人只知道佛教从西向东,理所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佛教是从西域传来的,其实大量写经是从当时的长安传到敦煌去的)。由于地处偏远,唐代发生在内地的几次灭佛事件对敦煌佛教并没有产生什么破坏性的影响。加之敦煌的吐蕃统治时期(公元786~848 年)、归义军时期(848~1036 年)和西夏(1068~1227 年)时期(党项人初信天、鬼、神,尚巫术,统治河西后开始接受并大力推崇佛教)都延续了佛教信仰,使佛教在敦煌的传播发展一直处于有当地统治政权支持的状态之下。用冯友兰先生的所谓“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来分析佛教在敦煌的发展与展现,“格义”应该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特别是在民众信仰和壁画之中,不“格义”无“连类”恐怕就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愿与对佛经的理解。大量表达民众信仰心理的愿文(也称发愿文)在表白心愿时从来都是佛教信仰加俺家祖宗,各路神仙共同祈求。壁画中佛教的帝释天和梵天演变成中国的东王公与西王母的事是常有的。[9]69这一阶段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首推“敦煌菩萨”竺法护。据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竺法护……祖籍月支,世居敦煌。他一生往来于敦煌与长安之间,先后47 年(266 年~313 年),译经150余部。”《高僧传》评论其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正因为是敦煌人,竺法护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敦煌菩萨’。让敦煌的名字和这位为中国佛教发展贡献巨大的高僧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10]154《高僧传》记录的另一个敦煌佛教人物是东晋名僧竺昙猷:“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根据马德先生推测,竺昙猷很可能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就在敦煌开窟修行了,这要比现在公认的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始开佛教洞窟的记录早上13年。
“教门”方式在敦煌写经和壁画中也有反映。敦煌莫高窟现存的三十多类经变画,如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涅槃经变、药师经变、华严经变等,不少就是依据佛教某一经典绘就的,为支撑“教门”时期佛教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煌的写经活动也多多少少受到不同教门思想的影响,在不同阶层的人群和信众中各有侧重。用冯友兰的思想方法,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与他不同的研究敦煌佛教及其艺术表达的分析框架。比如,从净土信仰、弥勒信仰、药师信仰、观世音信仰和维摩诘崇拜角度研究经变画也许更有意义和价值。对敦煌石窟艺术既有精深研究,又写过不少通俗介绍的赵声良先生在其《艺苑瑰宝——莫高窟壁画与彩塑》一书中专门对经变画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他指出:中唐以后,经变画的种类越来越多,成为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和审美观。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但纳入冯友兰三个阶段分析框架的说明还不多见。我们也许可以沿着这一思想做一些工作。
“宗门”阶段的佛教信仰在敦煌佛教活动中更是可以得到大量的印证。特别是“不道之道”“无修之修”,“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修行思想,可以说是敦煌佛教在民间流传的思想基础。由于敦煌卷子大量保存了这方面的鲜活史料,我们可能使冯友兰对禅宗特点的描述得到比内地史料更好地说明,从而也为敦煌佛教在唐代前后的地方特色找到更加哲学化的理论依据。
我们的理想不仅是将冯友兰“格义”“教门”“宗门”三阶段的解释框架引入敦煌哲学的研究之中,而且期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像冯友兰先生一样,抓住敦煌佛学思想的主题,顺着它的主题,说明它的发展。从而使敦煌哲学对敦煌佛学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甚至不同于敦煌学的特殊贡献。
(四)对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敦煌佛教文化的研究还可能受到冯友兰通论佛学多方面的方法论启示
冯友兰的哲学智慧在其佛学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治学方法也在这一领域彰显了巨大的解释力。敦煌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哲学解释,这与冯友兰对佛教史和佛学史研究的哲学解释十分相似。冯友兰的佛学观至少还可能给我们这样几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其敢下断语的勇气,可以给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对敦煌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以学术胆识的支撑;二是他对事物本质的看穿说透,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十分繁杂的敦煌学众多成果中得出哲学视角的分析;三是他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考与把握,可以使我们既把敦煌哲学纳入更加广阔的视野去思考和界定,又能够化繁为简、深入浅出,提出出自深入研究的重要结论,哪怕是冯友兰所说的“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四是辨名析理、释古喻今的方法,可能使我们敦煌哲学研究更具哲学特点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特色。
以上三个方面是我所理解的冯友兰通论佛学对敦煌哲学研究可能的启示,但这只是一个大胆假设的产物,不仅十分粗糙,而且风格也不尽统一,大量利用了别人的成果和自己的旧说,如何变“可能”为“可以”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