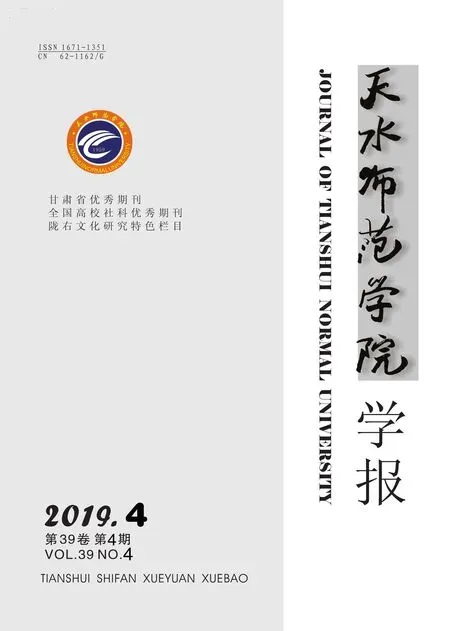乡村美学的核心内容和学术宗旨
郭昭第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741001)
乡村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们几乎面临着基本相同的人生课题,虽然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可能带来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基本课题,其中每个人所使用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也常常不是自己单个人以及某一临时成立的集体单独发明创造出来的,往往是依靠自祖上以来便广为流传甚或诉诸集体意识的乡村谚语深刻切入人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形式而得以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费孝通指出:“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到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了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1]48-49
一、乡村美学的核心内容
真正的乡村美学并不致力于建构一种概念范畴和知识谱系,更不执着于建构一种理论框架甚或理论体系,而是尽可能忠实地搜集罗列和展示一些事实。如维特根斯坦这样写道:“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哲学家的工作就在于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搜集提示物。”[2]76虽然不能说乡村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大自然的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也没有放弃对大自然奥秘和人生道理的深刻反省和全面总结,他们更没有放弃祖祖辈辈日积月累的无穷实践检验和生命验证,而且这些实践检验和生命验证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所谓专业实践和专门论证之中,更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和方式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用自己的整个生活乃至生命,以及世世代代的生活乃至生命在实践和验证着其哲学观察和感悟乃至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乡村美学的核心内容是将这些经过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实践和验证的哲学观察和感悟乃至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尽可能忠实地搜集和罗列出来。
乡村美学的核心内容只是搜集罗列和展示基于动物性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文明发展最核心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基于见朴抱素、复归自然的春夏秋冬之类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围绕基于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基于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来全面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民间表征和美学智慧。这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威廉斯看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大概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是理想的,是人类根据某些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第二种是文献的,是借助思想性或想象性作品记录下来的人类思想和经验;第三种是社会的,是包含在艺术、学识、制度和日常行为乃至特殊生活方式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3]50-51虽然威廉斯是对文化的定义进行梳理,但这一梳理也准确阐述了文化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作为理想的文化,是渗透于每一民族甚或地域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这种文化常常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是任何一种文化之最原始、最持久、最精妙、最核心的部分,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记载却常常作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得以传承和绵延的文化。第二层面作为文献的文化,是能用语言文字记载且已经用语言文字记载了的文化,是人们能借助文化典籍加以系统学习和掌握的文化。第三层面作为社会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是存在于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能用语言文字记载但尚未用语言文字记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人们能直接感知和体验,但由于尚未用语言文字加以记载而常常被遗忘甚或失传的文化。
作为理想的文化,涉及民族集体无意识,往往借重新发掘而有意义;作为典籍的文化,关涉民族典籍的传播与传承,往往借重新阐释而有意义;作为社会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关系民族特殊日常生活方式,往往借重新梳理和记录而有意义。而且作为理想的文化存在于世代相传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即使不及时加以研究,仍然可能完整且神秘地存在于这一民族每一个人根深蒂固的无意识之中,仍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作为典籍的文化,见诸文化典籍的文字记载,即使不进行及时阐释,如果这一典籍本身没有失传,仍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可能;但作为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却只见诸人们的普通日常生活,往往可能因为生活于这一时代这一地域人们的逐渐逝去,不再会有人以见证者身份去发现、梳理和复原往昔的日常生活方式,即使后来确实有人试图发现、梳理和复原这些日常生活方式,但限于各方面条件不可能直接感受和获取这些材料,因此难免存在诸多生疏和隔膜之处。乡村美学虽然可能涉及民族文化理想的重新发掘、相关文化典籍的重新阐释,但更多还是特殊生活方式的记录和重新梳理。尤其在当前中国普遍面临乡村的日益严重衰败甚或衰亡的情况下,记录和重新梳理往往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必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记录中国乡村基于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基于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等方面特殊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会远远超过对文化精神的发掘和文化典籍的阐释。因为见诸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以至生生而有条理的宇宙规律,所关涉的不仅是天地运行大道,而且是人类对世界的最高认识和感悟;也正是基于这一最高认识和感悟,才能法天象地,才能道法自然,才能借助天地自然大道总结出人生之道。人生之道离不开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都是事关动物性的特征,但生老病死常被人们赋予更多形而上的人生之道,有诗书礼乐文化的成分,至少人类所体会和感悟的生老病死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动物意义的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蒙昧和野蛮的文明特征和内涵,特别是人类所约定俗成的关涉生老病死的一些庆典和祭祀仪式等更非出自人的动物性本能,以及先天遗传,好多显然是人们经过家庭熏陶、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的潜移默化,以及后天的刻苦学习和训练所获得的生命意识,至少人类赋予其自身生老病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文化意蕴,将这些文化意蕴仪式化等显然必须经过后天不断灌输和学习训练才能获得。如迪萨纳亚克所说:“人类的仪式是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是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人类有意表演庆典,而不是像鸟儿筑巢或唱歌那样出于本能。然而,在仪式的表演之下,我相信潜藏着类似于使其特殊的一种天生的人类行为倾向。”[4]108至于衣食住行等最基本需要则很大程度上是动物性机能,特别是将其作为最后和唯一终极目的、并诉诸物质器皿乃至日常用品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人们也可能会赋予其一定文化元素,但就其最基本层面而言,仍然很大程度上带有动物性的形而下特征。诸如春夏秋冬以及相关二十四节气等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诸如此类自然现象特别是一年四季及其二十四节气的认识却彰显着人们对自然规律之最独具创造性的把握能力。当人们能将其一生婴幼儿、青少年、壮年、老年四个时期的生命节律与一年四季生、长、收、藏的自然节律相统一,并将其节日化、仪式化、同一化,一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时,所体现的便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和把握能力,更是一种生命智慧,以及是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生命境界。
宗白华有这样一段论述,他写道:“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具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就是一切现象和体和用。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最能表达出中国人这种‘观吾生,观其生’(易观卜辞)的风度和境界。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但这境界,这‘形而上的道’,也同时要能贯彻到形而下的器。器是人类生活的日常用具。人类能仰观俯察,构成宇宙观,会通形象物理,才能创作器皿,以为人生之用。器是离不开人生的,而人也成了离不开器皿工具的生物。而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峰,礼和乐的生活,乃寄托和表现于礼器乐器。”[5]410-411乡村美学将见诸物质器皿和生活用品的衣食住行作为特殊生活方式的初级形态,将见诸诗书礼乐乃至精神认知的生老病死作为特殊生活方式的中级形态,将见诸四季运行和天地大道的春夏秋冬作为特殊生活方式的高级形态,其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人类特殊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态和美学智慧,为行将或已经衰败的乡村生活方式保留一些痕迹。
乡村美学在记录和呈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春夏秋冬等方面的乡村特殊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进而关注乡村民间文学尤其谚语这一最基本的文化载体,借以发掘和表彰一个民族寓于最基本生活方式,及谚语歌谣等民间文学之中的最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研究乡村比研究城市更利于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研究某一地域某一村庄的民歌尤其谚语比研究某一时髦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利于把握一个地域一个乡村人们的文化命脉。这似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也许以为这是一个相当偏激的看法,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各种特征确实最大限度地存在于各自民族相沿已久的民间诗歌和民间谚语之中。黑格尔注意到民歌所具有的民族特征,他这样写道:“民族的各种特征主要表现在民间诗歌里,所以现代人对此有普遍的兴趣,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民歌,想从此认识各民族的特点,加以同情和体验。”[6]202相对于民歌,其实谚语的概括更精辟、更富于哲理,可以说是各自地域的人们祖祖辈辈相沿成习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的结晶,其中所蕴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并不仅仅经过了一代人的检验和证实,甚至经过了祖祖辈辈的检验和验证,比较而言常常比任何单纯的学者终其一生所获得的经验和智慧更经得起考验和检验。
二、乡村美学的学术宗旨
乡村美学搜集罗列和呈现基于动物性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文明发展最核心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基于见朴抱素、复归自然的春夏秋冬之类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理所当然避免不了表彰中国乡村祖祖辈辈相沿已久的因果报应法则。诸如:“凡事留有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7]35“在在言善言,行善行,交游善人。要得此脉满世界,则福德亦满世界矣。”[8]46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乡村往往将因果报应之类法则与民间信仰有机联系起来,且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衣食住行基本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基本生活内容、春夏秋冬基本生活习惯乃至禁忌之中。众所周知,中国乡村重视甚或迷信风水,尤其相信人出在坟里,财出在门里,但更强调“要看山上坟,先看屋下人”的古训,即使风水学专著如《绘图地理五诀》也明确指出:“足食得嗣,平安之地,可以人力求之。于封侯,大地多有奇形怪穴,鬼神呵护,以待有德,非人力可求也。”[9]1这一方面阐述了人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积善的重要性,是说积善成德较之人为寻求风水宝地更为有效。中国人之重视因果,更强调善恶有报。不仅诸如《绘图地理五诀》所谓“阴地不如心地”[9]1的观点典型体现了中国乡村重因果报应,认定积善成德胜于其他一切人力作用,而且如《周易·坤文言》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10]87类似观点也见于民间广为流传的《太上感应篇》和《心相篇》之中。如《太上感应篇》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11]102以及《心相篇》所谓“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福祸可知”[12]109都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念。
中国乡村不仅将诸如因果报应、积善成德作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将其与儒释道神灵和圣贤,及卓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有机联系起来一并作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李约瑟指出:“只要在中国生活过,在不同省份旅行过,就一定对许多美丽的祈福庙宇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庙宇不是供奉佛菩萨的,而是供奉泽被后世的普通人的。”[13]250-251所有这些在信仰基督教之类一神教的人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中国这一民间信仰却有真正意义的宗教所没有的历久弥新而无孔不入的力量,其影响几乎渗入中国大地每一个村落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可以说正是这种历久弥新、无孔不入,在信仰一神教的人们看来近乎迷信的民间信仰,却真正支撑起中国人心灵世界的独特价值体系,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日常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底线,几乎概莫能外。虽然诸如此类的民间信仰常常被误以为是封建迷信,但这种封建迷信并不单纯是愚弄和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而且更是抚慰人们心灵创伤,支撑人们含辛茹苦却无怨无悔地生活的精神支柱,更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却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其实中国民间信仰,并不单纯崇拜道教、佛教神灵,也崇拜儒家圣贤,也崇拜功绩卓著的历史名人,还崇拜包括泽被一个村落乃至一个家族的祖先,以及养育一家人使生命得以延续的三代祖宗。虽然几乎遍及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乃至所有村落的山神土地庙、家神庙及祖宗祠堂所供奉的山神土地、宗族家神可能并不占据中国道教和佛教的正统神灵体系的主要位置,也不一定有广大神通,但肯定有正统神灵所没有的有求必应的亲和力和事无巨细的养护力,而且较之其他正统神灵似乎更有召之即来、有求必应的灵验,常常能保佑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平安幸福,使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中国乡村所有诸如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历史人物的祠堂,以及家神庙、山神土地庙等庙宇和祠堂,对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的人们有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因冒犯神灵惨遭报应,或因敬畏神灵的善行而有善果的诸多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的灵验传说例证等,都以祖祖辈辈口头传承方式,于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教化着人们,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震慑和约束作用,以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构成了乡村民间信仰的基本内核。
这种看似有些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恰恰在最根本的观念层面为生活于这一方水土的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真正成佛成圣的最后通道,以致有着一神教所没有的破除迷信、自成佛圣的特点。因为虽然一神教也可能为信徒提供进入天堂的机会,这个机会也可能取决于信徒的虔诚信仰,但更取决于上帝或真主的恩赐,而且即使如此也不可能最终达到成为上帝或真主的层次;中国民间信仰不仅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几乎均等的机会,且并不取决于佛祖或玉帝的恩赐,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因自身的造化和努力,并能达到与圣贤、神仙、佛祖无别的境界。中国乡村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其内心深处拥有这样一种坚定信念:无论任何人,只要在阳世三家严于修身,积善成德,死后其灵魂都可以免遭阴曹地府的折磨和惩罚而脱离苦海,顺理成章地成佛成圣。所谓“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头顶三尺有神灵”之类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人们家喻户晓的普遍精神信念。诸如《太上感应篇》所谓“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11]106及《周易》所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14]645等都是筑起中国乡村人们内心世界最神秘精神支柱、最基本心理慰藉、最严密道德防线的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核。正是由于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的祖祖辈辈潜移默化,使得中国乡村的人们在心灵深处敬畏乃至崇拜圣贤,相信因果有缘、善恶有报,深信否极泰来、苦尽甘来,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甘愿受苦受难,无论遭遇多么悲惨的打击,多么严重的心理创伤,都能逆来顺受、无怨无悔。这也是中国乡村每一个人对人生智慧和辩证哲学的最基本也最朴素的领悟和体认。正是这一为普通人提供的成佛成圣、成神成仙的最后通道作为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才真正支撑着中国乡村的人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经久不衰,才真正成为中国乡村人们最强力的精神动力和最原始的心理情结。
这种似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其实与儒释道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儒家之“人人皆可为尧舜”、道家之“万物一马”、佛教之“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清楚地阐述了人与佛圣平等不二的思想,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民间信仰之所谓一切人只要严于修身、积善成德,都能自成佛圣的价值观念及体系。中国民间信仰不仅赋予卓有成就的历史伟人以崇高的神灵地位,赋予能保佑一方平安的祖宗及山神土地以崇高的神灵地位,而且也赋予养育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祖先以崇高的家神地位。这种在一神教看来绝对不可能的民间信仰和文化传统恰恰表明,不仅儒家之圣人,道教之神人、真人、圣人是人间圣者积善成德的必然结果,而且即使佛教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对生命大彻大悟的人间圣者,并不是有些人所误解的是至高无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佛教有所谓“佛不度人人自度”的说法。虽然佛祖曾发誓超度一切众生,但没有一个众生因佛祖超度而脱离苦海,《金刚经》有云:“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15]11虽然诸如祖宗三代神灵,以及家神土地之类民间诸神在其他人家乃至其他村落可能并不受普遍崇拜,但他们不仅因为有求必应、事必躬亲的亲和力,常常在特定地域特定村落特定人家的民间信仰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而且由于有着积善成德、自成佛圣的榜样示范作用,更是受到特定地域特定村落特定人家刻骨铭心的敬仰和崇拜。正是这些遍及不同地域不同村落不同人家的民间诸神,才真正筑起了中国乡村民间信仰最基本也最普遍的神灵体系,同时也以遍及各个地域各个村落甚或各个家庭的宗庙和祖宗祠堂作为载体标识着作为实实在在心理预期、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的功能,并且借助每逢初一、十五的民间祭祀仪式和行为,更加强化了这种自成佛圣的意识,且刻骨铭心地嵌入普通人心理世界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