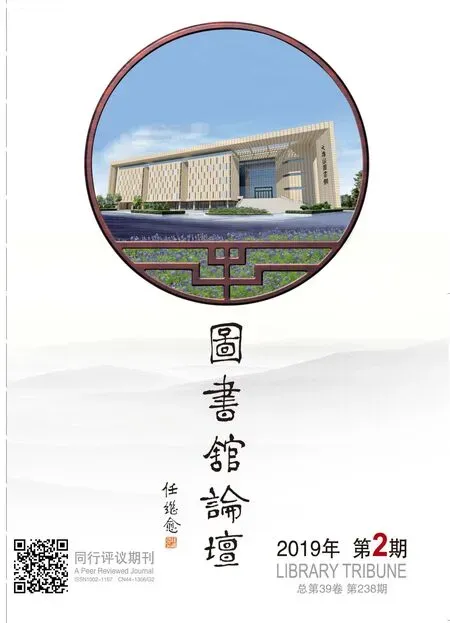粤诗文献整理与作品编纂*
杨 权
本文旨在对古近代以来的粤诗文献整理与作品汇编情况作简要的回顾,供希望了解此领域学术前沿的学者掌握相关信息。在展开讨论之前,笔者先对“粤”与“诗”两个概念作必要的说明。“粤”在本文的语境中是指今日的广东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属广东的部分(原钦州地区),其地域范围与旧时的“粤东”或“东粤”大致相当。“诗”是一种语言高度凝练且具有某种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只指诗,广义除诗外也包括歌、赋、词、曲、民谣等;在本文语境中,它只包括古体诗(古诗、楚辞体、新乐府等)与近体诗(律诗与绝句)。
1 古近代的粤诗创作与总集编纂
相对于华夏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与经济、文化向来发达的江南,在上古岭南曾是一个地方偏僻、人文不昌的蛮荒之域,在诗歌创作方面乏善可陈。进入中古以后,随着岭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与岭南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局面逐渐发生变化。唐代曲江张九龄的出现可谓粤诗立帜的信号,这位被誉为“文场元帅”的诗宗为岭南在诗坛争得了一席之地,也引领了粤海的百代诗风。自此之后,岭南诗家迭出,创作渐兴,唐宋出现邵谒、陈陶、孟宾于、余靖、崔与之、李昴英、葛长庚、区仕衡、赵必等名家,元则有罗蒙正、黎伯元等作手。经过数百载酝酿,元末明初,以“炉锤独运、自铸伟词”[1]例言的“南园五子”(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的崛起为标志,在岭峤形成了一个时间延绵长达数百载的地域性诗歌流派——“岭南诗派”。岭南诗派崇汉宗唐,诗风雄直,培育了特色鲜明的传统,推动了粤诗创作。继步五子,明代还出现了许多名家,如陈献章、丘濬、黄佐、区大相,如“南园后五子”(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如有“吾粤之太白”[1]例言之称的“牡丹状元”黎遂球、有“吾粤之少陵”[1]例言之称而被认为“直摩少陵之垒而拔其帜”[1]例言的陈邦彦、有“吾粤之灵均”[1]例言之称而被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认为开“粤东诗派”“先路”[2]274的邝露(三人并称“岭南前三大家”),如“南园十二子”(黎遂球、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邦瑊、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还有张穆、张家玉等。在这些标志性诗人的倡导引领下,明代粤诗创作出现繁盛的局面。清温汝能赞叹:“自唐以诗取士,海内多事声律。五岭以南,作者奋兴,日月滋广,遂蔚为奇观。明区启图尝荟萃诸集,编为《峤雅》,采择孔翠,芟简繁芜,自唐迄明,得五百余家,可谓盛矣!”[1]例言据笔者统计,自汉至元末,有诗作流传的粤诗人不到200家;而仅有明一代就有2200余家,考虑到文献散佚、资料匮缺等因素,实际参与创作的明代粤诗人还要多得多。
清代江苏诗人洪亮吉在《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中论及当时的粤诗创作:“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3]卷二这一说法虽包含有江南士人自谦的成分,却也反映出清代粤诗地位的提升。从宏观看,清代粤诗创作曾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形成于清初,标志是“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与梁佩兰崛起。清人林枫在《论诗仿元遗山体》之五写道:“岭南诗派屈梁陈,一代风骚鼎足身。”[4]1361与“岭南三大家”差不多同时或稍后的本地名家,则有梁朝钟、黄公辅、郭之奇、程可则、潘楳元、梁无技、方殿元、王隼、易弘等,以及以函昰、函可为首的华首台—海云系遗民诗僧群,以及与该系关系密切的和尚成鹫(论者认为“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5]586)。第二次高潮形成于乾嘉时期,以“岭南四家”(黎简、张锦芳、黄丹书、吕坚)、“岭南三子”(冯敏昌、张锦芳、胡亦常)、“梅诗三家”(宋湘、李黼平、黄香铁)、“粤东三子”(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等诗人集群出现为标志。这些诗家前呼后应,以出色的创作丰富与充实了本地诗歌文学的宝库。第三次高潮出现于近代,表现为岭南文人雅集普遍,诗社活动繁多。陈永正指出:“通过雅集活动,诗人互相交流切磋,品评高下,并培育了一批青年诗人。……还有一些外省入粤的诗人,也参与诗社的组织和活动,如越台诗社就是以‘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著名的诗人吴绮所倡议的,赵执信、潘耒、严绳孙、周在浚、徐釚、张尚瑗等一大批游宦诗人,都加入诗社唱和,通过这些创作交流活动,岭南诗家逐渐为中原、江左人士所知,也提高了岭南诗派在全国诗坛中的地位。”[6]这个时期的粤诗创作有不少人可称名家,如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黄节、朱次琦、康有为、陈伯陶、张其淦。而由嘉应黄遵宪发其端、新会梁启超张其帜的“诗界革命”,更是在诗坛掀起了一股变革巨浪,震惊全国。
岭南诗坛的振拔,诗人创作的兴盛,导致大量粤诗作品的产生。这些作品,除少部分因被收入作者的别集之中而得以存留之外,大部分未付剞劂,不仅不利于传播,而且随时都有散佚的可能。为使它们流于不坠,历代均有贤人雅士自觉担负起积聚、保存本地文学创作成果的责任,对它们勉力采辑,并纂为总集。
据文献记载,明区启图曾纂《峤雅》而未成。现存最早的岭南诗歌总集是明张邦翼编纂的《岭南文献》(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刊本)。入清后,粤诗创作的广泛普及为本地诗歌总集的编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骆伟《岭南文献综录》[7]著录,广东现存的本地诗歌或诗文总集数量不下200种,其中具总汇性质(即作品覆盖全粤)的有13种,分别是屈大均的《广东文选》(康熙二十六年广州三闾书院刊本),黄登的《岭南五朝诗选》(康熙三十九年),梁善长的《广东诗粹》(乾隆十二年达朝堂写刊本),陈兰芝的《岭南风雅》(乾隆五十年自刊本),刘彬华的《岭南群雅》(嘉庆十八年玉壶山房刊本),温汝能的《粤东诗海》(嘉庆十八年文畲堂刊本),凌扬藻的《国朝岭海诗钞》(道光六年狎鸥亭刊本),梁九图、吴炳南的《岭表诗传》(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顺德梁氏紫藤馆刊本),伍崇曜的《楚庭耆旧遗诗》(道光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南海伍氏刊本),陈堂等的《岭南鼓吹》(同治六年龙氏刊袖珍本),何藻翔的《岭南诗存》(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邬庆时、屈向邦的《广东诗汇》(民国三十年稿本),黄文宽的《岭南小雅集》(民国二十五年广州天南金石社铅印本)等。这类总集,除《广东文选》《岭南风雅》是诗文合集外,其余均为诗歌专集。若按朝代划分,属通代类的有《岭南五朝诗选》《广东诗粹》《岭南风雅》《粤东诗海》《岭南鼓吹》《岭南诗存》《岭南小雅集》《广东诗汇》八种,属当代类的有《岭南群雅》《国朝岭海诗钞》 《岭表国朝诗传》《楚庭耆旧遗诗》四种,属跨代类的有《广东文选》一种。
除上述具有总汇性质的集子外,在岭南还出现了各种形式不一的诗歌选集或合集。它们有的是郡邑之选,如明代陈琏的《宝安诗录》(已佚),祁顺的《宝安诗录》(已佚);明清之交蔡均的《东莞诗集》(已佚);清代陈珏的《古瀛诗苑》(钞本),顾嗣协、顾嗣立的《冈州遗稿》(康熙四十九年绿屏书屋刊本),罗元焕的《粤台征雅录》(乾隆刊本),言良钰的《续冈州遗稿》(道光二十三年松溪精舍刊本),黄登瀛的《端溪诗述》(光绪二十六年重刊本),彭泰来的《端人集》(同治六年刊本),张煜南、张鸿南的《梅水诗传》(光绪二十七年刊本),胡曦的《梅水汇灵集》(光绪十二年铅印本),邓淳、罗嘉蓉的《宝安诗正》(未刊),罗嘉蓉、苏泽东的《宝安诗正续集》(稿本);民国张其淦的《东莞诗录》(民国十三年东莞张氏寓园刊本),黄绍昌、刘熽芬的《香山诗略》(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温廷敬的《潮州诗粹》(稿本),王国宪的《琼台耆旧诗集》(民国七年琼山饶宝华校刊本)等。有的是家族之选,如清代陈恭尹的《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康熙三十三年黎延祖刊本),冯玉坚等的《冯氏家集诗》(咸丰十年冯光裕堂刊本),冯询的《冯氏清芬集》(光绪二年上海榷署重刊本),潘仪增的《番禺潘氏诗略》(光绪二十年刊本),黄映奎的《香山黄氏诗略》(稿本、光绪二十九年抄本)等。有的是师友之选,如清代李长荣的《柳堂师友诗录》(同治二年刊本)等。有的是闺阁之选,如近人黄任恒的《粤闺诗汇》(光绪刊本)。有的是方外之选,如清代徐作霖、黄蠡的《海云禅藻集》(道光、同治间刊本),周大樽的《法性禅院倡和诗》(康熙四十一年刊本)。有的是诸家合刻,如清代王隼的《岭南三大家诗选》(康熙三十一年自刊本),刘彬华的《岭南四家诗钞》(嘉庆十八年刊本),盛大士的《粤东七子诗》(道光二年刊本),伍元薇的《粤十三家集》(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诗雪堂刊本)。
为编纂这类集子,前贤们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受编纂能力与采辑条件限制,这些粤诗总集篇幅不大,所收作品有限。清人温汝能指出:“今所传《岭南文献》《广东文选》《五朝诗选》《广东诗粹》,或搜辑未富,或采取未精,均未足以尽其奇。”[1]例言以是之故,他殚精竭力,编成后出转精、作品更为丰富的《粤东诗海》,这是古代编成的最大粤诗总集。即使如此,也只有106卷,入集诗家1055人、作品数千首,远谈不上囊括历代岭南诗人创作的大部,更不说全部。
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古近代粤诗总集的编纂对岭南的文化建设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汇集了本地诗人的创作成果,保存了乡邦文学遗产。上述诗歌或诗文总集的编纂者对地方文献的征存大多抱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采辑,使众多诗人的创作逃过了损毁、散佚的厄运,从而虽然时历百载千年仍得以继续流传于世。总集所收作品主要来源于别集,而别集除常见刊本外,往往有数量众多的稿本存世。有些作品在入集前甚至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的。例如,凌扬藻辑《国朝岭海诗钞》卷九所收的王文锦作品、卷二十二所收的尹蓉作品、卷二十四所收的契清作品,便都属于这种情况。“至于诗歌别集已佚之作家,其作品更有赖总集以传。如清初吴文炜曾著《金茅山堂集》,今佚,《岭南五朝诗选》选其诗多达七十七首,数量较为可观,可以略窥原书之大概。”[8]至于未曾刊刻过别集的诗人,其作品更是因为总集的编成才得以流传的。
二是彰显了岭南诗家的创作实力,增强了粤人的文化自信。诗歌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集编纂向来是乡邦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长久以来,人们对岭南存有偏见,认为经济落后、人文不昌,其实“蛮荒”只是岭南的早期现象,后来局面已发生巨大变化。粤海诗坛不是没有大家,而是有许多大家,由于介绍宣传不够,因此不是广为人知,因为“岭海士习喜实行,耻浮名,故有著作等身、裒然成集者,亦取自怡悦,未尝辄付剞劂以问世”[9]。粤诗总集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低调,这些集子不仅凸显了岭南诗坛大家的创造实绩,也反映了一般诗人的写作水平,改变了外界对岭南的不正确认识,对粤人的自信起到了某种提振作用。
2 现当代粤诗文献的搜辑出版
不同时期编成的粤诗文献,不管是总集、选集、合集还是别集,不管是刻本、稿本还是钞本,都是岭南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非常值得后人珍视,因此自民国以来,便一直有留心乡邦文化建设的机构、团体与人士着力于对它们进行搜辑,并以不同形式出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粤港文化界、学术界的一批人士在著名粤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叶恭绰倡导下,以“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名义,系统搜辑、抢救粤人的珍稀诗文著作,编成丛书,成规模出版。1941编成《广东丛书》第一集,入集著作包括唐张九龄的《唐丞相曲江张文献公集》,宋余靖的《武溪集》(附黄佛颐的《武溪集补遗》),明黄公辅的《北燕岩集》、陈子壮的《礼部存稿》、黎遂球的《莲须阁文钞》、梁朝钟的《喻园集》等,多半为诗文集。受战争影响,丛书迟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全璧出版。1946年,叶恭绰自任主任委员,与简又文、陆丹林、黄荫普、徐绍棨等十余人组成《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筹划续编《广东丛书》。1947年《广东丛书》第二集编成,收入明薛始亨的《蒯缑馆十一草》等孤本,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紧接着叶恭绰等又辑编《广东丛书》第三集。后因内战,其事再难赓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一批高校学人有感于“岁月不居,屡经蠹鱼之蛀蚀;沧桑世变,每遭兵火之摧残”,“时愈久而版册弥湮,岁越迈而耆宿遂老”[10]编辑缘起,乃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指导下,成立《岭南丛书》编委会,黄灼耀、管林先后任主任委员,踵武前贤,分门别类,对以粤人诗集或诗文集为主体的地方文献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计划。项目开局便完成了十多种集子的整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被整理的文献包括南宋李昴英的《文溪存稿》(杨芷华点校,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明代孙蕡等的《南园前五先生诗》(梁守中、郑力民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欧大任等的《南园后五先生诗》(梁守中、郑力民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家玉的《张家玉集》(杨宝霖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陈恭尹的《独漉堂集》(郭培忠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邝露的《峤雅》(黄灼耀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梁佩兰的《六莹堂集》(吕永光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黎简的《五百四峰堂诗抄》(梁守中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宋湘的《红杏山房集》(黄国声校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维屏的《张南山全集》(陈宪猷等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995年版)等。这些粤人诗集或诗文集的出版对推动岭南文化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学者谢世与经费不足,整理出版工作未能持续下去。
除《岭南丛书》外,其他当代出版的丛书也收有粤诗文献。比如,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主持整理的《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入有清释函昰的《瞎堂诗集》,释今释的《徧行堂集》(正、续集),释成鹫的《咸陟堂集》(初、二集),2006-2008年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与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第二辑共分六册,分别是《清初岭南洞宗高僧三种》(中有释二严的《啸楼诗集》与释一机的《涂鸦集》),释函可的《函可和尚集》(中有《千山诗集》),释弘赞的《弘赞和尚选集》(中有《木人剩稿》《鼎湖山庆云寺外集》),释道忞的《木陈和尚选集》(中有《布水台集》《北游集》),释今无的《今无和尚集》(中有《光宣台集》),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并附释愿光编《法性禅院倡和诗》,均于2017年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近一二十年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库》,所收作品虽以专著为主,但间中亦有粤人的诗集或诗文集,黄节的《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1998年版)便是一例。还有一些重要的粤人诗集或诗文集经学者整理后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如刘斯翰校注的张九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玉宏校注的张九龄《曲江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熊飞的《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欧初、王贵忱主编的《屈大均全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香白点校的翁万达《稽愆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志辉整理的余靖《武溪集校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陈永正整理的《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经修订后更名为《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林子雄点校的《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黄国声主编的《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严志雄、杨权点校的释函可《千山诗集》(台湾“中央研究院”2008年版),等等。
近年广东文化学术界在地方文献汇辑出版方面的最重大举措是推出《清代稿钞本》(2007-2014)与《广州大典》(2008-2015)两部大型丛书。桑兵主编的《清代稿钞本》于2006年立项,是国家清史工程框架内规模最大的地方藏文献发掘抢救整理项目,也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历史未刊珍稀稿本、抄本出版工程,已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选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抄本和少量稀见刻本为影印对象,到2017年共编集出版八辑400册,所收内容多为清代文献,其中有不少是诗歌文献。以初编为例,收有诗集或诗文集144种,其中包括潘有为的《南雪巢诗钞》、何若瑶的《海陀华馆诗草》、何巩道的《越巢诗集》、唐大经的《舫楼诗草》、陈华封的《复斋诗钞》等数十种粤人诗集。续编中的诗集与诗文集作者,有南海招衡玉、叶官桃、陈如龙、谢兰生、朱次琦、梁达卿,番禺陈子瑞、梁松年、陈澧,顺德马肇梅、邓华熙,香山刘世重、黄培芳,新会黄炳堃,鹤山吕冠雄,东莞张其淦等16人是粤人。
《广州大典》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2005年5月启动,由陈建华、曹淳亮任主编,已由广州出版社出齐。丛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文献为基础,所收均为旧时广州府籍人士(含寓贤)的著述及穗版丛书,入选文献下限为清宣统三年(1911),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则以清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今中山、珠海)、三水、新宁(今台山)、新安(今深圳)、清远、花县(今花都),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今台山)为界。该书集部共123册,收录文献1294种,有相当部分是粤人诗集或诗文集。
值得一提的大型丛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影印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填补了学术界此前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出版的空白,共收入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分800册出版,2010年全部出齐。丛书提供了大量足资学术参考的原始文献资料,其中有很多是首次面世的善本、稿本、孤本。这部大型丛书也收录有粤诗文献,如释道忞的《弘觉忞禅师北游集》、释函昰的《瞎堂诗集》、释函可的《千山诗集》、释今无的《阿字无禪师光宣台集》、陈子升的《中洲草堂遗集》、程可则的《海日堂集》、屈大均的《道援堂诗集》 《翁山诗外》、陈恭尹的《独漉堂诗集》、张维屏的《听松庐诗钞》《松心诗集》《松心诗录》《松心杂咏》、黎简的《五百四峰堂诗钞》、李符清的《海门诗钞》、宋湘的《红杏山房诗钞》《红杏山房试诗》《红杏山房试帖诗》《丰湖漫草》《丰湖续草》、李黼平的《著花庵集》《吴门集》《南归集》、叶衍兰的《海云阁诗钞》、李文田的《李文诚公遗诗》、康有为的《康南海先生诗集》、梁鼎芬的《节庵先生遗诗》。
上述各种丛书及单行本的出版,既给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方便,也为当代大规模的粤诗总集的编纂创造了有利条件,功莫大焉。
3 《全粤诗》的编纂出版
岭南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与发育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一方面是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其母体文化的一般品格;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地自然、社会因素乃至海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岭南的地貌、气候、物产、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与内地均有明显的不同,粤诗产生于这样的水土之上,自然难免会被打上明显的地方烙印,表现出不同于他者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使对粤诗作品的系统全面汇编成为了必要;而当今的文献资料利用条件,又使这种系统全面汇编成为了可能。于是广东学术界在最近十多年便有了在前人的基础上编纂一部超大规模的诗歌总集《全粤诗》的盛举。
《全粤诗》原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规划项目,位列“七全一海”(《全元文》《全宋文》《全宋诗》《全明戏曲》《全明文》《全明诗》《全粤诗》《清文海》)之一。其编纂任务由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承担,汉代至明代各卷由陈永正主编,清代各卷由杨权主编(陈永正为荣誉主编)。项目在世纪初年启动,前后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商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的教师、学生与研究人员参与过编纂工作。2015年清代部分的编纂计划经过整合,成为是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岭南诗歌文献整理与诗派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岭南诗歌作品全编”)。《全粤诗》是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大陆唯一在编的大型区域诗歌总集,堪称广东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其编纂目标是把迄今存世的所有古近代粤人诗作悉数汇编入集,而不论朝代、作者与作品的体裁、题材、内容与载体。其编纂过程如下:先从文献综录一类的工具书与各种图书馆馆藏目录入手,辅以计算机检索手段,摸查粤人诗集或诗文集的版本信息,形成整理总目。在全面、系统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以复印、拍摄、下载、誊抄等方式采集各图书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私人藏家的收藏资源,或者以购买的方式获得已出版的图书资源,建立原始文献数据库。选定合适的工作底本来进行标点校勘,原则上尽量以原刊本/抄本为底本,近人、今人的整理本、覆刻本可作底本但不能径作底本;如果原刊本/抄本属善本,复制成本过高,或者收藏单位不让复制,则用近人整理本为底本,然后依原本复校,还原本来面貌。别集整理工作完成后,再从各种总集、省府州县志、山志寺志书院志、家乘族谱、金石碑刻及书法绘画作品中搜辑、采集无集作者的零星诗作或有集作者的集外诗作,并按照作者生活时代的先后把它们收入到总集之中。原则上“竭泽而渔”,所知必采,所见必录,不过整理对象只限于粤籍(包括落籍)诗人之作,寓粤人士之诗作不在采辑之列;整理的时间下限为宣统三年(1911),部分曾在清朝生活的重要民国诗人之作亦在整理之列。对每位诗人都提供一篇文字简明扼要的小传,俾让读者了解作者籍贯、生卒、科举、宦迹、创作、著述等。
《全粤诗》有很高的质量要求,不仅要求作品齐全、内容宏富,而且要求版本合理、文字精审。例如,新会陈献章诗,以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刻《白沙子全集》为底本,但参校明弘治九年吴廷举刻《白沙先生诗近稿》、明万历元年何子明刻《白沙先生全集》、明万历九年何上新刻《白沙子全集》九卷本、清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其中《白沙先生诗近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为罕见版本。整理者还从《陈献章诗文补遗》《岭南五朝诗选》《广东诗粹》、《石斋八月稿》《香山主人遗草》等总别集,《颂斋书画小记》《广东书画征献录》《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中国书画图目》《书法图史》《鹤山诗词四百首》诸书及明嘉靖《广东通志》等13种方志中辑出了不少集外诗,所收诗作比内容向称齐全的孙通海点校本《陈献章集》多56首。又如,揭阳翁万达诗,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道光约心轩版《思德堂诗集》为底本,诗作比通行的翁氏《稽愆诗》多115首。在《全粤诗》中,有不少诗作通过特殊管道采集而得。例如,收入卷三百九十三的番禺何其伟诗录自明天启版《鷇音集》,书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连《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未著录的海内孤本;收入卷四百八十三的区大伦诗,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所藏清初善本《区罗阳集》为底本整理;收入卷二百五十四的兴宁张天赋诗,以兴宁县图书馆藏明嘉靖孤本《叶冈诗集》为底本整理;收入卷五百六十九的东莞王猷诗原无刻本,以在其族内流传的抄本《壮其遗集》为底本整理;收入卷七十一的东莞陈琏的诗作,以香港学海书楼藏清康熙六十年万卷堂陈氏后人重刊的《琴轩集》为底本整理。
《全粤诗》是一项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耗费很多时间才可能完成的“巨无霸”工程。广东学术界不计成本编成这样一部超大规模的诗歌总集的原因在于:
首先,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发掘、抢救与保护岭南文化遗产的要求。粤籍诗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歌作品。它们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是研究诗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往来交游、创作活动与文学成就等的珍贵资料,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可为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民生、宗教、风俗等提供丰富的材料。由于水火虫蠹与兵燹政禁等原因,许多作品已散佚不存;而随着时间流逝,还会有更多作品面临损毁危险。只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全面系统地汇编,才有可能实现对这些作品进行有效的保存,使之流传久远。
其次,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广大社会读者的阅读利用要求。古近代粤籍诗人的创作一方面数量众多,一方面载体分散,想系统收集极为不易。出于种种原因,一些为公私所收藏的珍稀集子,一般读者很难接触,根本无法寓目,更谈不上利用。而动用学术界的集体力量,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超大规模的粤诗总集,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社会读者的阅读需求;而现代图书馆的收藏规模、检索手段与利用条件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再次,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摸查岭南的文学家底、展示粤诗人成果的要求。粤诗在唐代就已竖其帜,自元末明初到清末民初曾有过长达六七百年的创作繁荣期;然而现代的人们为视野所限,对历史上粤诗人的创作情况多无清楚概念,并不十分了解前贤有过什么样的创作,数量多少,质量怎样,成就多大,影响多深,分布多广,地位如何,等等。而编成《全粤诗》,历代粤诗人的创作情况便能获得系统展示。在从事此项工作的过程中,一些罕见的珍稀集子有可能会被发现,一些被忽略的杰出诗家也会“浮出水面”。
最后,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深化岭南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近年在各地纷纷兴起、此呼彼应的地域文化研究,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研究,重视从文献、史料、民俗、方言等元素入手,原因在于这些元素最能反映各地区的文化特点。粤诗不仅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最精粹的部分,编成《全粤诗》,将为岭南文化研究提供非常丰富也非常具体的文学素材,从而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
《全粤诗》的编纂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汉代至明代各卷在2008年前已编纂完成。该部分共有804卷,收入诗家2500余人,收录诗作6万多首,共分26册出版。至2017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2册,最后4册出版工作在2018年完成。清代各卷的编纂工作还在进行中,编纂团队已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到粤人诗集或诗文集1127种,总集40余种。这些集内作品已大致整理完毕,零散的集外作品则还在采编中。《全粤诗》的编纂工作将在2020年完成,全书字数在5000万左右,是一部篇幅超百册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