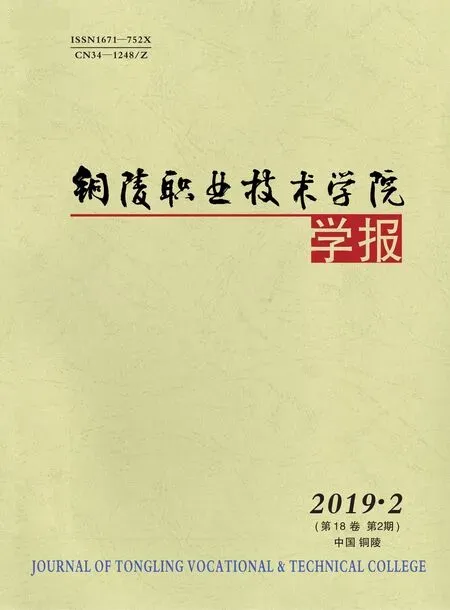雷州半岛石狗崇拜现象起源研究
郭伟精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雷州半岛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是古代土著文化,楚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汇地,多元文化的相汇共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雷州文化,其中最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当属于石狗文化。石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石狗崇拜,它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石狗的崇拜。在古代,人们用当地最常见的花岗岩雕刻出简陋的狗模型,并且在石狗面前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祈祷石狗能够实现自己内心的愿望。一直到今天,人们对石狗的崇拜仍然是有增无减,形状和功能各异的石狗雕像遍布整个雷州半岛,其数量庞大而不可数;每逢初一十五,人们都会举行石狗祭拜仪式,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有不少人给新生儿取“狗儿”、“狗仔”、“狗娃”等小名,给小孩戴狗仔帽、穿狗弄衫等,寄希望于石狗神灵能够保佑自己的小孩健康成长。这些现象都体现了石狗崇拜意识已经成为当地一种文化基因,它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探明雷州半岛石狗崇拜现象的起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雷州半岛的自然地理环境,百越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们对雷州文化的理解,充分领略雷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地理环境产生论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不同的气候类型会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性格,“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1]东南沿海地区的百姓靠海吃海,世代以海为生,因此妈祖庙和龙王庙的数量众多,常年都是香火旺盛。这些都体现了客观物质世界对人思想意识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样,外在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古代雷州半岛土著居民石狗崇拜观念产生的重要催化剂。雷州半岛背靠大陆,三面临海,纬度低,常年湿热多雨,森林湖泊密布,自然地理环境比较恶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2]《隋书·地理志》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3]887在这种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下,雷州半岛当地土著居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其所管八州,俗无耕桑,地极边远,近罹盗扰,尤甚凋残。”[4]其中宋代《太平环宇记·岭南道十二》中的《雷州》就直接记载了当时雷州半岛农业种植的实际状况:“州在海岛上,地多沙卤,禾粟春种秋收,多被海雀所损。相承冬耕夏收,号芥禾,少谷粒。”[5]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狗作为人类最早进行畜养的动物,无论是在先前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还是在后来漫长的种植农耕社会,它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不可或缺的帮手。狗的嗅觉非常发达,它对气味的敏感程度远超人类,它能够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快速捕捉到危险的信息,从而提前规避风险。其次,狗还拥有非常快速的奔跑能力,因此经过训练的猎犬能够快速追踪并且捕捉到猎物,这些猎物成为当时人们最重要的肉类来源。狗身上所具有的这些技能对当时还是过着刀耕火种和渔猎为生的土著居民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个体乃至整个部族的生存和延续。此外,在后世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狗在人类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广。雷州半岛旱涝无常,灌溉技术落后,因此旱灾频发,狗被人们看成是可以召唤雷神来为人间降雨的神兽。人们通过抬着披红挂彩的石狗游街,用鞭子抽打石狗,或是穿着特制的狗皮大衣在石狗面前举行各种各样的巫术表演活动等方式来达到“石狗求雨”的目的。古代雷州半岛森林湖泊密布,野兽众多,狗被人们当成是可以看守庄稼,看守田园的守护神。人们把石狗雕像放在门口,路边,水井旁,出海口,渴望石狗神灵能够保佑一方平安。在原始巫术的加持下,石狗更是被人们当成是地下坟墓的看守者和引导人们走向佛教中西方极乐世界的引路犬。总之,狗在古代雷州半岛土著居民生活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正是古代雷州半岛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严峻的生存环境导致狗在当地土著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雷州半岛石狗崇拜现象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图腾崇拜产生论
图腾崇拜是古代雷州半岛众多土著部族固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为后世石狗崇拜现象的产生和扩散提供了便利的传播条件。图腾是一个部族的象征物,是部族的族徽,同时也是一个部族最早期的崇拜对象。“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阿尔贡金人奥季布瓦族的方言totem的音译,本意是指“他的亲族”或“他的氏族”。在阿尔贡金人的文化中,图腾的含义是表示这个图腾中所代表的神和他是同属一个种族谱系的,所以神会用神秘的力量来保佑他或是祝福他。因此图腾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同时还有宗教信仰的意义。图腾崇拜是古代雷州半岛众多土著部族固有的传统,而它们每一个部族都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信仰图腾,这一点可以从它们的族名中看出来。《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3]1831明庄元贞《雷祖志》:“州(雷州府)旧有猺、獞、峒、獠与黎……”[6],“蜒、獽、猺、獞、峒、獠”都是当时常见的动物名称,“起初俚人以狸为图腾,僚人以獠为图腾,僮人以獞为图腾,傜人则以犬为图腾,所以过去他们的部族的名字‘狸、獠、獞、猺’都加犬字旁,这就是他们图腾的标志。”[7]从现今仍然存世可见的形态各异的石狗雕刻形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雷州半岛上土著部族固有的多元化图腾崇拜的传统。早期的石狗雕刻形象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呈现出比较明显而统一的“狗”的形象,而是在其身上掺杂着多种动物特征,呈现出“多兽形”的形象。在现在雷州半岛下面广大的农村中仍然散落着大量的 “半猫半狗形、半青蛙半狗形、半猪半狗形,半牛半狗形”等多种雕刻形状的石狗,其背后传达出雷州半岛土著先民朴素的信仰观念:猫能抓老鼠,从而可以保护宝贵的粮食;青蛙肚大多子,能够让人产生多子多福的想象;牛可以耕田劳作,它是部落最大的财富,可以和猪一起为部落成员提供为数不多可以吃肉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朴素的信仰观念指导下,它们才产生多元化的图腾信仰风俗。除了狗之外,猫、青蛙、牛和猪等动物都曾经是当地土著部族图腾崇拜的对象。在现雷州市附城镇榜山村雷祖古庙中仍然保存着一块战国时期的石碑,石碑前后都刻有图案,在它的正面刻的是一副牛图案,背面刻的是一副鳄鱼图案。后世的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雷州半岛上以不同的动物为信仰对象的两个部族进行会盟的标志物,因此将其称之为“会盟碑”,其性质类似于唐代中原王朝与吐蕃政权进行结盟的“唐蕃会盟碑”。牧野在《雷州历史文化大观》一书中说:“公元前771年楚成王熊恽‘受命镇粤’及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熊商灭越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中原部落南迁的社会背景。大约在这一时期,生活在扬子江的‘鳄’部落南迁雷州。经过一段时间的民族冲突与交流,‘牛’、‘鳄’部落最终和解融合。此碑是两大部落‘会盟’时的标志物。”[8]
在多元化图腾信仰的背景下,雷州半岛上的土著部族对狗的崇拜还经历了一个信仰统一的过程。正如汉族以龙为图腾,蒙古族以狼为图腾,藏族以牦牛为图腾一样,俚人是以狸为图腾,僚人是以獠为图腾,而傜人则是以犬为图腾,这些部族在崇拜多种动物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对狗的崇拜,这些多兽形的石狗雕像就反映了当时人们信仰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对狗的崇拜能够逐渐取代对其他动物的崇拜呢?追究其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汉人大规模地南迁促使民族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以及狗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三种主要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对狗的图腾崇拜逐渐取代了对其他动物的崇拜。历史上,中原地区常年连绵不断的战乱曾经给雷州半岛带来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给雷州半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跟文化,同时还极大地推动了多民族融合的进程,促使雷州半岛上的土著民族逐渐走向汉化。在多民族逐渐融合和同化的过程中,当地土著民族石狗崇拜的风俗逐渐被新迁入的移民群体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再加上狗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对“狗”的图腾崇拜逐渐从单一部族崇拜变成是全民崇拜。随着当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日新月异,宗教崇拜意识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但是一直到今天雷州半岛上的广大百姓仍然保留着对狗的崇拜传统,而早已不见对其他动物进行崇拜的痕迹。这表明石狗崇拜观念早已变成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并且在未来仍将持续不断地流传下去。
三、槃瓠起源说
“槃瓠”又叫“盘瓠”,槃瓠是古代人对犬(狗)的一种尊称。无论是在岭南百越民族的传说中,还是在历代官方正史中,槃瓠不仅是狗的祖先,而且也是百越民族的祖先。槃瓠生百越,百越变南蛮,百越和南蛮都是中原汉族对我国南方广大少数民族的称呼,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在先秦时期称之为百越,汉以后称之为南蛮。颜师古在为《汉书·地理志》做注时引臣瓒言:“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9]1669后汉服虔为其做注时说:“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9]1669《隋书·南蛮传》中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3]1831南蛮民族祖先的源流是槃瓠,这种说法早在《山海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10]
无论是“犬封国”还是“犬戎国”,它反映的应当都是古代以“狗(犬)”为图腾信仰的部族。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首次在《风俗通义》中详细地记载了“槃瓠生南蛮(即百越)”的过程,其书虽在宋以后已经逐渐散佚,但是其内容却被记载在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11]2829
唐代李贤为其做注时明确指出:“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也。 ”[11]2830《风俗通》即是应劭的《风俗通义》。清代卢文弨在《群书拾补》中说:“《风俗通义》隋唐志皆三十一卷,录一卷,至宋始作十卷,盖亡其二十一篇矣。”[12]这说明《风俗通义》一书在隋唐时期尚有留存,由此才得以在当时的隋唐志书中有所记载,这表明唐代李贤说的话是可信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的记载虽然有些夸大甚至荒诞,但是它仍然是对当时百越民族的客观描述:以狗为信仰的南方广大百越民族(南蛮)是黄帝的后裔,他们是远古炎黄部落下面的一个分枝,主要生活在南方人迹罕至的高山崇岭中,其民风彪悍作战勇猛,喜欢穿用草木编成颜色鲜艳的奇装异服,说着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话,有着与中原地区相迥异习俗。正因为应劭这段话是最早对古代以狗为崇拜对象的百越民族部落的生动描写,因此才会被范晔引用到《后汉书》中,作为官方正史而流传于世。晋代干宝在《搜神记》中描写槃瓠乃是从一个老妇人的耳朵中挑出来的: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蓠,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 ”[13]
在魏晋时期,当时的人们误以为只有长沙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才是槃瓠的后代,因此在文学史上诞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武陵蛮”典故。干宝在《晋纪》中记载:“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槃瓠凭山阻险,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槃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11]2830南朝宋盛弘之在《荆州记》中记载:“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11]2830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沅水》中的说法也跟他们遥相呼应:“水又迳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盘瓠者,髙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其狗皮毛,嫡孙世宝录之。”[14]干宝和盛弘之等人的记载从侧面证明了“槃瓠生南蛮”的说法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在此之后,槃瓠之种已经从长沙武陵蛮扩大为代指整个南方地区的百越民族,在后世文人的眼中,南方百越皆是槃瓠之后。槃(盘)瓠神话在我国南方的瑶、苗、黎、畲等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例如壮族有《龙王宝》、瑶族有《盘王哥》、苗族有《盘瓠与辛女》、黎族有《五指山传》和《狗和公主结婚》,这些民族都把槃瓠看成是它们民族的始祖。因此百越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槃瓠”。
雷州半岛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雷州半岛就属于岭南百越民族的范围。清嘉庆 《雷州府志》载:“(雷州府)唐虞之时属南交,夏称扬越之南……古为百越所居。”[15]南交即是南方交趾郡的别称,泛指整个岭南地区。《尚书·尧典》中说:“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16]17宋蔡沈《书集传》:“南交,南方交趾之地。”[17]清人孙星衍引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为《尚书》做注时说:“东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独不言。或古文略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趾不疑也。”[16]17《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尽少康之后也。”[9]1669上述材料表明雷州半岛自古就属于南方交趾郡的范围,同时也是属于岭南百越民族分布的范围。明代庄元贞在《雷祖志》中记载:“州旧有猺、獞、峒、獠与黎……”[6]这表明一直到明代,雷州半岛上仍然还保留着大量的俚、僚等土著民族,它们既是岭南百越民族的后代,同时也是槃瓠的后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雷州半岛上的人民仍然保留着尊狗尚狗的风俗就不足为奇了。
四、雷祖诞生说
雷神文化与石狗文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原来“槃瓠生百越”的基础上,雷祖诞生的神奇故事进一步推动了狗的神化进程。雷州半岛三面临海,纬度低,气候炎热多雨,一年四季都会出现打雷的现象,当地百姓经常会在地上捡到类似石墨的陨石晶体,再加上当地极富神奇色彩的雷祖诞生故事,因此雷州半岛经常被人们称之为“雷神的故乡”。狗与雷神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沈既济写的《雷民传》:“尝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狗,以耳动为获数,未尝五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旁,是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卵甲为豪族。”[18]宋人李昉在 《太平广记·雷二》中引用了唐人房千里在《投荒杂录·陈义》中的记载,其内容与沈既济的《雷民传》有大同小异之处。明庄元祯《雷祖志》:“州西南七里,有村曰白院,其居民陈氏,讳鉷者……业捕猎,养有九耳异犬,耳有灵机。每出猎,皆卜诸犬之耳,一耳动则获一兽,二耳动则获二兽,获兽多寡,与耳动之数相应,不少爽焉。至陈朝太建二年辛卯九月初一日出猎,而犬之九耳俱动。陈氏喜曰:‘今必大获矣’。鸠其邻十余人,共随犬往。至州北五里东,地名乌仑山,有丛棘密绕,犬自晨吠至日仄,无一兽出。猎人奇之,伐木而视。犬挖地开,获一大卵,围有尺余,壳色青碧,众俱不知为何物。陈氏抱而归家。次晨,乌云忽作,风雨雷电交至。陈氏大恐,置卵于庭,盛以小棹,遂为霹雳所开,内出男子,两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陈氏将男子与卵壳享(奏)明州官,官收卵壳寄库,男子交还陈氏养育,名曰文玉。”[6]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六《神语·雷神》中对狗与雷祖的故事也有记载:“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庙。神端冕而绯,左右列侍天将,一辅髦者捧圆物色垩,为神之所始,盖乌卵云。……《志》称:陈时雷州人陈鉷无子,其业捕猎,家有九耳犬甚灵。凡将猎,卜诸犬耳。一耳动,则获一兽,动多则三四耳,少则一二耳。一日出猎,而九耳俱动,鉷大喜,以为必多得兽矣。既之野,有丛棘一区,九耳犬围绕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径尺,携以归,雷雨暴作,卵开,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尝入室中乳哺,乡人以为雷种也,神之。”[19]
雷祖诞生的神奇经历让在平时里看似普通平常的动物“狗”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狗不仅成为雷祖座下独一无二的神兽,同时也成为当地百姓心目中的“灵兽”,“祥兽”和“瑞兽”。唐以后,后世历代朝廷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雷州半岛上俚僚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展现中央王朝的权威,对雷祖陈文玉进行了多次册封和加冕。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封陈文玉为“雷震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封陈文玉为“灵震显明昭德王”;泰定二年(1325年),元顺帝再次封其为“神威刚应光化昭德王”;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又封其为“宣威布德之神”。有史可查,历代中央王朝对雷祖陈文玉的册封多达14次。在朝廷不断地提高雷祖地位的同时,狗作为神兽的地位也随之日益水涨船高,这些活动在民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石狗崇拜的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只要有雷祖像的神庙,旁边必定也会竖有狗神的神像。因此,在后世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石狗崇拜意识随着雷祖文化的扩展而不断扩展,最终与其一起成为雷州本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结语
石狗文化是雷州半岛最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土著文化,同时也是岭南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石狗崇拜现象是雷州半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现象,探明雷州半岛石狗崇拜现象的起源,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雷州半岛的地理环境,充分挖掘隐藏在其背后的图腾文化、槃瓠文化和雷神文化,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加强对石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总之,石狗文化是雷州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跟物质财富,我们既要努力去保护它,同时还要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以此获得经济和文化上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