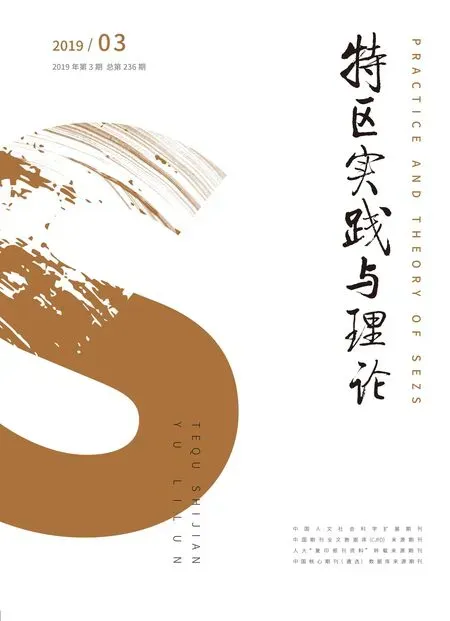国民党改组后的基层组织政治生态考察
罗 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与此相应,有关“政治生态”的研究方兴未艾,在概念界定、体系建构以及形成路径等方面有不少成果研究,让我们对其有了基本的认知。
要对一个政治组织的政治生态有个总体性把握,须从两大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政治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二是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状态。依此考察改组后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政治生态,可对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治理基础加以理性分析,虽说历史已告知我们国民党政权的结局,但适当地回顾与反思,方能以史为鉴。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国民党改组前基层政治生态背景及鹄的
20世纪初的中国基层政治,因传统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崩解及国家力量的弥散化,而呈“一盘散沙”状态,其表现就是军阀、土匪滋生,社会整合力量缺失,急需新的权威来重建秩序。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唯有自身组织过硬才能扭转政治衰朽的局势。“乱世”带给国民党的是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难逢的机遇。毕竟在一个弥散型、混乱不堪的基层社会里重建秩序并塑造起良好的政治生态并不容易,但换个角度,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被恰当地完成,必然能为其奠定深厚的合法性基础。
事实上,国民党也并非没有为此作出努力,1924年的改组活动就是实例。改组之前,国民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组织建设很不完善。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意识到党务革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当时俄共在宣传、组织体制上的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中的出彩表现,使其下定决心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力求将其“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纲领的政党,并用政党的力量改造国家”。①周晓辉:《“以俄为师”背景下国共两党早期党章建设及其比较研究》,《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1期。
此次改组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以俄共为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色在于,既能维持严密的组织内聚力,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正是国民党艳羡的。改组得到俄方大力支持,俄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派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进行指导,中国共产党也让骨干分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承担起不少改组的执行工作,在“中体俄用”①所谓“中体俄用”,即“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孙中山表示,此次“师俄”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学习的范围被限定在组织技术层面。的指导思想下,国民党广建基层组织,分化组织层级和功能,加深系统化建设。
从制度层面来看,此次改组为其“党国体制”的形成和运转奠定了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内容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主要部分组成,基本照搬俄共的章程,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4页。在组织网络的布局上,仿照俄共基层组织“支部”设立了区分部,将组织机构的触角突破了传统的县级政权,在县党部下面设置了区党部、区分部,借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得以大量且迅速地建立起来,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8000余处。1927年初区分部增加到一万余处。③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3年,第100-101页。不少人认为,此次改组将国民党塑造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现代化政党,然而制度设计的优化并不等于政治实践的提高,已有研究表明,国民党“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未能得其组织内蕴”,④周晓辉在比较研究国共两党早期的党章建设中发现,二者虽说均以俄共党章为蓝本设置起基层组织,但在实践中,国民党基层组织不健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考察国民党改组后的基层组织政治生态,可对这一观点加以佐证。
二、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内政治生态:弱意识形态下的党员吸纳和组织空转
政党内部政治生态能够决定其内聚力强弱,而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内部政治生态还会深刻影响到国家、社会体系的政治生态,决定其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社会治理的根基。国民党改组后基层组织内部的关系结构和政治运转,须从思想意识、制度设计及组织运转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
(一)意识形态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却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魅力的政党。虽然其党员数量在北伐期间数倍暴增,但忽视革命信仰的做法,使各派野心家和政客乘机加入,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⑤[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
有学者通过研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内容、功能发挥和发展变化,将其总结为“低势位意识形态”,⑥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 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政纲,聚焦于社会政治秩序的设计,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的最高纲领,因而其意识形态功能是低层次的,无法满足一般党员和群众的信仰要求,缺乏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⑦杜生权:《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低势位”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有学者发现,与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呈现弱势和重军队政府轻视党务的特点,导致三民主义无力渗透到基层。⑧李庆华、李玉英:《论民国时期(1924-1949)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此外,当时的国民党党员自身也对其意识形态不甚了解。“低势位”带来的影响无疑是负面且巨大的,意味着国民党对外无法主导、引导社会思潮的流变,甚至在社会领域里丧失话语权;对内则是内聚力不足和影响力低下,这极大地反映在党员吸纳过程中,以及党员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上。
(二)党员吸纳
政党对其成员的吸纳,或依靠价值观、意识形态,或通过提供现实的利益。革命党以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新政权为目标,成员要承担生命、财产等危险,如果个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与政党没有共识、以及这种共识没能达到人生信仰高度的话,是很难被吸纳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可带来现实的权力和利益,此时入党就多了一重个人发展的考虑。国民党不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魅力的政党,不少人加入其中首要考虑的是现实利益。追求个人价值无可厚非,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规训”申请者及成员,让个人利益符合组织目标。
然而,国民党的党员吸纳却极不规范,未能秉承俄共在这方面的严谨性。比如,俄共要求志愿入党者须经过一定的预备期,用来考察个人品质和意识形态信仰,防止思想不端、动机不纯者混入组织。而国民党的入党门槛至低、考察程序极简,“集体入党”、“强迫入党”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吸纳党员的方式,引发国民党党内政治生态混乱、恶化,基层组织无以发挥“战斗堡垒、革命基石”的作用。与入党门槛低下相对应的是脱党的随意,组织权威荡然无存。总之,国民党党内成员三教九流、乌七八糟,各怀心思和利益追求,不仅损坏国民党的形象和整合力,也使党内的政治生活和行为充满变数。
(三)组织空转
从顶层设计来看,国民党的组织触角突破了传统的县级政权,在县以下设置了区党部,区分部之下还设立了党小组,以深入到各个团体中去。然而这些均未能达到预期的“组织绩效”。表面上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数量得以迅猛增长,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8000余处。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①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3年,第100-101页。但其组织覆盖面仍然不够,因为建立了基层党组织的农村只占25%,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9页。而且这些基层组织大都有名无实,陷入空转,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党务经费紧缺。组织的运转需要投入不少经费和人才,人才尚且不论,单是党务经费就令其深陷困境。以广东省为例,当时国民党中央给各县党部规定的经费是每月270元,而县长每月的薪资是400多元,一县党部整个机关的经费还远不及县长一人的薪资。因经费有限,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放30元生活费外,其余委员和部长都不支薪,即便如此,县党部也没有余钱作为活动经费。大多数党务人员只得另谋生计,工作方面敷衍了事。县党部委员大都分散居住于方圆几十里的农村,“赴会”耗时耗力又耗钱,对于“每周必须开会一次”的规定,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③刘启能:《各县党部经费问题》,《现代青年》1926年第5期。
其二,组织管理混乱。这从国民党党籍管理上可见一斑。不少基层党部为完成上级摊派的发展党员任务,将旧党员重新登记一遍;有的党员因党部久不发党证而再登记入党一遍;对于变换工作生活地点的党员,也没有机构去及时办理党籍转移登记手续。一些县区党部连党员名册都没有。组织空转、管理混乱,使国民党党员生出“找不到组织”的感受,就党内政治生态而言,党员之间缺乏交流,无法形成亲密合作的关系,党员对党组织缺乏归属感和信任感。基层党员对组织残存的一点念想就是伺机捞点好处,这种组织是经不起丝毫冲击的。
三、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外政治生态:在党政团绅缠斗中沦为附庸
(一)党政之间缺乏耦合
国民党号称以“党治”为核心,改组后还形成了与政府系统双轨并进的权力结构,事实上却无法有效影响国家机制,在党政关系上完全处于下风,成为王奇生所言的“弱势独裁政党”。
最初的党政关系模式是在中央一级实行直接党治,在地方则不允许党部干政。后来,1926年10月通过的《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议决案》和11月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将省政府置于国民党中央、省委及中央政府三重指导监督之下。这个时期各地一般先设立省党部,后成立省政府,省党部对省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作用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到县一级,党政关系大致呈现三种模式:以党统政、党政制衡和以政治党,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党部凌驾于政府之上,但这种关系模式没能稳定下来。
1928年8月颁布的《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规定如果各级党部认为同级政府之举措不合理,可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从此党政制衡体制替代了以党领政的格局,地方党政之间唯一链接是中政会,地方党部不能干预同级政府。地方政府集财政、民政、教育、建设和人事等大权于一身,机构庞大;而地方党部的职责被限定在组训党员、宣传党义、引导民众和管理社团等方面,政事方面概不能问,稍有不慎就落下侵权干政的口实。国民党党章规定“地方党部监察委员会”具有“稽核同级政府施政方针及政绩之权”,政府系统则故意抵制来自党部的监督,使其丧失监察权。再加上地方党部因为经费仰赖政府拨发,惟有仰承其鼻息、萎缩行事。与此相应,基层党务人员地位低下。1929年,驻江苏东海县的独立第四旅旅长谭曙卿擅捕该县党部执委,并枪杀其中两人,此事激起全国党务人员公愤,他们一致要求严惩凶手,但蒋介石始则漠视,继而释放凶手,使地方基层党务人员心寒气短。
基层党、政之间缺乏耦合,关系极度失衡,弱势的党部沦为政府的附庸。这种畸形的外部政治生态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行为选择。
(二)派别斗争复杂化
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政治生态,因三青团的加入而复杂化,在多方力量的缠斗下备受挤压。以浙江为例可对这一现象大致了解。
1938年,蒋介石提出成立三青团以革新国民党,增强党的活力。不久,三青团浙江支团筹备会成立,各县、区、乡镇等层级地方分别设立了分团、分队,并很快成为基层政治的重要力量,这影响到原有乡绅和以CC系为主体的党方势力,使得基层权力斗争的硝烟并不比中央的内耗逊色半点。
首先,三青团极力渗入地方党部与政府。他们以参加党政小组会议为突破口,取得了与党、政在地方政权中同等的发言权;还参与各种参议会、临时参议会、国民大会的议员和代表的选举,以民意代表自居,左右民意机关。而且极力排斥、压制传统豪绅势力,设法控制保、甲、乡、镇长的人选,借助基层行政人员来拓展团务,扩张势力,控扼基层政权。1944年,蒋介石为增加战时兵源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三青团积极响应,征兵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功劳促使蒋介石将童子军由省教育厅改属浙江支团主管。此外,三青团的势力还扩展到地方警备和保安以及户政、田赋等领域,激起了乡村豪绅等地方势力强烈不满。
原本由党方力量垄断的教育文化事业,三青团也积极介入。1941年11月,浙江支团书记长陈苍正、浙江省党部代表石有统以及省教育厅代表赵欲仁等人,在永康旅行社举行了一次“党团关系及教育联系问题”座谈会,议定学生组织一律归三青团领导,并且设立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用以培训师资力量,训练全省教育人员和青年学生。对于文化活动,浙江省抗敌动员委员会最初规定“精神建设工作应由政府会同各级党部、动员委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其他有关团体负责办理”,到1944年,“浙江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则完全由“浙江支团部”接管。此后,歌咏、戏剧、漫画等各式宣传活动中都活跃着三青团员的身影。
三青团的渗透是全方位的,打破了原有政治势力的均衡,“党政团绅”四股力量激烈争夺,致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政治生态更加复杂、脆弱。各方都极力扩充辖下的机关组织,增加己方部属,导致基层机构急剧膨胀,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国民党在其中只有“被牺牲”的份儿。按照规定,党、团所需经费均由政府提供,但基层势弱、无力讨要经费的地方党部只能向党员收费,而如日中天、势头正旺的三青团却能从地方政府强支经费。
政治系统内存在多个行为主体是种正常现象,关键是要以制度规制各方政治行为,将它们规约在良性竞争机制下,将其互动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方能避免政治系统崩坏。然而,国民党基层组织所在的政治系统,各方陷入恶性斗争,没有权威力量来平衡,也没有制度化的行为机制加以约束,其结果就是基层政治混乱,民众苦不堪言,国民党政权尽失民心。
(三)基层组织丧失自主性
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执政党的外部政治生态,除了要考察其与国家政权系统内各股力量之间的关系状态,还要考察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涉及执政党的自主性,决定了国家能否形成一种正义的决策机制。民国初,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崩解,社会被劣绅、土匪或者军阀等势力把持,民众诉求无门。此种局面要求国民党保有自主性,在民众与乡绅之间实现平衡。
国民党执政之后尽量淡化其阶级属性,但它无法代表所有阶级,反而丧失了自主性。例如在农村,由于基层组织孱弱,国民党只能借助于原有的势力“乡绅”进行治理。以1934年成立的襄阳县第一区渔梁坪乡农会为例,该农会9名职员不仅拥有远超人均亩数的土地,还大都具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他们类似于传统乡绅,对农会的运作得到了政权的认可,当局则依靠他们推行政令。①魏文享:《农会组织与国民党党农关系的重建(1927—1949)》,《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不同的是,传统乡绅是“保护型经纪”,而国民党治下的乡村却被“掠夺型经纪”把持,国家政策和利益取向均与“劣绅”协同。这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有重大关联。“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出现了杜赞奇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致使“30年代自愿充任村长的只是那些无固定职业的大烟鬼或赌徒,即土豪或无赖”。②[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国民党与劣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利益交换关系,当局依赖劣绅汲取资源,劣绅则以党权横行乡里,加深了乡村政治的“无序”状态,国民党不仅不能在乡村社会实现贫苦农民与劣绅之间的平衡,而且作为整体的乡村社会与当局政权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无法形成,乡村社会长期处于被压榨、被过度汲取资源的状态,整个政治生态岌岌可危。
四、结语:非均衡的基层政治生态和无法逆转的民心丧失
国民党力图通过改组来获得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尤其将基层组织的建设视为重中之重,“以俄为师”的过程中也学了一套有关组织建设的制度方案,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党内权力争夺等历史原因,改组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之间偏差太大,这极大地体现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政治生态里。考察国民党基层组织内部政治生态状况,可以发现,国民党意识形态呈“低势位”,党员吸纳和内部晋升机制混乱,蚕食着组织内聚力;不仅如此,国民党基层组织陷入空转,种种情形致使内部政治生态的发展不良。其党外政治生态也同样处于极不平衡和不断恶化的情形中,党政之间缺乏耦合,在多方力量缠斗中沦为附庸,并且被恶霸劣绅等社会势力裹挟,丧失了自主性。
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绝非易事,也非一蹴而就,然而政治生态的崩坏却会在无形中发生、容易形成积重难返之势。国民党基层组织政治生态的全面恶化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最为直接的就是其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变得极为脆弱,而在民国战乱的时空背景下,无力扭转政治衰朽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