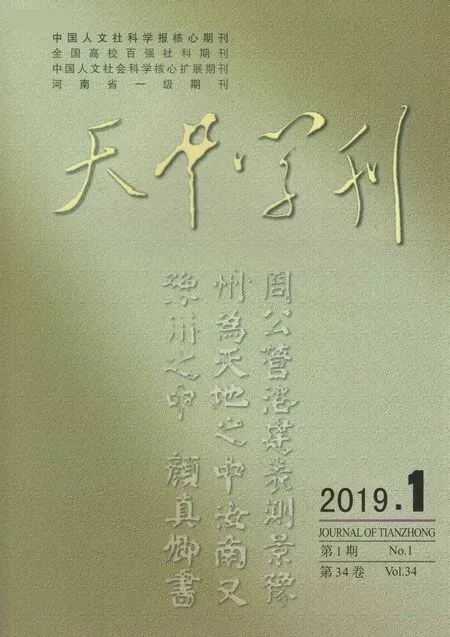刘伶《酒德颂》的文体学意义
赵俊玲
刘伶《酒德颂》的文体学意义
赵俊玲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刘伶《酒德颂》以酒德为歌颂对象,可从《诗经》为其溯源;它具有咏物颂与隐逸颂的双重特质;虽然其语言形式特殊,但颂体本无统一的语言规范,《文选》将之归为“颂”是合理的。《酒德颂》一方面反映了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另一方面受到赋和谐谑文等文体的影响,突出反映了“文体互渗”这一汉魏六朝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事实,是研究汉魏六朝文体互渗现象的典型作品。
《酒德颂》;颂体;变体;文体互渗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一篇《酒德颂》在文学史上名扬千古。实则,《酒德颂》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奇文,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此文被萧统收入《文选》,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扬雄《赵充国颂》、史岑《出师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并列入“颂”体,表明萧统对其文体属性的认定。然而,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虽皆详论“颂”体,但都并未提及《酒德颂》。《酒德颂》是否颂体文,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们的看法就不甚一致,后人也多有争议。
作为一种文体,“颂”以称美功德为旨归,挚虞《文章流别论》较早对其进行了全面论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1]1905颂体产生于对圣帝明王功德称美的需要。刘勰继承挚虞的观点,在《文心雕龙 · 颂赞》中,对颂体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2]313―315与挚虞一样,刘勰亦强调颂的褒述功德、颂美之用。以此反观《文选》所收5篇颂文,显然,《酒德颂》较为特殊,其他4篇皆是政治性颇强的褒述功德之作,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带有论述的性质,但主旨仍在对圣主需得贤臣这一君臣和合理想的向往与歌颂。而刘伶《酒德颂》则借“大人先生”以自况,极写饮酒之乐,表达作者对自由适性生活的向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问:《酒德颂》真如《文选》所列,是一篇颂体文吗?如果是,它在颂体文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具有怎样的文体学意义?
一、《酒德颂》属于“颂”体文
刘伶《酒德颂》虽然内容和形式都较为特殊,但将其归入颂体,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依据。
(一)可从《诗经》为其溯源
刘勰论各种文体的起源时曾言及:“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78颜之推《颜氏家训 · 文章》亦言:“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3]皆认为颂体源于《诗经》。在《文心雕龙 · 颂赞》中,刘勰根据其论文体“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更细致地追溯了颂体的起源:“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2]315―317再次强调“颂”源于《诗经》三颂,并以《周颂》之《时迈》为后世颂文规式。
《诗经》三颂中也有写及酒的篇章,《诗经 · 鲁颂 · 有駜》言: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载燕。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诒孙子。于胥乐兮。
此诗乃颂祷鲁公和群臣宴会饮酒的乐歌,其中对饮酒的欢乐场面有专门的描写,成为后世诸多写酒文学作品的始祖。汉魏六朝时期有关酒的文章遍及多种文体,如诗、赋、颂、赞、诫、启、引、书、箴等,一些作品重在写饮酒的场面,如邹阳《酒赋》;一些借酒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如扬雄《酒箴》;一些重在写饮酒醉状,如刘孝仪《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在这诸多写及酒的篇章中,刘伶《酒德颂》着重对酒以及饮酒为乐的生活进行了颂扬,与《鲁颂 · 有駜》的关系较他篇更为亲近,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
(二)《酒德颂》具有咏物颂和隐逸颂的双重特质
《酒德颂》通过咏物的方式,以颂体明情志,类于咏物颂。以《诗经》为源头的颂文,在后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之一即是描写对象的不断扩张,由颂扬先祖发展到颂扬当世圣帝明王,后又及于普通官吏、普通人,又由人而及物。如《文心雕龙》所言:“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2]321《橘颂》是最早的咏物颂。至两汉,咏物颂的创作就多了起来,如王褒《碧鸡颂》、崔骃《杖颂》、黄香《天子冠颂》、班昭《欹器颂》、蔡邕《五灵颂》等。魏晋及以后,沿两汉创作余绪,咏物颂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为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符瑞颂,如何晏《瑞颂》、薛综《麟颂》《凤颂》、沈演之《嘉禾颂》《白鸠颂》、鲍照《河清颂》、张畅《河清颂》、梁简文帝《马宝颂》等,数量庞大,与“颂”最初颂扬先祖、圣帝明王功德之意也最为契合。二为相对较纯粹的体物颂,如曹植《宜男花颂》、成公绥《菊花颂》、左棻《郁金颂》《菊花颂》《芍药花颂》等,虽主要笔力用于描写细物,但基本未摆脱儒家以物“比德”的传统,往往牵及道德说教,如左棻《郁金颂》言:“伊此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芬香酷烈,悦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钦。窈窕妃媛,服之褵衿。永重名实,旷世弗沈。”以郁金之芬香悦目谈及妃媛应名实俱佳。此类咏物颂在魏晋及以后大大发展,作品亦多。三为沿袭屈原《橘赋》托物言志的传统,题为咏物,实际目的在于吟咏作者情志的咏物颂,如辛萧《燕颂》云:“翩翩玄鸟,载飞载扬,颉颃庭宇,遂集我堂。衔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处此高凉。孕育五子,靡大靡伤。羽翼既就,纵心翱翔,顾影逸豫,其乐难忘。”表面写燕之自由适性,实则抒发作者羁于仕宦、志不获骋的郁悒。再如颜延之《赤槿颂》,以赤槿比况出身名门的世袭子弟:“华缫闲物,受色朱天,是谓珍树,含艳丹间。”语有讽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咏物颂可以借咏物以抒怀的功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如曹植《柳颂序》言:“予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今之士。”因《柳颂》正文不存,我们无从得知曹植如何借颂柳以讥当世之士,但作者咏物抒怀的用意却是非常明确的。赵幼文在为此颂系年时,即言其与建安年间曹氏兄弟争夺太子之位有关[4]。至江淹,作《草木颂十五首》,有序言云:“仆一命之微,遭万代之幸。不能镌心砺骨,以报所事。擢翼骧首,自至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职闽中。且仆生人之乐,久已尽矣。所爱,两株树、十茎草之间耳。今所凿处,前峻山以蔽日,后幽晦以多阻。饥猨搜索,石濑戋戋,庭中有故池,水常决,虽无鱼梁钓台,处处可坐;而叶饶冬荣,花有夏色,兹赤县之东南乎?何其奇异也?结茎吐秀,数千余类,心所怜者,十有五族焉。各为一颂,以写劳魂。”[5]这一系列颂文作于江淹仕途不得意、自感命运偃蹇之际,写颂的目的在于暂抒内心忧愁郁积之情,如《金荆》之“姱节讵及,幽意谁传”,《相思》之“公子不至,山客徒寻”,《豫章》之“七年乃识,非曰终朝”,《栟榈》之“不华不缛,可避工巧”等,无不寄寓着作者有才华而无人赏识的愤懑,又透露出终有一天会被人发现的渴盼,虽字字句句在写草木,却又字字句句在写自己。
实则,不仅咏物颂,其他一些题材的颂文可以用来抒写怀抱,也被文人指出。北魏高允作《征士颂》,其序言云:“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1]3653“长言寄意”,言之凿凿,明确写此颂的目的在于怀念昔日同时应征的一批士人,抒发知己零落的悲慨。刘伶《酒德颂》也是这样一篇抒发个人性情怀抱的颂体文,文中刘伶借大人先生以自况,言己嗜酒如命,酒给他带来了生命最大的快乐,可以忘记寒暑、利欲,可以傲视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宣扬了自己要隔绝世俗,独享隐逸生活的理想。如清人方廷珪评此篇所言:“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乃命题之旨。”[6]
同时,在颂体文中宣扬隐逸思想,也不是刘伶的首创。东汉后期,宣扬隐逸思想的颂文出现,如崔琦《四皓颂》、崔骃《四皓墟颂》、班固《安邱严平颂》等皆以平淡恬静的隐逸生活的描写,表达渴望超越现实生存环境,走向适性安然的愿望。魏晋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文士动辄有性命之忧,于是许多文士转而消极避世,企慕羽化登仙,加之玄学思想的盛行,借赞颂道家人物表达逍遥出世愿望的颂体文就更多了,如曹植《玄俗颂》,牵秀《老子颂》《彭祖颂》《王乔赤松颂》,潘岳《许由颂》等皆是此类文章,而陆云《登遐颂》更是歌颂了郊间人、王子乔、玄洛等21位登仙之士,规模宏大。这些隐逸颂中,班固《安邱严平颂》“无营无欲,澹尔渊清”、崔琦《四皓颂》“富贵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曹植《玄俗颂》“逍遥北岳,凌霄引领。挥雾昊天,含神自静”等对道家逍遥自适生活的描绘及对富贵的傲视,无不与《酒德颂》所表达相合。隐逸颂是汉魏晋颂体文的一支,虽然汉魏晋隐逸颂文全以歌颂道家人物的方式出现,且基本都采用四言韵文的形式,与刘伶《酒德颂》不甚相似,但在主体精神上二者却是一致的。《酒德颂》从思想主旨上来说,又可归入隐逸颂中。
(三)颂体语言形式并无统一规范
《酒德颂》的语言形式在颂体文中也较为特殊。颂体的形成受到了《诗经》的直接影响,形式上以四言韵文为正宗。就今存先秦至汉魏六朝颂体文篇章看,也确实以四言韵文者居多。但与众多文体一样,颂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变体。在汉代,颂体文就有散文式、骈散结合式、骚体与四言结合式、骚体、杂言等诸多形式类型。如汉代的第一篇颂文——董仲舒《山川颂》,作品中穿插引述经典原文,骈散结合,行文自由,便于解说经文,表达情致。而如东方朔的《旱颂》,则全用骚体,表达久旱无雨之时作者的悯农怜生之情。而即便是同一作者的颂体文,也并不采用统一的形式,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为三言、四言与骚体的组合,《东巡颂》则为杂言体,三言、四言、六言句式错杂运用。至建安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自觉,人们对词采日益重视,颂文又呈现出向四言韵文回归的趋势,但仍有骚体、杂言等式,如繁钦《砚颂》全用骚体。傅嘏《皇初颂》杂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实乃杂言体,如“于是天地休豫,灵祗欢欣。嘉瑞云集,四灵允臻。甘露霄零于宫庭,醴泉冬涌于中原。白雉素鸟,丹芝朱鱼。鳞集群萃,不可胜书。信应天之美瑞,受命之灵符也。然后览公卿之谠议,询百僚之典谟。天子乃登雕辇,戴羽盖。佩玉锵锵,銮声哕哕。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导神气。于是建皇初之上元,发旷荡之明诏”一段,叙述与描写相结合,单行散句时时间出。而且自汉至魏,对颂体文用韵与否的要求也不严格,吴曾祺就言:“颂必用韵,而亦有不用韵者,如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是也。”[7]6662即如上举傅嘏《皇初颂》,虽大部分用韵,但单行之句亦常有。显然,刘伶《酒德颂》不符合正统的四言韵文形式,但不能以此判断它不属于颂体,因在汉魏时期,非四言韵文的颂是大量存在的。《酒德颂》数句一韵,句式不求整齐,四言、五言、六言等间用,自由空灵而洗练,一如文章表达追求自由适性的主旨,也一如作者狂傲不羁的个性,自是文章中缚不住的。
总而言之,《酒德颂》以酒德为歌颂对象,可从《诗经》具体篇章为其溯源。它具有咏物颂和隐逸颂的双重特质,虽然不合正统四言颂文之式,但颂体本无统一的语言形式规范,《文选》将之归入“颂”体是合理的。刘师培评《菊花颂》等言:“与三代之颂殊途,然亦颂之一体。盖虽非述德告神,而与‘美’之旨弗悖焉。”[8]以此来评《酒德颂》亦然。不管怎么说,其主旨还在于颂美酒德,颂美逍遥自适的生活境界。
二、《酒德颂》的文体学意义
(一)《酒德颂》反映了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
《酒德颂》的文体归属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疑问,原因在于它不属于颂体文的典型,但它反映出了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
颂体虽源出《诗经》,但在后代的发展演变情况较复杂。刘勰论颂体,即有正体、变体、谬体、讹体之分。所谓正体,指用以颂美功德的颂文;所谓变体,指那些颂美中有讽刺和颂物之作;所谓谬体,指受赋、序等文体影响而带有其他文体的某些特征的颂文;所谓讹体,指内容有颂美、有贬抑的颂文。基于宗经的主张,刘勰对颂体在后世的演变不满,但却道出了魏晋六朝时期颂体流变复杂的事实。于此,后人亦多论及,如吴曾祺《文体刍言》言:“颂为四诗之一,盖揄扬功德之词。其初本臣子施之君上,后则自敌以下,亦相与为之。其以称古人以寓仰止之意者为更多,甚至器物禽兽之微,亦藉以见意。盖文人游戏之作,非正体也。亦有名为颂而实非颂者,如韩退之《伯夷颂》是也。”[7]6661―6662林纾《春觉斋论文》言:“《商颂》《鲁颂》,用之以告神明,若《原田》《裘鞾》,一出诸野夫之口,一用为刺讥之辞。至训‘颂’为‘诵’,此颂之变体也。三闾《橘颂》,则覃及细物,又为寓怀之作,非颂之正体。于是子云、孟坚,用之以美赵充国、窦融,已移以颂显人,晋而上之颂天子矣。此颂之源流也。”[7]6340他们描述的皆是颂体文施用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与此相应,颂体的语言形式也在不断扩张,评论家也多有提及,如贺复征言:“后世所作诸颂,皆变体也。其体不一,有谣体,有赋体,有骚体,有箴铭体,有散文体。”[9]方熊补注《文章缘起》云:“后世所作皆变体也,其词或用散文,或用韵语。”[10]二人皆道出了颂体语言形式在后世的发展中并没有一定之规的事实。《酒德颂》抒怀言志、论颂酒德的内容,诸种句式相杂、变动不居的语言形式,其实正体现着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较充分地反映了此体善于创新的精神。
颂体文的多变,是与这种文体的性质密切相关的。颂体本是一种以“因文立体”的方式产生的文体,如郭英德所言:“因文立体有两种略有区别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11]随后郭先生即以“颂”体为典型例子,论述这种文体生成方式。因颂体产生于作品的不断累积与总结中,只要不变其最重要意旨——颂美精神,就可归入此体,并推动这种文体不断变化发展。
(二)《酒德颂》反映了汉魏六朝文体互渗的事实
《酒德颂》不仅体现着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更有着超越一篇颂体文的文体学意义:它反映了汉魏六朝文体史上的一个事实——文体互渗。
汉魏六朝是文体发展演化的高峰时期,各种文体不仅有纵向的发展过程,更有横向之间的联系、渗透和影响,以至于当时大多数人难明二体界限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汉魏六朝时期的学者文人已有认识,如蔡邕《独断》论及戒书言“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12],表明的是戒书与策书的互相渗透。桓范《世要论》对东汉末赞像、铭诔、书论等文体淆乱的情形进行了批评。挚虞《文章流别论》论文体往往强调各种文体的应有特征,批评一些作品的“失体”。《文心雕龙》关于文体之间横向影响、互渗的言论就更多了,如《铭箴》言“夫箴颂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2]420,指出箴、铭二体在功能上的交叉。《论说》篇言:“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2]669―673这里提出“参体”一词,指论说与传注由于目的的一致性,而致性质趋同。《祝盟》篇言“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读之赞,固周之祝文也”[2]372,指出哀策与诔文、颂文、祝文等由于功用的接近而致界限的难明。《诔碑》篇言诔“传体而颂文”[2]442,言碑“其序则传,其文则铭”[2]457,又指出诔与传、颂文,碑与铭文等的交互影响。《哀吊》篇言“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2]485,指出一部分吊文与赋体的相似性,贾谊《吊屈原文》是文还是赋的争论实为明据。《奏启》篇言:“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2]873表明启这种在南朝才盛行、相对较为晚出的文体,身上实集聚着奏文、表等文体的功能与特征。《通变》篇所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2]1079―1081,总括道出了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包括其他文体的渗透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事实。关于具体作品受到其他文体影响渗透,而文体归属难于界定或文体性质不明的事实,在汉魏六朝更是屡见不鲜,如萧子显《自序》言:“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13]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为了突破某种文体固有创作模式的束缚,在写作时往往特意借鉴其他文体。文体互渗实际是文体进行自我更新,以求更强盛生命力的一条途径。
颂文在汉魏六朝时期之所以不断“变体”,实与这种文体总是在吸取其他文体的特征,受到其他文体的渗透、影响关系莫大。即如前引《文章流别论》言“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指出的是汉代颂文受到汉赋的影响。《文心雕龙 · 颂赞》篇亦言:“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2]327颂体受到赋的影响,当今学者亦论之多矣,如王德华《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王长华、郗文倩《汉代赋、颂二体辨析》,易闻晓《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等文,不仅探讨了赋对颂体渗透的现象,还探求了背后的原因。其实不仅是受赋的影响,颂体与诸多文体都有互渗的情形,如《文心雕龙 · 颂赞篇》所言:“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2]334其意在严格区分颂与赋、铭两体,其前提是颂与这两种文体的界限模糊。来裕恂《汉文典》言:“班、傅之《西巡》《北征》,流而为序,马融之《广成》《上林》变而为赋,韩愈《伯夷颂》,又似乎论,其流别不无少异焉。”[7]8646在赋之外,又指出颂与序、论等文体的交越互渗,实则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就多有学者以之为论,认为其为赋或为论、赋结合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更言:“又或变其名而实同颂体,则有若赞,有若祭文,有若铭,有若箴,有若诔,有若碑文,有若封禅,其实皆与颂相类似。此则颂名至广,用之者或以为局,颂类至繁,而执名者不知其同然,故不可以不审察也。”[14]黄侃所列文体,或在文体功能,或在文体形式,或在施用对象,或在创作目的等方面,都有与颂体交叉的情况。刘伶《酒德颂》非常突出地表现了颂体与其他文体互相渗透的事实,显示出《酒德颂》受到了大赋的影响。
如前所言,挚虞、刘勰等皆论及颂体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大赋的影响,但二人所言马融《广成》《上林》受大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铺陈手法的运用。而《酒德颂》受大赋的影响则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即其假设人物问答与谐谑性。《酒德颂》所假设人物有两方,一为大人先生,一为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双方一正一反,一宾一主。宾对主之唯酒是务怒目切齿,于是以礼法进行游说,然《酒德颂》并未像大赋那样把重点落在游说的言语上,而是重点描述了大人先生纵酒之态与饮酒后之自由适性,以及其傲视二宾之意,令二宾昂扬而来势颓而去。这种假设宾主以成文的写法显然来自大赋,而对主宾之情态进行刻画亦存在学习大赋的痕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重在主宾对话,对假设人物的描绘仅有数字,左思《三都赋》亦然。张衡《西京赋》则有言:“有凭虚公子者,心侈体忲,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是以多识前代之载。言于安处先生。”“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怃然有间,乃莞尔而笑。”然而,大赋对于主宾双方的描绘虽渐多,但与《酒德颂》直接相关的则是曹植的《七启》。《七启》假设了玄微子和镜机子主宾双方,玄微子隐于大荒之庭,乃乐道好静之人,镜机子前往说之:“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独驰思于天云之际,无物象而能倾。于是镜机子闻而将往说焉。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对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潜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飘飖焉,峣峣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若将飞而未逝,若举翼而中留。于是镜机子攀葛藟而登,距岩而立,顺风而称。”《七启》对玄微子所居离世清静的环境和其轻禄好静、自由适性的思想与生活进行描述,而在《酒德颂》中,大人先生对于适性自然的追求也被作者强调。《七启》中,作者以大量对话写镜机子以“道德之弘丽”说服玄微子,而在《酒德颂》中,这些被“陈说礼法”一句一带而过,表现出其作为颂体,虽受大赋的影响,但仍在竭力保持自身文体特征的倾向。
颂体源于廊庙文学,本是一种极为庄重严肃的文体。《酒德颂》之前的诸多颂文虽也受到了大赋的影响,但表现在铺陈手法的运用上,而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颂文本身的严肃性并无影响。假设人物以问答,本身就带有谐谑意味,《酒德颂》采取假设人物的方式,已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作为颂文的庄重严肃性。而在具体行文中,谐谑化的倾向则进一步被加强。《酒德颂》颂扬酒,而言酒有德,就是谐谑的表现。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二人在文中是陈说礼法之人,本应面孔严肃,作者偏用“奋袂攘襟,怒目切齿”这样夸张的动作与表情来反讽,让人想象之下忍俊不禁。而将二人比为“蜾蠃之与螟蛉”,除了表现出作者傲视一切的精神,实又在极意的贬低与嘲讽中换来读者会心一笑。汉赋外,《酒德颂》实还应受到了谐谑文体的影响渗透,采取了夸张、反讽等手法,向游戏之作的方向发展。至宋代,苏轼作《东坡羮颂》《油水颂》《猪肉颂》《食豆粥颂》《鱼枕冠颂》等,以颂为游戏之笔,应算是对《酒德颂》谐谑特质的回应。
可见,《酒德颂》受到赋、谐谑文的影响,带有一些综合性的文体特征,这一方面使它的文体属性显得复杂,另一方面则展现出汉魏六朝文体交叉互渗的文体学实际。
总之,刘伶《酒德颂》虽然内容和形式都较为特殊,但与《鲁颂 · 有駜》的关系更为亲近,也即可从《诗经》为其溯源。同时,它具有咏物颂与隐逸颂的双重特质。另外,虽然刘伶《酒德颂》的语言形式特殊,但颂体本就无统一的语言规范。因此,《文选》将之归为“颂”是合理的。这篇颂文不仅在颂体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丰富的文体学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颂体流变复杂的特性,另一方面它受到赋和谐谑文等文体的影响,反映了汉魏六朝文体发展史上文体互渗这一事实,可作为研究汉魏六朝文体互渗现象的典型作品。
[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1.
[4]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7.
[5] 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0―191.
[6] 方廷珪.昭明文选集成[M].仿范轩刻本.1767(乾隆三十二年).
[7]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51.
[9]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任昉.文章缘起[M].方熊,补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J].学术研究,2005(1):122―127.
[12] 蔡邕.独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12.
[1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2.
2018-09-13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W062)
赵俊玲(1981―),女,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
I206.2
A
1006–5261(2019)01–0089–07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