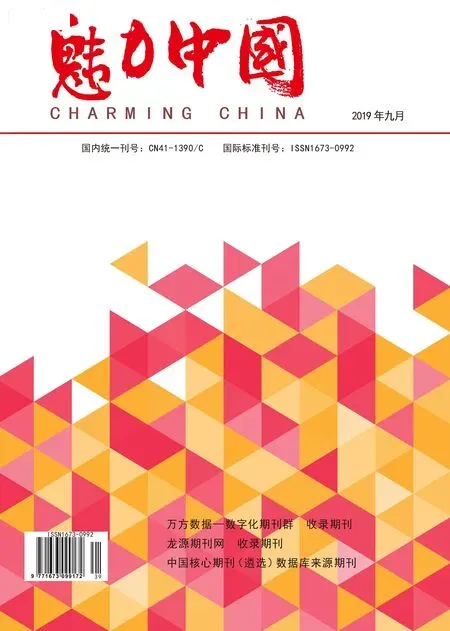西奥多·波伊斯研究(节选二)
何青1 何春1 米切尔2
(1.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7 ;2.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米切尔教授对西奥多的研究深入细致,人物描写手法多样,或从大处着眼,通过全景式人物肖像画,展现西奥多的高大和坚毅;或从细节入手,以西奥多的胡子作为切入点,通过描写西奥多探索者一样的眼睛和像陷阱一样紧闭的嘴巴,凸显西奥多的冷峻、温和、自卑等复杂的内心世界。不论西奥多抬头仰望天空,或低垂双眼看书,都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品读一个个精彩瞬间,仿佛在谛视一幅幅西奥多的生活照,不能不为作者的妙笔生花赞叹。正是这些生动的描写,使西奥多的人物形象格外饱满、鲜活,使读者能更好地把握西奥多的丰富性格,更深入地了解西奥多的作品。
西奥多大部分重要的摄影代表照片或别的照片都摄于1924年至1943年十九年间。作为各种肖像的标准,我们先引用J.B.查普曼在1928年3月出版的《书商》期刊第315页中精辟的语言描述:
他看上去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棱角分明,显得坚毅;浓密的灰色头发覆盖在他高耸的额头上,凸出的眉毛下那双眼睛以探索者坚定的目光凝视前方。这张脸也有幽默感,因为虽然嘴巴像陷阱一样紧闭,但几乎有着爱尔兰人长度的上唇和那双偶尔闪烁的敏锐的蓝眼睛弱化了他的严肃性。几乎在东沙伦顿任何一个下午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穿着普通斜纹花呢衣服的男人。他喜欢走在那条小路上,经过旅馆,走到高地上。
令人好奇的是,查普曼在这里应该将“探索者的凝视”归于西奥多,因为“探索者”是他在《创世记的解读》(1907年)中的第一个“自我改变”的文学形象。实际上,“Zetetes”是这个对话中交谈者的名字,是西奥多隐藏在自己身后的面具,但这个名字,根据希腊语zetein是“去探索”的意思,被恰如其分地注释为“探索者”。此外,这是一个与皮浪怀疑主义特别相关的名称,皮浪认为智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心灵的宁静。这一章节所附载的文章,有一幅同样引人注目的旋涡派艺术家威廉·罗伯茨所绘的铅笔画(原版现存放在布拉德福德美术馆),他的瘦削、呆板的人物形象为《新圈子》的封面增添了光彩,这幅画作为卷首插图于1926年首次出现在该杂志上。同年,它也被用作两个故事《坚强的女孩》和《新娘》的卷首插图。罗伯茨的首次尝试似乎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热情,但在写给《新圈子》的书商和经销商查尔斯·拉尔的信中,西奥多宣称这个版本的画像取得了巨大成功。拉尔已经寄给西奥多一幅装裱的画像。另外四位作家赫伯特·厄内斯特·贝茨、艾尔弗雷德·埃德加·科珀德、莱斯·戴维斯和利亚姆·奥弗拉哈迪也有类似的铅笔肖像画,他们都是短篇小说大师,可以说他们是拉尔稳定的肖像模特,因为他对他们的作品特别关注。可能除了科珀德,所有这些人偶尔都会与拉尔一起开车去拜访西奥多。有些出现在《新圈子》中的画像,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可以快速研究的人物外貌素材——这与西奥多和科珀德的精心描述不同,他们对罗伯特独特的明暗法描写尤为细腻。
从某种意义上说,1921年雕塑家史蒂芬·汤姆林一搬工作室到东沙尔顿,就“发现了”西奥多。经过“一段漫长而骄傲的沉默”,1923年初,他从伦敦写信给西奥多,对贝丝卡及其居民表达他的诚挚情感。在沙尔顿时,他已经雕刻了西奥多的半身石膏像,大概是用青铜或石头重新制作的;但是在1923年1月24日的这封信中,他坦言:“我给你做的石膏像在路上无法挽回地摔成了碎片。”唯一记录就是他骄傲地坐在作品旁的一张照片,石膏像被摆放在树桩上摇摇欲坠。似乎为了弥补损失,他后来建议西奥多拍摄宣传照片:“班尼说最重要的是为了宣传,你应该好好进行最新的‘肖像研究’。”然而,第二年,当《书商》的编辑要求拍照时,西奥多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在1924年5月30日的回信中,他答应让“村里的摄影师”拍照,但同时提供几个星期前由大卫·加内特的妻子蕾拍摄的一些快照,他补充道:“桥上的宝贝是大卫·加内特的小儿子理查德。”虽然大部分快照不适合《书商》,但他们确实提供了西奥多难得的轻松一面,显然有小孩子陪伴让他很放松,而且事实上他一直在微笑。然而,在其中的一张相片中,蕾·加内特捕捉到西奥多独自一人以其幻想的姿态,在高沙尔顿的背景下,坚定地凝视着天空。因此,这与道格拉斯·格雷近二十年后的肖像一样,备受人们欣赏。这张照片被认为适合发表,随后与马克·翁立的评论一同出现在1924年7月24日出版的《书商》中。
加内特一家在贝丝卡始终受欢迎,而同一时间拍摄的一些其他照片显示这通常会引起西奥多的密友小圈子的慌乱和焦虑,正如西奥多在1924年9月13日的信中坦率地向蕾·加内特所表明的:“几天前,我们和奥托琳及她的丈夫在这儿……我很高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非常喜欢奥托琳和菲利普·莫雷尔,但是我们感到非常担心。”西奥多所有潜在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都会在这样的场合流露出来,而且,越来越厌恶旅行。根据格特鲁德的日记,1924年9月8日莫雷尔夫妇拜访西奥多;约翰·库柏·波伊斯为下午茶回到柴德约克,而莫雷尔夫妇则“与西奥多一起喝茶”。奥托琳夫人是个有强迫症但很成功的摄影师,她拍摄了这个场面,其中有两张组合快照被收入奥托琳夫人专辑(1976年)。其中一张照片中,菲利普·莫雷尔朝西奥多望去,而西奥多握着一个小小的牛奶搅拌器,特别坚定地凝视着什么。另一张照片,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的西奥多似乎远离了奥托琳夫人的相机侵扰,就像远离午后的阳光一样自在。拜访回来后,奥托琳夫人于1924年11月5日写信告诉西奥多,奥古斯都·约翰非常欣赏他的作品,希望“约翰能为你画一幅画,那总比拍十几张可怜的照片好!”事实上,奥古斯都·约翰已从奥托琳夫人那获得西奥多的地址,三天后就联系了,他写信给西奥多,表示非常欣赏西奥多的书,希望能见面;但直到12月30日,他们还是没能会面,当他抵达时,后面紧跟着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约翰也住在多塞特郡帕克斯通附近的奥德尔尼庄园,而劳伦斯从1923年起就住在莫顿附近的云雾山。这个会面始终没有到来,直到1932年,我们才听到很多消息说计划要画肖像。后来成为杰拉尔德·布雷南夫人的美国诗人加梅尔·沃尔西告诉卢埃林·波伊斯,说约翰渴望以非常务实的语言描绘西奥多:“我希望他如愿,因为这是一种宣传,而且可能会促使一些人购书。”1923年安排了几次画像,12月19日约翰写信告诉西奥多,他在上次拜访时感冒了,但“会在圣诞节后过来完成肖像”。然而,根据一个未发表的记载,当约翰发现肖像的内部背景被破坏时非常生气,立即毁掉了这幅画。于是,他不得不从头再来,仅凭他的草图和记忆去画。这种情况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持久的努力却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许除了道格拉斯·格拉斯,约翰捕捉到比许多相片所看到的更温和、更忧郁的西奥多。也许最近西奥多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迪基在东非去世了,显然他决定放弃写作——这一切都反映在悲伤的眼中?现存放在泰特画廊的这幅肖像,于1958年皇家学院夏季展览(5月3日至8月17日)上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埃里克·肯宁顿,约翰·纳什,以及斯宾塞兄弟吉尔伯特和斯坦利的作品。
格特鲁德也许是波伊斯家族中最有艺术天赋的,而且只有她接受过正规训练。她曾在伦敦短暂学习,两次在巴黎学习(1913年和1923年),在巴黎时她对塞尚的作品特别感兴趣。第二次从巴黎回来不久,她开始创作西奥多的油画,第一次尝试家庭系列肖像。她的创作动力可能源于1924年2月22日回国前在巴黎完成的自画像。在找到住所前,她一直与西奥多住一起。她在3月13日的日记里首次提到:“内附油画的书。西奥多·弗朗西斯·波伊斯”;4月3日,她去诺维奇参加埃塔姨妈的葬礼,而后又继续画西奥多肖像。画中的西奥多坐在他最喜欢的高靠背扶手椅上,右边摆着一堆凌乱的书。格特鲁德画的其他家庭成员肖像,也许除了她父亲独自享用晚餐那张肖像外,都给人们完全不同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更平衡的明暗对比。格特鲁德用红铅笔画了另一幅她兄弟的画像,标注的日期是“1935年7月4日”,据报道,这与R. H. 沃德画的《西奥多兄弟》(1935年)中约翰和卢埃林·波伊斯的肖像一致。旁边是长相古怪、鹰钩鼻的约翰,还有卢埃林,在沃德看来,卢埃林的满脸胡子暗示了“古代先知的某些东西,正如米歇尔·安吉洛所设想的那样”。这个版本的西奥多很容易辨认,但令人失望的是画像平淡无奇,就像《隐士的独白》中的托马斯先生,“只会像一只寄居蟹一样爬到进它的外壳”。1937年初(2月5-19日),格特鲁德在新邦德街的库玲画廊举办画展,约翰·库柏·波伊斯、G·B·查普曼、伯尼·奥尼尔博士、路易斯·威尔金森和多拉·威廉姆斯等许多亲朋好友都出席并观看了画展。包括约翰、卢埃林和西奥多在内的很多家庭的肖像画都被公平地定价为75英镑待售中。当格特鲁德看到三位老年女人对这些画像很感兴趣时,她猜测她们是“西奥多的崇拜者”。
汤姆林敦促西奥多去拍的工作室照片终于在1934年由摄影师霍华德·科斯特拍摄,科斯特自称是“男士们的摄影师”,是当代时尚摄影师埃米尔·奥托·霍普的继任者。科斯特也在《时尚》杂志社工作过。西奥多这张照片被《书商》委托运用蒙太奇剪辑组合“文学堤坝”39位文学人物,是为庆祝该期刊于1934年12月与《伦敦水星》合并之前的最终发行量而设计的。其中最著名的其他文学人物包括:赫克斯利、米德尔顿·莫里、康普顿·麦肯齐、普里斯特利、肖和威尔斯。西奥多(6)被安排在后排,在A.P.赫伯特(5)和约翰·巴肯之间的后面位置,象征性地处于文学界的边缘。《书商》的封面构成很巧妙——中间有张桌子,暗示一种文学上的最后晚餐,但对个人肖像而言是不公道的。幸运的是,科斯特拍摄的西奥多肖像也被大胆地用作《帕奇上尉》(1935年)的书皮插图,从书中可以欣赏到照片的细节。科斯特在拍摄西奥多时,让他目光直视镜头,从而捕捉到了坚定目光背后折射出的奇特性格和智慧;同时,他让西奥多轻松地摆放双手和手臂,弱化了他的严厉态度。此外,西奥多在家很有安全感,熟悉的环境使他更放松,这一点从照片背景里的贝丝卡客厅的细节可以看出。
引发最多评论的是西奥多冷峻的嘴——仿佛拧成了一根细线条。查普曼在1928年描述得很好,“西奥多的嘴巴像陷阱一样紧闭。”R. H.沃德补充道:“他的嘴……似乎很痛苦,这些痛苦都直接压缩在那两片薄薄的嘴唇里,在整个早上的谈话过程中只微笑两次。”1948年,马克·霍洛维发现,“他脸上最具特色和最有趣的特征是他的嘴——向内折叠,很微妙,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讽刺、幽默、寂静无声的愉悦,和不可捉摸的幽远。”1967年,西奥多去世很久之后,肯尼思·霍普金斯发表了开创性研究论文《西奥多兄弟》,把科斯特画的西奥多肖像放在文中,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如何解读他那冷峻的嘴。”艾丽莎·格雷戈瑞向西尔维娅·汤森德·华纳汇报了她通过马尔科姆·埃尔温获悉的各种评论,其中包括奥古斯都·约翰,他认为西奥多的面容呈现出悲惨和饱受煎熬的神情,他相信维奥莱特是导致她丈夫西奥多不快乐的原因。西尔维娅·汤森德·华纳不耐烦地回应这样的“谬论”,虽然她承认有时看到西奥多“像狼人一样冷峻”。她争辩道“在那张特别的照片上,是刻板的而不是真实的肖像——他的嘴巴定格在一条致命的弧形上,而不是一条冷峻的曲线上。”为朋友辩护使她盲目诋毁一位广受赞誉的职业摄影师的成就。然后,她把维奥莱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说明维奥莱特是拯救西奥多的工具,而不是造成他痛苦的原因,并提到他在萨福克耕作时不快乐的日子:“那里存在某种危机,有些人深陷其中,伤痕累累。”这最后的断言是一种误导,说明她对西奥多生命中的一段时期知之甚少。
结语
大千世界,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米切尔教授通过深入研究,从西奥多的照片着手,尤其是以西奥多的胡子作为切入点,巧妙地运用人物肖像描写,包括人物的五官、神情、脸色、衣着、体态、姿势,以及语言、动作等,并把他放到具体的事件中,加深读者对西奥多的印象,领悟西奥多的思想、性格和气质,更好地理解西奥多作品的内涵与外延。同时,圆满地体现了作者对西奥多文学研究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