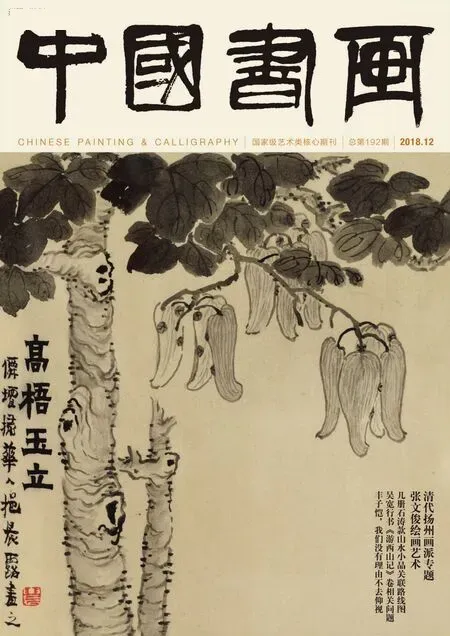书法现代转型中的身份认知(第十五讲)
◇ 主讲人:胡抗美
◇ 时 间:2018年10月14日15:00 18:00
◇ 地 点:《中国书画》美术馆
一、回到传统中看书法
今天讲座的这个题目准备了一段时间,也是我长期的思考。书法身份的认知就是要通过讨论书法的定义、职能等来明确书法艺术的定位。它关系到什么是书法、书法是不是艺术、是什么样性质的艺术,也关系到我们学习书法的方向,以及大众书法审美的目标。由于书法与实用长期结合在一起,其书法身份一直处在模糊状态,尤其在书法转型中,最容易对其身份产生误解。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书法实践,为书法现代转型进行了多视角实验,提供了足够的条件。放眼世界,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瓦解,以及知识商品化等后现代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这是这个转型期的国际背景。着眼于国内来看,对书法传统与创新的认识参差不齐,导致各种各样的消费书法现象出现,有人说书法是写字,有人说书法是文化,有人说书法是视觉艺术,有人说书法是抽象艺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质上,反映的是书法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知问题。书法一方面被泛化,缺乏门槛意识和最起码的敬畏,另一方面被群殴、被恶搞,缺乏艺术意识和最一般的审美常识。
面对这些书法身份认知的危机,我倒觉得我们有必要或必须回到传统当中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蔡邕的书法观切入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在《九势》当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里讲了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自然”,认为书法艺术功能就是表现自然。什么是自然?《荀子·王制》里把自然万物分了四个类,即水火、草木、禽兽和人。其中,他认为人是最重要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也有义。这个“义”在那个时代显然是指礼仪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人“最为天下贵也”。因此“书肇于自然”就产生了两个书法的定义:第一个就是“书者法象”,认为书法是对自然万象的一种效法,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物象的观察理解、取舍和想象。第二个定义就是“书者心画”。书法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流露,这种流露被我们的古代书论说成是字如其人,后来到了刘熙载干脆总结为“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个理论在书法史上塑造一个又一个伟大书法家的形象。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阴阳”。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一句话:阴阳是中国书法的指导思想。就是说书法创作如离开了阴阳学说,那就不知其本。纵观书法史,蔡邕的书法阴阳观提出之后,历代书家、书论家们都是围绕着阴阳美学这个命题来进行深入探讨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形势”。形包括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它简要成点画结体、组行、区域、墨色和空白等元素,归纳起来就是空间构成。势包括用笔的提按顿挫、速度的轻重快慢、组合的离合断续等,归纳起来就是动感和节奏—实际上它讲的就是一个时间性。所以形和势在我们现代的书法理解当中,我认为应该是书法家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或者说是书法家观察世界、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方法。形和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比如说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在教书法的时候,她就强调形和势的结合统一:写一个点它综合为“高山坠石”,写一个横归纳成“千里阵云”,写一个竖比喻为“万岁枯藤”。点的形如石头,光有这个形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从高山往下坠的那种势。这个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通过体积、重量、方向和速度来体现的。“横若千里阵云”“竖若万岁枯藤”也是这样。
蔡邕也好,卫夫人也好,他们都是在书法意识的前提下,对书法造型功能的强调,如果只是完成日常的实用写字,把字写准确、写工整就可以了,那就用不着“自然”“阴阳”“形势”和“一点若高山坠石”,也用不着“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更用不着“公孙大娘舞剑器”和“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因为这些才是书法层面的要求。
二、书法史上的几次转型
要认知今天的书法身份,那肯定就要了解它的历史,我们看看书法史上的几次转型。
比如说篆隶问题。隶变的过程,实际就是把篆书的那根曲线(或弧线)拉直,并把它切断,然后命名为“侧、勒、弩、趯、策、掠、啄、磔”,开始了书法的笔法笔势建构。隶变的核心是“变”,但必须要认识到变中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就是篆书的那根线的质量,所以我们讲书法的身份认知,当然就应该从这根线开始,从书法艺术的自觉期开始,循着这个源头、这根线来往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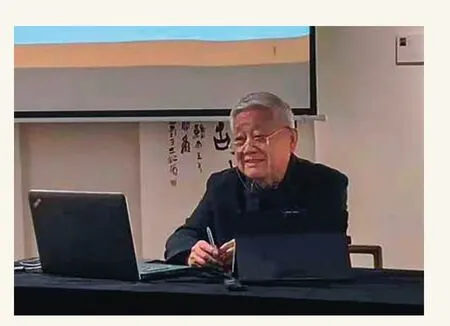
第十五讲主讲人
第一次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就是魏晋新体的产生。第一次转型中历史选择了王羲之。王羲之的实质是什么?是一种精神。王羲之的精神第一就是创新,第二是他的继承,第三是以他为代表的大批书法家构建的魏晋传统。魏晋传统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是篆隶为本。所以我们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难度并不是飘逸和秀美,而是朴厚灵动,就是用篆隶的线创造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所以,我们在认识王羲之的时候,我觉得有魏晋的王羲之,有唐代的“王羲之”,有唐以后的“王羲之”,有当下的“王羲之”。王羲之只有魏晋时代的一个,但“王羲之”是发展变化的。
第二次转型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就是说,从魏晋到公元581年,再到唐代,这一阶段书法并列存在着两大风格:一个是王羲之为代表的精致一路,另一路就是北朝的相对粗犷的传统。北朝也好,南朝也好,它们都来自秦汉。应该说,到了初唐,书法的确是进入了法度“建设”的阶段。以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为核心的各种法度相继建立,强调了入笔、收笔、转笔,而冷落了那一段漫长的行笔表现,这一段行笔正是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个篆隶的传统。忽略行笔中法度构建者的笔下并不缺乏古法,问题是必然造成后世人对行笔的疏忽。面对这种情况,实现这次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是颜真卿、张旭和怀素。颜真卿的墨迹本《竹山堂连句》(尽管有人质疑)、张旭的《古诗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是这个时期篆隶笔法笔意提醒的代表作。从唐代的一些抄经到宋之后,我们看到篆隶古法是逐渐在丢失—看看这些抄经的入笔、转笔等,几乎都无可挑剔,可是它中段虚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因为这些经生写手跟初唐那些大家,跟后来的颜、柳都没法比。
第三次转型,我们以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描述这样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即书法的法度开始松动。宋代书法的笔法基本上是口诀化了,过去的屋漏痕、锥画沙、飞鸟出林……这种形象的东西相对就少了,而口诀化,像数学公式一样,因此就降低了人们对笔法、技法理解上的难度,书之妙道之类的“秘诀”就不再神秘了。米芾的“八面出锋”“风樯阵马”向中锋提出了挑战,规矩、法度变成了创作当中的工具,而不再是表现对象。我认为这是米芾在转型过程当中创造的奇迹。米芾的作品图式前所未有,即使从我们现在的现代性观念出发,米芾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当我们面对他的作品时,能说他没有法度吗?显然不是,他只是把法度分解了,由在一个点画内完成,变成了在几个点画内共同完成,甚至在一个字、在一行当中完成,所以他的笔法由表现进入了运用。
在这个转型期当中,黄庭 坚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庭坚转型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线条变化的两个极端。所谓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把点画拉长为长长的线,另一方面又把线条缩短为点,一方面拉长,另一方面缩短,一方面左右摇摆,另一方面还有上下的穿插。当然黄庭坚在转型过程当中最大的贡献还不在此,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强调篆隶为本这个观念。他针对当时学《兰亭》者不识笔意(就是忘掉了篆隶的笔意)的情况,强调篆隶笔法的重要性,他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他这里讲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你写哪一种书体,都与篆隶同法同意,即在笔法和笔意上是一样的。我们当下书法创作的问题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第四次转型是在复古与转型较量当中进行的。赵孟頫的复古主要表现在泥古、拟古、摹古上。赵孟頫书法的篆隶笔意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点画之间的关系上。赵孟頫生活在外族统治下,按理说,书法和绘画是他表情达意最好的选择,但是他选择了沉默,沉浸于拟古和摹古,“表情达意”在赵孟頫的作品中体现得不是很明显。对书法来讲,赵孟頫这种复古的影响十分强大,几乎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元代转型代表性人物是杨维桢。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用笔墨来进行自我表白,来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赵氏的复古反而远离了“二王”,杨维桢他们的笔下才表现出更多的“二王”精神。但赵孟頫的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以赵孟頫来替代“二王”,形成了以赵孟頫、文徵明等为替代品的“二王”形象—这跟我们今天的展览也有很大的关联。现在的展览为什么写得千篇一律,问题就在于取法不古,对“二王”缺乏真正的了解。而杨维桢就逆“替代品”思维而行,把自己的眼界开放到“二王”之前的篆隶,开放到章草,从而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一个高峰。
第五次转型出现了群体性、多样性的特征。我们上述这些转型都是一些代表性人物,但到了明代,我认为转型的书家几乎成了一个队伍,而且这个队伍当中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转型的个性。徐渭的癫狂,尤其是用行书的符号来写狂草,是史无前例的;黄道周,从理论上说,他把“二王”阐释得非常到位,但是看他的作品,体现的只是“二王”的精神;倪元璐,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书家,左右开张,用笔以方折为主,非常张扬;张瑞图创造了一种新的结体和行气的模式,结体紧,但行距宽,超越了人们的审美惯性;第一个张扬墨的人应该就是王铎;傅山在转型当中干脆喊出了“宁丑毋媚”……所以我认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转型的群体,以各种不同的姿态表现了自己的心性与意愿。
第六次转型就是碑学运动。其背景,一个是刻帖的一刻再刻,出现了“二王”、魏晋包括唐的信息的失真,人们苦心临帖的结果却渐行渐远;第二个就是台阁体、馆阁体在科举制度的保护下盛行;第三个就是甲骨文等这些新出土的材料也导致了这次转型。这次的碑学运动,是对帖学的提醒、纠正补充和捍卫,同时,一方面使篆隶书的创作与实用脱离,另一方面取得了碑帖结合的成果。
第七次转型主要是在20个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的转型我觉得具有被现代性特点。一个就是科举制的废除、硬笔的引入,倒逼书法向学科化、专业化发展;第二个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书法理论中史无前例地引入了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开拓了书法理论的视野;第三个是碑学思潮在这个时期结出了丰硕成果,出现了这个时期特有的书法范式—民国范。
书法的身份在这几个转型中不断被确认。
三、当代书法的身份认知
对于这几次的转型,我们的认识可能并不一致,但对前六次应该都比较熟悉,而对最后这一次很生疏,并由此而对书法产生诸多误会,导致书法身份认知遇到了新的危机。首先面临如何定义的问题。我觉得,书法的工具材料以及书法的表现方法、表现内容是定义书法的重要参考内容,把这些都包括进去,是给书法一个有意义的定义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书法是使用毛笔,通过汉字造型来表情达意的艺术。这个定义提出了判断作品的标准:一、书法的思想情感性;二、汉字的不可动摇性;三、技道关系的规律性。我着重讲一下工具与材料。书法的工具是毛笔,材料是汉字,这是不可动摇的。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外国人写字,亦有好坏的区别,但是以写字作为美术看待,可以说绝对没有。因为所用的工具不同,用毛笔可以讲美术,用钢笔只能讲便利,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美术。”林语堂说:“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蒋彝说:“汉字的结构为书法家提供了种种机会,利用每一个笔画,利用毛笔的每一个动作,进或退,顺或逆,重或轻,湿或燥,疾或徐,密或疏,肥或瘦,粗或细,连或断,来表现艺术才思。靠着毛笔的每一个运动,书法家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宗白华说,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一是毛笔,二是汉字。等等等等,不一一列举。
我们还可以从书法的内容来看书法的身份。那么书法作品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书法作品的内容和文本的内容是什么关系?书法的内容是通过笔墨的变化、行气的流动、各种造型元素的组合对比等表现出来的。按梁启超的说法是通过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和个性的表现体现出 来的。林语堂说:“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冯友兰也曾说:“书可以离开其所表示之意思,而以其本身使人观之而感觉一种情境……如雄浑,秀雅等,可使人感觉各种之境,而起各种与之相应之情。”熊秉明指出:“中国人欣赏书法,也并不就非把文字读出来不可,许多草书往往是难于辨读的,在我们没有辨读之前,书法的造型美已给我们以观赏的满足。所以真正的书法欣赏还在纯造型方面,等到读出文字,知道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或五言律诗的时候,我们的欣赏活动已经从书法的领域转移到诗的领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