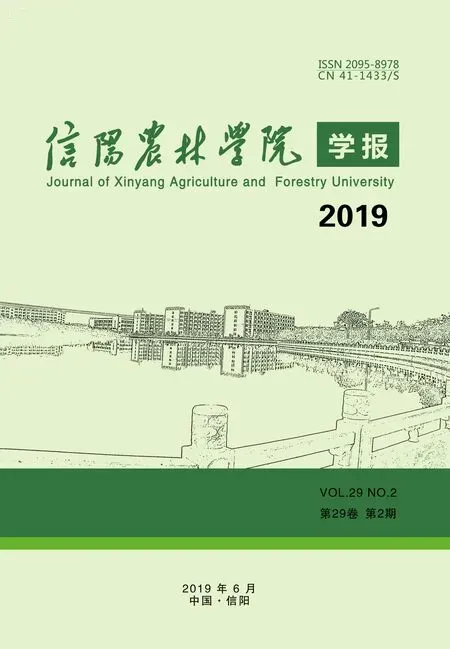三权分置下土地经营权性质研究
高林娜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大于经济利用功能,农地之上的身份性用益物权难以实现农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农地之上权利的权能被不当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立下,农地权利权能混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阻碍了农地流转。在保障农地对农户基本生活保障作用的前提下,放活经营权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1 土地经营权政策设计目标
以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生产经营制度尚并未发挥其“统”的制度优势。究其原因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将流转范围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此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流转难以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做强集体土地所有权,加强对农地使用的管控,破除农地在流转中的身份性,必须在法律上明确承包权的成员权性质,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成员权之间的关系。增设土地经营权是盘活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与农地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
农地作为财产的一种,具有财产性。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财产的价值被充分发挥才能够充分激发利用者的积极性。农地经营具有投资周期长、消耗资金大的特点。资金问题是困扰农业生产经营的难题。我国物权法规定耕地使用权不得被抵押,农地的融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理清土地经营权,畅通融资渠道,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解决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问题。
2 土地经营权性质的歧见述评
学界基于立法论、解释论、实践论就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提出了物权说、债权说、债权物权二元说、权能说等观点。其一,物权说。有学者将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定性为用益物权[1~5],并提出此权利是派生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次级用益物权”[6]。有学者提出“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将土地经营权视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设立的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7]。其二,债权说。有学者提出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性权利,该权利的得、丧、变更统一适用债权法的规则[8~9],并认为原承包经营权人将该宗土地交由第三人经营,属于“债权利用权”[8]。其三,债权与物权二元说[9~10]。此种观点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和经营期限相联系,认为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的属于债权,基于物权性流转的属于物权。还有学者认为权利期限5年以内的为债权,5年以上的为物权。其四,权能说[11]。该学说认为经营权是一种既可来源于用益物权又可来源于租赁权的权能,而非一项独立的权利。
上述有关土地经营权之法律性质的观点,除权能说无法照应三权分置政策的制度设计外,其他三类观点都从法理的不同维度对土地经营权法律性质进行了解读。其中,债权说者是从解释论视角理解土地经营权的,以土地经营权不符合一物一权原则与传统物权派生理论为由将其定性为债权;物权说者多从立法论视角探讨未来的土地经营权的应然定性;物权债权二元说者则是基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对土地经营权实然定性。笔者认为,三种观点争论的本质在于对物权和债权的性质与保护方法认识不同。目前,在我国的财产法体系中,物债二元的保护模式尚未被打破。对一种权利进行定性不能仅仅依据其不符合传统立法原理界定。目前,支持经营权债权论的学者多是从经营权物权化与传统理论相左进行论证,而未从物权和债权的区别以及物权和债权的保护方法不同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经营权系物权亦或是债权应从实践需要角度思考。
对经营权权利性质认识的不同,引起了对三权分置政策的不同理解,进而导致权利的派生路径不同。三权分置政策提出后,学界形成了两种三权分置的立法设计。一是原有制度与三权分置并行,即土地经营权系流转性权利,在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过程中产生。此时,农户享有承包权,农地的实际耕种人享有经营权。经营权的性质可为物权,亦可为债权。二是在立法上重构农地权利,以法律的形式明晰各种权利的权能,形成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核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为基础的农地所有及利用体系。持并行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立法上另起炉灶重构三权不符合我国农村改革稳步进行的立法方针,并且无法解决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对两权分立制度的路径依赖。持重构观点的学者认为,并行的立法设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法律上各项权利权能交叉混乱,更不能完成改善集体所有权弱小的局面以及政策改革的目标。
“三权”的权能存在完全与定限的关系,因此需要法律对每项权利的权能进行设计,在立法上单纯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予以分离是变相地将承包经营权做空。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孱弱的背景下,这一做法极有可能造成集体经济继续衰落。因此,释放农地的价值必须有强大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稳定农民的收益权,保障亿万农民的生活。
3 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证成
3.1 物权性利用较债权性利用之优势
首先,不动产具有价值大,不易移动,权利变更程序复杂等特点,其利用存在债权性利用与物权性利用两种。债权性利用与物权性利用的核心都在于发挥不动产的使用价值,但二者的客体和权利效力是不同的。物权性利用强调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和排他性,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意思表示,在使用上只需遵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即可。债权性利用的核心在于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主约定物的利用方式,其作用力表现为请求,需借助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物权性利用因其性质和效力能够解决目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期待利益保护、农地使用性质不被改变等问题。其次,物权化的债权的财产利用方式在本质上仍属于债权,债权的物权化本质为为债权赋予一定的物权效力,该物权效力发挥是在维护债权的相对性,促使双方履行契约。因此,物权化的债权性经营权不能满足经营权自由流转的需要。最后,债权的交换价值与担保价值无法与物权相较。无论是将经营权的债权性化为应收账款还是将其归入权利性抵押以实现其担保债权的功能都缺乏可行性与正当性。
3.2 经营权与传统民事权利体系的协调
物权性经营权定性有益于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科学的农地权利体系应实现农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担保价值在法律框架下的发挥,保障农民的权益,避免集体利益被不当侵蚀、农地性质被不当改变,充分维护经营主预期利益。在农地权利体系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核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权益保障之核心,经营权是农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担保价值发挥之核心[12]。两权分离制度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模糊与权能受限导致现实中出现集体土地所有权虚化现象,其核心价值大打折扣。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农地的实际占有、收益、有限处分的权利,其在权利体系中扮演着发挥土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及担保价值的角色。三权分置改革即是做实集体所有权、做虚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成员权。唯有确立物权性质的经营权,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经营权的权能,划定各种农地权利的界限,农地权利体系才能科学规范。
3.3 物权性的土地经营权之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新增了“土地经营权”一节,并规定了土地经营权的产生、流转条件、合同的效力及担保,但对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未做出明确规定。为落实三权分置政策,修正案指出农地的实际经营主体发生转变时不再必须由农村承包经营户经营。可见,土地经营权系权利流转中发生的权利,但认为其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派生是否合适值得商榷。物权法定来源在于法律对财产利益的重点保护,其是本源性与归属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农地利用权的变更不是单纯地农民财产利益的变更,更是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资本涌入农地市场后,农地的使用权将由家庭承包经营户转向种田大户、农场主,国家应加强调控。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内容、效力是目标稳定实现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