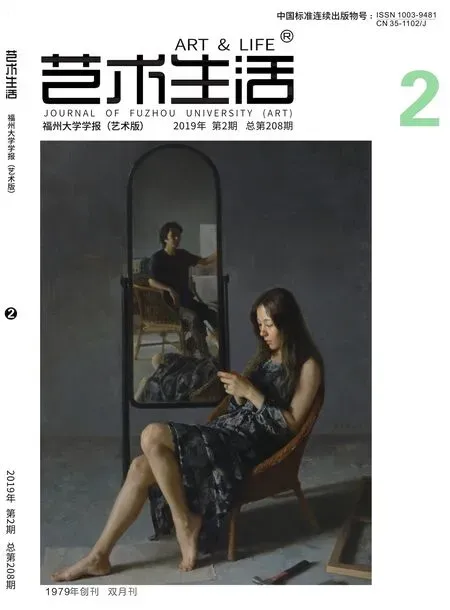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和重庆中国美术学院
韩 靖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526000)
1942年6月,在南洋各地举办赈灾画展宣传抗战近四年的徐悲鸿返回重庆,继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同年10月,国民政府中央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骝先先生为宏奖学术,提议利用由“庚子赔款”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提供经费开办中国美术学院,每月经费1万元,由徐悲鸿担任院长[1]。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所领导的这所美术学院不是美术院校,而是美术创作、研究机构。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员实行聘任制。中国美术学院聘用的研究员有张大千、吴作人。除知名画家外,徐悲鸿还聘请一些青年画家为副研究员,如李瑞年(初期兼任秘书)、陈晓南、艾中信、孙宗慰、张倩英等。在外地兼职的副研究员有张安治、黄养辉、冯法祀、沈福文、费成武等。助理研究员则有齐振杞、宗其香。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大都是徐悲鸿所在的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老师或者追随徐悲鸿写实主义艺术道路并得到其指点、提携的年轻艺术家。
1942年10月25日,当时《商务日报》刊登了“国立艺术研究院徐悲鸿院长在筹备中”的消息:“国立艺术研究院刻已筹备就绪,院长为名画家徐悲鸿,研究员闻已聘定陈晓南、张安治、孙宗慰等八人,并已在四川灌县觅得院址,于磐溪设立工作,并悉画家陈晓南即日赴川东购办绘画器材云。” 11月,徐悲鸿为选择院址,亲自前往勘察,《中央日报》于11日报道:“美术家徐悲鸿为筹备中国美术院选择院址,特已于十日自渝起程赴蓉,转灌县勘择。闻离灌县城赴青城山之路上,傍山有一广宇,风景清幽,颇宜绘事……”
中国美术学院的院址设在重庆郊区磐溪的石家花园的石家祠。徐悲鸿和在重庆的研究员全部搬进入住,朝夕相处,共同切磋艺术,提高画技。
中国美术学院是除中央大学艺术系之外,徐悲鸿推行他的写实主义创作观念的又一重要阵地。学习引进西方的写实技法和创作方法,在民初的“美术革命”风潮中呼声最高,康有为、陈独秀包括徐悲鸿都曾写文章撰述。但在此后的艺术实践中,写实主义并没有取得显著的创作成绩和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被史家称誉的1927—1937的“黄金十年”中,从学习西方来看,现代主义显然取得的成果更多,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中国早期的艺术留学生,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法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要远远大过古典或者写实。所以回国之后,这些留学生也更多地将现代艺术的观念带回了国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内举办的几个重大展览上都可以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力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写实主义绘画的薄弱和处于劣势。并且,无论是在1927年上海私立中华艺术大学主办的联合画展上,还是1934年的艺风社的展览上,徐的写实主义都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如叶秋原撰写的《联展归来》中写道:“徐先生似乎太注重于实在对象之再现!而一方稍为忽视些理想对象之现露。”绿荷所撰《美术联合展览会》写道:“迂腐的思想,执着他固有的成见,绝端不容纳新的或是进一步的思想。”
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徐悲鸿借双徐之辩,将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以及野兽派等大师骂了个狗血喷头,算是公开表达他的艺术立场,大概也有“出口恶气”的意思在里面。
正是因为战争的来临,严峻的现实形势,家国天下的集体文化心理,使得整体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无法继续下去,而关注社会人生为艺术标榜的写实主义等到了它的时代。其实早在1937年于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上,表现劳工题材的现实主义绘画就已经开始占据上风。如陈晓南的《建设时期》,孙多慈的《石子工》、李剑晨的《掘芋》、赵作忠的《劳动代价》等,其中作者多为徐悲鸿所在中央大学的师生或者写实主义的拥趸。这些作品,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或者米勒的作品。
而徐悲鸿本人在这次展览上的作品则是描绘广西抗日名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眺望》(原名《广西三杰》),一幅无论从题材还是色调都近似于宣传画的作品。
不管怎样,徐悲鸿这一路写实主义的胜利着实不易。因此,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终于使得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抗战中完全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徐悲鸿为自己艺术理念的胜利倍感兴奋,他在1942年发表的《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抗战改变吾人一切观念,审美在中国而得无限之开拓,当日束吾人之一切成见既已扫除,于初尚彷徨,今则坦然接受,无所顾忌者,写实主义者是也……战争兼能扫荡艺魔,诚为可喜,不佞目击其亡,尤感痛快。”[2]
抗战时期,徐悲鸿更是以极大的热情鼓吹写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方法,更加自觉地培养写实主义的年轻艺术家。而中国美术学院的创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舞台。正如徐悲鸿所言:“把国内有才能有理想的画家集中起来,创制以写实的技巧表现生活内容的作品,想开一条新艺术的途径。”[3]
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中,徐悲鸿再次阐发了他的写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并再次表达了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极端排斥和厌恶,认为“西洋艺术输入中土”,只是“进口许多污秽之物”,即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主义艺术,而中国自身就有“名山大川”,种种“丰繁博厚之花鸟虫鱼”,以及“数千年可征信之历史,伟大之人物,种种民族生活状态,可供挥写”,因此绘画“振之道无他,以人之活动入画而已”,也就是注重写生,走进生活,关注社会人生,取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徐悲鸿以写实主义理念领导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同仁也自觉追随和践行徐氏的领导,在创作中注重艺术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艾中信回忆说:“进中国美术学院以后,我遵照徐先生的教导,主要在生活中写生作画,酝酿创作题材。我于1943年冬天先到川西,后又转赴湖南安江前线写生。在战地写生中和国民党新六军联系时,凭我的一张中国美术学院的聘书,竟得到许多方便,这是与徐先生的名望有关的。”[4]冯法祀被聘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之时,正跟随抗敌演剧四队参加抗日宣传。徐悲鸿在给冯法祀的信中写道:“我聘你为副研究员,你仍留在演剧队,每年缴画若干幅。”冯法祀在追忆师徒之间的这段往事时写到:“我体会他这样做,既鼓励我努力作画,又不让我脱离生活,这也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艺术思想的体现。1943年,我将新作品《铁工厂》《第一把锤手》《开山》和战地写生画多幅,再次请他检查,他极其兴奋地肯定了这些作品,并提出新的要求。他说:‘这些画,群龙无首,你应选出一张画,进行加工创作。’他帮我挑选了《开山》这幅油画速写,要我立即着手大幅油画创作。为了进行这张创作,我在重庆北温泉呆了一年。”[5]
1943年7月下旬暑假期间,徐悲鸿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人员到灌县和青城山写生。除了在青城山写生,他们还经常去附近的灌县写生,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捕捉到纸面上。[6]
徐氏写实主义团队的代表人物有吴作人、冯法祀、艾中信、陈晓南、孙宗慰、齐振杞等。在徐悲鸿的众多弟子中,吴作人的名气最大。1928年,吴作人入南国艺术学院,在徐悲鸿主持的美术系学习。同年秋转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工作室学习。20世纪40年代,吴作人赴西部写生,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海、敦煌、康藏等地的边地风情和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生活,拓展了写实主义创作的新领域和新意境。徐悲鸿在1945年《中央日报》发表《吴作人画展》评论文章,特意指出:“作人一本吾人之写实主义作风,孜孜不懈,时以新作陈出为人所称道。”[7]
孙宗慰,1934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在校期间得到徐悲鸿赏识。1938年抗战爆发后,孙宗慰和吴作人、陈晓南、文金扬开赴第五战区前线宣传抗日。同年10月经徐悲鸿力荐留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41年随张大千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1942年又跟张大千去青海塔尔寺,见到蒙、藏少数民族热闹非凡的庙会。孙宗慰为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生活所吸引,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进行写生,创作出《藏族舞蹈》等具有浓郁民族风的油画作品。徐悲鸿看到孙宗慰的这些作品后,非常高兴,不仅聘他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而且亲自撰文表达了对于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肯定和期待之情:“尚我青年均有远大企图,高志趣者应勿恋恋于乡帮一隅,虽艺术家应以开拓胸襟眼界为当务之急,宗慰为其先驱者之一,吾寄其厚望焉。”[8]
冯法祀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1937年毕业时,他本可以去法国继续深造艺术,却在同学的影响下,投奔了红色阵营,并且跟随抗敌演剧队四队,辗转于桂、赣、黔、川数省,历时多年进行抗敌宣传。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冯法祀笔下的写实主义画面更为生动感人。冯法祀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有《靖西老妇》《演剧队歌手》《镇南关》《木瓜树》《俄孔的兵》《开山》《演出之前》《捉虱子》和《石林》等。这些在流亡途中和战争间隙创作的作品,散发着泥土和硝烟的气息,是真正符合徐悲鸿写实主义理想的创作,冯法祀也成为老师最为钟爱和给予厚望的弟子之一。1938年徐悲鸿从重庆写给远在武汉的冯法祀的长信中,由衷地表达了对冯法祀独特的艺术生活的肯定乃至向往:“倘若我非因身体不佳,决不令弟一人为中国美术事业受此艰辛。”[5]
虽然是以表现抗战题材为主,但是冯法祀的作品绝对不是概念化的和题材先行。他曾说:“我画的宣传画不是漫画式的符号,都是写实性的人物,人物都是经过推敲的。”[9]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冯法祀总是能够提炼出事物最生动本质的细节,作品既富有宣传的力量,又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创作于1946年的《捉虱子》是冯法祀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军人在战斗的间隙捕捉身上虱子的细节表现出艰苦的抗战生活,令人动容。
齐振杞虽然不是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教出来的科班学生,却受到徐悲鸿的器重,1943年,26岁的齐振杞就被徐悲鸿聘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并在抗战后随徐悲鸿北上,成为执掌“国立北平艺专”之后的主力干将之一。齐振杞也是非常出色的写实主义画家,先后有《北京街头》《拾煤渣者》《东单小市》《菜市》等佳作问世。描摹北方古都市井风俗,充满生活气息。另外又有《嘉陵江上》等风景画作,《袭击》《冲锋》《负伤》等抗战题材作品。《双人肖像》是他的人物画作代表作,描绘一对普通夫妇肖像,人物刻画传神而自然—男人手持烟卷,有些茫然而疲惫地看着前方,女人手不停歇地织着毛衣,却定格在抬头的一瞬间,似乎看到了画外的观众。可惜,这位非常有前途的写实主义画家,却于1948年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2岁。
1944年初,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第一届展览,全部展品约150件,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粉画、竹画、书法。其中徐悲鸿的《奔马》《山鬼》、孙宗慰的西北边疆写生、冯法祀的战场素描、黄养辉的肖像画最惹人注目。从展品可看出抗战时期新写实主义美术的成长。陈树人在《中国美术学院画展献辞》中指出:“中国美术学院之创立,悲鸿先生领导多数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和精纯的绘画技能的优秀同志。用他们的心血来灌溉图画的壮朵,这次展览,就是他们力作的结晶。”[10]
然而,作为写实主义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却也并没有创作出多少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抗战题材的作品。徐悲鸿直接取材于现实的创作也只有1937年初到重庆时创作的《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少数作品。影响最大的是1939年创作于新加坡的《放下你的鞭子》,但是画面主要描绘的还是女演员王莹的角色造型。徐悲鸿更擅长表现经史题材,始终难以摆脱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而他在重庆期间公开展览表现现实关怀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马、雄狮、公鸡等为表现主体的“借物咏志”类绘画。虽然“借物咏志”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毕竟和真正的写实主义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徐悲鸿本人在解放后曾自我剖析:“我虽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人民大众。”[11]
抗战时期,写实主义通过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平台,通过徐悲鸿以及众弟子的艺术实践得到了发展壮大,并为写实主义在抗战时期向以“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为旨归的新写实主义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整体来看,徐悲鸿及其所领导的写实主义团队,即使在民国时期,已经流露出偏向宏大叙事,甚至阶级意识,配合现实政治宣传等倾向。虽然事实上徐悲鸿的精神气质如其早年合作者田汉所说“是一个古人”,然而徐悲鸿所体会过的生存艰辛和任侠好义的性情却最终使他倾向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美术以及艺术观念,从而为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能够成为1949年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重要力量埋下伏笔。然而写实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基于人道主义之上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批判,以及对于平凡人生的记录。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创作的作品即表现出了对于平凡生活的关注,比如在1927年联合画展展出的《远闻》一画,表现咖啡馆一角一个埋头读信的女孩,虽然表现的是公共空间,但深入到了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件成功的写实主义作品。但是后来他很少再有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抗战时期,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其他写实主义画家那里得到了表达。如吕斯白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表现四川乡下生活的《庭院》,秦宣夫的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反应时代风云的《母教》等,还有符罗飞的以速写式的有着表现主义意味的艺术语言记录普通灾民生活、批判社会不公的作品,可以说,这些画家和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创作团队一起,在抗战时期共同为写实主义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院址设在北平艺专内。抗战胜利后,因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经费不支,乃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1947年,中国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的展厅里举行联合美展,这是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创作团队的集体亮相。关于这次展览,李天祥撰文写道:“徐悲鸿先生和艺专新聘教师们的作品展览,却完全是另一天地,使长期处于被屈辱、被欺凌几近麻木的古城北平为之震撼。在展览会上我看到了徐悲鸿先生《愚公移山》《奚我后》《会师东京》等巨作,也第一次看到冯法祀先生的巨幅创作《演剧队的晨会》。这些作品使我热血沸腾,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看到的不仅是艺术作品,而是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灵魂。”[12]
中国美术学院的名义维持至1949年北平解放,但是徐悲鸿所创立的写实主义美术体系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跨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