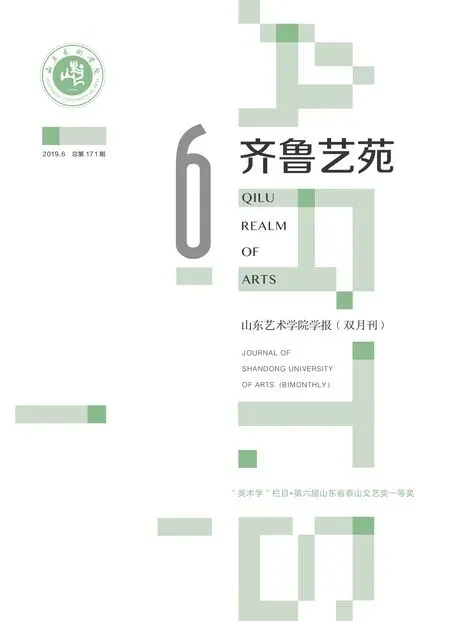李渔的艺术管理思想与实践之刍议
昝 桐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李渔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产业的先行者”,是因为在明清之际繁多的戏班中,李渔的戏班是较为特殊的。这主要表现在除了具有其他戏班相似的娱乐、营利性功能外,李渔的戏班还具有较完善且独特的经营与管理理念。由于受到李渔戏剧创作研究的影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忽视了李渔在戏剧创作和戏班演出之间的管理关系。事实上,正如叶长海先生指出的:“戏班是一种群体性的艺术活动,又是一项社会的文化事业,因而它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各种经营管理活动。”[1](P192)因此,笔者将以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等著作为主要依据,并结合相关史料,对李渔的艺术管理思想理论的形成及实践,进行粗浅的梳理与分析。
一、李渔的艺术管理思想成因
(一)个人原因所迫
李渔出生在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后移家金陵。虽然一直生活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但他始终是一介布衣文人,没有官位与俸禄。在衣食无着的时候,对那些能以才艺致富的文人很是羡慕。在没有组建戏班之前,李渔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卖文所得。除了替人写序、楹联之类的文章收取微薄的报酬外,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出售自己的文集、传奇等作品。特别是由他编写的剧本,在当时颇受欢迎,正如范骧在《意中缘·序》中所言道:“凡遇芳筵雅集,多唱吾友李笠翁传奇……当事诸公购得之,如见异书,所至无不虚左前席。”但这依然不足以使李渔摆脱困顿文人的境遇。
直至康熙五年(1666),李渔游至陕西观看当地伶工表演自己的剧作《凰求凤》时,精通戏曲表演的乔姬建议李渔组建自己的戏班,目的是“此后主人撰曲,勿使诸优浪传,秘之门内可也。”[2](P97)次年李渔游至兰州时,又纳王姬等若干少女。至此,乔姬、王姬等人的加入,使得李渔的戏班初具规模。戏班组建起来,李渔便开始进行管理。因为组建戏班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姬妾们的演出而增加收入,同样也是戏班从事营利性演出的动力。一般而言,蓄养戏班需要大量的财力及人力支撑,而李渔的优势在于他既不需要购买大量的剧本,也不需要招聘演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戏班管理与运营的成本。
(二)社会原因造就
自两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形成了以瓦肆与勾栏为演出场地的经营场所,从而构成了由民间艺人(即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商品经济市场——市民阶层(即艺术产品的消费者)近似现代商业演艺产业的形态。特别是明清朝之后,随着全国商业活动逐渐南移,最终形成了以长江水道为途、江浙地区为核心的全国性商业流通网,使得这些商路所覆盖的地区具备了演艺产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及观众基础。
康熙七年(1668),李渔北游回家后,即带领戏班从金陵出发至安徽,途径江西后抵达广州进行出游。这条线路与当时的商业流通路线完全吻合,这并非是一种巧合。从中可以看出,李渔是带着较强的目的性选择路线。李渔自幼生活在商业气息浓重的江浙地,所以在北游后发现当时的北方城市的市场化经济较弱,对于演出行业来说没有足够的观众基础。因此,李渔北游后选择了长江以南的商路沿线,并将其作为今后的商业演出范围。换而言之,这次出游实际是李渔的一次市场考察,为其后来的演艺经营市场布局奠定了基础。
二、李渔的舞台监督管理
舞台是李渔的戏班进行演出活动的重要载体,从剧本编写、导演排练直至演出,李渔始终贯穿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李渔从内容创作、表演形式、演员等方面都有着较为系统的舞台管理措施,这类似今天的艺术总监的职责作用。因为舞台演出的质量好坏,将直接影响戏班的收益。在其著作《闲情偶寄》一书中,前半部分的内容就是他对舞台监督管理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
(一)对内容创作的管理
《闲情偶寄》中的第一章“词曲部”,主要谈的就是演出内容上的规范与规律。如“词曲部”的题词是这样说的:“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3](P7)由此可见,李渔深刻认识到了演出内容的社会功能性,所以赋予了内容创作的劝善戒恶的社会属性,并将这种价值取向作为了内容创作及演出的宗旨。
从“词曲部”的具体内容来看,李渔将内容创作的主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归纳,分别是:“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等。不难看出,李渔对内容创作管理进一步深化。其中将“结构”置于内容规范的最前端,是因为“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4](P11)也就是说,在李渔看来,无论在创作的形式上还是规模上,结构之端是抽象的,是剧本的立本之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如主题不佳,李渔则认为“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此外,李渔在给戏班编导剧目时也会亲身实践,书中有云:“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5](P57)
李渔正是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舞台监督管理的核心思想着眼于剧本创作的结构上,把握剧本创作与演出内容的内在规律,为自家戏班及其他戏班提供了演出内容的价值内核与标杆的管理导向。
(二)对表演形式的管理
李渔的剧本创作及改编,最终的输出点是搬到舞台进行演出。因此,李渔利用自编自导的实践经验,在《闲情偶寄》第二章的“演习部”中,提炼出了由内容创作到表演形式中程序化的先后关系,即:“选剧第一”“变调第二”“授曲第三”“教白第四”“脱套第五”,有效的将内容创作与表演形式珠联璧合。
在每一个环节中,李渔都分别从舞台传播到受众接受的角度,阐释了如何规范舞台呈现中的问题。例如在“选剧”中,李渔列出了两条标准:“别古今”、“剂冷热”,即在面对不同题材、不同内容时如何处理恰当的方式。
在不同题材面前,李渔倡导:“古本既熟,然后间以新词,切勿先今而后古……旧曲既熟,必须间以新词……听古乐而思卧,听新乐而忘倦。”[6](P84)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古”与“今”,我们可以适当的理解为严肃题材和娱乐题材。也就是说,在编选剧目时,首先要表演熟练的传统且严肃的剧目,因为传统内容已是精益求精,即可以展现演员的扎实功底,也可让观众赏心悦目。但也不能一味的追求传统,还要兼备娱乐功能的新剧题材,从而达到耳目一新的演出效果。
在面对不同的词句内容时,李渔意在冷热调剂。冷静之词,文雅之曲,常常令人生倦。“然尽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文章极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难稍加润色,插入管弦?”[7](P86)意思是,在面对词句高雅而内容通俗的作品时,应当添加一些衬托词句的辅助手段,从而达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传播效果。如“是以人口代古乐,赞叹为战争,较之满场杀伐,钲鼓雷鸣,而心不动,反欲掩耳避喧者为何如?”[8](P86)
(三)对戏班人员的管理
艺术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的管理,特别是以演出为核心的戏班组织,演员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以现代艺术管理学中舞台监督的角度来说,对表演艺术团体的管理,通常分为行政管理和演员训练两个方面。这在李渔的戏班中都有所体现。
演员的行政管理就是对其提出相应的严格要求,以保证整个演出团队的利益和正常运转。对于李渔的戏班而言,大部分演员是其家眷。上文提到的乔姬与王姬,即是李渔的姬妾,亦是戏班的台柱子。李渔在面对这样的特殊关系时,仍然体现了其行政管理的原则。即强调演员“才”和“德”的重要性,并且注重树立典型。如他曾夸赞乔姬:“同侪三五尽芳华,谁不推崇让尔先。鹤立鸡群无傲色,骥随驽后亦恬然。”[9](P208)显然,李渔以“有才不傲,无才不妒”的品德作为考核演员的标准。相反,对于戏班中的妒而败类者,李渔的态度则是怒而遣之。
在演员的训练方面,多见于《闲情偶寄》中的“声容部”,从“选姿”“修容”“治服”“习技”等方面,无不详细地规定了演员在平常训练中所要注意的事项。如“选姿”部分就从“肌肤”“眉眼”“手足”“态度”等四个方面,要求演员如何对自己的神形及肢体进行训练。在演出过程中,李渔还担任了戏班的艺术指导。如他和王姬“即不登场,亦常使角巾相对,伴麈尾清谈。”[10](P217)这种以实际指导作为舞台监督的方式,不仅使李渔的戏班表演更具专业化,也增强了表演团队的协作能力。对戏班的舞台监督管理工作,同样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李渔的演出经营管理
李渔在完成舞台监督管理工作后,接下来考虑的则是如何经营他的戏班,以便能够适应市场进行商业演出。除了上文提到的市场考察外,李渔同样也做了许多近似现代制片人的经营管理工作。
(一)出色的筹资能力
在现代的演出经营活动中,组织一次商业演出通常首先需要制片人去寻求各种各样的赞助,以支撑演员的排练、剧务的筹备、演出的宣传等事宜。李渔作为戏班的管理者,筹备资金自然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务,并且融资的手段多样。
其一,因地制宜获取资源。据相关史料记载,早在顺治六年(1649),李渔还未涉足戏班经营时,便在家乡主持过修建水坝、祠堂等公益事业。因此,在筹资募捐方面业已积累了相关的经验。如康熙十一年(1672),汉阳当地正在为修葺鼓楼而筹资,恰逢李巡游至此,便代郡守撰写了《汉阳府重建鼓楼创立马头募缘引》一文。文中借用政府财政预算以及郡守带头捐款的方式,达到了筹资的最佳号召力。后来这也成为李渔带领戏班巡演过程中考察市场的方式之一,即“每至一方,必量其地之收入,足供旅人之所。”[11](P204)因此李渔先后去过福州、杭州、苏州、汉口、北京等富庶之地进行巡演,并热衷于当地政务之事,结交政府官员,为之后的演出实现名利双收的效果。
其二,利用名人效应融资。在杭州生活期间,李渔已是家喻户晓的编剧、出版商,并由此结识了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当他听说李渔即将出版新剧本时,作为粉丝与读者的他便提出愿意为剧本作序,并赠送银子作为赞助。这一举动让李渔发现了一种获取资金的渠道,将个人作品出版的同时,还吸收有特殊需求人群的文章或其他作品,这有点像今天“蹭流量”的意思。对于李渔来说,既满足了自己的出版需求,还可以借此获得额外的资金,这对其戏班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效益。
其三,打造平台影响力。在管理戏班的同时,李渔主要经营着自己的书铺——芥子园,以此为平台结交了诸多文人雅士及达官显贵,并时常在这些人物面前进行剧本的试演活动,因此获得了这些人的“缠头之赐”,即馈赠。如“缠头已受千丝赠,锦句何殊百宝钿”[12](P332),无论馈赠的是金银还是物资,李渔亦都使用在了戏班的经营之中。所以这种馈赠亦可视为对戏班演出活动的资助。
(二)精准的市场运营
李渔作为集作家、导演、艺术总监、制片人于一身的戏班管理者,最终面向的是大众消费者。对市场的把握及营销的运作,是小说畅销及演出盈利的必需前提。因此,李渔把观众奉为首位,始终以观众需求作为演出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根据观众的实际情况和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的市场细分及营销策略。
其一,针对不同地域的观众,李渔采取了因地制宜的营销模式,“如所演之剧,人系吴人,则作吴音;人系越人,则作越音,此从人起见者也。如演剧之地,在吴则作吴音,在越则作越音,此从地起见者也”[13](P124);其二,着眼于女性市场。李渔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深知演出市场的最大消费者是达官显贵及其家眷们。所以李渔的小说及编演的剧目,更多的选择是以女性视角来描写风花雪月的故事。如《怜香伴》《风筝误》《凰求凤》无不是以女性的角度作为剧本的原创点,尤其是《怜香伴》中直接大胆的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女同性恋作为题材。这即符合了当时男权文化中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也迎合了女性观众的猎奇需求;其三,依据受众的欣赏趣味,及时更新演出剧目。李渔通过观察发现“今人喜读闲书,购新剧者十人而九,名人诗集,问者寥寥。”[14](P27)所以在演出中尤为注重剧目的通俗机趣及情节的离奇。在剧目创新的道路上,李渔最忌网罗旧集,追求“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的效果。这样不仅能够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兴趣及持续关注,还可以使戏班的受众市场最大化。
(三)超前的版权意识
在现代演出行业中版权得不到保护,任由他人及机构进行翻演会造成版权所有者的经济损失,亦是对版权管理不当的表现。因此,版权的保护与开发是当下艺术管理中的一大课题,而对于300年前的艺术市场来说也不例外,李渔同样被盗版问题一度困扰着。但经过长期的市场经营摸索与实践,李渔很快便展现出了超前的版权意识。
在版权保护方面,李渔以身作则,将“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但由于当时印刷行业已发达,很多书商靠翻刻各种典籍、传奇、小说等作为发财之道。作为畅销书作家的李渔,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据说他的作品只要在杭州一问世,三天后江苏、南京等地就有书商盗印。为此,李渔四处奔走,查找源头,与人打官司,但收效甚微。后来李渔索性搬到了南京,由此建立了私宅兼具书铺的芥子园,并别出心裁的设计了“芥子园名笺”,印于出版的文集、传奇等作品上。同时公开发表声明:“金陵承恩寺中有芥子园名笺五字署名者,即其处也……”,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李渔的版权,同样也成为了其建立品牌、开发版权的一种方式。
随着作品颇具名气,李渔发现了版权价值扩大的商机。比如白话小说《连城璧》,其雏形最早鉴于李渔在顺治时期刊行的小说集《无声戏》及《无声戏二集》中,后将二书重新编排,易名为《连城璧》。得到市场效应后,再经改编,添加新作,推出了《连城璧外编》,并与《连城璧》合称为《连城璧全集》。同时,由于戏班的存在,李渔还完成了从小说内容到商业演出这一产业链的上下游对接,这与当下网络文学IP改编为影视剧的价值产业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此后的小说出版中,我们甚至可以在目录下看到“此回有传奇即出”的字样。由此建构了以小说版权为核心,衍生商业演出的价值循环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李渔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IP产业的领航者。
小结
综上所述,李渔从作家到文化经营者的转变,从内容创作升级为内容制作,这其中的过程必然离不开其艺术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虽然尚未达到现代艺术管理体系的标准,但其管理与经营的经验,为清末职业化的戏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了解艺术管理的渊源提供了研讨价值。
虽然中国古代演艺管理实践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还有待挖掘。艺术管理虽属新兴的专业,但它并非真空出现,而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相信,艺术活动始终伴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挖掘前人的艺术管理思想与实践,一方面有助于艺术管理学科发展的借鉴与思考;另一方面对我国艺术管理的史论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