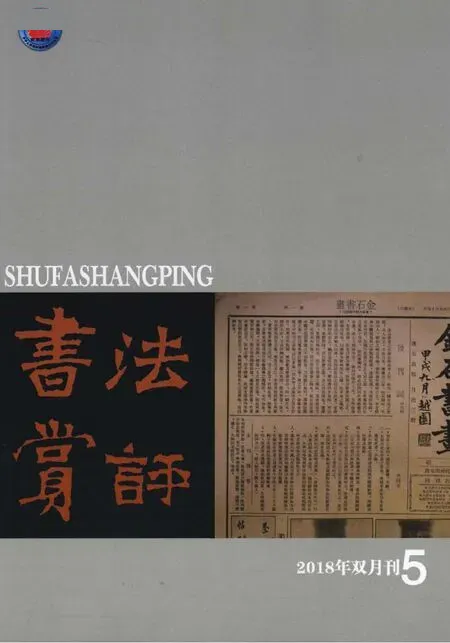崂山 “西晋石刻”书者考略及审美分析
在崂山刻石中,西晋刻石历史最为悠久,位于沙子口街道北姜哥庄社区北侧的烟台顶之巅。西晋石刻于一石之上分两处,每处从右往左为 “勃海朱耒武 (一列)晋太安二年岁在癸亥 (一列)平原羌公烈”和 “高阳刘(一列)初孙 (一列)魏世渊 (一列)晋太安二年”。[1](下称 “朱耒武刻石” “刘初孙刻石”) 《崂山文化遗产图鉴》中认为: “石刻虽不十分工整,但仍可从其粗犷的笔迹中得见汉隶余韵,并已显现出向魏碑转化的趋势。”[2]但是刻石上仅存四个人名和三十二个字,翻阅古籍群书,关于崂山西晋刻石虽有收录,作者信息却一无所知。本文试图结合西晋末年的历史背景和冀州的人口流徙等资料,对作者进行考究,然后比对同时期的刻石进行了艺术审美分析,以期对崂山刻石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晋太安二年 (公元303年),是西晋末年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根据 《晋书·地理上》可知,在西晋末年时期,高阳国、勃海郡和平原国均属于冀州,平原国位于南部,其北部接壤勃海郡。高阳国位于冀州北部,与河间国与勃海郡相望。在三郡国之中,平原国距离崂山最近 (相当于今天德州到青岛),这在西晋时期亦是路途遥远。那为什么三郡国之人会不远千里来到青州长广郡的烟台顶附近呢?笔者认为,平原国和勃海郡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内迁和并州流民涌入造成的;高阳国则主要由于天灾引起。
首先来看平原国和勃海郡。史书中并不见平原国和勃海郡因为少数民族内迁而导致人口流徙,但是可以参考冀州的邻州——并州。 《晋书·匈奴传》: “匈奴与汉人杂居,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莫不有焉。”又根据刘掞藜 《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 “匈奴人这许多杂入山西汉族之内,当然也要大大的兴起 ‘生存竞争’,而匈奴人 ‘天生骁勇,弓马便利’,山西汉族实在不能抵抗……山西的汉族开始向南流入河南。”[3]由此可知,并州人因匈奴内迁而流徙。冀州同样也受到乌桓少数民族的内迁。从 《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可以看到,乌桓分布于勃海郡和平原国接壤的区域,占据不小面积。两郡国必然与并州遭到匈奴内迁因此 “生存竞争”一样。这是两郡国外迁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并州人流徙到冀州,与当地人形成 “生存竞争”导致冀州人外迁。刘掞藜 《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 “山西的汉族遂大大的 ‘并州饥馑,数为胡寇所掠’, ‘就谷冀州’。”由此可见一斑。并州的乐平国和新兴郡相距冀州的平原国和勃海郡不远,极可能是流民迁入之所。冀州的平原国与兖州和青州接壤,但入兖州有泰山阻隔,入青州更加方便。根据刘掞藜研究,公元298年至公元307年冀州像河南和山东流徙一万多户,人数达到十万之众。并州东北接壤冀州西部、西南和并州,也是并州流民迁移之所,而位于山东的兖州、青州和徐州北部相对生存竞争小,尤其青州东部和徐州北部,是流民迁入的极佳之地。因此,勃海郡的朱耒武和平原国的羌公烈应该是因为并州人和乌桓人迁入而引起生存竞争流徙到长广县烟台顶附近的。
再看高阳国。高阳国位于冀州北部,接壤幽州,滱水、滹沱河等四条河流过境,尤其中北部水系发达,三水交汇。根据 《晋书·五行志》记载: “晋惠帝元康八年冀州大水,太安元年又遭水灾,其前一年,则遭旱灾,水旱交至。”晋惠帝元康八年为公元298年,太安元年则为302年,前一年则为公元301年。冀州五年内旱涝大灾则有三年,民不聊生,纷纷流向东南。北有水患,西有流民,东部是海,只能向冀州南部和兖州、青州流徙。高阳国的刘初孙和魏世渊极可能就是随着流民来到长广郡烟台顶附近的。
综上所述,崂山西晋刻石中朱耒武、羌公烈、刘初孙和魏世渊为冀州迁入长广县的流民。但是,西晋刻石的书者未能确定。从两处刻石的风格上来看: “朱耒武刻石”书风较为统一:结体较为拘谨,笔画舒展性较弱,应是一人所刻; “刘初孙刻石”在笔画和结体方面略存差异,书风不太一致,应为魏世渊和刘初孙两人所刻。其中, “高” “阳” “太 “二” “年” 长横皆有 “燕尾”, 与 “世” 相异; “高” “晋” 转折处竖画外扩, 而“魏”却内敛。因此,笔者认为 “高阳刘初孙晋太安二年”应为刘初孙所刻。
另外,由于刻石年代久远,长久以来在不同的版本中有着 “朱耒武”和 “朱泰武”的争论。以崂山区史志办公室等大部分版本中都认为是 “朱泰武”,而 《崂山文化遗产图鉴》中则认为是 “朱耒武”。通过原地的考察和字形的分析, “朱” “耒”两字下半部分结构相同,刻石中亦极其相似,撇短捺长,撇捺夹角很窄,若为 “泰”则很难容下 “水”部。因此,笔者也认为是 “朱耒武”。
最后,两处刻石在审美风格的差异和楷书风格的渐变亦值得关注。 “朱耒武刻石”虽然在字形上有隶书的扁平的风格,但在笔画上显现出了北碑的风格,撇捺时见粗顿,捺向侧面伸展,横画超出字形边界,风格奇肆,与同时代陆心源 《千甓亭古砖图释》中收录的 “西晋太安二年万岁不败残砖”风格相似。 “刘初孙刻石”的隶书意味更加强烈,在长横上有明显的燕尾,微见波折,结体工整,风格朴实粗犷。这种审美风格的差异可能与地域差异有关。
但是综合两方刻石的笔画、字形来看,都体现出了 “意削减,楷意增强”的明显风格。在字形上, “朱耒武刻石”和 “刘初孙刻石”虽然大小不一,但除了 “朱” “公” “太” “平” “世”之外,其他字都呈现出方正后者高拔的楷书风格特征。在笔画方面,以 “朱耒武刻石”和 “刘初孙刻石”中的 “武”和 “高”为例。楷书中的 “武”在上边两横笔画中,皆为上短下长,而在隶书中则为上长下短,如下:

而 “朱耒武刻石”中 “武”则明显呈现出楷书的笔画特征。这不仅表现在横画上,还有斜钩的倾斜度方面,显然倾斜度更加垂直,与楷书笔画基本相同。再以 “高”为例。 “高”在楷书中上边长横明显比横折钩中的横短,在隶书中却上长下短,如下:

而 “刘初孙刻石”中 “高”则明显呈现出了楷书的笔画特征。在长横上也明显没有了蚕头燕尾和波磔的隶书特征。但是在点画上,则明显脱离了隶书 “以横代点” “以竖代点”的特征,奠定了楷书点画的重要基础。而在“口”的结字部件上则依旧保留着隶书的特征。
综上所述, “朱耒武刻石”和 “刘初孙刻石”在笔画、字形方面既保留了隶书的遗韵,又出现了楷书的特征,但是楷书的锋芒更加显露,是隶书向楷书转变的重要代表,与青岛大泽山刻石一道构成了地域性隶楷书体转变的历史见证,在青岛地域性书法史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注释:
[1]王保生: 《崂山文化遗产图鉴》,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2]王保生: 《崂山文化遗产图鉴》,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3]刘掞藜:《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 《禹贡》第4卷第11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