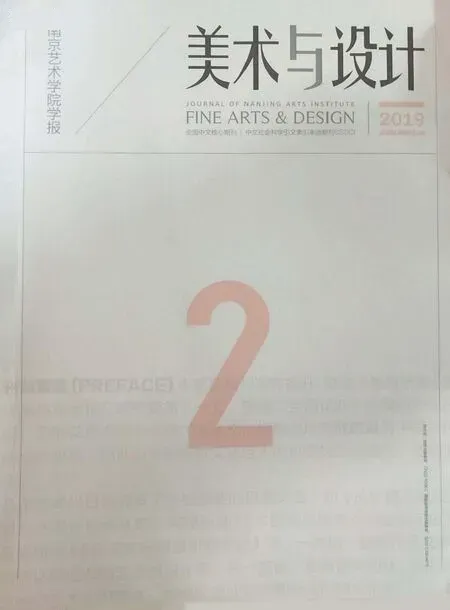“王画”
——陈独秀“美术革命”的思想闸门
曾小凤(中央美术学院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北京100012)
通过研究吕澂“美术革命”的批评视景[1],笔者发现,陈独秀关于“美术”的批评视景与吕澂和鲁迅二人都不同:他既不关心吕澂切实提出的如何从“美术之弊”达到“美育之效”的教育改革方案,也无意于像鲁迅一样对中国美术界发出“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而是要树立起“美术”这一宗的“革命”对象。这在客观上呈现为三种相互联系和制衡的批评立场:吕澂的“美术革命”在根本上指向的是民初以来美术教育的问题,这促使他自觉地关注“美术”这一门的学科属性,如在“革命之道何由始?”中阐明的四事——“美术之范围与实质”“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欧美美术之变迁”以及“美术真谛之学说”[2]等,实际上是要建立以“美术”为核心范畴的学术知识系统。鲁迅的“寂寥之至”,其实是从肯定以上海美专为代表的美术教育事业出发,对五四时期中国美术界所作的一种总体观察,他关切的是美术家的思想问题而非美术教育的体制问题。这与鲁迅以“美术家”为中心的批评视野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只有“进步的美术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美术界的前途。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则是把批判的激情集中到了特定的艺术门类——“中国画”上,并旗帜鲜明地喊出“革王画的命”。
这就将“美术革命”的矛头对准了“王画”,它关切到两个方面:第一,“革王画的命”这个议题,是在陈独秀对“王画”所作的批判和否定中获得它的意义的。第二,“王画”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这一对象性特征决定了陈独秀“美术革命”的性质。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切地探讨“王画”这个概念及其运用本身,也即,作为概念的“王画”到底特指什么?“王画”是如何在陈独秀关于“美术”的批评话语中被建构成革命对象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开启陈独秀“美术革命“思想闸门的入口。
一、作为权力话语的“王画”
所谓“王画”在陈独秀这里不仅是一个单一词汇的运行问题,而是与“清朝的三王”“王石谷的画”“王石谷的山水”“王派”“王派画”等相连接,乃至与“中国恶画”“迷信” “复写古画”“恶影响”“画学正宗”“盲目崇拜的偶像”“最大障碍”等词和概念相涵容互动,共同构成的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倾向性的权力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王画”相关的语词中,陈独秀并没有直接用“四王”一词,反而是确切地讲到了“清朝的三王”“王石谷的画”和“王石谷的山水”等。查阅清代画史著录,可知“四王”是一个晚出的概念,更常见的是“二王”或“两王”“三王”等名目。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比较时兴的是用“两王”或“二王”的名目来称号王时敏和王鉴,这在时人题赠王翚(字石谷)的诗画以及论著中尤为常见;而“三王”之说,是在王石谷与乃师“二王”(王时敏、王鉴)齐名画坛时流传,这于王士禛的诗文中屡见不鲜。据阮璞先生考证,“三王”名目在清代画史中流传时间最久,甚至到了名列“四王”之一的王原祁在画坛崭露头角之时还很流行;而“四王”之说的出现及流行,一则是在“四王”其人已经谢世之后;二则多见于道光、咸丰以降的画史著录,包括“四王吴恽”“四王吴恽六大家”等用例[3]。
不难发现,在清代画史的“二王”“三王”及至“四王”的名目递演中,王石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离开了他,“三王”之说不复成立,而“四王”名目亦难以演绎而成。纵观王石谷的一生,早年得“二王”赏识提携,画艺精进;中年驰誉丹青,与乃师齐名而享誉“三王”之称;晚年荣宠于清廷,受命绘制《康熙南巡图》。这样显赫的经历,在张庚编纂的《国朝画征录》中卷之首的“王翚”条中有详细记载。
张庚的评述有两点特为重要:其一是强调王石谷与“二王”的画学渊源,谓“石谷既神悟力学,又亲受二王教,遂为一代作家”;其二是借康熙初年两位名家曹溶和吴伟业之口称“石谷,画圣也”。作为清代第一部记叙当朝画家的断代画史,《国朝画征录》是于王石谷去世二十年后刊刻 ,张庚的论评可谓是一种盖棺定论。而清代及民初知识人通过他的画史论著,奉称王石谷为“一代作家”乃至“画圣”,自在情理之中。直到陈独秀1919年喊出“革王画的命”时,王石谷才被推下“画圣”的神坛。只不过,这场革命的突破口是“王画”而非“四王”。这就涉及到陈独秀“美术革命”的对象性问题,也即他到底是要革谁的命。
如果陈独秀是要革“四王”的命,为何他不直截了当地打出“革四王的命”的旗号?毕竟“四王”作为一个画史中既有的知识概念,它在公共舆论的传播过程中不会引起任何误读,注重报刊媒介宣传的陈独秀不应忽视这一点。相比之下,“王画”却是一个不自明的概念,它的概念内涵取决于使用者的叙述语境,如明人汪珂玉在《珊瑚网画跋》中是用“王画”指称王维的画。而在陈独秀这里,“王画”首先是一个围绕“王石谷的画”展开的概念,但这种关联是复杂的,主要体现在他谈论王石谷的方式上。首先,陈独秀并不是从清代“四王”或“四王吴恽”的整体视野入手,而是把王石谷单独抽离出来,从他的作品——即“王石谷的画”、“王石谷的山水”等——出发进行尖锐地批判和否定。这其实是有意避开清代画史既成知识概念的束缚,把“王石谷的画”作为独立于画家本人的一种象征系统来加以评判:一方面,陈独秀很容易在言说中发展出一套具有价值倾向性的说辞,诸如“王石谷的画”是“中国恶画的总结束”,“王石谷的山水”是“迷信”等;另一方面,一旦这类说辞离开了特定的指称对象(如王石谷),它自身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漂浮的能指,像“王派”以及“王派画”等概念的涵义更多地是受着叙述语境而非所指的调控,因此很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认知混乱。比如“王派画”,我们只能从陈独秀所说的“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一句中作出推断,但与吴历同时代的不仅是王石谷及其“石谷派”,还有王原祁的“麓台派”。究竟谁是陈独秀所指的“王派”,就难分辨。
可见,要从陈独秀的《美术革命》中寻求“王派画”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是徒劳的,因为以上两种“王派”都可在同一叙述语境中找到立论的根据,最终难以避免认知上的矛盾和相互抵触。这说明,陈独秀的“王画”概念在根本上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它的概念内涵需要放在具有明晰性的“王石谷的画”和不自明的“王派”或“王派画”的相对关系中去界定,正是其涵义的明确部分与模糊部分所提供的张力,构成了“革王画的命”的想象空间。而“四王”其实是与“王画”这一概念内涵自身的那一部分模糊性(如“王派”“王派画”等)有直接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在陈独秀那里可以完全等同起来。
二、陈师曾论“王派”
耐人寻味的是,率先在“四王”“王画”以及“王派”等概念之间建立起对等关系的是陈师曾。早在1918年5月,陈师曾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作演讲时,就系统论述过清代山水画的源流及派别情况,“王派”即为其中之一。这篇演讲稿最初是以《陈师曾先生演说清代之山水画》为标题,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1日至10日;后又以《清代山水之派别》的篇名,重刊于北大画法研究会主编的《绘学杂志》1920年第1期的“专论”栏中。
梳理这篇演讲稿的结构和关键词,便可发现其中隐含着一条以清代“四王”画派为中心的逻辑脉络:何为“王派”?——“王派”之“根源”——“石谷、麓台二派”及其“流弊”——“厕乎四家”的吴伟、恽寿平、吴历——“飘然世外”的石涛、朱耷、石溪——“脱离王派”的金陵八家。很显然,陈师曾论述的着眼点始终在“王派”。对于“四王”之外的清代山水画家,他是用“厕乎四家”“飘然世外”以及“脱离王派”等范畴来一一概述。与一般的画史著录在体式架构上作纯粹实证式的考证注疏或印象式的妙悟鉴赏不同,陈师曾是以一种理性的自觉选取“四王”画派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以此切入,对“有清一代之山水,王派实有左右画界之势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王派”的得势,“厥有数因”:
四王之画,气魄沈雄,风韵悠远,源远流长,诚足楷模一代,此其一也。于时康熙践祚,政治休明,帝王提倡文艺以歌颂太平、润色宏业。王派之画,气象雍容,适与风气相应,此其二也。又当时言书法者,皆宗松雪、香光;言诗者,率崇梅邨、渔洋、牧斋、竹坨,而四王之画可与成联络之势。可知文学美术关系之故,亦风会使然,此其三也。夫以帝王提倡于上,烟客等扬拘于下,故靡然从风,至今不绝。[4]
不用说,陈师曾是把“王派”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注意到了特定的时代风尚,如“康熙践祚”的太平盛世以及诗书画一律的审美趣味,在“王派”成为清代正统画派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借用叙事学探寻文学话语潜在的结构与功能的观点,这段论述在体式架构和思维方式上已经显现出现代批评的话语方式特征:陈师曾对“王派”之所以成为清代正统画派的分析,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印象式、感悟式的评点,而且是将批评对象——“四王之画”——纳入到自己富于逻辑思辨的论述框架中,作出创造性的思考和解读。其中,陈师曾对“王派之画”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特别是康熙盛世)的关系的考察,尽管继承了中国传统批评中惯用的“循其上下而省之”“旁行而观之” 等手段,但他并不停留于时代环境和社会风化等外缘现象的考证与罗列,而是以“四王之画”的风格为前导,将其“诚足楷模一代”的审美特质摆在了“厥有数因”的第一位。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这一“气象雍容”的艺术风格与康熙盛世“提倡文艺以歌颂太平、润色宏业”的“风气相应”,决定了“王派之画”一跃成为有清一代山水派别中的主导画派。
这在阐释上深入到了“四王之画”的风格与“风气”的关系层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陈师曾这段从风格与“风气”两者的互动关系考察“王派之画”的论说,或许可以从钱钟书1940年写作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出发来作总体考量。按照钱钟书的观点,“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尽管“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但“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5]。对于陈师曾来说,风格与“风气”的这种内在统一性,一方面体现在他把“王派之画”所具有的“气象雍容”的审美特质归根于康熙盛世文艺风气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传统批评那般用单一的时代政治因素解释文艺作品的风格,而是将之看作是“四王”创作的“潜势力”和“背景”,由此肯定了“四王之画”的时代风格及其审美价值。这一批评思维,有意偏离了传统批评用“循其上下”和“傍行而观”的考证之眼代替审美批评的局限,具有较强的现代色彩。
然而,陈师曾的《清代山水之派别》于两年后(1920年)重刊于《绘学杂志》时,却是改成了“二因”,原演讲稿中谈康熙盛世的文艺风气对“王派之画”风格特质的影响一条,被有意删略了。如此一来,陈师曾用以强调“王派”何以在有清一代画坛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链条被割裂,这使他自身陷入了逻辑上的悖论:首先,康熙盛世的文艺风气作为他论证“王派”何以在清代画坛得势的主因之一,是与“四王之画”的风格特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不仅“四王”的创作始终处于康熙盛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且连同与它形成“联络之势”的书法、诗歌等都构成这一“风气”的一部分。因此,离开了康熙盛世的文艺风气这一外因的整体性考察,也就意味着陈师曾开宗名义指出的“四王之画,……,诚足楷模一代”的论说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早在1928年,美术史家俞剑华在论现代中国画坛状况时,就把以陈师曾为代表的北京画家群体命名为“摹古派”[6]。这一评价尽管抓住了京派画家整体取法于古的绘画风格特征,但在五四及20年代反传统的政治文化气候中,它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存在于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与现代绘画的“态度”中。借用五四时期流行的说法,“摹古”意味着“守旧”,是中国画“衰败”的象征。正是在这样一种视“摹古”为中国画“衰败”的心理状态中,以陈师曾为首的北京画坛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新艺术运动中“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 。这一历史定位,几乎左右了当代美术史家对于民初北京画界的认知[7]。吊诡的是,这一否定性判断的价值标准,是在艺术的本质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外化的观念下被定义的——艺术家的“天才”特质变成了创造艺术品并制定其评判标准的主因。而“天才”观念的产生,并非出自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文艺批评术语,它在五四及20年代的文艺界成为了一种权威话语。像鼓吹“美术革命”的陈独秀,很自然地以“发挥自己的天才”一条作为美术家“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以“改良中国画”的“理由”[8],便是这一来自西方的文艺批评观念在现代中国文艺界发生影响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三、“石谷派”之流弊
这里牵涉到从康有为、陈师曾到陈独秀等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改革事业的基本判断,并非只是个文化策略的问题。关于“四王”,尽管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称其是“稍存元人逸笔,已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已同邻下,无非无议矣”[9],但这一论评并非特指“四王”,还包括“二石”在内。他是将清代画坛的“四王”和“二石”一并视为“元人逸笔”的集大成者,二者在他以唐宋绘画为“正宗”的画学评价体系中自然是“无非无议”。这说明,康有为论评“四王”的着眼点,并不是从其画派本体出发,而是建立于他视文人画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根源这一论断之中。也即,康有为真正批判的是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传统,而“四王”和“二石”正是这一脉的集成者。
有意味的是,民初知识人对“四王”的论评取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传统的尊卑态度。与康有为鄙薄“元四家”及至“四王、二石”形成鲜明反差,陈师曾之所以给予“四王之画”如此高的评价,与他尊崇“元四家”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一点,首先可从陈师曾1918年5月的演讲见出:当他论述“四王”的师承时,明确讲到“清之四王,师承明末余风,故其家法仍宗元代四子,或融铸二家,自开面貌;或私淑一家,略加变化,要不外出于南宗”,并用了诸如“笔法苍劲,气味高淡”“雍容华贵,适合当世”之类的品评术语加以涵括,建立起“清之四王”与“元代四子”在画法风格上的直接渊源。其次是他1921年,为文人画作价值辩护时,更是直截了当地在《文人画之价值》中反问道:“四王吴恽都从四大家出,其画皆非不形似;格法精备,何尝牵强不周到、不完足?”[10]这一以“元四家”之名为“四王”辩护的意图,清晰可见。
这意味着,在陈独秀喊出“革王画的命”之前,有关“四王之画”的论评在民初知识人那里就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 ,而对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传统的尊卑态度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显然走的是鄙薄“元四家”的路子,他是循着文人画在明清的影响路径,最后把矛头明确指向了“王石谷的画”。按陈独秀的说法,就是“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8]。这与康有为归罪于“元四家”进而批判“四王”的学理路径明显不同。问题是,为何陈独秀要着重批判“王石谷的画”,而不是“四王”或“四王”中的其他人?
如果考察晚清民初北京画坛和书画市场的王石谷热,便可知陈独秀此说并非无的放矢,但有矫枉过正之嫌。事实上,“四王”画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两支是以王石谷为宗的“娄东派”和以王原祁为宗的“虞山派”,二者在清代画坛各定一尊的态势可于方薰的《山静居画论》 见出。到了民初,这两支宗派在北京画坛几乎独占鳌头,而且流弊滋生。对于这一现象,陈师曾的论述最为精当,他在演讲中说:“自康熙以迄乾隆,惟石谷麓台二派最盛。即至今日,凡工山水者,率二派之支与流裔也。然学者既众,流弊遂滋矣。”在此,陈师曾是把民初北京画坛的颓风与“石谷麓台二派”的“流弊”作了富于意味的关联:在他看来,“麓台派之流弊”是“徒有形式而笔法气韵去之远矣”,而“石谷派之流弊”在“秀润”,“秀润之弊,软弱随之,致供搔首弄姿,以取悦庸众之嗜好,超旷拔俗之风替矣”。尽管这是就“二派之支与流裔”而论,并非批判王石谷和王原祁本尊的绘画,但从中亦可见这两派势力在民初北京画坛岌岌可危的舆情。这是其一。
其二,在陈师曾的这场演讲前,同为导师的贺履之曾于1918年4月26日在北大校长室作过有关中国山水画的讲话。在谈话会中,贺履之特别讲到了晚清民初书画市场中盲目追捧王石谷画的现象。他说,王石谷的画因被同光以来的鉴藏家“力为提倡一时”,以至不少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不吝以重金搜求,使得“其价值乃至轶宋元诸家而上之”。对于这一“异数“现象,贺履之最担心的是学画的人难免以“临王”而“奴隶一世” 。其实,民初北京画坛因袭模仿王石谷画的风气,与清末号称“中国画家第一”的姜筠和“曾任东三省知府”的陈衍庶的力推有直接关系,二人“同师石谷”,遂使石谷画“声价倍增”。值得玩味的是,陈衍庶是陈独秀的继父,曾“于琉璃厂设崇古斋文玩铺”,他“买石谷画,偶闻佳品,虽远地必亲至”[11]。反观陈独秀,他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8],此“王画”很可能就是指王石谷的画。
不难看出,五四前夕的知识人就“四王”的认知既非一概而论,也非一味推崇,而是抱以相当理性的批判精神。就王石谷而言,真正被列为批判对象的是他的传派——即直接或间接以王石谷为宗的画家,而非王石谷本尊。这一点,在陈师曾所述“石谷派之流弊”中,讲得很清楚。也即,陈师曾对王石谷之画是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所痛斥的其实是王石谷的传派。在他看来,即便是那些“学石谷画而佳者”,也“仅号秀润”。正是出于对王石谷和王原祁传派之流弊的认识,陈师曾得出了以下结论:
王派流裔甚众,流弊亦多,如于王画中寻生涯,必不能得其佳处。即使有成,亦难超乎乾隆以前诸家之上。且其画之流传者伪托为多,真迹难得,欲寻其笔墨,鉴其风韵,颇不易也。
这里,所谓“王画”和“王派”在概念上达成了相关性,它们实际上是围绕“四王”画派展开的言说,在概念内涵上与后者几乎没有差别。值得注意的是,陈师曾提出的“如于王画中寻生涯,必不能得其佳处”的观点,其意大致可解为:并非“王画”本身无“佳处”,而是很难“得其佳处”。质言之,“王画”自有“佳处”,只是“必不能得”。原因有两点:一,“王派流裔甚众,流弊亦多”;二,“其(四王)画之流传者委托为多,真迹难得”。再联系贺履之所说的“临王”现象以及黄宾虹后来形容民初画家“以汤雨生、戴鹿床配四王”[12],可知陈师曾1918年5月的这场演讲特以“王派”为主线来论述清代之山水画的现实针对性。应该说,陈师曾是在清醒的审时度势中,就“王派”的创作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注意到了有清以降及至民初北京画坛影响最著的“石谷派”和“麓台派”的流弊所在,由此辩证地得出:“如于王画中寻生涯,必不能得其佳处”的结论。这一批判性认识,着眼点始终在“王派”的利弊两端。这对民初传统派画家从“奴隶一世”的“临王”中清醒过来,更为理性地认知“四王”,当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文人画”的价值危机
尽管陈师曾意在批判“王派流裔”而非“四王”本身,但他主张脱离“王画”寻生涯的结论却无意充当了陈独秀“革王画的命”的注脚。1920年6月,北大画法研究会创刊的《绘学杂志》在重刊陈师曾1918年这篇演讲稿时,竟刊落了“石谷派之流弊”中的“派”字,变成了“石谷之流弊”[13]。此举不知是否为勘误,但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这也标示着民初知识人对“四王”的认知在1918至1920年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价值转捩:从理性地批判“四王”传派之流弊转向了非理性地批判“四王”本尊。
在笔者看来,陈师曾这一“默认”的删改,恰恰反映出了批评家的批评与艺术家的创作一样,同样受到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和制约。按照汪晖分析,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观点,“鲁迅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或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他恰恰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他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14]301与鲁迅一样,陈师曾也是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次年(1901)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又同于1902年入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到了毕业的那年(1904),鲁迅是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在遭遇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弃医从文,而陈师曾则于同年秋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科。这一相似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晚清民初大多数在中西两种文明之间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如果说鲁迅是“在”而“不属于”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任何一种文明;那么,此说同样也适用于陈师曾。只不过,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乃至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种文化取向的选择上,二者却是截然不同:鲁迅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14]307,而陈师曾则是努力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种文化取向中寻求文化价值危机的解决之道。
其中,陈师曾的深刻在于:他一方面要对五四时期那种断然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论说保持警惕——如陈独秀“革王画的命”的激进观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晚清民初由民族生存危机引发的文化价值危机的影响。这决定了他既无法像鲁迅那样决绝的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也难以化身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守护者。正是在这种两难中,陈师曾把目光投向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失语状态的“文人画”,并试图从文人画的创作主体——文人——的思想与人格层面出发对其进行一番现代阐释。在《文人画之价值》中,陈师曾所概括提出的文人画之四种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与其说标明了一种论评文人画之价值的方法,倒不如说建立了一种克己制人的价值信仰、一种道德律令。
这一批评视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知人论世”传统。作为儒家诗学的一种观念,孟子的“知人论世”在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注解后[15],成为近世批评家从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其人”与“其世”)读解诗文的理论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王国维在“人格”这一中西批评的契合点上对儒家诗学批评所作的创造性转化。如他于《<红楼梦>评论》之后所作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年),尽管所采用的文体和评论语式都是传统的,但他所构设的理论体系却是有赖于现代意义的批评思维,这具体体现在他对屈原《离骚》的创作心态及其美学精神的阐释中。在王国维看来,屈原《离骚》的审美特质受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特别是地域文化)的影响只是外缘因素,最重要的是,诗人独具的人格与审美性情在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阐释路径,在温儒敏看来,是一种“以外化内”的批评思维,即“以外来理论去观照、调整和补充传统的批评,寻求中外批评的契合点,最终达到‘中外汇通’”[16]。而这一“外”落脚在王国维的批评理论中,便是结合叔本华的“赤子之心”论、尼采的“血书”说等西方近代哲学与美学理论资源[17],完成对传统诗学批评的创造性转化。
显然,王国维对屈原文学精神的探求之所以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知人论世”拉开了距离,正因为他把批评的视野放在了个体人格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上。这里,他用以研究屈原《离骚》美学精神的“人格”概念,已经不同于具有道德理想色彩的儒家“人格”说,而是一个深受叔本华、尼采思想影响的审美批评概念,相当于一般所谓的精神结构。对比来看,陈师曾对于文人画之价值的辩护,不仅注意到“时代的思想变迁”对于文人跻身绘事的实际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影响必须经过文人的“精神”和“人格”中介,才能折射到创作中 ,这与王国维以屈原的人格精神为着眼点考察其文学创作的批评视野具有内在一致性。只不过,相较王国维游刃有余地借用叔本华的“欧穆亚”概念切入屈原的人格与创作心态的研究 ,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无论是在体式还是批评话语上都缺少这样一种先锋性姿态,因而在表面上甚至予人以一种传统诗学批评的印象。
回到陈师曾写《文人画之价值》的五四前后,评论界正流行在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批判乃至否定中获取文化改革的动力。其中,无论是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把“中国画学”的“衰弊”归根于“专贵士气为写画正宗”的文人画理论,还是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中批判“专重写意,不尚肖物”的“学士派”,他们立足于中西社会文化比较的批评视野,实际上都离开了对“文人画”这一中国绘画史上特有现象的历史考察。而在陈师曾之前,历代有关“文人画”的理论学说可谓汗牛充栋 ,但这些论说绝大多数都是印象式、即兴式的,很少有人对“文人”这一精英文化群体的人格及其绘画创作的关系作过富于学术眼光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显然在文人画研究的学术史上带有首创性和开拓性。更重要的还在于,陈师曾并未沉潜于史料的搜罗考证,而是第一次用“人格”这一亦中亦西的批评概念重构文人画的价值,其目的是要探寻把握文人的人格精神与创作风貌的关系。
如果说,“五四”诚如胡适所言,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无论中与西、新与旧)都需要拿“评判的态度”分别出一个好坏来[18];那么,陈师曾从文人的“人格”出发来重新估定“文人画”的价值,又何尝不是他在更为深沉的民族文化危机中重建个人价值信仰的一种主观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系列文化取向危机中,我们往往过于专注于陈独秀所声言的“破坏”本身——包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19]等罪案,而忽略了这种“破坏”正是每一个新文化人以“反传统”这一否定性的方式对待传统与自身的表征。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在“反传统”过程中,主体(新文化人)与对象(传统)的悖论关系:尽管新文化人是以“反传统”作为他们存在的基本模式,但“‘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世界或传统的理解方式就在传统之中”,因此,他们对“传统”的批判与否定也就“导致了对自身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在汪晖看来,只有鲁迅才真正洞悉了“自身的历史性”——即“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用‘自我否定’来解决‘反传统’与主体的传统性之间的悖论关系”[14]306-307。对于陈师曾来说,他并不是靠鲁迅式的“自我否定”来解决这种主体价值信仰的危机,而是像伽达默尔那样在自身历史性的洞悉中引申出对“传统”的本质价值的辩护,《文人画之价值》或许可以作如是解。
事实上,如果循着陈师曾对“四王”传派因袭之风的批判理路,民初传统派画家别求新声于“四王”之外,自然是题中之义。而1920年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传统派画家,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下集体守护文人画的价值。这一行为本身,集中反映了民初中国画学已在根本上离开了自律性演进的道路,而融入到五四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变革逻辑中。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王画”这个概念其实就像一面聚焦镜,它到底是指称“四王之画”“王派画”还是“王石谷的画”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类因循守旧的绘画的代名词,成为了封建王朝艺术衰落的象征。这种带有独特价值逻辑的话语,深刻地规约着民初及至当代中国画家的画学取向,亦影响着“文人画”在20世纪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