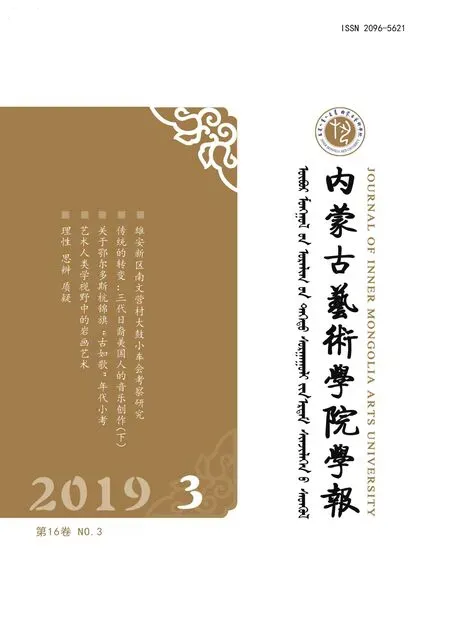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一)
(英国)约翰·休伯特·马歇尔 著,马兆民 译,武志鹏 校
(1.英国社会科学院伦敦;2.敦煌研究院 甘肃省 敦煌市 73200;3.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 北京 100020)
在《古文字研究》一书中,马宗达(Majumdar)先生总结道,这尊舍利塔的遗迹盒,楼梯遗迹护体栏杆上的铭文都和一号舍利塔地基,护堤遗迹楼梯栏杆上的铭文一样属于同一个时期,都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个结论已经被一号以及三号舍利塔的楼梯上的铭文(编号618,620 以及722)证明存在了,这两尊舍利塔的供养人是同一个人,一个来自柯罗罗的某个Arahaguta。另一方面,铭文中很明显地注释出了三号舍利塔的基柱直到一号舍利塔的塔门被竖立起来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后才加上去的。这个栏杆(参见94d)几乎八英寸高,盖梁有一英尺八英寸高,上部建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这些高度都不包括他们装饰粗糙的基底。像楼梯的上部,走廊以及栏杆,后者的棱,浅浅地刻在了一个凹面段,装饰成了传统的荷花图案,其手法很大胆,根据雕塑家(参见93 c ~f)不同的幻想,每个栏杆的上部内容都不一样。从后期南面塔门来看,很明显这里的栏杆和大舍利塔以及第二舍利塔栏杆有一样的入口;按照这样的方法类推其它的舍利塔,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在其他主要点上还有这样的入口。因此栏杆就会在每个扇形板上有22 个门柱,包括通道的,或者总共88 个门柱。
紧跟着地面栏杆的,是南面附有丰富雕刻的塔门(南塔门),这扇门是桑奇塔门中最新的一扇,它在公元一世纪初(参见93 及95 ~103)被很恰当地安放了上去。到它被竖立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碎片堆积在了游行路径的周围,最底层上升了一到二英尺,因此,它隐藏了原来的通道表面,藏在了最低的上升楼梯的视角下。为了能使后者显现出来,把古代的累积物移除势在必行;但是挖掘在靠近楼梯最下面处停了下来,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对塔门地基的任何形式的损坏。
这座塔门高17 英尺,其浮雕风格和大舍利塔的四个通道上的浮雕风格是一致的。毫无疑问,它的一圈也一模一样地装饰有同样级别的任务,包括了夜叉,夜叉女,四大天王以及同样象征着信念的人物:三宝和法轮.对于这些雕塑的阐述解释,读者可以查阅95 ~105 反面的描述,以及第三部分M 弗彻对他们更深的解释。作者对于浮雕风格的讨论会在第二部分。
遗迹的密室是被吉尼·坎宁汉姆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完好无损,遗迹在穹顶的中心,和排屋护堤在同一平面上。覆盖着遗迹的是一个五尺长的板皮,里面有两个石质盒子,其盖子上都铭刻着一个早期婆罗米人的名字。南面的名字是舍利佛;北面的名字是摩诃摩伽勒。我在舍利塔附近废墟中找到的这些盒盖是一块2.08 平方英尺而不是吉尼 康宁汉姆书中所述1.5 平方英寸的Nāgourī 石做的。在舍利子盒子里面是一个平的用6 英寸宽3 英寸高的白色块滑石做的罂坛,上面盖着一个黑色,有光泽的土陶(已破损)碟子,在两边,有两小块檀香木,吉尼 康宁汉姆的想法是:这两块木头是从葬礼的火葬的柴火堆那里带出来的。罂坛里面是一小块碎骨和数个珍珠,石榴石,青金石,水晶还有紫水晶;盖子的内面上用墨水写着“Sa”的字样,这无疑是“舍利塔”梵文的缩写。在摩诃摩伽勒舍利的盒子里有第二个块滑石罂坛,多多少少比舍利子的要小,同样,在盖子内面也有“Ma”那样的缩写;里面只有两小块碎骨。埋葬在这两个罂坛里面的遗体是两个众所周知的佛祖的信徒。他们都是婆罗门世家的人,都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是删阇耶的学生,他们离开了他们早期的老师,并且在他们余生忠诚地跟随着乔达摩。在佛教中,他们在上座部很有名,排名仅次于佛陀导师。他们是在佛陀涅槃前几年去世的。这个遗址不是唯一一个竖立起来敬仰这两位信徒的。第二个Satdhārā 的舍利塔,距离桑奇六七公里之间,也保存有他们遗骨的一部分;根据法显和玄奘的记载,在马图拉,本来有另外一个舍利塔供奉着他们的遗骨,和他们遗骨一起的还有富楼那满慈子,优婆离,难陀以及罗睺罗。舍利佛是两位圣僧当中更为著名的一位,他是在王舍城(Rājagriha)圆寂的,据说在他的遗迹上又树立起了一座舍利塔。可能就是在这座舍利塔中,山琦,Satdhārā 以及马图拉的舍利子才被找到,但是什么时候找到的,被谁找到的,这些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吉尼 康宁汉姆提出他们很有可能是由阿育王在释迦摩尼遗体同一时期被分配的,但是吉尼康宁汉姆抱有这样的幻想:山琦的第三座舍利塔以及大舍利塔的基柱都是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建造的。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仅第三个舍利塔,还有附属舍利塔都不会早于巽伽时期,这样的话,吉尼 康宁汉姆的推断就不再成立了。事实上,阿育王很难和分配这些佛陀门徒的舍利子这件事挂上什么钩。正如我们所知,在他摄政期间,这个帝王无疑一直推崇佛陀崇拜,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所推崇的崇拜是佛陀自身所禁止的;也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表明在以后的时期里阿育王对这些佛陀门徒的舍利子遗址进行扩建过。此外,当我们讨论这些马尔瓦舍利塔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清楚,毗廸萨曾经是巽伽王室的家,华氏城是孔雀王朝的首都;乍看起来,很有可能这些卓越的遗址其实是在某个巽伽国王时期,而不是阿育王时期建立起来的,其造型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尽管在后期,可能在城中新添了一些比较浪漫主义的建筑物。在吉尼康宁汉姆的考察之后,舍利塔的遗骸完全变成了废墟(参见95),作者不得不在它脱落的废墟中将它重建。收藏家科尔已经在1882 年将附有雕刻的通道重建了。
三号舍利塔东北边后面就是另外一个尺寸更小的舍利塔,此塔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废墟。现存的塔身是按照三号塔的风格建造的,无疑其建造年代和后者一致。和低处游行路径上的板皮残余物被标记过,现在还在,在地面上,楼梯上,或者护堤栏杆上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栏杆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一块球型顶藏设圣骨的四方体(又称宝匣)栏杆,雕刻精湛的顶盖石在这尊舍利塔的南面被发现了,它很有可能是这些栏杆的一部分。这块顶盖石(参见104j)有5 英尺7 英寸长,但是一端是破损的;在它的外表面上装饰着起伏的荷花和叶子,还有鸟儿栖息在他们中间。
另外一个在山顶和巽伽时代有关的舍利塔是六号,它的位置稍靠近18 号寺庙的东面,在主平台末尾的南端。这个舍利塔的中心像三、四号舍利塔一样是由当地点缀有削片的砖搭建起来而成的,很明显这个舍利塔和其他的舍利塔属于同一个年代。然而,现存表面的砌石墙更为现代一点,它很有可能还在七或者八世纪才加建上去的,到了那个时候,原来的表面很有可能已经坍塌了。后期的石料都被铺在了很平且装饰地很好的道路上,厚度从二英寸到六英寸不等,中间还插入了更短的道路,上层建筑和底座的底部都因为这些过道而被加强(这种结构是完全在以前的建筑结构中找不到的)。像这个遗址中世纪大多数舍利塔一样,后者在平面图上是方的,没有那么高的高度。每个边的测量长度大约是39 英尺6 英寸;它的高度大约是5 英尺4 英寸。作为这个建筑早期中心部分的一个例证,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这院子老墙的低处,使用与它的中心结构一样的石料构成的,院子地面那一层要比现在的地层低数英尺。在之后的时间里,这些墙的上部被修好了,像舍利塔本身,使用的是更小更整洁的石料。
高原上的其它舍利塔都属于中世纪。他们当中最显眼的应该是在六世纪建造的五号舍利塔(参见115a)。像所有中世纪时期的舍利塔一样,它的中心是由碎石和泥土构成,表面铺成了一排一排,整洁细长的石料,其基脚和六号舍利子相同。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基座是一个圆形而不是方形,其直径为39 英尺。它南面伸出的是一个Nāgourī石料做的底座,其建筑设计和建筑样式都表明,它的建造时间是七世纪。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座佛像的底座,在若干年后又错被放在了大舍利塔的游行通道上,在南大门的对面(参见125e)。这个基座本身的模雕要比大舍利塔游行通道上的基座模雕的雕刻手法先进一些。
我们将要谈及的和五号舍利塔同时期的,及高于西南角的七号舍利塔,以及在17 号寺庙(参见105a)的两排舍利塔,他们分别是:12,13,14,15 和16 号。这些舍利塔的建筑风格都是一样的。它们基座是方的,用碎石以及泥土构建而成,表面用整齐的石料装饰,在一周又有基脚来加固。其中有几个中心有一个小方的罂坛;剩下几个是实心的。由康宁汉姆打开的七号有七英尺高,七号舍利塔中被证实没有舍利子。四面仍然残存的是后来的排屋,排屋使底座的尺寸从28.05 平方英尺扩展到了38 平方英尺。排屋本身的设计要比舍利塔塔身的设计更为现代化,这一点证实了它是建在了废墟层的这一观点。从排屋的北面伸出的建筑,很有可能是与其同一时期的建筑,这些延伸出来的部分可能是人们推测的经行大道或者一条大道,在它西边的末端建有两个普通的圆形小舍利塔。
十二号舍利塔中的罂坛已经完全被毁坏了,但在已经倒塌的石墙中间,我们找到了一个贵霜王朝时期的柱角雕塑,使用马图拉砂岩雕刻而成的(参见123d)。柱角有8.25 英寸宽,很不幸的是,装饰在其表面将近一半的浮雕以及写在上面的铭文已经被毁了。剩下的浮雕上是一尊坐姿的菩萨像,菩萨的右边有两个信徒的左手拿着花环。铭文(830 号下文)记录了名为Vishakula 一个女儿对弥勒菩萨的供奉。
在十四号舍利塔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雕像,不像上个案例中的雕像那样躺在废墟中,这尊雕像放在罂坛西墙,它的面前是另外一堵保护墙(参见105b)。这尊佛陀雕像作禅定印双腿交叉而坐,和冥想的姿势很相似。像上面所说的基座一样,这尊也是用Mathurā 沙石做成的,也是马图拉流派的作品,但是它的面部特征,尤其是嘴唇,眼睛还有用传统方式处理过的头发,一点都不模式化的衣服质感都表明了它是早期笈多时期,而不是贵霜王朝时期的作品。由于这尊雕塑在被供奉进来之前就已经被磨损过了,这更加例证了这个建筑是相对晚期的作品,在其他基底上的应该是大约公元七世纪的作品。很有可能这尊雕像是从早期笈多王朝时代的神龛中带来的,随后慢慢腐朽,作为一种特殊崇拜的物品被埋葬在这里埋葬旧的祭祀雕塑,或者整个,或者不完整的,在佛教舍利塔中是一个惯例,这个惯例在中世纪时期很普遍;因为我发现不但在桑奇有这样的例证,在鹿野苑,袛园精舍以及其它遗址中都有。
当大舍利塔被围起来的时候,像所有更著名的佛教神龛一样,包围它们的是高原周围大小不同的舍利塔。塔门中的大多数似乎在1882~1883年的探险中已经被清除了,当时这个区域栏杆周围60 英尺的舍利塔都被清除了。除了上面描述的那些,还有剩余的主排屋东侧舍利塔群和七号舍利塔也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大量堆积起来的残骸对他们起到了保护作用,还有像在菩提伽耶和鹿野苑找到的大量坚硬的石质舍利塔。在这些建筑样板里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分别是我平面图上的28 号和29 号,他们坐落于靠近31 号寺庙楼梯的左右两边。这两个小舍利塔都有很高的方形底座,其飞檐和基脚都是早期笈多王朝时代的风格,同时同貌。然而他们的内部结构就不是那么的雷同了。楼梯西边的那个从里到外都是由石头做成的;但是东边(29)的那个,其基底大约有8平方英寸,有一个大尺寸砖头构成的核,这个砖头无疑是从更古老的建筑中拿来的。在这个核的中心,从地基算起,3 英尺高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罂坛,在里面有一个很小的粗制土陶杯子做的骨灰盒,上面盖着一个类似结构向里弯曲的盖子。在这个粗糙现成的容器中,有一小块骨舍利子以及一些破碎的上等精美瓷器花瓶,这些花瓶是在孔雀王朝以及巽伽王朝年代制造的。正是这个破损花瓶中,且完整的保存了舍利盒,让我们不用去再怀疑这个舍利子之前是在另外一个更为古老的神龛中受供奉的,在笈多王朝早期,当这个舍利塔开始被风化的时候,它被转移到了那个更小的建筑物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舍利塔以前所在的舍利盒碎片。在同样一个舍利塔上部(大约表面以下1 英尺3 英寸处)底座处,有一个马图拉沙石的人物雕像在105c,上面的铭文记(829 号)记载了这个雕像是世尊释迦摩尼,并由瓦斯贵霜钠国王统治的第22 年,由名叫Vidyāmatī 人建造而成的。其雕刻风格是典型胡吡色伽时期以及华苏戴瓦时期的马图拉流派。
直到最近(近来),人们普遍认为,印度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孔雀王朝统治时期开始的—主要是受外来古希腊人的影响;而且,无论之前存在过什么样的艺术,后来的最好的,天然的,原始的都体现在了原材料上,如木头,粘土或者油漆这些可能已消失很久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梵语学者一致的将印度文化的价值点都归结于印度雅利安人的入侵,而在这些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学中,没有任何事情表明了他们掌握了任何水平的技术,在建筑或造型艺术方面都没有。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古希腊人到来之前,这里仅有很少的可寻找的建筑和艺术的资料;同时此推论仿佛被丰碑自己本身给证实了,因为最早的含有任何骄傲的艺术价值的遗迹都是阿育王在公元前三世纪建造的石柱,它们是外来灵感的产物,然而更多真正地成就了印度丰碑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原始的风格,也有那些从木制模型复制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的则是,那时候孔雀王朝时期的木材是印度建造者使用的主要的材料。要是这个长期建立的观点代表了印度艺术起源的全部事实的话,我们就几乎不必要为了跟随它从头的演变而穿过桑奇本身了;因为据我们的所见所闻,阿育王时期最好的石柱之一就矗立在这个地方,同时从其建立的时代到公元—最困惑我们的时期—我们拥有着由最完整的和指导性的雕刻群组成的桑奇遗迹。远远开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然而,现在显然的是印度艺术的根源延伸到了铜器和石器时代。此艺术长史中的一个章节已经被最近在哈拉帕(巴基斯坦城市)和摩亨佐-达罗(摩亨佐-达罗(公元前2600年~前1800年),又称“死丘”或“死亡之丘”(Mound of the Dead),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城市,大约于公元前2600年建成,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摩亨佐-达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早期古代城市,有“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大都会”之称,该段时期的其他古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及克里特文明。多认为是由古印度的白种雅利安人入侵之前达罗毗荼人(即矮黑人)所缔造的都市文明。摩亨佐-达罗的考古遗址在1980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与哈拉帕文明并称为古印度文明的代表。)的革命性的发掘所揭露了,同时,我们已经可以知晓,在雅利安人到来很久之前,印度都拥有自己的杰出的文明,可与同时期的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文明相提并论。尽管此文明的遗迹很大部分是因其功利主义而非艺术特性而存,然而这里有很多非常高级的创造性的艺术例子,包括小雕像和甚至未被斯克里特最好产物超越的刻印章。因此,任何阐述历史中印度艺术紊乱的起源的尝试,都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早期的成就;实际上,这不仅对于印度艺术是真实的,对于其古代文化的每个方面几乎都是真实的,因此,无论印度文明的时代有多么久远,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其作者与非雅利安的印度人紧密相关的,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其人口的组成;同样不能质疑的是后期的印度要将其许多的机构和信仰以及其物质文化归功于这个古老的文明。这些影响已经扩展到在宗教范围内被广泛地证实。就流行的印度教而言,不算多言的是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编织延续了能追溯到印度河时代的教派和条例—编织延续了教派的石头,水,树木,动物,男性生殖器像(林迦)和女性外阴像(作为印度教性力派教徒崇拜象征的女神生殖器图),湿婆,大地和地母神。如果这些古老的教派对佛教做出的贡献少于印度教的话,那么桑奇雕刻和巴尔胡特塔雕刻则提供了很多来自远古宗教信徒的神物和神学教义的复制品:象征和护身符,树木和动物,夜叉和夜叉女,那迦和龙王Nāgarājas。由于所有的天竺菩提树都可被伪装成佛陀的菩提,它还被认定为是印度生活和知识之树,因其来自于远古时代;同时尽管女神拉克希米(拉克希米,又称“吉祥天女”或“财富女神”。印度教女神。传说她是毗湿奴大神之妻。在印度教徒心目中她是吉祥、财富和社会繁荣的象征,故家家都设供奉她的神龛,每天清晨向她膜拜祈祷。其画像多为美女,面带微笑,头戴王冠,身穿珠光宝气的衣服,坐在露出水面的莲花上。有四只手,上面两只各持一朵莲花;下面两只,一只作下雨的手势,另一只抬起作祝福姿式。身旁常有抱琴的辩才天女和象头神相伴。)可被视为佛陀之母,女神的繁荣因太古老和熟悉的典型而容易被弄错。那些名字可能被改写了,但是狂热崇拜却没被改变。
当然这些崇拜对象不是佛教从流行宗教里接收的唯一元素。这里肯定还有其它更多抽象的和无形的特征;例如,因缘和轮回,宗教虔诚的观点(以对一个神的虔诚信奉求得自身的解脱),这些教条是佛教也正如印度教从非雅利安人源头继承的,但是在自然界中事物却不被借代到具象艺术中成肖像。然而,我们也不必再进一步追寻这个宗教主题。我们参考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些特殊领域的来自过去远古时代的残余物,同时,要是这些被发现的残存物不属于艺术领域就令人惊讶了。然而,印度艺术绝不是像印度宗教一样保守的。远古时代和早期历史时代的艺术毋庸置疑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他们潜在的精神背叛了他们的亲密关系,这在他们对动物变身的直觉中尤为显著——一种认定其为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哈拉帕(Harappa)是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原先拉维河流域的一座城市,距离萨希瓦尔约35 公里。现代哈拉帕城附近有一个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的防御性城市遗址。Harappa 系指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有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有以反映繁育动物为主的艺术形式)。刻印章特点的感觉,因其是桑奇的浅浮雕,但是在如此相距甚远的两个时代,当然这不能说明他们是相同的。在桑奇,最具严格意义代表的是大象;而不会言过其实的是回归自然本质的真实的描绘的各种野兽姿势是不可超越的;事实上,具有说服力和不可预知的是动物和人类形象的自然性,在桑奇,那组成了这些雕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另一方面,在摩亨佐—达罗的大象,尽管它们雕刻的足够好,但也逊色于一些隆起的公牛和北美野牛;更多的是,当后者展示其对于自然的精心观察的时候,吸引我们更多的是它们的精心的时髦款式而不是其质量,但在这我并不是暗示说桑奇的浮雕缺乏时髦感;因其南面通道(Pl.15)上的大象有其自己明确的新款式,使得它们得到了通道其它动物没有的吸引力。然而总的说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特别的形象绝对比印度河刻印更有特色,同时,那不矫揉造作的纯真也正是桑奇浮雕的品质保证。
但是,无论风格多么小的差异—考虑到那消逝的长久间隔时期,要是这些没有其本身那样显著的话,那就令人惊讶了—仍然保持真实的是,桑奇雕刻违背了同样天生的对动物变身的理解和描绘它们为其两三千年前之前的先辈的天资。另一方面,在所有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遗迹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是一条线索就发现了传统装饰主题的,如全开和半开的莲花,悬浮的花环或者迂回的匍匐植物图案,这些都表现了过去两千年间印度艺术的特点,同时形成了其不同派别不同时期之间简单易辨的联系。在这我们谈论的不是宗教象征和形式,正如我们已经所见,他们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红铜时代,但只有那些来自基础工作的具有纯粹装饰的和高度风格化图案的印度雕刻和油画在其列,同时,必须是只因艺术的延续性而不朽的,区别于宗教和传统。关于这些图案,桑奇艺术与亚述(亚洲西南部之古国)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建立了比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更近的关系。
关于这些和那些标志着桑奇浮雕是怎么样和什么时候的传入印度的,我们将在后面处理阿育王时代官方艺术的时候做出讨论。这里不得不强调一点的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有关这些图案与印度河时代或者红铜时代文明同时期的地域。就他们而言,这儿似乎曾经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性的时期间有过一个几乎完整的延续性的突破。这对于雕刻技术是相当正确的。反之,对于那些印度河时期的雕刻者们,他们在“记忆形象”和法律“正面描绘”契约中已经本质地释放了他们的艺术,同时也在没有古老刚度的踪迹下学会了完全地模式化他的形象,从其历史性时期的继承者的粗糙的产物可以看出,显然那些旧时代的非石头模具化雕刻技术已被完全遗忘了,同时这些课程都不得不从新习得。
因此,印度历史性艺术到史前艺术的联系就和早期的希腊极为相似。在两个国家中,抽象艺术都在铜器和青铜时代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在两个国家中,它的进程都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被打断;其记忆也在后来的黑暗时代被遗忘。所有从这些入侵中幸存的就是流动在人们血液中的内在的艺术性,以及除了灭绝才可被磨灭的语言和宗教元素。在再次艺术盛行之前,其技术就必须要在几乎开始时候被再发现。在希腊,在公元前第五和第六世纪之间其取得了成就;在印度,则在三个世纪之后。在希腊,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们在其自己的道路上受到了埃及,雅利安和波斯艺术教育的帮助;在印度,他们不得不增加希腊人的经验作为辅助。
现在转到幸存的桑奇雕刻—最早就是在25-6页上描述的阿育王石柱的狮子柱顶和24 页的标准碗和55 页的毁坏的宝伞。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这些物体有三个共同的特征—并且其它此时期所知的官方艺术品也具有的特征:其材料是来自城市采石场的冷灰色硬砂石,其凿边是极为精致尖锐和准确的,其表面也打磨地如玻璃一般出色。打磨石头的过程不得而知,专家们模仿制作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尽管在显微镜检查中表明它们仅仅是得益于腐蚀剂的帮助,而没有任何人工的上釉。打磨石头已在印度所有的时代被实践过了,同时,我们目前需要看到的是桑奇大塔通道上的浮雕最初是打磨和上色的中世纪雕像。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认真,而不是跳入总结,因为一个被打磨的石头肯定有一个对应的孔雀王朝日期。后来的工匠们不能够取得和其孔雀王朝先辈们一样程度的光泽光辉是真实的,但这也只是看到了片面,因为其它砂石不是都是像期望的多样的砂岩那样有细密纹理的以及有能够被打磨到如此一个程度的能力。因而,如其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极富经验的眼睛和偶尔的岩石显微镜检查来辨别其打磨的不同时期。
在所有阿育王时期的雕刻中,在桑奇和鹿野苑的两个石柱的狮子柱顶无可厚非是最好的。尽管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它们因等级而矗立在不同位置,其原因在Pl.107 被指出,其两者的相似之处却是明显的:一个钟型柱顶支撑的圆形算盘,并装饰着四只站立的狮子—这是两者都有的设计,同样,其风格也极为协调性的一致。在另一方面,这有显著而细节的差异。如桑奇之例,其钟型柱顶没有像鹿野苑的那样矮胖,它更适合于在高高的石柱节略缩短的顶部位置而立;在鹿野苑的那一个是平坦的。前者的算盘明显比后者的要薄,装饰着四对鹅-可能是佛陀追随者的象征—交替着通常的金银花图案;在后者中,其装饰着四个动物交替看管四方的法轮:马,大象,狮子和隆背的公牛。在前者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四只狮子是独立站在算盘上的;在后者中,狮子托起了法轮,如Pl.106d里描述方式举在它们之间。这些不是仅有的差别。虽然石柱在材料和技术上是相同的,风格也极为协调一致,桑奇柱顶缺少了微妙的艺术性,那种更好的形式的感觉。两组狮子都展示出同样的肌肉紧张程度,以及结合着同样有条理的结构质量的生机勃勃的现实感,这正是艺术家们为了追求其与碑石建筑特点和谐而作;但我们不禁想要谈论的是其缺少多少真实的自然性,多少桑奇野兽模式化的说服力和重要性,多少膨胀胸部而不成比例的宽度,多少伸展腿部的空间度,多少手工制作差异的鬃毛。两个柱顶最初的设计是出自于一个人之手,同一个艺术家也几乎不能辨别,但是在工艺上的差异使得其肯定的是真正的桑奇雕刻柱顶是出自于一些稍欠天赋的助手之手。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谁是艺术家且在什么时候来设计这些柱顶的,以及在其背后是什么样的传统背景?他是一个印度人还是外国人?当然他不是印度人。公元前三世纪,当这些碑石建立的时候,印度本土的艺术还处于相当不成熟的境地。雕刻,尤其是装饰性雕刻,包括浮雕和环形雕刻都是极为普通的,但其是在木头或其他非永久性的材料之上,同时,它们的任何样品都没有幸存下来的。然而,其发展的阶段可以相当准确的定位到随后世纪在桑奇和其它地方的雕刻,同时可以较肯定的说它完全不能代表此种水准—代表了后来被认定的当时世界最高的艺术,古希腊时代都不能胜任的产物,按我们所言,就是珀加蒙(古希腊国王)祭坛。实际上,甚至更多这样的情况;这两个柱顶对于印度艺术的精神完全是异形,同时在其艺术史上也没有后继的学派和时段表明可能被相信是产生了它们。
然而,如果那艺术家不是印度人,那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二十年前,我指出仅仅是一个具有艺术天赋和经验的亚洲的希腊人创造了桑奇柱顶,同时我也以为阿育王从巴克特里亚(大夏古国)带来了这个雕刻家以及和他一道的其他人。我表明了巴克特里亚,因为很显然的是此柱顶的作者不仅洋溢着希腊人的传统,也显现出了伊朗人的影响,从很多原因可以看出,他灵感的来源最有可能的就是巴克特里亚。我所指出的巴克特里亚,它曾经是阿契美尼德波斯的总督辖地,同时也在此之前养育了强大希腊人殖民至少三代人,他们生活在孔雀王朝统治的开始的时候,因此在希腊文化的或个人希腊风格的观点传播到印度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发挥了绝对的作用。如被铭记的光滑而无凹槽的以这些lāts 阿育王石柱,以及其钟形的柱顶和打磨地光泽的表面为特点的柱体,都是可以按迹追寻到波斯起源,更重要的是,在阿育王石柱雕刻的法令上,一个强大的波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原因给我一个坚定的推测是巴克特里亚。但那个艺术家是否是巴克特里亚人,就其曾经在希腊学校里训练或者他对伊朗模型的熟悉,可知这是没有合理疑问的。当然我们不能认定所有阿育王碑石都是由一个雕刻家负责的,显然是很多人,同时所有的雕刻者也并非都具有相同的能力。我赞成很多雇佣的印度人辅助了那些外国艺术家的手工打造部分工作的观点,以及这些助手们也负责了一些略显逊色的雕刻的观点。然而我从始至终坚持认为,在那个时期,是没有能够做出像桑奇柱顶如此完美形式的模式化粘土或雕刻的工匠的。更重要的是,尽管桑奇柱顶具有相对的次等性,但我认定这不大可能是一个仅有一点或没有早期石刻知识的印度学徒的作品。
我认为有关这些雕刻的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地认同,同时也得到了Hargreaves 哈格里夫先生在鹿野苑意外发掘的孔雀王朝头部和残片新的证实,这些遗迹尽管都是当地工艺,然而各种细节,尤其是那些花环和冠有墙壁花冠的头部,都表明了此时期这肯定受到了西亚的强大影响。这些观点也得了进一步的认同,在Ludwig Bachhofer 博士的《早期印度雕刻》一书,他提到在桑奇和鹿野苑柱顶的狮子特征与希腊作品是同一等级地相似,但却是明显区别于印度的,如对“颧骨和触须”和深陷眼睛的不同处理,明显与印度突出的眼睛形成对比。虽赞同我的观点,由于这些柱顶的雕刻者洋溢着古希腊亚洲艺术的传统,Bachhofer博士认定他是个印度人,对于此艺术家是怎样和在哪里习得了如此超群的石艺,他不打算做出解释。很多被印证的实例是东方的君主派人去请外国的有技术的工匠,但我不曾记起他们派遣了自己的工匠出国去学习的例子。在有关苏萨宫殿的法典中,大流士告诉我们那些建筑和装饰其的不同国家的工匠是怎样被聚在一起的。“加工石头的工匠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和萨迪斯人;锻造金子的金匠是米堤亚人和埃及人;加工išmalu 的是萨迪斯人和埃及人;烧制砖块的工人是巴比伦人;装饰墙壁的是米提亚人和埃及人。”如果那时候阿育王招揽了来自巴克特里亚和其它地方的希腊人帮助建造巴连弗邑(巴连弗邑,又称波咤厘、华氏城,印度古地名,位于今天印度巴特那。位于恒河边,西元前490 年,阿阇世王在此兴建小型城堡(梵文称Pātaligrama),因此得名。稍后,它成为十六大国中摩揭陀国的首都。)的宫殿和法典石柱的雕刻,他仅为跟随着先前伟大国王将法令作为自己的模型一样—被很多印度君主模仿的先帝,直到德里的蒙兀儿帝王时代。然而,可能Bachhofer 博士认为他提到的印度雕刻家是在印度学习希腊模型艺术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总结到,在这些石柱设计之前,希腊雕刻家就已经找到了去印度的道路,因为明显不可能的是如此沉石的雕刻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被进口的,同样不可能的是,从对其少量的观察,印度的工匠已经成功地掌握了雕刻艺术的秘诀。要是我们首先假定希腊雕刻家在印度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些对于印度智慧完全外来的特殊柱顶归结于他们呢?但是,对于Bachhofer 博士的理论,这里有另一个不可逾越的异议;因为,如果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印度人已经能够设计和雕刻如此的柱顶,那怎么会在一个世纪之后,当大量的希腊人在旁遮普定居的时候,以及这儿已经有很多来激发印度人的希腊艺术模型的时候,他没能做出比桑奇2 号舍利塔和巴尔胡特塔栏杆更高级的浮雕?如果Bachhofer博士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别无选择地认为早期印度雕刻艺术拥有了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历史:它几乎在其诞生的时候就取得了最成熟的结果,后来又返回到了一个原始状态,然后在经历了所有艺术应该经历的阶段,才最终变得成熟。对于那些不太熟悉艺术史的人这是一个容易赞成的提议。与Bachhofer 博士相似的观点在史密斯的《印度和锡兰的精细工艺史》中被提了出来,令人好奇的争论是那里没有外国人能够掌握与众不同的鹿野苑柱顶算盘上的印度动物!这实在是一个太令人好奇的争论了,因为在算盘上的印度动物仅仅是大象和隆背的公牛,两者没有谁是特别的。那些大象的眼睛太大了,在其看来它是低于很多雕刻在桑奇通道上大象的标准的,同时,隆背的公牛对于一些刻在印度印章上的华丽的动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唯一真正生机勃勃的骏马是用典型的希腊艺术手法刻画的,绝不是我所想的印度人的艺术。史密斯争论的肤浅是注定的;因为一个希腊艺术家不可能在刻画大象或者隆背公牛形象时像当今的欧洲艺术家有更多的困难;同时被用于后者的不计其数的实例以显著成功的标志完成了任务。
以上所谈论的和大多幸存的阿育王碑石仅仅是此时期皇家或官方艺术的代表,正如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宫殿只是阿契美尼德皇家艺术的代表一样。与这样的皇家艺术一道,在紧随的两个世纪里,毋庸置疑这里流行的通俗艺术注定取得一个显著的发展。在阿育王统治时期这种流行艺术还处于一个古老的状态。迄今我们无从所知的是在孔雀王朝到来之前这是其自己的历史;我们仅能做出的假设是,随着印度文明的衰落,其艺术也本质上消亡了,但是当印度雅利安人入侵的暴雨与压力的到来的时候,它又逐步以新的较谦卑的伪装开始出现,就如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艺术一样,它一直保持在一个或多或少静止和未发展的状态,直到与那些更先进的具有艺术的人的接触才赢得了其迅速的增长。在孔雀王朝时期,这流行的艺术主要是在木头和其它打磨的材料中有所表现,用于皇家碑石的保存,因石头还没开始盛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样品仅仅是一些赤土陶器。然而,从这些以及后时代的石雕像和浮雕,我们可以较安全地推断出,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印度艺术仍然处于和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艺术一样的未曾跨过的以来自Prakham 单面精细加工形象的未发展阶段,同时浮雕工艺也几乎不能达到以桑奇第二舍利塔栏杆的古代雕刻为代表的阶段。
顺便附带说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本土孔雀王朝艺术特点是被一个归属于青铜小舞女caurī-bearer 女性圆雕像引起的困惑,此于1917年被发掘于巴特那(印度东北部城市)附近的Dīdargaňj。将此雕像归属于孔雀王朝时期的唯一原因就是它是砂岩所建和打磨表面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种石头的多样性在孔雀王朝之后的很多朝代都被雕刻者们沿用,也知道打磨雕像和浮雕的技艺被传承到了现代,当在我们纪元之前的一世纪桑奇通道建设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这是Dīdargaňj 雕像风格高度发展和清晰的模型特点所属的时期,同时,这是除非有更强有力证据证明其孔雀王朝起源的时期。
阿育王碑石对后世佛教艺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孔雀王朝时代,佛教寺庙的艺术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按照法令的规定,任何具有人形象的代表物都必须禁止雕刻,而可允许的装饰物也被限制于那些最简单的设计,主要是花型类的图案,尽管它毫无疑问带有典型的印度人的魅力和典雅,但其不是对信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形式。因此,艺术领域本质上是清晰的,同时,阿育王建造的碑石也是不值惊讶的—菩提伽耶的寺庙,众多整齐一的巨石柱和其统治时期广为流传的更多的砖块和泥土而成的舍利塔—这些都点燃了寺庙的想象和改革了其初期的艺术,甚至如帝王的作为国家宗教的舍利塔的机构也正在改革其精神。只要寺庙里允许的简单装饰被采用到了打磨的材料和指定的厢房,普通房间和僧人们的大殿,就几乎不能期待它们会获得关注,或者它们对宗教艺术产生过可观的影响。但当过去阿育王的雕刻者展示石头可以替代木头的时候,当他们打破静止仿制人物形象的规定和建立被后代人视为鬼神之作的雕刻碑石的时候;当帝王为了自己利益建造的舍利塔,得到了其永恒宗教崇拜价值的时候—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整个佛教艺术就此而改变;没过多久它就被视为教导和熏陶信仰的有价值的方式;不计其数的阿育王碑石复制品被建造—舍利塔和石柱—对前者刻上浮雕的无法估计的努力表明了其导师的出生或去世。因此,一个新的僧侣艺术应运而生,其中由先前帝王建造的舍利塔和石柱成为了其最显著的特点,同时,被重复地作为佛教信仰的象征,而其它象征性的和装饰图案也源于此。
阿育王碑石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到现在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只有少数被保存了下来,很多有关此艺术的内容和图案不为我们所见。因此,不可能肯定的是,它是起源于此还是其它那些早期派别里的西部亚洲特征。然而,所有指向这些特征的事物都是在孔雀王朝时期(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旁遮普的印度希腊君主统治时期)就抵达了印度,而不是之前时候。可以提及的格伦威德尔猜测到了西部亚洲人的特征是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的旁遮普省和犍陀罗省,同时起初这个猜测也貌似是可信的;对于那些比这些被吸纳为波斯世界性艺术的形式和图案更可能的艺术,难道是紧随在波斯人对印度征服的觉醒之后?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考古学上的发现对于此问题的新视点都不能证实格伦威德尔观点。在塔克西拉和印度所有同样的地方,阿契美尼德艺术都曾期望展示出自己而不仅仅是被作为发现的遗迹。事实上不仅这是令人惊讶的;必须被铭记的是阿契美尼德艺术不仅仅代表了波斯人传统的,本土的艺术,还代表了孔雀王朝艺术所展示的印度本土艺术;这是一个对很多外来的不同元素的混合物的弥补,同时,我们也不会相信它有足够时间在波斯自然化,并被视为其国家艺术的期间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这些人们虚构的皇家法典的影响,无可厚非是很显著的,而且我们也十分相信它们对波斯艺术特点也留下了持续性的印象,但是模仿和吸收的过程自然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在其影响可以扩大到印度这么远的地区之前,阿契美尼德人的权力就在减弱,尽管其延续了大流士三世统治下的印度省份,不可能的是,从赛瑟斯(波斯王)时代(或者可能在那之前)起,他们的文化或艺术就已经对犍陀罗和旁遮普产生了直接影响。(未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