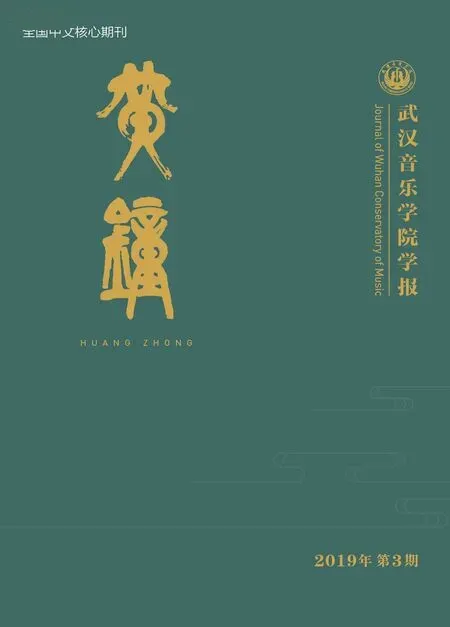坎坷行尽,终见康庄
——“流行音乐分析”的学术发展历程
赵 朴
流行音乐吸引了众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目光,这些来自不同视角的研究在方法上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社会学、文化学和民族学为理路,观察流行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语境”(Context)研究;二是以流行音乐本身的语言形态和结构逻辑分析为基础,进而作出音乐意义阐释的“文本”(Text)研究。文化批判学派在流行音乐研究开展的初始阶段是主力军,受其影响,解读流行音乐社会意义、文化价值的“语境”研究占很大比重,跳过音乐形态分析只谈“文化”,甚至成为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流播深远。20世纪70年代始,音乐学界开始正视流行音乐的研究价值,他们对音乐语言技术分析的重视使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气质与前一派大相径庭,“流行音乐分析”逐渐成为流行音乐研究中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流行音乐分析”,西文对应为“Popular Music Analysis”。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目前尚无文献对这一术语进行内涵和外延的阐述,是否把它作为“音乐分析”(Music Analysis)的学科分支也有待商榷。尽管如此,确实已经有大量通过深入分析流行音乐形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作出音乐意义阐释来研究流行音乐的专著和论文出现,这些文献在实质上建构起了“流行音乐分析”的概念。英、美等国家的学者们在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相对成熟,在他们的研究中,“流行音乐分析”已经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方法。
经过多年的尝试和积累,目前“流行音乐分析”的学术成果已蔚为壮观。①笔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数据整理和分析,详见赵朴:《流行音乐研究者的“寻宝图”——〈流行音乐理论与分析:研究与信息指南〉评述》,《人民音乐》2019年第2期,第93-95页。本文试图追溯流行音乐研究中形态分析路径的源头,并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观察其成长态势,描绘出“流行音乐分析”的学术发展图景。
一、 阿多诺及结构分析的惯性延续
回溯流行音乐研究的历史,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关于流行音乐的一系列论述大致可看作这一领域的滥觞。就目前所知,阿多诺论及流行音乐的文章主要有《论音乐的社会情境》(“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1932)、《永别了爵士乐》(“Farewell to Jazz”,1933)、《论爵士乐》(“On Jazz”,1936)、《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的退化》(“On the Fetish-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1938)、《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1941)等。②Theodor W.Adorno,Selected by Richard Leppert:Essays on Music,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p.288-317,pp.391-500.在这些著述中,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阿多诺对流行音乐展开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批评的匕首和投枪。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文论,在赞叹其视角独到、文笔犀利的同时,也不禁对阿多诺写作时因美学立场、时代背景造成的视野局限和因流行音乐当时本身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的误读表示遗憾。英国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对阿多诺提出的“流行音乐的被动消费”“流行音乐的消费需要并产生精神涣散”等观点曾发出质问:“流行音乐消费真的像阿多诺论述的那样被动吗?菲里斯所提供的销售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流行音乐的消费比阿多诺所认为的要主动得多。很明显,音乐的亚文化用途正是处在这样主动鉴别的锋利的刀口上。”③[英]约翰·斯道雷编著:《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回望阿多诺,并非意在品评他流行音乐研究中的得失,而是提请今日学界注意他在研究和写作方法中的两个特点:
第一,即便阿多诺是以文化研究为学术出发点来观察流行音乐,即便阿多诺是一位批判学派的代表和擅用“演绎”方法的理性主义者,即便“阿多诺的批判者常常以‘缺乏经验上的论据’为由对其理论进行质疑”④赵勇:《追求沉思还是体验快感:流行音乐再思考——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批判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54页。,即便阿多诺行文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严肃音乐的高扬和对流行音乐的“仇恨”,⑤赵勇:《追求沉思还是体验快感:流行音乐再思考——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批判理论》,第53页。他对流行音乐哪怕最鄙夷的看法也是通过对流行音乐本身进行分析得来的!尽管这些分析本身带有片面性,但是音乐形态分析,确定无疑是他发声的基点。在《论流行音乐》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达到对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准确的判断,只有严格审视流行音乐的根本特征:标准化。流行音乐的整体结构被标准化了,甚至规避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如此。标准化涉及从最常规到最特殊的特征。最著名的就是歌曲的副歌段包括三十二小节、音域限制在九度之内的规则。”⑥Theodor W.Adorno(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On Popular Music”(1941),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0,p.302.音乐整体结构的组织性及其关联的细节的可替代性,几乎是阿多诺观察、对比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形态时唯一的切入点。
第二,阿多诺在音乐品味上明显的古典主义美学立场,使他在对比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在结构和细节层面的区别时,明显对分析(书写)严肃音乐作品形态带有更大的热情,对贝多芬作品的举例更是信手拈来,这与他古典钢琴训练的深厚学养和师承贝尔格十二音作曲法的作曲家身份是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他在分析流行音乐形态时却失之潦草,急于归纳、抽象出所谓的“共性”,在几乎不曾拿出任一首具体的流行音乐作品分析为例证的情况下,放弃“辩证”的基本立场而单方面贬斥流行音乐在艺术表现层面的价值,有失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体统。诚然,就连批判者也承认“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并非完全不合理,这种分析适用于盖·隆巴多和安德鲁(Andrews)姐妹,也适用于‘凯迪拉克’和‘性手枪’(Sex Pistols)”,⑦[美]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陈祥勤译,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第219页。但当他进行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比时,单纯以形式主义美学出发,以音乐结构分析为丈量尺度,用大段对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结构组织设计的缜密有机来反衬流行歌曲结构的机械化、模式化,用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中主题旋律布局的密合连贯来反衬流行音乐中细节与整体的割裂,显然有失公允。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所作的文化批判,对流行音乐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点毋庸置疑。除了他的研究结论值得我们一再思考外,他在音乐分析中暴露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对流行音乐进行分析,以传统的音乐结构分析视角切入是否合理?流行音乐研究是否应该拥有更具针对性的形态分析方法和美学标准?)同样值得后人加以探究。历史的回响大约发出于四十年之后。
二、批判学派及歌词分析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摇滚音乐爆发,似乎每首热门歌曲都能拿来验证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生产“标准化”“伪个性化”论断的英明。但是到了60年代,当“不列颠入侵”(British Invasion)把英国摇滚推向世界,特别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谁人乐队(the Who)等英国乐队和鲍勃·迪伦(Bob Dylan)、沙滩男孩乐队(the Beach Boy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等美国乐队/乐手横跨大西洋产生了“美妙的共鸣”⑧歌曲《美妙的共鸣》(Good Vibrations),是沙滩男孩乐队在20世纪60年代的名作,在摇滚音乐语言发展历史中有重要的意义。时,摇滚音乐家巨大的创造力真正迸发出来,音乐形态极大丰富,音乐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多诺理论阐述的基石——流行音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及由此导致的音乐形态的“标准化”——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如果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手法和日新月异的新风格是学者们望而却步、逐渐远离,甚至放弃在研究流行音乐时以形态分析为基础展开论述的原因,那也只是原因之一。
当摇滚乐为主导的流行音乐彻底改变了大众音乐生态,其关联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霸权、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社会性别及女性主义等一系列命题,在社会文化学者看来无疑是待挖掘的学术富矿。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文化批判学派衍生出的批判音乐学研究给予流行音乐研究极大的关注。在一部重要的流行音乐研究文集《论唱片:摇滚、流行及文字书写》⑨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0.中,英国音乐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和安德鲁·古德温(Andrew Goodwin)挑选了三篇论文作为流行音乐研究的奠基文献: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聆听流行音乐》(“Listening to Popular Music”,1950),社会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的《流行歌曲中的求爱对白》(“The Dialogue of Courtship in Popular Song”,1957),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与帕迪·霍内尔(Paddy Whannel)合著的《年轻的听众》(“The Young Audience”,1964)。
这三篇先驱性的文章虽然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但是“都试图把年轻人的音乐从学院的蔑视中拯救出来”⑩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p.2.,而且他们都遵从共同的策略:“他们认为流行歌和摇滚乐的商业化生产是理所当然的(大众文化批评所描述的标准化、市场操控等),但是提出年轻人的音乐消费比大众文化理论中暗示的要更加主动、更有创造性、更为复杂。”⑪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p.2.毫无疑问,这批文章都把流行音乐视作社会学、文化学范畴的研究对象,关于这种状态的因由,编者西蒙·弗里斯在编辑绪言中开门见山的指出:“流行和摇滚音乐的学术研究植根于社会学,而非音乐学(直到现在,流行音乐在音乐学中充其量就是个边缘兴趣)。”⑫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p.1.要知道,弗里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对流行音乐作品本身的分析只涉及歌词。《流行歌曲中的求爱对白》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作者霍顿以235首流行歌曲为对象,以戏剧情节发展的方式将其中的歌词所表现的求爱阶段加以分类,包括“序曲:期待与梦想”“第一幕:求爱”“第二幕:蜜月”“第三幕:爱情衰落的过程”“第四幕:孤独”,⑬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and The Written Word,pp.15-21.文中例举的歌词达到196首之多,充分剖析了流行歌曲中歌词创作对“我”“你”个体交流的偏好,并定量地分析说明哪个求爱阶段的主题更受青睐。通过歌词的修辞学分析,作者的论述延伸到青年文化、性征、个体表达及身份确认等社会文化研究领域。
歌词比音响在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上要直观得多,引述歌词往往更方便研究者进行诠释,以达成对歌曲内在,甚至超越歌曲本身的意义的阐发。而且,“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而且写过剧本”⑭张华:《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的访谈》,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351393/?type=rec,引用日期:2017年12月20日。,对他们而言,分析文字比分析音乐更为驾轻就熟。
在流行音乐研究历史中,这种方式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甚至会看到在很多著述中,对流行音乐的分析基本等同于对流行歌曲中歌词的分析,这在非音乐专业研究者的著述中尤其常见:王彬在其博士学位论文⑮王彬:《当代流行歌曲的修辞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修辞指涉(歌词)文本修辞、运作修辞等,而完全与音乐语言修辞无关;美国作家亚历山大·泰鲁(Alexander Theroux)于2013年出版了一部摇滚歌词研究的专著《摇滚乐的语法:20世纪流行歌词中的艺术与淳朴》⑯Alexander Theroux:The Grammar of Rock:Art and Artlessness in 20thCentury Pop Lyrics,Seattle:Fantagraphics Books,2013.。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对音乐本身运行机制的理解及进一步的音乐意义阐释直至将音乐“书写”形成文字,每一步都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多非音乐专业人士并不具备这种技能,从擅长的角度切入意涵宽广的流行音乐研究,也是他们的本能选择。
批判学派对流行音乐的关注提升了流行音乐研究的“合法性”,至少在大的文化研究范畴中,学界对流行音乐是否值得严肃研究的态度有所松动。于此同时,阿多诺等上一代学者的研究中对音乐本体给予关注和分析的做法却被忽略了。
三、音乐学、“新音乐学”及跨学科视野下的流行音乐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起,音乐学自身的发展方向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转移。1965年,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发表‘美国音乐学侧影’一文,指责美国音乐学界缺乏反思,缺乏价值判断和审美批评,呼吁音乐学从实证主义的死水中走出”⑰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期,第100页。克尔曼原文标题也被译为《美国音乐学概况》,Joseph Kerman:“A 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Journal of American Musicology Society,18(1965),pp.61-69.,掀起英美音乐学界倡导“文化音乐学”(Cultural Musicology)的浪潮。1985年,克尔曼的著作《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⑱[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汤亚汀校订,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进一步震撼了整个西方音乐学界,揭开了“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的大幕,而“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究成为‘新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取向”⑲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第43页。。与此同时,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对传统的音乐学研究施加影响。不满英、美音乐学中重“历史”轻“体系”、重“文本分析”轻“语境解读”的实证主义传统,“五、六十年代⑳尤其以1964年梅里亚姆发表的著作《音乐人类学》为标志。(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以梅里亚姆(A.Merriam)等民族音乐学家为代表,呼吁将一切音乐现象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研究西方音乐的学者们出于对以前音乐学那种只管音符、不问其他的实证主义的倾向不满,也纷纷要求音乐学全面靠向民族音乐学,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考察西方音乐”㉑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第113页。。英美音乐学界奉为圭臬的实证主义传统受到激烈挑战,引起他们的学术反思,其学术价值观、研究视野、方法论都发生了转变。
在这波从学术观念到研究范式整体转向的巨大浪潮中,实证主义主导的传统音乐学和注重音乐外部语境研究的“新音乐学”似乎在反思后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在克尔曼看来“不应该只停留在音乐史实(facts)的陈述上,而必须对已梳理清楚的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因此,他强调音乐学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ticism)”㉒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第42页。。克尔曼的理念被于润洋先生以《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实践为一种“音乐学分析”的研究范式:“音乐学分析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㉓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0页。
这些都是“济世良方”,但对于年幼体虚的流行音乐研究而言,一是太猛,二是太晚。流行音乐研究不期然就迷失了方向。
起步于社会文化研究的流行音乐研究本来就缺少英美音乐学传统中的实证方法根基,对找寻音乐“事实”和“证据”、阐明音乐语言“内在指涉”和“内部肌理”的渴望远不及对音乐进行文化阐释的兴趣。此时,音乐学学科方向的转变无异于火上浇油,使流行音乐研究只停留在外围而无关音乐自身的做法显得愈发合情合理。情况一再恶化,就连身为音乐社会学家的西蒙·弗里斯都无法坐视:“没有几个摇滚乐评论家关心它的音乐,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对社会学的关注胜过对声音的关注。”㉔Simon Frith:Sound effects:Youth,leisure,and the politics of rock’n’roll,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3,p.12.译文转自郭昕:《音乐学术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研究》,《音乐研究》2013年第5期,第87页。弗里斯发此感慨是在1983年,而早在十年之前,音乐学家中最早进行流行音乐专题研究的威尔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就斩钉截铁地指出,研究披头士的音乐“没有其他选择除非从音乐事实出发;没有描述它们的方法除非用已被接受的术语”㉕Wilfrid Mellers:Twilight of the Gods:The Beatles in Retrospect,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p.16.。令人遗憾的是,二十年后的2003年,音乐学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仍不得不撰文指出“我认为任何排除了音乐声音、不去解释为什么人们被某一特定声音而非其他声音所吸引的流行音乐的文化分析,至少从根基上是不全面的”㉖RobertWalser:“Popular Music Analysis:Ten Apothegms and Four Instances”,Allan F.Moore(ed.):Analyzing Popular Mus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1-22.。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朝向“新音乐学”的转向对流行音乐研究也不无益处。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研究视野扩大,音乐学家们终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音乐学术意义上的流行音乐研究。菲利普·塔格(Philip Tagg)不禁感慨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学院派认为应该要开始认真研究流行音乐了,而是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来逃避它。”㉗Philip Tagg:“Analysing Popular Music: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Popular Music,Vol.1,No.2(1982).Reprinted in Richard Middleton(ed.):Reading Pop:Approaches to Textual Analysis in Popular Musi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2.
然而,致命的问题此时开始凸显:面对流行音乐这种在观念、形态和行为上都迥异于严肃艺术音乐的新样式,音乐学界缺乏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分析理论和方法。之前的音乐理论家们要么认为流行音乐在形态特征方面看上去过于“简单”而不屑一顾,要么因为对曲目了解程度实在有限而无从下手。如果站在今人的角度试着理解他们,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很多音乐学者毕竟不是在流行音乐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艺术音乐喂养出的听觉习惯塑造了学术研究思维定式。理解于事无补,问题毕竟还是明摆着,如果逃避——跳过本体分析直接进入意义的阐释——那与社会文化范畴的流行音乐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
1970年左右,老一辈音乐学家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音乐学领域开始出现最早一批流行音乐研究专著,爱德华·李(Edward Lee)的《人民的音乐:大不列颠流行音乐研究》㉘Edward Lee:Music of the People:A Study of Popular Music in Great Britain,London:Barrie and Jenkins,1970.(1970)、亚力克·怀尔德(Alec Wilder)的《美国流行歌曲:伟大的发明家们1900—1950》㉙Alec Wilder:American Popular Song:The Great Innovators 1900-19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1972)、威尔弗雷德·梅勒斯的《众神的黄昏:披头士回顾》㉚Wilfrid Mellers:Twilight of the Gods:The Beatles in Retrospect.(1973)是其中的代表。综观这些著作,基本是以传统的音乐学研究方法来观察流行音乐作品,例如以出版的纸质乐谱作为音乐分析的首要文本,以拆解零件式的结构分析视角看待音乐中的节奏、音程、旋律、和声、曲式、歌词等要素。这种“常规”操作以如今的流行音乐研究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说明音乐运行机制、描述音乐内在肌理方面也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不过,这毕竟开启了专业音乐学术领域研究流行音乐的大门,意义重大。
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美国和欧洲爆发了“婴儿潮”(Baby Boom),这一代人的成长不但催生了以摇滚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爆发,也造就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学者。菲利普·塔格、西蒙·弗里斯、理查德·米德尔顿(Richard Middleton)、罗伯特·瓦尔泽、艾伦·摩尔(Allan Moore)、沃尔特·埃弗雷特(Walter Everett)等当今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名家都属于这一代。他们的成长伴随着英美摇滚乐的蓬勃兴起,从生活经历来看,其青年时期都是浸淫摇滚乐中的,对音乐本身的亲近和稔熟使他们无障碍地投身于学术研究,并且具有流行音乐内行的学术视角,“学者—歌迷”㉛Richard Middleton:“Popular Music Analysis and Musicology:Bridging the Gap”,Popular Music,Vol.12,No.2(May,1993),p.180.集于一身的角色塑造对于流行音乐研究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八九十年代,这批学者的渐次成熟开创了流行音乐研究的新局面,他们表现出学术思维开放、理论方法多样、知识结构丰满、眼光独到切中要害等特点。
从梅勒斯和米德尔顿这对师徒㉜米德尔顿在英国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正是梅勒斯。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代流行音乐学人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在梅勒斯《众神的黄昏:披头士回顾》一书中,作者以历史研究为框架,对披头士的录音室专辑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并纳入了乐队解散后成员早期的单飞专辑。在对作品的音乐语言展开具体分析时,基本使用传统的音乐分析方法,集中于调、和弦、动机、配器等元素的标识,并把它们与歌词结合进行创作思维的解读,这与音乐学中艺术歌曲的研究方式并无太大差别。再看米德尔顿发表于1990年的著作《研究流行音乐》㉝Richard Middleton:Studying Popular Music,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在内容上融汇了音乐与文化两大研究范畴,涉及史学、哲学、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音乐分析等研究领域,并关联科技、政治等方面。作者在第二章以其独到的见解回应了阿多诺对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区分的片面性分析表述;第四章详细解读了音乐学在应对流行音乐研究时的问题,并以一些具体案例来说明音乐学和“新音乐学”研究方法在流行音乐研究中的适用性。作者以大量的作品形态分析来支撑理论阐述,应用的方法和路径囊括了申克尔分析法、动机分析、曲式结构分析、句法分析、认知过程分析及民族音乐学中的分析方法等,分析作品范围也覆盖了摇滚、民谣、爵士乐、索尔、放克等体裁。两相比较,后者掌握的分析手段更有针对性、曲目范围更宽、理论视野更开阔,换句话说,作为一名流行音乐研究者而言,更内行。
不难看出,米德尔顿研究流行音乐的理论方法已经超出了音乐学,甚至是“新音乐学”的范畴,与民族音乐学、语言学、心理学交叉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态势,这正是流行音乐研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还有学者在评价西蒙·弗里斯的流行音乐研究时说到:“不仅主张流行音乐的跨学科研究,而且身体力行,他的研究往往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音乐学、文学研究、历史和哲学研究于一体。”㉞王彬:《流行音乐呼唤新的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70页。菲利普·塔格也在论文《分析流行音乐: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明确指出:“研究流行音乐是一件跨学科的事。音乐学依然落后于这个领域内的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这对音乐学家而言不利与有利并存。有利之处在于音乐学家能够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来赋予分析一个恰当的视角。的确,研究应该以这样的起点展开:论述音乐的分析完全不涉及社会的、心理的、视觉的、姿态的、仪式的、科技的、历史的、经济的、语言的方面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方面与所研究的声音事件涉及的体裁、功能、风格、(再)表演情况和聆听的态度是互相关联的。不利之处在于音乐学的‘内容分析’在流行音乐领域中仍旧是一个未开发地带及某种缺失的环节。”㉟Philip Tagg:“Analysing Popular Music: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Popular Music,Vol.1,No.2(1982).Reprinted in Richard Middleton(ed.):Reading Pop:Approaches to Textual Analysis in Popular Music,p.74,78.
流行音乐研究中跨学科的视野在塔格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在扬弃社会学研究成果、设计新的研究策略的同时,他点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突破的两个关键词:声音事件、内容分析。
塔格这篇发表于1982年的文章是笔者目前所见第一篇把“流行音乐分析”提升到专题研究层面并加以系统阐述的论著。如今,缺乏针对流行音乐作品的形态分析方法这个一直困扰流行音乐研究的难题,受到学界日益重视的同时,在跨学科研究意识普及的背景下,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攻克。
塔格发展出一套使用符号学的方法对流行音乐语言信息作出分类分析,而后再加以社会学、意识形态诠释的分析范式;米德尔顿则在1993年的论文《流行音乐分析与音乐学:桥接鸿沟》中旗帜鲜明地建议“直接采用对‘姿态’理论的探究”㊱Richard Middleton:“Popular Music Analysis and Musicology:Bridging the Gap”,p.177.,雅诺斯·马霍提(János Maróthy)的节奏理论、格哈德·库比克(Gerhard Kubik)的非洲音乐多中心运动理论等民族音乐学家的先期成果成为他的理论基础;摩尔在其1993年的著作《摇滚乐:首要文本:发展摇滚乐的音乐学》㊲Allan F.Moore:Rock:The Primary Text:Developing a Musicology of Rock(2nd ed.),Burlington,VT:Ashgate,2001[1993].中指出音乐学传统中对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的分析依然能够对流行音乐分析发挥作用,而且更要以“音盒”模型为基础,将科技影响下的新维度加入,特别要关注效果器、合成器、录音等技术环节带来的音色改变;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在其1998年的著作《分析音乐的多媒体》㊳Nicholas Cook:Analysing Musical Multimed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7-173.中,以麦当娜的歌曲《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为例,阐述了他“影像音乐学”的分析范式,这种综合分析范式囊括了流行音乐录影带文本形态中歌词、音乐、影像、表演等多维度的分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已经成为当前以音乐分析为基础的流行音乐研究中令人兴奋的景象。在一派欣欣向荣甚至令人应接不暇的态势下,菲利普·塔格的前瞻性再次显现:“很清楚的是,以一个整体性的途径来分析流行音乐是唯一可行的,……这种途径明显要求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有希望去掌握其知识范围。”㊴Philip Tagg:“Analysing Popular Music: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p.78.“流行音乐分析”的多学科、跨学科属性客观要求研究者们加强彼此的交流合作,甚至是团队工作,流行音乐研究学术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
继1971年首部流行音乐研究专题刊物《流行音乐与社会》(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创刊之后,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米德尔顿和大卫·霍恩(David Horn)联手创办了《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这份刊物后来成为流行音乐学术研究领域国际公认的权威期刊,此外,专题研究学术刊物还有“英国音乐学家德里克·B.斯考特和斯坦·霍金斯(Stan Hawkins)于1994年创办的《流行音乐学》”㊵郭昕:《音乐学术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研究》,《音乐研究》2013年第5期,第82页。。1981年,在查尔斯·哈姆(Charles Hamm)、弗里斯、塔格、霍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Music,缩写为IASPM)成立,这是目前流行音乐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除了以欧洲和北美为主要活动区域外,在亚洲(日、韩)和拉丁美洲也设有分部,该组织的北美分部另设学术期刊《流行音乐研究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Music Studies)。学术期刊和国际组织等学术平台的设立,对流行音乐研究者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流行音乐研究的日益蓬勃,也在推动“流行音乐学”(Popular Musicology)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㊶学界对这一“学科”门类的“合法性”还有争议,如艾伦·摩尔在他编撰文集的引言中就提到这个术语的“误导性”,详见Allan F.Moore:Analyzing Popular Music,p.2.
“流行音乐分析”作为流行音乐研究的结构基础,愈发受到学界重视,尤其在博士学位论文层面有着突出的表现。据托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编纂的《流行音乐理论与分析:研究与信息指南》(Popular Music Theory And Analysis:A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Guide)㊷Thomas Robinson:Popular Music Theory And Analysis:A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Guide,NY:Routledge,2017.统计,自1970年至2014年,在英美等流行音乐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至少有51篇博士学位论文以音乐分析为主体展开流行音乐研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此类研究成果呈现井喷之势:2000年之前共10篇,2000-2014年就有41篇,这标志着以“流行音乐分析”为基础的流行音乐研究已经成为了一支生机勃勃的学术力量。
结 语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坎坷的“流行音乐分析”,在今天呈现出开放多元的学科理念、丰富的研究方法和扎实的文献成果,建立起自身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流行音乐研究才得以建立“文本”与“语境”并重、整体趋向平衡的良性发展态势。
回溯“流行音乐分析”的学术发展历程、理清流行音乐研究整体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或将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流行音乐研究提供观念和方法上的借鉴。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流行音乐曾在一段时期遭受着文艺批评不公正的对待,更遑论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这种状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流行音乐自身的蓬勃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次全国性的流行(通俗)音乐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界对流行音乐的正视和流行音乐学术研究的开启。进入新世纪以来,流行音乐在我国日益活跃的文化生活中绽放出愈发夺目的光彩,也因其与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而引起了众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同国际领域的流行音乐研究如出一辙,我国的流行音乐研究也大都偏向以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流行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语境”研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很多是源自或直接取自西方的文化批判学派的。同样类似的是,我国的音乐学者起初对研究流行音乐也是兴趣索然,相对主动的是一些有着音乐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但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与流行音乐相关的民族、身份、场景等论题。不难发现,这样的研究是在“重复西方研究者昨天的故事”,对音乐“外围”的关注掩蔽了对音乐自身意义生发系统的理解,其中的学理失误前文已有详述。我们不见得要把他人已经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观史知今当思进退,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可喜的是,随着我国新一代音乐学人的成长,建立在音乐形态分析基础上的流行音乐研究成果也已经开始出现,这既是研究者以扎实的音乐学术功底为依托的自主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国际前沿研究理念的接轨,更是一代伴随着流行音乐成长的青年音乐学者对流行音乐发自内心热爱的真实写照。相信,我国的流行音乐学者会逐渐习惯“两条腿走路”,“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并重,走上流行音乐研究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