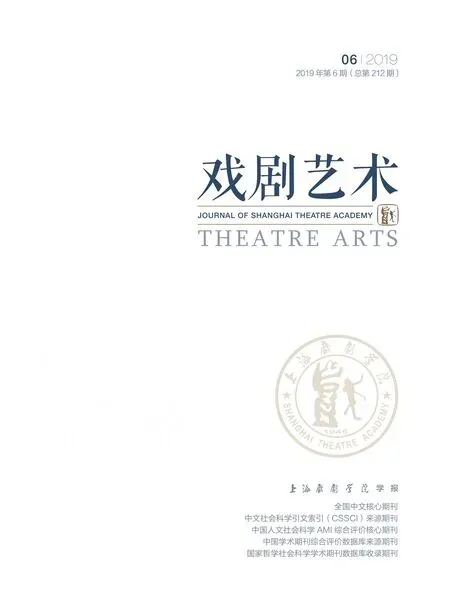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傀儡戏
——读《中国傀儡戏史》的启示
2017年,叶明生教授所著的《中国傀儡戏史》一书面世,笔者不敢称其研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认为《中国傀儡戏史》应该是一部开创性引领我国傀儡戏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千百年来,中国戏剧(曲)的理论学说多以研究主流戏曲为主,对于傀儡戏(又称木偶戏、木人戏)这一曾经出现在汉唐百戏第六位的艺术门类则似乎未予重视,傀儡艺术一直以来被视为诸多戏剧艺术的“边缘”部分,不作为戏剧(戏曲)的整体中值得一提的部分。在我国的史籍记载中,傀儡戏更多出现在遣怀诗文中,主要是借物(傀儡)喻人、借戏抒怀。而在正史和地方志中,对傀儡戏的记载和其他艺术种类相比可谓是言之甚少,主要是将傀儡戏作为一种存在的民俗现象或艺术活动加以记录,一笔带过。
造成这种情况大概有三点原因。一是因为傀儡艺术所用的傀儡戏具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奇淫巧技,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抵制与禁止,因此缺乏正史记载。二是因为傀儡艺术的起源与丧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其独特的表演方式被部分文人视为不祥,加上古代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因此缺乏文人重视。三是因为在傀儡戏的祭祀功能逐渐转变为娱乐功能后,傀儡戏与其他艺术的功能开始重叠,尤其是戏曲的日益成熟,使傀儡戏的演绎内容和所表现出的演剧形态与其他戏曲种类有着高度重合,或者说是依附于其之上,导致戏曲研究者和创造者对于傀儡戏的研究仅是稍加记录,而更多研究的重心则是人戏。因此,对于傀儡戏的历史记载不如其他艺术完整,甚至夹杂在某些戏曲剧种的记载之中,非常难以形成系统。
这种现象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好转,学术界逐渐出现了研究傀儡戏的著作和文章,如王坟所著《傀儡戏之点点滴滴》(1932年),佟晶心著《中国傀儡剧考》(1934年),孙楷第著《傀儡戏考原》(1944年)等,这一时期的傀儡戏研究重在溯源,并且对傀儡戏的发展脉络做了初步的探索。当代,我国对于傀儡戏的学术研究状况略有改善,李昌敏的《湖南木偶戏》,黄少龙的《泉州木偶艺术概述》,白勇华、洪世健的《南派布袋戏》等著作相继问世,但这些大都是介绍本省的傀儡(木偶)艺术,印数很少,影响也不广泛(1)刘厚生:《中国木偶艺术》(序言),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并且绝大多数为当地院团的建团史及建团后的发展介绍。真正系统地将中国傀儡史进行梳理的,最早应属丁言昭先生所著的《中国傀儡史》以及刘霁、姜尚礼先生的《中国木偶艺术》,但可惜二者所著图书篇幅不大,著者自己也说:“只是把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木偶发展的重要史料进行较浅显的介绍。”(2)丁言昭:《中国木偶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页。“只是简略的概况介绍。”(3)刘厚生:《中国木偶艺术》(序言)。当然,书中所提到的种种无疑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进入21世纪,郭红军、赵根楼先生所著的《中国木偶艺术史》、台湾学者曾永义所著的《中国偶戏考述》是较为重要的研究傀儡艺术的著作,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笔者认为《中国傀儡戏史》超出了其他一般描述性的傀儡戏史书的价值。首先在于该著作通过其他史著少见的资料将官方、文人阶层、宗教与民间各种形态的傀儡戏的发展演变纳入研究范畴,以大量详实而新鲜的史料填补傀儡戏史研究的部分空白,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傀儡戏从整体到细节的全面认知水平。此外,该著作更大的价值在于中国傀儡戏研究的方向性问题以及由此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叶明生教授通过深度的观察与研究,为中国傀儡戏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可能,其在理论视野和思想方法上的启发意义,甚至超过了具体论述所取得的成绩。
一、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傀儡戏的乡土性问题
中国传统戏剧(戏曲)形成于民间,生长于民间。民间性是中国传统戏剧(戏曲)的重要特征,傀儡戏亦不例外。傀儡戏起源于民间,兴盛于民间,当城市傀儡戏式微之时,亦流传于民间,在农村遍地开花,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然而,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傀儡戏日渐被西方傀儡戏所冲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留学回来的文人学者的思想意识中,傀儡戏不过是走街串巷的“无聊的东西”,是一种需要拯救的艺术样式,甚至曾充当过话剧表演的反面教材。但同时,他们也承认傀儡戏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认为只需要除掉那些“麻醉的,有毒的,古语的,陈腐的成分,而来改编或新创那革命的进取的今话的新式的作品,到民间去切实地传播,不但对于文盲有丰富的文艺教育的效用,就是对于文化人,因为它们能付以直觉的生动而深刻的印象,所以同样地有价值”。(4)杨晋豪:《行动文艺论》,《申报》(上海版),1939年1月7日,第15版。
由此,中国的传统傀儡戏逐渐演变为新式的傀儡戏。无论是陶晶孙创作的新式木人戏(傀儡戏)还是虞哲光先生等人的新式创作理念影响下的傀儡戏,都表明着中国近现代以来所创作的傀儡戏是对西方木偶戏的大幅度接受或者说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而中国本土的传统傀儡戏却由于这种新式傀儡戏的兴盛日益边缘化,渐渐淡出了城市民众的视野,转而隐匿于乡村,如今又随着民间老艺人们的逐渐逝世与传承人的青黄不接,在农村中也日渐消亡。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由地方编写的研究当地傀儡艺术的书中,更多的是以当地院团建团后的发展史替代了当地历史悠久的傀儡民间艺术史,大量民间傀儡戏却缺乏足够的挖掘、保护与研究。种种情况表明,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方面,中国现在进入大众视野的傀儡戏是一种来自于城市文明的、去乡土化的现代傀儡戏,现代傀儡戏的发展和研究固然重要,但因其无法完全代表中国傀儡戏的真实面貌,在其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另一方面,深藏于乡村的中国传统傀儡戏始终无法进入大众视野,这使中国传统傀儡戏失去保护这一情况势必比历史曾发生的更加严重,对中国传统傀儡戏的研究也会更加匮乏。于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傀儡戏很可能面临着从学术到艺术创造都即将消亡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一本真正的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傀儡戏的史书的出现,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傀儡戏的史书出现,一本真正讲述中国传统傀儡戏的史书出现,来为解决以上的困境提供基础保障。
叶明生教授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站在傀儡戏是乡土戏剧的理念基础上,深入农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他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的木偶戏已不是傀儡戏的本来面目。”(5)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第39页。只有深入农村和傀儡戏剧种的家族坛班开展长期深入的调查,才可以寻根溯源。而如果“在国内农村或国外剧院看了几场戏或做了一点访谈,于是便大呼小叫,大谈‘发现’”,这样的成果“依然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可以看出,叶教授以傀儡戏的民间乡土性为核心的这一研究原则的提出,是有感于当今傀儡戏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的。而叶教授是当之无愧地看出偏颇、全力给以纠正、最终又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
一方面,傀儡戏的乡土性体现在傀儡戏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在当下,对于傀儡戏的研究中,傀儡戏和民俗之间的密切关系恰好是学术界多所忽视的。好在《中国傀儡戏史》一书中,我们清晰可见傀儡戏的民间力量。叶教授认为,“我国民间,傀儡戏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它与民众的世俗生活中之人居生态关系十分密切”。叶教授用翔实的史料描绘出一幅傀儡戏的民间兴盛的画卷:元朝统治者虽禁演民间戏剧,但傀儡戏的迎神赛社和禳灾祈福演出时而有之;在明朝时,社会流行的傀儡戏主要为了借戏遣怀和寿诞庆喜;至清代,傀儡戏甚至与救产护婴产生联系。此外,新婚、建屋、水火之灾、新开水井、打虎、惩罚违反乡规等场合皆要做傀儡戏。通过《中国傀儡戏史》一书对傀儡戏与民俗之间密切联系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傀儡戏兴盛的原因就在于其深深扎根于民间,服务于广大人民,能够有机地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文化诉求和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乡土性还表现在傀儡戏作品的内容上,它不同于士大夫的雅文化,傀儡戏的故事内容更多是符合广大乡村百姓的一种审美情味。 叶明生教授解开了傀儡戏剧目中的乡土性特点:宋元时期,傀儡戏故事内容有歌舞戏《鲍老舞》;杂剧《蔡伯喈》《彩衣堂》《西厢记》;南戏《太平钱》等。明代又出现了神话剧如《夫人传》《华光传》《九龙记》等,清代傀儡戏不仅继续沿袭杂剧、南戏、梆子线腔、乱弹,还出现了三小戏、花骚戏。 傀儡戏的剧目内容的乡土性不仅体现在民众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惩恶扬善等故事中,还热衷于表现乡村乡里的故事,比如《王婆骂鸡》《李翠莲》《卖豆腐》《割韭菜》等。这种“调侃戏弄类娱情小戏”是傀儡戏的传统,“是唐宋‘弄郭秃’之遗风”(6)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443页。,这种充分展现劳苦大众生活、充满民趣的故事,恰恰代表了傀儡戏一直存在的乡土性特点。
我们知道,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艺术,一定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中国傀儡戏延绵二千余年,至今仍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舞台上,一定是具有充分的民间基础。通过叶明生教授的书,可见中国传统傀儡戏剧的乡土性是数千年傀儡戏发展延续的根本,而想要保护中国传统傀儡戏,势必要从其民间乡土性入手,因此,叶教授此书不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传统傀儡戏这一非物质遗产保护,如何制定更好的政策保护它们?我想,应从其民间乡土性入手,寻找影响其发展的根本力量,才能探讨其发展和保护的未来方向。叶明生教授对于中国傀儡戏的民间挖掘和整理,或许可为政府制定具体可行的保护政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客观看待中国传统傀儡戏的信仰功能问题
任何艺术都有实用功能,傀儡戏亦不例外。傀儡戏实用功能不仅在于其娱乐功能,更在于其具有民间宗教信仰功能。傀儡戏从起源开始就与祭祀、神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陪葬所用之俑,到丧家之乐,再到戏剧表演。无论傀儡戏如何演变发展,始终贯穿其演变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承载着民间百姓的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我们或者可以说,傀儡戏其实可算是民俗祭祀仪式戏剧的一种。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傀儡戏戏具——傀儡形象的特殊性。乡土社会中的信仰活动多围绕神灵展开,作为神的象征与化身,神像在乡土信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让神明在现实中变得具体可见。(7)李生柱:《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可以说,神像代表了人们对神佛的想象与观念,是民间信仰的象征的具象体现。傀儡与神像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在我国的村庄,经常可见刻木为偶供奉的神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曾记载两汉封禅的泰山庙内的神像:“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8)赵敏俐,尹小林主编:《国学备览(第5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325页。可见傀儡戏表演所用戏具和神像相比,从用材上和称呼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神像灵性的获得是通过仪式中各种社会群体的视觉互动和认同观念共同建构的,由于傀儡戏和神仙雕像一样采用偶来实现人物形象的外化呈现,这就使傀儡戏的表演戏具也可以通过社会群体共同认知的视觉和观念形象来将神像转化为傀儡。某种程度而言,傀儡戏的戏具就是一尊缩小的神像,实现了神佛——神像——傀儡的转化。
在我国民间,有些木偶戏(傀儡戏)表演的地点必须为当地的庙宇,在某神明的诞期,供奉该神明的村庄要有相应的敬神活动。木偶戏(傀儡戏)表演即是这些敬神活动中最为常见的一项活动。(9)李文杰,梁晓:《广东吴川木偶戏发起表演的民俗缘由及其组织形式》,《教育教学论坛》,2017年第44期。人们在礼敬神明时邀请木偶戏(傀儡戏)演出,通过木偶戏(傀儡戏)传达一种仪式感和民间对宗教敬仰的需要,村民在看待木偶戏(傀儡戏)时自然多出了一种如同敬畏神明的心态。(10)何颖川:《塘坊乡木偶戏礼俗文化之探析》,《传播与版权》,2017年第10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傀儡戏最主要的实用功能其实是在于满足民间信仰,众多信奉神明的人民相信通过傀儡戏的仪式表演可以驱邪避灾祈福禳疾,作为仪式戏剧的傀儡戏,它的宗教信仰的属性是大于艺术属性的,其宗教魅力也是大于艺术魅力的。
叶教授的书中用大量的资料弥补了以往傀儡戏史中对于傀儡戏剧宗教仪式属性缺乏足够研究的遗憾,他认为自宋元开始,与“都市木偶高度戏曲化”不同的是,南方的部分民间傀儡戏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巫道结合的道路。“以傀儡行法事的‘香火戏’在江南各地兴盛起来,其名称随之被地方所改变,或称‘阳戏’、‘提阳戏’、‘愿戏’、‘梨园教’。”(11)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261页。叶先生以详细的史实和严密的考证,展现出了仪式傀儡戏和道教闾山派巫法相结合的宗教戏剧的活动情况;介绍了傀儡戏与佛教的结合,如在中元节盂兰盆会上演傀儡戏《目连救母》等;介绍了以提线傀儡为法事特征的民间道教“梨园正教”;对于江西的“傩戏”和“傀儡戏”共同表现的情况也有所涉及。
另一方面,叶明生教授还指出了传统傀儡戏“神异化”的现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其一,傀儡戏“因其有神秘的传说史,加之多于祭祀仪式中演出神话戏,故其木偶身亦被民间神秘化”。(12)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415页。叶教授通过对《阅微草堂笔记》和《漳州府志》等史料的分析,挖掘出了明清时关于傀儡戏的神异故事,为古代傀儡戏在民间被赋予神秘色彩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二,傀儡戏的“神异化”现象是傀儡戏历来被统治者或士大夫阶层所禁演的原因,由于傀儡戏的“神异化”特点具备极强的宗教属性,使士大夫阶层深深不安,故统治阶级予以明确的禁止:“此乃道释教谢神体质,禁之放进凡五世矣。”(13)清嘉庆十二年惠安县百奇村郭纯甫撰《郭氏族谱》,引自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313页。其三,对于将宗教信仰和傀儡表演结合的行业机制,如坛班的设立和傀儡师的社会地位也做了大量的文献剖析:由于具有“通神鬼”的能力,傀儡表演者的道师身份被民间所尊重,傀儡师可以参加科考进入族谱,证明了傀儡师(尤其是提线傀儡艺人)的社会地位应高于优伶。这些资料在其他傀儡史中只是简略带过,叶教授用大量史实进行对傀儡戏的“神异化”分析,从侧面印证了其和仪式戏剧之间的关系。
叶教授深刻地指出:“我国无论古今南北之民间傀儡戏,其均在宗教与祭祀的氛围中发展起来,并在民众的宗教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作用。这种宗教祭祀的社火、醮仪无疑是为傀儡戏提供生存的载体,也是傀儡戏发展的温床,是我国傀儡艺术得以生存的重要生态环境。”(14)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313页。叶教授对于傀儡戏作为一种民间宗教信仰仪式戏剧做了系统梳理和理论阐述,构建了傀儡戏特殊宗教形态结构的框架,为傀儡戏的宗教文化活动补充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填补了傀儡戏在这一方面研究的部分空白,使傀儡戏的学术高度和艺术价值得到提升。
由此也引发我们深度的思考,从汉代起源的俑到丧家乐到傀儡戏,中国传统傀儡戏的民间宗教信仰功能是一条贯穿了二千年的古文化的重要线索,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历史文化印记,具有深厚的历史、宗教文化价值和神秘的审美色彩。如今,傀儡戏中这种民间宗教文化的因素正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亡,仅仅留下了其娱乐功能。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仪式戏剧存在的地方傀儡戏,其在表演风格、体现手法和艺术理念上势必会难容于今天的戏剧艺术之中,如果一味地以戏剧艺术的要求来看待仪式戏剧,势必会产生傀儡戏艺术价值低下的片面看法。面对傀儡戏艺术的未来发展,我们必须对仪式类傀儡戏和艺术类傀儡戏加以区分,对仪式类傀儡戏加以重视,不能忽视傀儡戏的宗教信仰的一面。正如叶教授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批判和摒弃,就会伤害到民族文化的根基”。(15)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593页。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我们应将傀儡戏的仪式戏剧这种艺术形态深深挖掘并加以保护,而并非简单地从艺术特色和艺术形式上加以保护,以更合理地传承民族文化。
三、着重探讨中国传统傀儡戏的戏曲性问题
傀儡戏、古代百戏与成熟的戏曲艺术都表现出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百戏与戏曲艺术、傀儡戏之间表现出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是戏曲艺术对傀儡戏而言所呈现出的亲密关系。前者表现为艺术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交流、融合并逐渐走向成熟,后者表现为成熟的艺术形式基因之间的再度洽释,并以新的方式被傀儡戏重新挖掘与继承,进行特色的凸显。
自宋元以来,傀儡戏一直处于和戏曲艺术发展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从简单的古代歌舞、角抵戏、百戏到戏曲初始阶段的杂剧、南戏、话本再到成熟的戏曲形式,傀儡戏艺术也同样是由简到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多种多样的姊妹艺术进行学习、吸收与融合,不断地与戏曲艺术各种时期的形态进行“联姻”。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戏曲特征始终贯穿于傀儡戏之中,难分彼此。自明清以来,戏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昆为首的戏曲百花苑,戏曲艺术有了蓬勃的发展。 傀儡艺术也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不自觉地沿袭、借鉴了戏曲艺术中丰富的表现性和审美特征。傀儡戏从剧目内容、外部造型、声腔表演等方面都与戏曲艺术在审美视角与舞台呈现上高度趋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傀儡戏自古以来就是由人操作傀儡表演的 “戏曲”,是中国戏曲艺术另一种独特的演绎方式。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仿佛出现了一些转变,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戏剧的大幕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拉开帷幕,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中国的文化受到了冲击,而文化改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的艺术样式产生了“新旧”两个体系,一个是被正式命名为“话剧”,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新型艺术样式;一个是被贴上“落后”标签,积极寻求改良的“戏曲”。由此形成了中国 20 世纪戏剧格局长期的二元并存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傀儡戏也受到了极大冲击。如果说戏曲艺术在改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性特点和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那么城市的傀儡戏为了积极寻求突破,则摒弃了戏曲的艺术特征,转而采取了和话剧结合的方式进行演出。改良的内容包括了舞台布景的写实设置,声光电的配合运用,故事情节的国际化,对白以话剧对话方式为主,辅以音乐。换言之,原本属于戏曲艺术的傀儡戏开始走向了话剧创作的道路。在20世纪中后期,绝大多数城市傀儡戏偏向于话剧艺术形态的现象越演越烈。(16)在我国泉州、漳州、晋江等少部分地区,城市傀儡戏的戏曲性依然保存发展得很好。傀儡戏与戏曲的关系,似乎只能从农村傀儡戏中才可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渊源。至此,傀儡戏产生了归类的问题,它究竟属于戏曲艺术?还是话剧艺术?无法分类的傀儡戏如今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局面,“新旧”二剧兼可演绎,但又不能划分到任何一种艺术样式之中。另外,由于20世纪初,改良傀儡戏的文人更看重的是傀儡戏的儿童教育功能,上演的儿童傀儡戏更为人所熟知,于是傀儡戏在中国便又被划分为儿童剧的一种,这显然是一种错误。
现代傀儡戏的创建与发展,在近百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现代傀儡戏也形成了一定的风格特色,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中国傀儡戏表演的民族特色在一些方面存在减弱的现象。表演风格的混杂带来人们对中国傀儡戏属性的质疑和归类错误的认知。第二,中国傀儡戏的发展虽从戏曲起步,但在现代化进程与时代发展的影响之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保存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民族特色。
叶教授出身在戏曲世家,他显然很清晰地看到了傀儡戏戏曲性丢失会造成中国傀儡戏民族性消亡的严重问题,深刻地认识到戏曲对于中国傀儡戏的巨大意义。因此在叶教授的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傀儡戏、古代百戏和成熟的戏曲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汉代歌舞百戏对傀儡的催生作用到盛唐散乐中的傀儡子及其歌舞表演节目《郭老舞》,从“超诸百戏”的木人舞到瓦舍勾栏里的杂剧傀儡表演,从宋代参军色致语之程式到明代傀儡戏行当的划分,从傀儡戏伴唱曲调格词到腔体演唱的成熟,从路歧人到傀儡社会和行业机构“苏家巷”的形成。《中国傀儡戏史》把傀儡戏从先秦到20世纪的发育、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勾勒梳理和浓墨重彩的记述与评论。叶教授通过对戏剧史料的高度归纳、严密的考证和精到的学理剖析,把傀儡戏的高度戏曲化现象、戏曲剧种的分布以及随着时代的潮流观念的变化等一一铺展开来。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民国时期的文化运动的反思。叶教授认为:“虽其时胡适等人不乏文化变革之初衷,对后来的戏剧改良有一定影响,但他们仅凭自己留学者的优越身份,一片救国的情怀,为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竟然毫不顾及自己作为戏剧的门外汉,借用《新青年》的阵地,肆无忌惮地推崇西洋戏剧,全盘歪曲打杀传统戏曲,其激进思想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危害性极大。”(17)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592页。叶教授对于傀儡戏的发展危机认知如此精辟且深刻,如今,这种视中国傀儡戏的戏曲性特点为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面的观念依然存在于一些艺术创作者心中,这是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的问题。固然社会进步和时代潮流使傀儡戏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如果对于傀儡戏的戏曲属性不能正视甚至无法加大延续力度的话,将导致中国传统傀儡戏的根源断绝,也将使中国傀儡戏的民族性遭到人为的摧残和毁失。这正如叶教授所言那样:“这种教训应当永远儆戒。”(18)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第593页。
笔者认为,叶明生教授所坚守的傀儡戏史的研究思路,恰恰是解决中国傀儡戏发展至今天不得不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方法。叶教授开放的视野和独到的史家眼光不仅指引我们领略到傀儡戏无穷的宝藏,而且给我们方法论上的启示,授予我们去打开傀儡戏宝藏的钥匙,使我们未来可以以此为基础,去攻克一个个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傀儡戏的史籍资料匮乏且零散,要从如此散乱而浩繁的历史陈迹中梳理出傀儡戏发展的线索和其与民俗、宗教、艺术方面的关系,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叶教授用了二十余年来搜集各种文献和资料,最终成书,其学术勇气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当然,书中有一些观点尚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但总而言之,叶明生教授所著的《中国傀儡戏史》一书对我国傀儡戏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