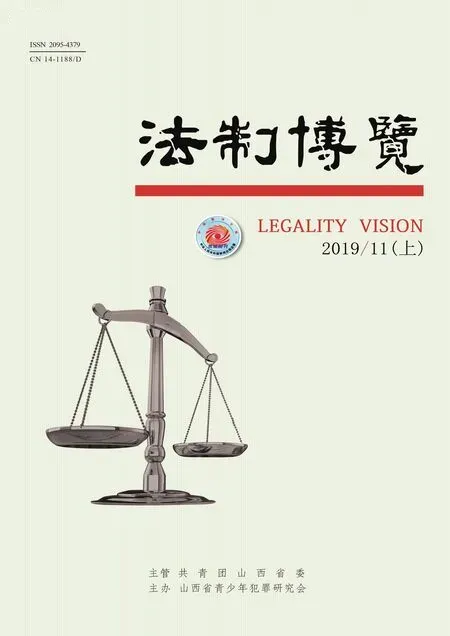案例教学法在法理学课程中的运用
许小亮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引言:法理学课程中的案例教学的问题
在法科学生的课程教学中,法理学的教学具有独特的地位。相比于部门法学来说,法理学并不直接面向真实的法律生活,而是面向部门法学所提供的基本概念本身,法理学的基本任务是对部门法的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体系化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的教学就是面向概念本身的作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面向法律思维本身的作业。相比于法律史而言,法理学教学欠缺历史经验的维度,也很少对思想演化和制度变迁中所蕴含的原因进行考证和分析,因此其缺乏历史经验的维度。①在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都欠缺的情况下,如何把抽象的法理学课程讲授好,且让学生容易接受,对法理学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了缓解法理学课堂的抽象性、枯燥性,也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理解晦涩难懂的概念思维,很多学者主张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但是,观察现有的对于法理学课程中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的案例教学法更多地使倾向于对部门法中的案例教学法进行挪用。这种挪用本身使得法理学的课堂不得不重复部门法的知识,更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二是现有的案例教学法对于案例的择取更多地以历史和现实中的热点案例入手,欠缺对法理学概念和体系的考量,从而使得案例教学呈现碎片化的趋势,不利于学生的体系性的法律思维的培养;三是现有的案例教学本身只是抓住了法理学的知识面向,并未呈现出法理学的伦理面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无助于学生通过法理学的学习去把握法的根本或基本问题,反而构成了学生理解法的基本或根本问题的障碍。
因此,有必要反思法理学课程中的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以及案例的选择、分析和批判等问题。首先,案例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案例让学生能够直接把握到法学中的根本问题,所以法理学课程中所讲授的案例一定是能够反映法学根本问题和难题的案例,一定是将诸多法律问题融汇在一起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既可能是由真实生活所引发的,也可能是由著名的思想家通过思想实验而提出的。其次,在进行案例教学时,必须考虑到案例本身与所要讲述的概念和体系之间的契合性,因此,对于案例的择取不能单一的考虑某一个部门法,最好的方式是在真实的案例中选择类案,然后从类案中抽象中普遍的法理问题,这样的案例教学既能够给学生以概念和体系的直观,又能够使得抽象和枯燥的法理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第三,案例的择取不能够如同民法和刑法那样只从生活中最为简单的现象出发,而应该触及人们对于生活关系的批判性思考,进而指向一种良好的生活模式的选择和追求。这也就要求案例的择取有着价值上的考量,即我们所讲授的法理应该是一种良善的法理。②
二、核心和根本案例的构思与择取
毫无疑问,法理学中的根本问题和根本难题所引起的案例择取与构思问题会以如下陈旧的方式被提出:它们依据何种标准被择取?依照何种基点被构思?要回答这一陈旧但却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构成了法理学中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构成了法理学中的根本难题?根本问题是被解决了的与此同时对整个学科体系起着奠基作用的问题。根本难题是未被解决的但构成了整个学科体系的边界的难题。前者构成法理学的本原问题,后者构成法理学的边界问题。按照长尾龙一的说法,法理学的本原问题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起源、法律的原理和法律的最高支配问题。③因此,核心和根本案例的构思与择取必须围绕以上三个问题而展开。
就法律的起源来说,核心和根本的案例的择取要从三个维度进行:生存的维度、生活的维度和生命的维度。现代法律的逻辑起点即在于对人的自我保存的肯认,因此在讲授法律的起源时,应当构思并找寻真实世界中对于人的自我保存的问题进行探讨的真实案例,围绕这种案例所进行的法理学讲授,将会呈现出易懂和活泼的特点。就此而言,富勒对于洞穴奇案的构思及其对这一案件所衍生出来的法律解决方案的讨论可以作为核心和根本案例的构思与择取的典范。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极为类似的案例,譬如英国的“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案”。从生活的维度来看,法理学课程中的案例一定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在一个简单的生活案例中,能够勾连起人们法律生活的不同面向:民事的面向、行政的面向和刑事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生活案例的择取就需要考虑不同责任和不同法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也一定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见的案例。因此,为了说明法律的起源,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说明“有社会即有法律”这一罗马法谚的有效性,有学者举出了醉酒交通肇事所涉及到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问题来说明。这就非常有效地解释了法律的起源在生活层面的呈现问题。而在生命的维度,法律的起源必须呈现出其价值的面向,也即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生命本身的神圣性和完整性。所以,要让学生从法理的角度理解生命的意义,就必须在生命开始之初和邻近死亡之时这一时间节点上寻找典型案例来加以说明。譬如,对于胎儿的保护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就不仅是一个部门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法理学上的一般权利的界限问题。对于是否允许安乐死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刑法的问题,而是法理学上生命权这一概念本身是否可蕴含死亡的权利这一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价值选择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法理学对于权利概念是否能够同时容纳在生活中相互对立的概念的并立的问题。
而在法律的原理的问题上,相关案例的择取应当遵循德沃金所提出的“疑难案件”的标准。因为对法律原理的讲授,肯定会涉及到对于法律原则适用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一定是在针对“疑难案件”的场合才有意义的。而法理学中所谓的“疑难案件”与部门法中所谓的“疑难案件”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法理学中的“疑难案件”本质上并关涉法教义学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法哲学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对于法理学课程中的“疑难案件”的选取更多的应当考虑的是法律本身的合目的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最好呈现领域就是宪法裁判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一般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不同国家的宪法判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法理学课程体系中的法律关系、法律效力、法律规范的结构、法律解释的方法、权利保护的方法等问题为基准,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相关案件进行择取并加以分类和整理,引发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促进课堂讨论的进行。
法律的最高支配力问题说到底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问题。在法理学的课程中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案例化的处理。必须集中于时间跨度长、社会影响大并且能够彰显法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案件。在这方面,这几年来对于冤案的平反,对于相关争议案件的及时回应,都一再彰显了法律的最高支配力问题,也使得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和方针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在法理学的课堂中,对于上述案例的分析和提炼,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法治这一基本价值的信心,也有助于法理学课程的可接受性程度的提升。
三、类案的提炼:法律适用的精细化
法理学的学习除了涉及到法律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和难题外,还涉及到位部门法的理解和适用提供方法论指导的问题。因此,法理学课堂中对于案例教学的引入不能够与部门法中的案例教学相混同。部门法中的案例教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确定的个案中划定法律的适用范围,准确理解法条的语义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并在法体系的视角下思考法条的可能解释空间。也就是说,部门法的案例教学是对涵摄方法的详尽使用。用拉伦茨的话来说,就是对案件事实的个别部分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中的各种要素的判断。④但是在法理学的教学中,我们需要做的并非是部门法的工作,也即,我们并不是针对某个个案而对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进行讲授。我们所讲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所考量的毋宁是,在不同的类似案件中,是否存在着一般的要素,只要具有这种一般的要素,我们就能够将这些类案归入到同一法律概念之下,通过这一归入,我们能够实现所谓法律适用的精确化目标。⑤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中的案例教学与部门法中的案例教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是一种二阶的案例教学法。这种二阶的案例教学法是建立在部门法的一阶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的。要实现这种案例教学,除了要求法理学的课程与部门法的课程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衔接外,还要求任课教师在法科生的整体培养方案中对于部门法的案例的择取和讲授进行统一化的处理。
那么,作为二阶案例教学的法理学案例课程与部门法的一阶案例教学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认为,二阶案例教学与一阶案例教学之间存在着如下三种意义上的对应关系:首先,一阶案例教学时二阶案例教学的基础,但是一阶案例教学存在着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不同法域的规范性问题的统一思考;二是缺乏对不同法域中类案的动态变化的把握,因此,二阶案例教学的存在就力图为一阶案例教学提供两种意义上的统一性:规范判断的统一性和价值的统一性。规范判断的统一性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跨法域的法律思维模式的形成,类案动态的把握并不是以规范为指导的把握,而是以价值为指导的把握;其次,二阶案例教学的形成标志着法科教育从不同类型的、相互间关联性甚弱的法律思维模式,进入一种统一的、有强大的理论支撑的法律思维教育。能够使得法科生突破部门法教育所设置的专业藩篱。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通过对于民法上的要件事实论和刑法上的构成要件理论的提炼,可以在法理学的课程中赋予法律解释以普遍形式。再次,法理学中的二阶案例教学有助于对部门法中的案例教学形成一种价值性的审查或批判,从而鉴别出部门法案例教学中的成功与不足。
如果法理学的课程中能够贯彻上述的类案比较方法,那么法理学的课程至少可以实现如下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将法理学中诸如自由、平等这类抽象的价值观赋予了案例形态,并且能够在类案的比较中逐步实现对自由、平等价值的判断基准;二是在法律思维的层次确立类型化思考的基础性地位;三是促成法律论辩的产生。
四、价值问题在案例教学中的呈现路径和方式
在部门法的案例教学中,对案例的分析和评价主要是围绕着实证法而展开的,对于脱离实证法规范的道德问题一般采取中立的态度,并不过多的涉及。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的案例教学是高度技术化的操作规程。但法理学课程中的案例教学的旨趣却与此截然不同,其更多地使要通过案例去呈现相互冲突的价值命题,并且通过对法律规范的批判性分析来揭示出如何运用规范性的思维去面对多元且相互冲突的价值,在这种规范性的思维框架下,案件事实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冲突只具有“初显性”的特征,从根本上来说,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是相互支撑,自我构筑的,其既不依赖于事实,也不依赖于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课程中的案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案例,而是价值真理在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呈现。正是在不同的“案例”的呈现中,价值真理才显现其独特的体系和脉络。法理学的教学必须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呈现出这种价值独立和价值统一的问题。⑥
正是由于法理学案例教学中对于价值统一问题的自我意识,才使得法科教育摆脱了传统的工匠式的教育,从而进入到通识教育的领域。正是在这一教育领域中,法律人的高傲和庸俗的思维模式能够通过对于伟大心灵的价值教育的温顺领悟中获得升华。通过法理学的案例教学,我们可以有效地将通识教育中的基本要求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引入到法学教育中,从而实现法科教育在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也确证如下古老命题的正确性,法学不仅是关乎人类事务的知识和技艺,其也涉及到神圣的价值问题,其不仅是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简单诉诸,而是通过科学的方式去实现正义,拒绝非正义。
[注释]
①[日]青井秀夫.法理学概说[M].有斐阁,2007.5.
②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第五版)[M].法律出版社,2016.32.
③[日]长尾龙一.法哲学批判[M].信山社,1997:210-211.
④[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165.
⑤[德]齐佩利乌斯.法律方法论[M].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104.
⑥对案例所具有的这方面的意义的详细探讨,可参阅Ronald Dworkin,Justice for Hedgehog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