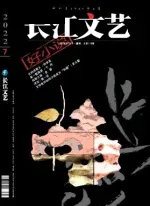不一样的世界

1 平行但是不同
每个人都有一双眼,每双眼里都有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信赖自己的眼,以为自己眼里的世界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以为别人看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世界。
其实不一样。
不错,是有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比如张三看到了李四走过去,王二麻子也看到了。李四走过去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得到了张三和王二麻子的共识。
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世界很有限,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两个目击者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描述,这种时候客观便消失了。事实不再是事实,世界的轮廓忽然模糊了。将前面的例子进一步往深里探究,你会发现是事实(世界)本身出了问题。张三看见李四走过去,王二麻子站在张三身边却没看见;王二麻子说张三见鬼了,活见鬼。如果我们将每个个体所看到的当作事实,我们就得到了两个事实。所以我说是事实本身出了问题,有,或没有。
日常生活里这样的例子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我一辈子是个做文章的,在文章这一行里这样的例子绝对不少。两个人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的文章却大相径庭,写出同样文章的反倒凤毛麟角。职业使然,我对所谓的客观世界有极深的疑窦,甚至以为那只是个虚妄的说辞。世界有,但是绝无客观,每一双眼里的世界都是他的主观。身边一些聪明的读书人会说我是唯心论,换一顶大帽子叫唯心主义者。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到中国的官本位制度。读书做官是中国的传统,升官发财光明正大,正统的人生之路。当然另有一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在路的两侧相伴辅佐,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诸如廉正清明,诸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走人生正途绝没有错,许多人在走,许许多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忽然有一天国家媒体告诉你,有一百多万官员失足落马,你会作何感想?他们走的不是人间正道吗?他们不是有知识的聪明人吗?他们肯定是人群中最聪明的属于精英的群落,他们在人生之路上比普通人要出类拔萃,他们受到众多普通人的青睐,在人群中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天之骄子。
中国古有法不责众一说,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不约而同地做了坏事恶事,一定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一定是世界本身出了问题。官员成了高危职业。
高危职业也是预备役就业者慎入的职业。过去说高危职业,专指那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工行业,与粉尘打交道的行业,容易受伤死亡的行业。今后的年轻人还要走读书升官的路吗?
说官员是高危行业似乎不公平,毕竟读书升官是自孔子以下中国三千年以来的国之大统,久经考验,大旗不倒。怎么到了今天,突然就成了高危行业了?若要论证,恐怕根源不在职业本身,问题肯定出在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
所以我说当下的世界是个看不懂的世界,与我儿时的世界已经是两个世界。
46年前我十七岁,一个初中生下乡变身成一个知青。那时候的世界山青水绿,随时会有野生动物冲进你的视线,或者在你的视线里消失。那时候你渴了,可以随时掬起溪水一饮再饮,不用担心有化肥农药。那时候的老师教你的是诚实守信利他。那时候你的心里干净得像一片白雪,一个小小的过失会令你寝食难安。那时候父母和社会教会你鄙视钱,鄙视不劳而获,鄙视投机取巧。眨眼之间,连我这一辈子都还没到尽头,怎么世界忽然就完全变了?世界换了一张脸,一张不同的脸,令所有那些还在的人惊愕和陌生。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不是说地球已经有45亿年的历史吗?刚刚才45年,连家园本身都陌生了,都变得不认识了。
就是这同一个世界,不同的人还是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精明的人看到机会,困窘的人看到绝望,商人看到钱,朴实的人看到生计,官员看到愿景,心存浪漫的人看到希望。他们眼里的世界不一样,很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2 病患的世界
我是个生了大病的人,肺上长了肿瘤。按一般的说法,性格内向偏抑郁的人易生肿瘤,积郁成疾是中医基本医理之一。我外向,不是抑郁的性格,心里容不得丝毫的隐忍,有怨有气必得当场释放出来,按理说绝不该生肿瘤之疾。
我也曾想过外因,诸如生病前刚刚装修新房置办新家具,是否因为所说的苯和甲醛导致了肺疾。毕竟肺是呼吸器官。没有谁能给我答案。
但我心里有了这个结,就把苯和甲醛当作假想敌,尽最大可能将它们拒之门外。谁都知道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完全拒绝任何人也做不到。我能做的也只是将那些苯和甲醛含量最高的物件列在禁入家门的名单上,比如复合板,其它含有胶和树脂的家具用品用具。我尽量使用天然材质的东西:木头,钢铁,玻璃(硅),藤器;尽量少用化学物品:塑料,化肥,药物。
我是病人,完全不服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把用药限制在最低水平和最小范围。除了肺疾,我还患有脑栓塞,严重的糖尿病,胆结石,肝囊肿,关节炎,静脉曲张,习惯性胃肠炎。我日常只为糖尿病注射门冬胰岛素,关节炎发作时偶用风湿膏,拉肚子用诺氟沙星止泻,其它药物一概拒绝,拒绝到医院做任何意义的体检。
在病患世界里,我无疑是个异类。老母亲三年前去世。生前几十年里老人家完全是个药罐子,每天数次,每次有数种十几二十粒药片,一大把尽皆投入口中,要满满一杯水才能将所有药片送服咽下。一个家庭中的两个病患,两个都需要面对药物的世界,两种态度截然相反。我是她生的,母与子。
我自己也很难说我和老妈谁是对的。老妈活到了84岁,我和她生病的种类不相上下,我不敢说我会活到她那个年龄,但我会爱惜生命,力争活得更久。我想说的是,即使血脉相连,病患的世界也不止一个,而且彼此间差异巨大。
老妈是无神论者,她怕死,有了病她无条件听医生的。她看过的每一个医生,都被她视作救命恩人。叫她手术就手术,叫她吃药就吃药,遵医嘱是她的信条,她从不怀疑。
我是唯心论者,我信命,信我的病便是我的命。我不信医生,不信医学,我认定医生医学都是生意,生意不是患者的出路。命中注定的东西,我选择听天由命。治得好的病我治,有了伤口该缝的缝,该止血的止血,该消炎的消炎;拉肚子我吃止泻药,疼痛我吃止疼药,仅此而已。治不好的病我不强治,强扭的瓜不甜,强治的结果只会将病情恶化。我提倡尊重每一个个体,哪怕它是上了你身子的疾病。尊重它,与它和平共处,与它相安无事,这是我对疾病的信条。我不与我的疾病作战,我认定作战只会两败俱伤,最终同归于尽。
你看,两个人眼里的世界是不是不同?当真不同。
我说老妈怕死,是指她在对待医疗的态度上。他们那一代人差不多已经全都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代人的寿数比我这一代,比我的下一代要短。从老妈五十几岁开始,她身边的同龄人就开始做减法了。张阿姨走了,李叔叔走了,黄伯伯走了,徐婶子走了。从她五十几岁,这成了一个经常性话题,年复一年三十年如一日,她一直在面对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走向冥界的事实。粗粗在心里算一下,我听她提起过的她同辈人的死亡,肯定超过三十次。我自诩是个不错的心理学家,以我的经验和判断,面对了太多的熟人的生和死,老妈的神经已经千锤百炼异常结实,早已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对于死亡早就不放在眼里,死亡早成了家常便饭。换言之,她可能曾经怕死,那也只是曾经而已。面对了太多的死之后,怕死已经成为习惯,说怕死也只是不想死而已。习惯早已战胜了恐惧,没有恐惧的怕,还是怕吗?真的很难说。
说说另一个病患的例子,他现下是我的邻居,南糯山姑娘寨的邻居。他是我的老乡,是我极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比我小十岁,也是几年前生了病,脑溢血。
生病前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上了山,后来他也生病了。他的病经过一段时间恢复,情况有所好转。有一天他说想到我这来看一看,我俩的共同朋友就陪着他来我这。对他而言这是一次非凡之旅,因为他一次就确定了来和我作伴。他在我的帮衬下,在距离我百米远的地方选中了一块宅基地,建房建了两年,近日刚刚竣工。正在筹备杀猪上新房。
对待疾病,他比我的态度更积极。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劳动四小时,从无或辍。劳动四小时在外,他还规定自己每天徒步四千米。他是脑血管疾病,思维和肢体动作都发生了障碍,活动康复是最有效的恢复性治疗。他的积极态度和毅力令我钦佩,真的很佩服他。
但是有一点我不理解。在我看来是他想不开。我说的是疾病没在心理层面给他带来大彻大悟,心理还停留在从前。
他是典型的社会精英,是一个企业的法人总经理,是被人尊崇仰慕的一族。他是个有面子的人,而且好面子。毫无疑问,在过往的人生路上,豪奢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喜欢气派,他在山上造的房子当然是最气派的。四层豪宅,层层有西式柱瓶的围栏,富丽堂皇气势非凡。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自然而然不足为道。
要说的是很小的一件事,家具。因为此前他看过我的家具,也让我带他去我买实木藤器家具的店铺。我说过,我最在乎的是家具的材质,我对所有的复合板心存忌惮。他选了一套藤器沙发,其它实木家具显然不中意,没考虑。这都在情理之中,毕竟家具终日与你为伴,入眼不入眼都看缘分。
他的房子很大,需要的家具很多。他另外定了三套普通卧房家具,两套大卧房家具,一套办公家具,一套大客厅家具,一套茶室家具,一套餐厅家具,加上先定的普通客厅家具(藤器)。规模巨大,接货和安装工程也忙了两周。
一切妥当后,我和家人过去参观,我马上发现了问题。按常情常理,人家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同原本在情理之中,我完全可以看了当没看见;但是我认为问题严重,不说不行。就是复合板问题。我知道家具从全国各地发货过来,且钱已全部付掉,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了熟饭。所以我不说全体,我只说局部。我说的是卧室。因为人与卧室的关系最为紧密,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卧室。
可以确定的,大床的床板是复合板,四门大衣柜的所有壁板包括门都是复合板,梳妆台的板材是复合板。虽然已经开门开窗多日,板式家具仍然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令人窒息。不仅如此,与主卧室相连的是办公间,那一大套中式的超大办公桌老板椅连同背后的四门中式书橱,也都是复合板材。
我是肺疾患者,我把令自己患病的根源确定为苯和甲醛,是新家具造成的祸患,虽然其中只有少数几件复合板材家具。所以我不能容忍复合板,尤其是气味强烈的复合板。
我劝他换掉卧室的那一套,如果可能也换掉办公室的那一套,因为办公室与卧室只隔了一道门。他不是肺疾,他不当苯和甲醛是一回事。可是我的肺出问题之前,也没有肺疾。我是患上肺疾之后才将责任追查到苯和甲醛头上。
不用说,他没换。谁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去对自己的生活做很大的改变。但我们是邻居,我们每天都会见面,我们每周都会到对方的家里去坐一坐。只要我去到他家,我就忍不住旧话重提。一个月有四周多,一年超过52周,我不知道我还会去他家多少次,也许100次,也许1000次。我猜我已经把换家具的话说了不下5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揪住这个话题不放,再说上50次500次。
有我这样一个朋友,是不是很烦很啰嗦?我猜不出他的感受,他一辈子当领导,是大人物,大人有大量,他从未表示过不耐烦。他不表示不耐烦,我就当他不烦,该说我还是会说。如果你怕浪费,又不是要你扔,你可以把它挪到别的房间,反正你空房子还多。如果你手头紧,你可以买便宜的杉木松木,虽然不够华贵漂亮,但毕竟是实木。香柏木是个不错的选择,不是很贵,又有天然的柏香,视觉上也不廉价。
谁也不想生病,生病是桩很无奈的事,病患的世界不一样。
3 孩子的世界
我有两个儿子,哥俩的年龄相差22岁。
第一次当父亲的时候虽然我也不是孩子了,但是心态还停留在孩子的状态,所以第一次当父亲当得并不称职。孩子13岁之前都在老一辈身边,这是终生的歉疚和遗憾。
第二次当父亲情形有了不同,孩子一直在身边。我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命运却让我又一次当父亲。接受前面的教训,我把许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用心和不用心到底不一样,短短几年里我已经发现了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我和孩子妈妈的,有的问题是孩子自己的,还有的问题是时代的,还有的问题是社会的。
回望自己这一辈子,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两件事。我小时候是个喜欢想事情的孩子,我那时就发现有两件事最大:唯心还是唯物;有神还是无神。经过反复比照思考,我选择了唯心和有神。这两件事让我终生受益。
比如我生了病,直面生死,因为唯心和有神,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认命,相信一切是上天的安排。一旦坚信生病是我命里的东西,面对它就很坦然,既不怕当然也就不慌。
我还是知道有许多人生了病就崩溃了,慌不择路有病乱投医,先给病吓个半死,然后开刀化疗放疗给治死。我什么也不做,只是想想怎么就生了病,想病是借了水路到我身体里来的,想换个地方换换水。居然一晃就过了十年,居然还活得结结实实开开心心,居然又写了10本书。
唯心论有神论帮我渡过了人生最大的难关。
那些时代的和社会的问题也让我困惑。我知道自己,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大多数人相冲突,我该怎么教我的孩子。
小儿子7岁了,每天都会拿不止10个为什么来烦我。这其中就包括诸多与认识论有关的问题。我们国家奉行的是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儿子在学校和社会获取的知识,与他老爸的话有诸多相悖诸多冲撞。小孩子眼里容不得沙子,同一的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对孩子是一个困境。他在非黑即白的年龄,于是想当然地非此即彼。
他还不懂得这是一个辩证的世界,可以即黑即白,可以即此即彼。混沌的世界是孩子小小的年龄所无法理解的,世界的复杂不属于孩子,甚至不属于大多数成年人。这些道理我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孩子交流,语言在这里无能为力。
同时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与社会通行价值相反的观点讲给孩子。我明白它会给孩子的内心造成混乱。孩子的世界简单,在孩子的世界里条理清楚是非分明。孩子的心里该不该很早就陷入混沌和黑暗,这同样是我想不清楚的问题。
另外一些问题我不纠结,虽然我也知道我的立场与时下的社会彼此并不见容。但我还是愿意把我的立场我的结论明明确确地给他。
我和孩子妈妈的问题。妈妈更多着眼于有用,种菜是为了有菜吃,养鸡是为了鸡蛋。我更关心无用,养孔雀无用,既舍不得吃蛋又舍不得拿孔雀当菜肴,养孔雀只为了养眼只为了好看。爸爸妈妈各说各的,孩子如何理解和接受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些共同的认知,诸如钱是坏东西,名利是坏东西,撒谎和贪婪是坏品质,能知恩图报的是好人,人要爱自然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人要多读书以告别愚蠢,凡事不要玩心眼,做你想做的事不要以妨碍和伤害别人为代价,如此等等。我愿意孩子在遇到疑窦时,我的立场能帮他做出选择。
孩子自己的问题不少。不是指他提出的问题,是指发生在他身上的。孩子很虚荣,他把得到老师表扬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不能容忍自己不如别的同学。他要做班里第一个到学校的人,为此经常要跟家人为难,埋怨家人耽搁了他。他要作业全优不出任何差错,他每天为此长时间纠缠住妈妈,弄得妈妈烦不胜烦。他对自己当班干部充满渴望,对老师的每一次指派都尽心竭力,同时又担惊受怕会出差错。他对照料他生活的外公很不尊重,认为老年人的迟钝就是无能,就是不如自己,他对外公颐指气使,为此被妈妈呵斥被爸爸责打。
我很纠结。我很想告诉他爸爸不希望他当干部,不希望他日后当官;我很想告诉他,作业错了没什么了不起,错了被批评,以后就会少错不错;我很想告诉他,不懂得尊重老年人就是不懂得做人,日后一定是个糟糕透顶的人;我很想告诉他,遵守时间很好,不迟到很好,但是为了受表扬拖着全家人为你提前到学校作秀很不好;你要表现自己,你要受表扬,你要虚荣,那是你自己的事,全家人不支持你这样。
依我的性格,我很想直截了当这么说。但他是孩子,我知道这样说的结果会很重地打击他,我只能委婉地跟他谈我的看法。我告诉他,你当干部可以,但你不可以告同学的状。孩子的告状和成人的告密都是很坏的行为。我说你小学当干部爸爸不反对,中学以后爸爸会反对,爸爸不希望你日后当官当领导当管理者。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儿时是百分百的科学主义者,那时我崇拜科学,崇拜创建科学体系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可是后来我的立场变了,我不但不再崇拜科学,而且对科学带给自然带给地球的戕害深恶痛绝。孩子上学学的是知识,其中有八成是科学知识。在孩子眼里我是所有人里知识最渊博的那个,孩子很多问题会找我;如何面对孩子永无尽头的问题,成了我的难题。
眼下面对的只是眼下。孩子刚上小学,小学有小学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日后成为怎样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方向。当下最好的职业都是赚钱多的职业,我不喜欢钱,所以不希望孩子以后成为能赚钱的人。能赚钱的是能人,能与人周旋,能在阴谋和争斗中胜出,我没这种禀赋,从遗传学意义上,我的孩子也应该不具备这种禀赋。
面对事实我们都需要实际一点,我于是想到关于幸福指数的话题,我的孩子也许有机会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去力争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也为他做了起码的铺垫,在完全没有污染的大山之上营造了一个贴近自然的家园,创造了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但是我只是我,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甘愿蜷缩在大山的一个角落,一辈子与世无争。
我们今天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我不在此一一列举。笼统地说分数是孩子的大灾难,孩子幼小的心灵被灌满了竞争的毒液攀比的毒液,争第一压倒别人成了孩子最大的愿望。想想真是可怕。另外一部分影响来自学校之外。
孩子从小就知道当官的有钱的都是大人物,是人上人。爸爸妈妈对这些人毕恭毕敬,老师校长对这些人毕恭毕敬,这些人每天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指手画脚张牙舞爪,这些人住豪宅开豪车吃大餐穿名牌,全社会都在向这些人表达仰慕。久而久之,这些人便也成了孩子的楷模和偶像,成了孩子争相效仿的榜样。这些人在人群当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一切构成了孩子教育的另外一套课本,更权威的课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力量。
这不是一个老师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不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是时代本身。以金钱和权力为中心的时代,肯定是最坏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
大儿子高中去了欧洲。欧洲11年令他成了个欧洲孩子。欧洲也不是没有问题,欧洲孩子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欧洲的孩子心里会干净一点,不那么拜金钱教拜权力教,心理不那么扭曲。我对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认同,也没有任何应对之道,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儿子的教育,无奈之下又想到了欧洲。毕竟我远离社会和人群,也没有兼济天下的宏愿和能力,我能做的极其有限,唯有独善其身而已。况且我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送另一个孩子去欧洲谈何容易。
我自己的孩子的世界比我儿时的更小更令人绝望。
4 属于个人的世界
其实从来只有一个世界,当下属于个人的那个世界。
曾经一个官员朋友在一个相当亲密的饭桌上,义正词言地指责我自私,说我为了满足一己田园梦,将老婆孩子拖到山上受苦受罪。在他眼里,我的无限美好的家园无异于地狱。我尽情享受我的世界的美好,在他眼里就是造孽。
我不知道话题被指的我的老婆孩子作何感想,他们都在场。但是有一点我有把握,我老婆爱我,她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关心我的健康;而我上山以后的身体比先前好,而且好得很多,仅就这一点便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快乐;所以上山这件事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对她不是受苦受罪。我说我有把握是因为查出病患的那一刻,我们有过一次痛彻心扉的深谈。我的健康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心结,上山的结果我就是健康了。
我也知道她是个乡下孩子,不像我那么爱农村爱乡下爱山上,去城市去都市或者出国都令她开心。我们彼此深爱对方,也无话不谈,但她从未表达过离开山上重新回到城市的念头。家园很大,而且我们经常会有朋友来。作为主妇她很辛苦。她偶尔会表达更喜欢一个小家,小家更温暖也更轻省。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她动没动过回到城市的念头。
同一个世界,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官员朋友眼中的地狱,却是我眼中的天堂。我老婆怎么看它是另一回事。
也是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17岁看它和64岁看它也不一样。时间让同一个世界分身,呈现出不同的世界。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时间有自己的戏法(相对于魔术我更喜欢戏法)。我记得有一个古希腊的先哲说过一句关于时间的箴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回望一下,我的世界里从来只有对形而上的热情,从来只有对诗意和智慧的执着,从来只有浪漫和无边的幻想,从来只有家人和友情。世界自己在变化,我的世界一如既往。

《随方就圆2号》傅中望木直径150cm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