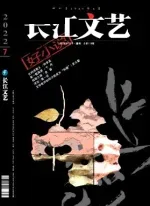陌生人

从跨进店里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选对了地方。座位都像是从老式火车上搬来的,背靠背,绿色的椅套,每个位子上可坐两人。每张原木餐桌上都垂下两个罩形的吊灯。几个挂满绿萝的木架,将大厅里分隔成好几个空间。与大门相对的尽头,是一整面玻璃墙。沿着玻璃墙只摆放了一排座位。那儿还只有一对情侣模样的人,在差不多是正中的位子上相对而坐。这天是我和妻子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我提前一个小时下班,来到了这家酒店里的牛排店。妻子喜欢吃牛排,曾经我们常去的,是一些商场里的连锁店。来这里还是第一次。之前我在网上了解过,这家店里的牛排材质和环境都很不错。环境这一点已得到了验证,尤其是坐在窗边,从我所在的二十九楼望下去,可以看到广阔而平静的江面——平静得仿佛并没有流动。江边的道路上有不少缓慢移动的行人和车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他们)也显得如此平静,如同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本身并无目的和方向,只是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前进。尽管已是黄昏,夕阳也已西沉,但窗外的光线依然充足,而且似乎还将一个劲地充足下去。时间难道是静止了吗?或许这就是等待的滋味。
我掏出了手机,在微信上对妻子说:我已经到了,等你。妻子的回复马上就来了:在路上了,还要几分钟。
没想到来到我身边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窈窕的身材,脸颊却显得饱满,也就是有点俗称的婴儿肥,皮肤白皙而光洁,眼睛明亮,年纪大约二十五六。染成棕色的短发笔直地垂在肩上,带黑色竖形条纹的白衬衣扎进一条黑色七分裤,脚上是一双墨绿色休闲平底鞋。她将一个白色小肩包扔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然后大大方方地在我对面坐下,问我是马上点餐,还是再等一会儿。我愣了好一会儿,才问她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等的是我妻子。她立马笑起来,一双大眼神采奕奕,说我总算有了点幽默细胞。我又说她一定是搞错了,而且我妻子马上就过来了。她朝我翻了个白眼,问我有几个妻子。这句话激怒了我,所以我沉下脸来,一言不发地瞪着她。这倒使她显得更加兴奋起来,一脸喜色地说我演得真不错,同时扫视四周,似乎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观看我的表现。我想着妻子随时会过来,没什么兴致和她纠缠,于是掏出手机拨打了妻子的电话。一阵并不熟悉的手机铃声在对面的椅子上响起,只见她抓起那个白色肩包,从里面掏出了正在欢叫的手机。她一滑开接听键,两个陌生的声音便在我耳畔响起:我亲爱的老公,你现在在哪里呀?
我的头脑里闪现出多种可能性:我对面的女人拿了我妻子的手机;妻子和我开了一个目的不明的玩笑;妻子和另一个女人交换了记忆;我自己的记忆被人换走了……但这些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是否还要继续面对这个不是我妻子的女人。如果这确实是一个玩笑,我可不愿奉陪。是的,我是一个缺少幽默细胞的人。于是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那个陌生女人马上跟了出来。在门口的时候,她挽住了我的手臂,同时在我耳边嘀咕:你是不是真的失忆啦?她的身上有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妻子的气息,而且她明显比我妻子高了好几公分。她的表情已显得有些焦虑。我试图脱离她,但她又加了一把劲。我只得拖着她前行。我说我没有失忆,我清楚记得我妻子的样子。那她是不是比我好看呢?她立刻询问。我没有回答,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但女人的逻辑总是这么让人无奈。
接下来,陌生女人主导了我的一切行动。她又变得兴奋起来,急于证明她就是我的妻子。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准确地说出了我家的地址。在车上的时候,她依然紧紧地挽着我,仿佛我随时会跳车逃跑一样。不得不承认,她确实长得很好看,至少比我妻子要好看,但我丝毫感觉不到欣喜,而且时刻有将她推开的冲动。到了家门口,她率先掏出了钥匙。门顺利地开了,然后她以一位女主人应有的从容与熟练,从家里一些隐蔽的角落翻出了我和她的一些合影,还有我们的结婚证书。你看看吧——她以一位胜利者般的得意,将它们扔进我的怀里。我在那些照片上看到了我和她的亲密身影,而在那张结婚证上,名字、日期全都符合我的记忆,只是照片上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妻子却完完全全是两个人。
我像被电棍击中一样瘫倒在沙发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都不是玩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失去了我所熟悉的妻子。妻子现在去了哪里呢?是被卷入了某个神秘的时间虫洞,还是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不,她一定是存在过的,我记忆里有关她的那些画面依然如此生动和鲜明,但她在现实里的身影,则已凭空消失,消失得那么突然和彻底,即使在那个自称是她的陌生女人身上,也已不见丝毫踪影。因为悲伤和恐惧,我蜷缩在沙发上簌簌发抖,那个陌生女人则紧紧地搂着我,不断在我耳边说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但她每说一次,都使我更加地肯定:她已不在这里。
陌生女人煮了两碗挂面作晚餐。我没有动筷,她也吃得不多。她一直在叨叨不止,分析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反复建议我明天就去看医生。她还宽慰我说,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说不定睡一觉醒来,我就能够恢复正常了。我很想跟她说,我感觉自己再正常不过,而不正常的很可能正是她自己。但我知道这样的话她肯定不爱听,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爱听。
晚上她睡卧室,我睡沙发。她问过我几次,是否确定不和她一起睡。我说很确定。我感觉得出,她反复的询问不过是想考验我。果然,最后她对我说,我的坚定让她很开心,因为目前她在我眼里,毕竟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我想,女人的逻辑真是很可怕的。
我整晚都没有睡着,脑子里始终在想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在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前,我今后恐怕都会难以入睡。夜里我几次悄悄溜进卧室,借着手机屏幕上的微弱光线,俯身端详沉睡中的那个陌生女人有没有发生变化。什么变化都没有。夜晚无比漫长,而我既不想看电视,也不想玩游戏。眼看着窗口开始发白,我又跑进卧室里去打量那女人的脸庞。还是没有变化,这使我对自己的一夜无眠深感沮丧——如果是睡过一觉醒来,结果是否就会不一样呢?
陌生女人从卧室里出来后,我们对视了一眼。她无疑也和我一样失望。她在去上班之前,说我的气色很差,最好不要去上班,不过可以去看下医生。我只同意她一半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医生。
我决定在微信上向主任请假。找到主任的微信号时,我发现他的名字没变,头像上的照片却是另一个人。于是我再看其他人的头像或发在朋友圈的照片,也全都是一些陌生面孔。我扔下手机,站在窗边俯视楼下。尽管是在十二楼,楼下的那些身影还是可以分辨。站在那里好长一段时间,一个熟悉的人我都没有发现。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仿佛自己正往楼下坠落,而楼下的那些事物则都漂浮到了半空。我闭上眼睛,头抵在窗户上,竭力抗拒着从脚底升起的一阵阵寒意。
中午的时候,陌生女人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去看医生。我说我还在家里。她又问我下午会不会去,我没有作声。一阵沉默之后,她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挂掉了电话。其实我很希望她能再跟我说点什么,因为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妻子,她完全可以命令我下午一定要去,而我则很可能听从她的命令,尽管我依然相信自己并不需要医生。
在冰箱里找了点吃的,一瓶酸奶,还有几根火腿肠。火腿肠我只吃了一根,其他的又都放了回去。整个下午,我都躺在沙发上,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那些短促的梦里,我一次次梦见自己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醒来之后发觉自己的眼眶已经湿润,不知道是因为幸福还是伤心。
听到门锁的一阵响动,我抬头盯着门口。进来的依然是那个陌生女人,而在她身后,还有好几个陌生人。一位五十几岁的妇女一马当先,越过陌生女人来到我身边。她先是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将手背贴在我额头上。没发烧啊,她朝其他人嚷了一声,还试图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但我缩了下身子。你连我都不认得了啊?她从我身边弹开,也不知是出于惊恐,还是想让我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目光转向陌生女人,想要从她那儿寻找答案。在一阵慌乱的叫嚷声里,我明白过来,身边的人是我的母亲。这一点我当然无法怀疑,于是我马上从沙发上翻起身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角落里。想不起来了吗?我母亲挨着我坐下,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想把她的手推开,但好歹忍住了。她的眼睛里已涌出了泪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也来到我身边,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差点就对他说声“你好”,但马上意识到这会显得很傻。事实上,从母亲和哥哥看着我的眼神中,我已感觉自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所以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不记得他们了,只是他们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母亲和哥哥全都皱起眉头,并快速地对视了一眼。很显然,他们不仅没有听懂,而且很可能觉得我是在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给他们。所以我决定尽量不再开口,因为不管我说什么,都会显得很傻。
嫂子和我七岁的侄儿并没有走到我身边来。在我们彼此看来,这显然并无必要。但母亲还是招呼他们,要他们也过来让我看一看。她或许以为,让我多看几个人,认出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吧。嫂子只是朝我点了下头,小侄儿则在喊了一声“叔叔”后,继续好奇地打量我。这个陌生的孩子长得很可爱,似乎也很懂事,但我并不感到亲切,甚至还有一点害怕。我转过头去不理他,嫂子就把他给拉走了。
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外面吃饭。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和母亲差不多大的妇女,她和母亲打了个招呼,然后视线在我们的脸上打转。我感到母亲有些紧张,连问了她几个问题,她老公怎么样,她女儿女婿怎么样。母亲是在转移她的注意力。出门后,那妇女和我们分开了,母亲立刻小声地问我,是不是也不认得那个阿姨了,我说不认得了。母亲点了点头,好像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饭桌上有些沉闷。小区边上的那家饭馆我是熟悉的,但人都已不认识。我一个劲地打量那些服务员,也打量旁边的那些顾客。家里人都只是埋头吃饭,显然都不想在公共场合讨论我的事情,而别的事情,又似乎全都无关紧要。记得从前我们一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话题总是源源不断,从彼此的工作,到小侄儿的教育问题,琐琐碎碎一大堆。我怀念那样的时刻,所以情绪越来越低沉。而母亲和陌生女人隔一小会儿就扫一眼我,这让我更加难以忍耐。我推说去上卫生间,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很长一段时间。出去的时候,发现陌生女人在卫生间外等着我。她说母亲他们已经回去了,又说母亲明天还会再来看我。看她那样子,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我想如果她是我熟悉的妻子,我一定会拥抱她,并且想方设法地宽慰她,但现在,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她还要委屈,仿佛是她,以及其他那些人,把我原来的生活给偷走了。
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上班。昨天我已在微信里向主任请了几天假,说是家里有事情要处理。以我对主任的了解,他不会问我有什么事情的,但现在这个陌生的主任马上就问了我。我想了一下,然后回复说,是妻子身体方面的问题。我不喜欢撒谎,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只是我说得比较含糊,而且对方也不好再问。主任果然没有再说什么。早上我打车去了单位那边。我让司机把车开进了大门,然后让他停靠在能看到办公楼的路边。我没有下车,而是坐在后排打量进出那栋大楼的人。全都是一些陌生人。因为害怕被人发现,没多久我就要司机把车开出去。车子驶出大门的时候,我有了一种永别的感觉。
晚上我和陌生女人在家里吃过饭,母亲过来了。她带来了不少东西。一些吃的东西,她说是给我补脑的,一些她说是从寺庙里求来的灵符,要我把它们贴在家里的门上。还有一把桃树枝,是用来给我驱邪的。她先是盛了半碗水,然后把桃树枝在水里蘸一下,接着就用桃树枝在我头顶挥舞。做完这些之后,她隔一会儿就问我有没有效果。我说没有,她就说应该每天都试一下。我说这个恐怕作用不大,她就显出伤心的样子,说试都不试,怎么会知道呢?她又说起一些别的办法,比如杀一只公鸡,把血抹在我的脸上,或者是从老家抓一把土,包起来放在我的枕边。我没有再反驳她,因为我感觉她似乎更在乎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在乎对我有没有效果。
母亲走后,陌生女人又和我说起看医生的事。我没有再抗拒,甚至还和她商量起来。我说我先去看一下精神科,她却说应该要先去看脑科。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的精神肯定没有问题,也许只是大脑里的血管有些堵塞,类似于脑血栓,而脑血栓是会导致失忆的。我说我没有失忆,过去的事情我全都记得。可是你不记得我了啊,她一脸的委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记得全世界,偏偏就不记得她。我知道跟她没法聊下去了,便说我明天就去看脑科。
因为是周末,陌生女人陪着我一同去了医院。面对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医生,我说了自己的状况,陌生女人在一旁补充,并暗示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医生频频点头,而且始终面带微笑,仿佛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我不禁心动,觉得或许还真的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听我们讲述完了,医生便问陌生女人可不可以先出去一下,他想和我单独聊一聊。女人出去后,医生起身去把门关上,然后坐在椅子上板着脸孔,问我是不是假装失忆。这让我大失所望,几乎是带着怒气回答说我并没有失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假装。医生倒是又笑了起来,不过是换成了冷笑。他说我这种情况他听说过,某个地方也有一个男人,因为在外面有了情人,想要和妻子离婚,就假装失忆不认识妻子了,妻子当然受不了,就主动和男人离了婚。最后他建议我有什么事就和妻子好好商量,而不要采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我回报给他一个冷笑,随后气冲冲地摔门离去。
我到了医院门口,才发觉陌生女人并没有跟来。我想她可能是在向医生询问出了什么事情,而医生也很可能会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她。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等她,便先回了家。陌生女人直到很晚才回来。一看她的脸色,我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她什么话也不说,还故意不看我,自顾自地洗漱了一番,就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我想她正在气头上,所以最好不要去跟她解释,而且她也并不是我的妻子,我似乎并没有必要跟她解释。然而卧室里传来了哭泣声,断断续续,仿佛是被压抑着,又仿佛就是不想压抑。卧室的门并没有锁,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进去。陌生女人扑在床上,脸朝床头那边。我在床头坐下,手触到她湿润的脸庞。我要她不要再哭,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聊,她却哭得更大声起来。也许是为了方便痛哭,她还从床上坐了起来,把背向着我。我看到床头柜上有纸巾,给她抽了几张递过去。她用纸巾擦了脸,然后掷到地上,我便又给她递纸巾。如此反复几次,她终于止住了哭声。
我感觉时机已到,便说我并没有情人,她应该要相信我,而且以她的精明,我要是有情人,不可能骗得过她。我知道你没有,她凶巴巴地回应我。“那你这是为什么呢?”“那要问你自己。”她的逻辑还是让我无所适从。“你看,我就知道是这样。”我不知道她知道什么。“你连话都懒得和我说了。所以——”我害怕她说出“所以”后面的话来,但我不能堵住她的嘴巴。“你是不爱我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失忆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根本就不爱我。”
(2) 盾构推进时应计算浆液配合比,严格控制注浆压力,及时调整注浆参数,以提高注浆质量。确保浆液能够填充土层孔隙和盾尾间隙,而不会发生土体劈裂,注浆压力过小会导致浆液还未及时填充孔隙便已进入初凝阶段,造成填充不密实[12]。
对于一个陌生人,我当然不能说爱,但对于妻子,我又不能说不爱。所以我无话可说。而我的无话可说,对于她来说,就等于不爱。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她朝我甩过来一张泪水涟涟的脸庞。我又给她扯了张纸巾,但被她一把推开。
“你说啊——”
我知道只要我说一声“爱”,事情就会圆满解决,但我的回答是:
“爱是要看情况的,如果你现在还是我熟悉的样子,那我当然爱你,但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还没有说完,她就又哭哭啼啼起来。我感到厌烦,便起身走了出去,给她关上门,又回到了沙发上面。
接下来的日子,陌生女人每天都是很晚才回来,看到我也是视若无睹。母亲也很少再过来,因为她发现我并有按她的心意把灵符贴在门上,桃树枝也不见了踪影。偶尔母亲过来看一下我的时候,只是坐在离我很远的一张椅子上,一言不发,一脸的悲伤。我想她肯定也以为我不爱她了。我很想跟她说她没有必要再来看我,如果不想来,或者来了也没意义,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但我知道这样的话只会让她更感伤害。
我经常在晚上出去。每次坐电梯或穿过小区的时候,我都生怕碰到认识我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选择走楼梯,在小区里也总是走在昏暗的地方。而每当碰到什么人,对方又似乎想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便假装并没有看到,或者是装作在看手机。我想自己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冷漠的印象,有时心里也会感到一阵不安,但我始终无法对那些陌生的面孔作出亲热的表示。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商场,而且是离小区较远的商场。我去商场既是为了买第二天的食物,也是为了让自己不感到寂寞。一个人待在家里,尽管有各种方式打发时间,但我还是会不时想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和热闹。
商场里那些陌生的面孔让我感到亲切,因为我知道他们全都不认识我,不会对我显得亲热,而我也不必回报以亲热。我们对彼此的冷漠显得理所当然,谁也不会在意。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他们中有谁想要和我说说话,我一定乐意奉陪,或者有谁想要我帮个忙,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也多半不会拒绝。我自己就多次想和身边的某个人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无法克服内心的羞怯。
有天晚上我去了母亲所在的地方。她和哥哥他们住在一起。哥哥住的是联排别墅,小区里环境很好,保安也很严密,陌生人轻易无法进去。我尾随一个中年女人,想要和她一同进去的时候,门卫把我给叫住了。他警惕地盯着我,问我想要干什么。我突然感到一阵恼怒,大声地说出我要去的是哪一栋。“您是业主吗?”我没有回答,他便又问了一遍。于是我要他好好地看看我,看认不认识我。他将我仔细端详了一番,突然像想起来似的“哦”了一声,然后主动给我打开了大门。哥哥这里我来过多次,门卫或许是真的想起我来了。
哥哥家楼外有一片小树林,我就坐在那里面的一张椅子上。我盯着哥哥家那边,只见一楼和二楼都亮着橘黄色的灯。那温暖的灯光让我怀念曾经和家里人一块待在里面的场景。其实就当时来说,那并不是多么美妙的体验,因为每次我和妻子都多少有些拘谨,总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顾忌哥哥尤其是嫂子的感受,但因为母亲的缘故,我们又不能不去那里。
我试图再和陌生女人好好谈一谈。我想跟她说,虽然我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但我们还是可以和谐相处,一起去面对一些问题。当然她依然可能会和我说爱不爱的问题,而我依然无法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我可以把话说得更加清楚一些,她也不可能完全不讲道理。由于她回来得很晚,所以那天我发微信给她,要她回家吃晚饭。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打算做几样她最喜欢吃的菜。想当初她同意跟我在一起,和她喜欢吃我做的菜有很大关系。不过我有点担心她的口味是否已经改变,因为据我的观察,她的许多习性都已和从前不一样——这也是我一直无法接受她是我妻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在微信上没有回复我,我便给她打电话。前面两个电话都没接,我再打的时候,电话里每次都说用户正忙。我想她很可能已把我拉黑,便一心等着她晚上回来。
她回来的时候已近半夜,显然喝了酒,脸色酡红,身体还有些摇晃。我试图去搀扶她,被她推开了。我挡着她去房间的道路,她倒没有抗议,几步跨到了沙发那里,然后猛地坐了下去。我问她喝了多少酒,她没有回答,我又说她这么晚了喝酒不安全,她应该叫我去接她。你有那么关心我吗?她对着我笑,笑得有点狂放。我想到妻子从来不会这个样子,心里一阵悲凉。“你不是要和我好好聊聊吗,怎么又不说话了?”“你今天喝醉了,我们可以下次再聊。”“我没有喝醉,我心里很清楚。”她也许确实没有喝醉,但我已没有再聊的欲望。“我心里很清楚,你这个人就是冷血,而且还很虚伪。”我虽然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但我无力反驳。“你看,我说对了吧?还说要和我好好聊聊,现在又一句话都不说了。”“我们明天再聊吧。”“明天?明天我就不回来了。”“你要去哪里?”“反正不是这里。”说着她就站了起来,朝着卧室那边走去。我依然可以拦住她,但我知道拦住了也没有意义。这次她猛地关上了房门,并且还传来了按下倒锁的声音。
第二天她果真没有再回来,打她的电话,也还是“用户正忙”。
母亲也没有再过来。每天我都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每看到一个地方或一样东西,都想起曾经的一些事情。妻子的身影似乎布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让我的大脑一刻都无法安宁。我越来越频繁地外出,即使是白天,我也会突然走到外面去。我在一些街道或公共场所随意乱走,或者是随便坐上某趟公交车,坐在靠后的位置,看一些人上来和下去,看窗外闪过各种各样的事物和风景。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妻子的身影也随时会出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一个角落。
那天黄昏的时候,我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路上人很多,也许是因为到了下班时间,但我又不大确定那天是否是工作日——我已有阵子没有工作日和周末的概念。突然一个三十来岁、戴着黑色塑料框眼镜的男子挡在我面前。他发出了一声惊呼:“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本能地想要躲避,但对方脸上的那种喜悦让我心生犹疑,甚至还有些感动。也许对方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吧,而且能和什么人说说话,也是我现在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回应给他一个微笑。“你现在是要去哪里?”他继续一脸喜悦地问我。我说不去哪里,就随便逛逛。“那你和我一起去吃饭吧,还有好几个人。”他接着说出了好几个我所熟悉的名字。我曾经确实偶尔会和那几个人聚一聚,而眼前这个人的名字,我也大概猜测出来了。“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主动问他,想要从他的话里找到更多信息。“还不是老样子,你呢?”“我也是老样子。”“我们有多久没见了?”“有好几个月了吧。”“我们还是应该多聚聚。”“是啊,要多聚聚。”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我还是无法确定他的名字,但无疑我们已显得十分亲热,一起亲密地朝聚会的地方走去。
聚会地点已经有好几个人,都是男性,年纪都和我差不多。我的出现引发了一阵喧闹,有人说我最近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给我发微信也不回。我想起确实收到过一些微信,但为了避免麻烦,我一律没有理会。我向他们表达了歉意,说最近手头有一件急事,忙得没怎么看手机。他们便嚷着要多罚我几杯酒。我酒量一般,从前总是尽量躲酒,但这回我毫不推却。我的爽快让朋友们很是满意,一个个不断地夸赞我,好像我为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一样。从大家的交谈中,我把每个人的名字都搞清楚了,于是为了掩饰心虚,我开始不断喊出他们的名字,后来便改呼为“兄弟”,他们也全都亲热地回应我。不知不觉,我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人动容,谁也无法怀疑我们的亲密。
分手的时候,我早已晕晕乎乎,几乎忘记了眼前是一群陌生人,而且想要和他们每一个人拥抱。他们也想要拥抱我,所以我们就一一拥抱了下,并定好了下次聚会的日期。这样的感觉真好。在离开人群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觉回到人群之中的可贵。我突然急切地想要和那个陌生女人以及所有的亲人重聚,他们诚然是陌生人,但我依然是如此地需要他们。我深知自己的过去已经坍塌,但我的生活还将继续。一个人的生活,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维持下去的。我随时都可能失去工作,丧失经济来源,而更重要的是,我必将无法承受那日复一日的寂寞——迟早有一天,我都会走向那些陌生人,去和他们说话,去和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我决定明天就去那个陌生女人工作的地方(我已知道明天是工作日),我要告诉她我爱她,今后无论她还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爱她。除了爱她,我别无选择,但这个我不会告诉她。我想我还会对所有的亲人朋友,所有单位里的同事,以及小区里碰到的任何一个人,展示我的礼貌和热情,如果他们中也有人问我爱不爱的问题,我会说:我爱。
第二天一醒来,我便记起了昨天的那个决定。我把自己好好修饰了一番,面对镜子一次次练习微笑,随后就带着微笑走出了家门。我坐上了出租车,希望能尽快见到那个陌生女人。当出租车驶上横跨江面的大桥,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到了火球般红彤彤的朝阳、天地间被金色光芒驱赶的淡雾、泛着粼粼波光的江面。在含着水汽的清爽晨风的吹拂下,我全身舒畅,感到自己正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我瞪大了眼睛,打量着四周的一切,包括出租车内那破旧而肮脏的椅套、冷冰冰的金属隔栏、一个黧黑而眼睛通红的中年司机。我发现这一切都是可爱的,而我为什么就不能爱上这一切呢?是的,我需要爱,我不能不去爱。十几分钟后,我走进了妻子工作的那栋办公大楼,对每一个遇见的人,无论保安、保洁阿姨、前台小妹,还是那些只是前来办事的人,都展示我的微笑。不久我就推开了妻子所在的办公室大门,径直来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她正坐在那里,这时朝我转过脸来。我还没有说话,却听到了她那礼貌的柔和声音:先生,您找谁?

《三女神》徐文涛纸本丝网105×70cm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