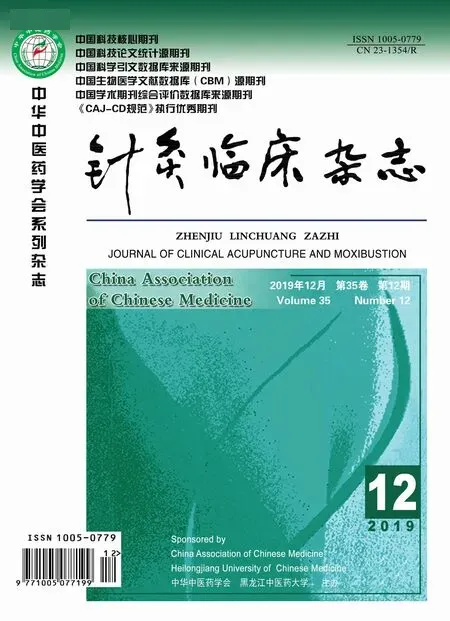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在缺血性脑卒中中的研究及针灸干预机制*
李文倩,李忠仁,傅淑平,储继红,姜鹏君,彭拥军△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2.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脑卒中是当今世界上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是造成60岁以上人群致残及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每年约有1500万人患有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占其中的87%[1]。1942年C.H.Waddington首次提出“表观遗传学”概念,最初定义为研究生物发育机制的学科[2],而随着生命科学、遗传学等不断发展,其概念曾多次转变,现指不涉及DNA序列改变的可遗传表型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在脑缺血病理生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针灸作为中医学的重要部分,被广泛应用于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的各个阶段。多项研究表明电针在脑卒中急性期通过调节缺血区血流、抑制神经炎症、抗细胞凋亡、促进血管神经发生等机制发挥脑保护作用,在卒中恢复期促进功能恢复。表观遗传调控特点与中医的整体观念等理论契合,故基于表观遗传学研究针灸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中发挥的作用,可为该病的防治寻找新的靶标,为针灸治疗提供更多客观科学的支撑。
1 缺血性脑卒中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表观遗传学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改变基因的表达或细胞的表型,主要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microRNAs (miRNAs)转录后调节、非编码RNA的干扰。研究发现脑卒中后的一段时期,在梗塞周围区域会发生类似于神经发育期的改变,神经可塑性增加,包括血管神经发生、少突胶质细胞生成、突触发生和轴突生长等,有助于缺血后的神经功能恢复[3-4],表观遗传学调控很可能是介导该过程的潜在重要机制。
1.1 DNA甲基化与缺血性脑卒中
DNA甲基化是一种可逆的表观遗传机制,是在DNA甲基转移酶(DNMTs)催化下,CpG(cytosin-guanine)二核苷酸序列中的胞嘧啶发生甲基化,通常启动子的甲基化抑制基因的表达,而低甲基化与基因转录有关。
DNA甲基化和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及功能预后等方面都密切相关。基因特异性高甲基化是介导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如启动子甲基化水平的增高抑制血管紧张素II 2型受体(AT2R)的表达,增加新生大鼠缺血缺氧后脑组织的损伤[5]。妊娠缺氧致糖皮质激素受体(GR)基因启动子DNA甲基化增加,使转录因子早期生长反应蛋白(Early growth response protein 1,EGR1)和Sp1与GR基因启动子的结合减少,进而抑制大脑中GR基因表达,提高新生大鼠大脑对缺氧缺血性损伤的易感性[6]。动脉粥样硬化作为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多项研究发现全基因组DNA高甲基化是其伴随特征[7-8]。然而,亦有研究发现血液中DNA低甲基化与卒中发生率的增加相关[9]。
脑缺血使DNA明显受损,同时引起基因表达的改变。缺血再灌注后的组织中DNA甲基化水平比对侧大脑半球显著增加[10]。MMP-2是缺血性脑卒中重要的调节因子之一[11-12],由表观遗传学调控[13],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参与早期损伤和后期康复,研究发现男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MMP-2基因甲基化水平较低,且在小血管卒中尤为明显[14]。DNA甲基化与神经发生和突触可塑性等生理修复机制有关。抑制DNA甲基化可抵抗缺血,减轻缺血及氧化应激诱导的血管神经损伤,同时特异性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10]。研究发现DNMTs抑制剂,如Zebularine、5-氮杂-2-脱氧胞苷可降低脑缺血损伤中DNA甲基化水平,发挥神经保护作用[10,15]。此外,通过DNA甲基化测量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生物学年龄与卒中发生风险及不良功能预后相关[16]。
1.2 组蛋白修饰与缺血性脑卒中
DNA在细胞核内的浓缩是通过与组成核小体的4种带正电荷的核心组蛋白H2A、H2B、H3和H4的八聚体结合而实现的[17]。组蛋白翻译后修饰,如乙酰化、磷酸化、甲基化、泛素化等可通过影响 DNA 染色质浓缩和转录稳定性等过程,影响基因的激活或沉默[18]。大量证据表明组蛋白修饰在调节脑缺血性损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9]。
组蛋白乙酰化和去乙酰化分别与基因的表达和抑制相关,由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Ts)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共同调控。多项研究发现在缺血中心及其周围,组蛋白H3乙酰化[20-21]以及H4乙酰化[22-23]水平普遍降低,继而出现广泛去乙酰化并造成严重损害,而通过抑制HDACs促使许多缺血保护相关基因的表达增强,减少梗死面积,抑制炎症反应,保护神经及促进功能恢复。脑卒中后5~7天缺血抑制HDAC2的表达可增加梗死周围神经元的存活和神经可塑性以及抑制神经炎症,促进神经功能恢复[24]。在缺血大脑中HDAC9表达上调,而敲除HDAC9可抑制IkBa/NF-kB和MAPKs信号激活产生的神经炎症,从而减轻脑缺血损伤,发挥神经保护作用,靶向 HDAC9可能是治疗缺血性卒中的有效策略[25]。抑制HDAC3致H3K9的乙酰化水平升高,进而促进神经保护基因(Hspa1a, Bcl2l1, Prdx2)的转录和表达,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对缺血损伤的耐受[26]。另一项研究发现组蛋白甲基转移酶G9a和SUV39H1在诱导脑缺血损伤中具有关键作用,而抑制G9a和SUV39H1可以通过增加缺血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启动子区域的H3K9乙酰化水平,上调BDNF表达,增加神经元的存活,促进神经发生,发挥神经保护作用[27]。缺血再灌注损伤可激活细胞凋亡通路,最终导致细胞死亡[28]。Bax和Caspase-3是脑缺血时神经细胞凋亡的重要启动子,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含Jumonji结构域蛋白3(Jumonji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s-3, JMJD3),通过催化H3K27me3去甲基化,激活两者的表达,启动神经细胞凋亡机制,而抑制JMJD3可减少梗死面积并改善神经功能缺损,是保护脑卒中后神经元免于凋亡的潜在治疗靶点[29]。
1.3 miRNAs转录后调节与缺血性脑卒中
miRNAs是一种数量丰富而小的(20~25个核苷酸)非编码RNA,通过阻断信使RNA向蛋白质的转化来调节基因转录[30],它既是中枢神经系统(CNS)发育过程中重要的调节因子,同时也在各种CNS损伤中被调节,在血管生成、神经发生、少突发生和轴突生长中发挥重要作用[31]。研究发现,miRNAs广泛参与脑卒中后的细胞凋亡、神经炎症、氧化应激、血脑屏障完整性、神经血管发生等病理生理过程[32],这也使miRNAs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在缺血后的大脑及血液中的miRNAs表达发生改变,且特定的miRNAs在CNS中具有独特的细胞特异性时间表达模式[33]。因此确定不同miRNAs在脑卒中的各个阶段及区域的表达十分重要。
1.3.1 miRNAs可作为生物标志物 血液中的miRNAs可作为诊断和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以及判断预后的生物标志物[34]。miRNA-125b-2*、miRNA-27a*、miRNA-422a、miRNA-488和miRNA-627在脑卒中急性期中一致上调,且不受性别、年龄及其他干扰因素影响[35]。miRNA-125a-5p、miRNA-125b-5p和miRNA-143-3p的表达在脑卒中急性期特异性升高,且敏感度高于CT[36]。此外, miRNA-21[35-37]、miRNA-24[37]、miRNA -210[38]、miRNA-221[39]、miRNA-145[40]等亦或为脑卒中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1.3.2 miRNAs与细胞死亡 脑损伤的增加和细胞凋亡的增加有关。其中,Bcl-2蛋白家族在调控细胞凋亡中具有关键作用。miRNA-181a在缺血中心表达增加,但在缺血半暗带减少,抑制miRNA-181a可通过上调抗细胞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减少神经细胞死亡[41];抑制miRNA-497、miRNA-15a/16-1亦可增加缺血梗死组织中bcl-2和bcl-w的表达,减少梗死面积并改善神经功能预后[42-43]。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调节神经细胞的生长、分化和存活,是真核细胞中最有效的抗细胞凋亡生长因子之一。抑制miRNA-186-5p、miRNA-320、miRNA-1等可通过调节IGF-1通路,抑制细胞凋亡,显著减少梗死面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44-46]。而上调miRNA-381靶向LRRC4基因可减少神经元凋亡、促进神经损伤修复[47]。
1.3.3 miRNAs与神经炎症 miRNA let7i在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的表达下降,且和梗死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可通过靶向CD86、CXCL8、HMGB1基因,调控白细胞的增殖、活化与募集,为调节卒中后炎症反应的潜在靶点[48]。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大脑中的miRNA-210水平增加,抑制miRNA-210可下调促炎症因子(TNF-α,IL-1β,IL-6)和趋化因子(CCL2,CCL3)的表达,减轻缺血后的炎症反应,改善脑损伤[49]。脑缺血后miR-3473b通过靶向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3, SOCS-3)基因,增加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炎症损伤,抑制miR-3473b或潜在治疗靶点[50]。
1.3.4 miRNAs与脑水肿 缺血性脑卒中可引起血脑屏障功能障碍,其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脑水肿,而维持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可减轻脑损伤。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eptidase 9,MMP-9)在缺血性脑卒中中的表达显著增加,和神经元损伤、细胞凋亡、血脑屏障开放后的脑水肿及缺血再灌注伤等相关,多种miRNAs可调节MMP-9表达,如miRNA-539可通过抑制MMP-9的表达,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51]。缺血显著增加microRNA-130a水平,抑制miR-130a可减轻脑水肿,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梗塞体积,改善神经功能[52]。
1.3.5 miRNAs与神经血管发生 miRNA-124a[53]及miRNA-210[54]通过靶向Notch信号通路分别促进卒中后神经及血管生成;miRNA-133b通过来自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的外泌体转至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调节基因表达而促进卒中后功能恢复和轴突重塑[55]。缺血大脑中miR-365的表达显着增加,通过靶向Pax6抑制星形胶质细胞向神经元的转化,而敲除miR-365可促进神经发生并减轻神经元损伤[56]。miR-199a可抑制低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而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coding RNA, lncRNA) Snhg1靶向抑制miR-199a促进血管生成[57]。
2 针灸通过表观遗传调控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衡动”的思维模式,与表观遗传调控随外部环境变化出现可逆性改变的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卢圣峰等[58]将表观遗传学应用与针灸理论之中,提出中医的阴阳转化与组蛋白的乙酰化、去乙酰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阐述针灸的理、法、方、穴、术的物质基础。但目前关于针灸从表观遗传调控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相关文献报道不多。如通督调神法预处理可能通过上调miRNA-290、miRNA-494的表达,降低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APQ4)相对表达量,亦可通过调控miRNA-664的表达,降低MMP-9相对表达量,诱导脑缺血耐受,减轻脑水肿而实现脑保护[59-60]。配对免疫球蛋白样受体(Paired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B,PirB)参与抑制脑卒中后轴突再生,而电针可以增加缺血半暗带中的miRNA-181b水平,并通过miRNA-181b直接靶向PirB mRNA来调节PirB、RhoA和GAP43的表达,从而促进神经行为功能恢复[61]。此外,miRNA-9和炎症因子的分泌呈负相关,在 NF-кB信号通路中至关重要,后者是介导或加剧脑缺血后炎症损伤的中心环节。研究发现电针曲池、足三里可能通过上调miRNA-9的表达,调控NF-κB信号通路,抑制信号通路相关促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1β 及IL-6的分泌,从而对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62-63]。针刺百会、足三里可通过上调miRNA-124、抑制层粘连蛋白和整合素β1的表达而减少缺血再灌注大鼠的梗死面积及神经功能损害[64]。电针亦可上调miRNA-132,靶向抑制SOX2基因的表达,促进脑卒中后轴突再生及神经行为功能恢复[65]。在心肌缺血大鼠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电针可通过上调VEGF启动子处的H3K9乙酰化水平,增加VEGF的表达,从而诱导血管生成[66],而根据前文所述的H3K9乙酰化水平与神经保护作用的相关性,该靶点或针灸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潜在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3 展望
虽然近年来随着卒中单元的建立,对缺血性脑卒中超急性期的干预降低了死亡率,但在神经保护和康复治疗方面仍面临很大挑战。而在2010年进行的1项随机化系统研究和荟萃分析指出,针灸可有效地促进脑卒中后的恢复[67]。关于针灸干预缺血性脑卒中,介导缺血耐受、神经保护、抗细胞凋亡、促进神经血管发生及功能恢复等多种表观遗传学机制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基于理论分析及目前提出的各种相关假说和研究发现来看,表观遗传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发展的机制,而且有利于该病的早期诊断,并为针灸理论提供更客观科学的支持,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新的证据。但两者在各自发展和结合过程中均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目前表观遗传学主要包含上述几种调控方式,各方式在大脑的生理、病理过程和适应性反应中协同作用,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尚不明确,或仍存在未知调控方式的可能;此外,表观遗传学和中医理论虽有相似渗透之处,但两者又是不同的理论体系,如何有机结合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针灸干预缺血性脑卒中的机制研究及临床疗效已经大量文献报道,但在基因水平关于其通过作用于哪些位点,如何影响基因表达的研究尚少,目前仅在动物实验中初步证实了某些基因调控位点,但在临床试验中能否通过针刺相关穴位作用于相同的位点、激活相同的通路、产生相同的调控作用,还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验证。若能通过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客观阐述针灸干预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机制,势必为针灸临床应用提供更有力的科学理论支撑,更为针灸的发展和推广带来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