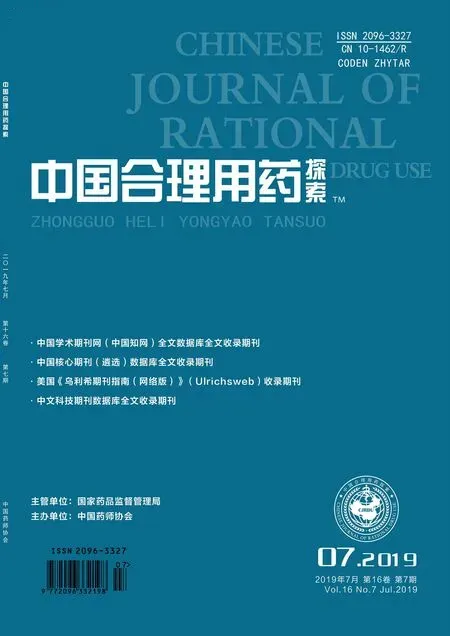探讨中药产生毒性的原因及其对策
王彦坤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医院,河南 通许 475400)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药物。中医把人体分为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偏胜偏衰则为疾患,以偏治偏是中医药治疗的基本原则。《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根据中药药性对人体伤害程度分级为小毒、有毒、大毒,并明确规定了剂量。然“毒”已涉及中医药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毒理学”已成为中医药理论的一大特色,其涵义从最初的毒草发展到药物,药物偏向,到药物的毒副作用;从病因、病位、到病症、病机,发生了更大的演化和延伸,涵盖范围宽泛且意义复杂多变[1];“药”与“毒”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毒对疾病而言有利,对身体而言则有害。古书记载“药性有毒、无毒并非专指毒的为害有无,而是泛指药性的强弱、刚柔、急缓,大凡药性强烈,作用峻猛者谓之有毒;药性柔弱,作用缓和者谓之无毒”。明代张景岳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性,是以气味之有偏也。”但是产生毒性原因,不仅仅在于药物这种偏性,还在于人们使用药物中误用混用。为了避免和减少中药中毒事件的发生,合理应用中药显得尤为重要。
1 毒性产生的原因
缺乏对中药毒副作用、不良反应的正确认识;缺乏科学、客观的中药安全性评价方法;未遵循各项正规操作规程,滥用误用是产生毒性的主要原因。
1.1 品种多用药混乱,辨证不准配伍误
中药的基源品种有数种之多,基源品种不同,所含化学成分、作用机制、生物活性及药理毒性也有所差异,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问题普遍存在,造成中药滥用、混用现象,最终导致中毒。如木通有三种来源,分别为木通科植物、毛莨科植物的川木通和马兜铃科植物的关木通,前二者木通无毒,而马兜铃科关木通可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地区习惯用药不同,北方习用的山豆根为北豆根,是防己科植物蝙蝠葛的根茎;南方习用的是广豆根,是豆科植物柔枝槐的根,广豆根的毒性大于山豆根,如两药分辨不清,容易导致不可逆性肌肉坏死。不辨真伪,误将混淆品作正品使用,如将有毒的香加皮作五加皮入药;桑寄生本无毒,但寄生在有毒植物上的桑寄生就含有毒性成分[2]。
中医注重辨证论治,应用中医药理论对人体综合辨病辨证,结合病人病因病机及季节、地域时间对症选药,随症加减。如治疗咳嗽的蛇胆川贝散和复方川贝糖片,经辨证属于肺热咳嗽、痰多者,可选用蛇胆川贝散;属于风寒咳喘者,应选复方川贝糖片。“是药三分毒,有毒猛如虎”,一方面每一种中药都有一定的偏性,鉴之不准、制之不当、用之不妥,便会成为毒药,如给肝阳上亢病人服过量细辛、肉桂等辛热药物会引起血尿、鼻血;另一方面个别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药理作用剧烈,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相近,使用不当会致中毒或死亡;配伍要明确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但工作中违背配伍原则,善自配伍而导致中毒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乌头与贝母、瓜蒌、半夏等配伍毒性增加。
1.2 炮制失度,缺乏养护
炮制是降低或消除药物毒性、烈性或副作用,增强药效的主要方法。炮制所用辅料、方法及操作者掌握程度不同,则炮制目的就不同。如砂烫马钱子时受热程度不同,有效成分士的宁的含量也不同,温度达到210℃以上,士的宁含量以1.56%降至1.15%,温度达到270℃以上,时间达到4 min以上,士的宁含量将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临床疗效[3],故在炮制马钱子时应掌握好温度及时间,以便保持药效[4]。再如巴豆有效成分与毒性成分均存在油脂中,要求巴豆油控制在18%~20%为宜[5],但实际工作中很难达到规定要求,而出现中毒现象。品种混乱、生熟不分、炮制失度、造假现象严重、辅料标准不统一、工艺流程简单是炮制失度的主要因素[6]。
药材储藏时通风除湿、防潮、避光、卫生条件差、门窗封闭不严,且无遮阴措施,易致药材外观、颜色、水分丢失及泛油虫蛀等现象,使药材霉变,增加黄曲霉含量而产生毒性;养护不当,矿物药材会出现潮解、风化、氧化分解,甚至出现物理化学变化。如红升丹(Hgo)在遇强光及热源时易逐渐析出水银而成剧毒品;轻粉遇光逐渐分解生成有毒物;雄黄置阳光下曝晒,会变为黄色的雌黄[7],应避光密封、阴凉处储存[8]。
1.3 药物过量,个体差异
药物以量而能,以量而用[9],药量使用恰当,剂量准确,能起较好的治疗作用;反之,则损害机体。在求愈心切的心理支配下,盲目加大用量或超量用药会发生中毒,轻者身体不适,重者呼吸麻痹而死亡。如肉桂过量服会发生血尿;细辛过量服则发生眩晕、肾损害;斑蝥素达到30 mg可致人死亡。用药时要注意用药时间,过长过久均引起毒性蓄积。另外人体体质强弱不同,对药物耐受程度也不同,如身强体重用量易大,身弱体轻用量则易小,对幼儿、老人、孕妇慎之再慎,特别对过敏体质发生过敏反应及中毒的几率较无过敏史患者高出4~10倍。
1.4 煎煮不合理,剂型失宜
中药煎煮可以消除或缓解中药的毒性,而煎煮不当则可导致中毒;《医学源流论》说的“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于此”,“方虽中病而服,不得其法,则非特之功,而反有害”。这说明如何煎服中药举足轻重,如川乌应先煎久煎,所含的有剧毒的双酯型生物碱易被水降解,服之不会中毒。由于中药药理毒性成分较复杂,选择剂型要根据病情、药物特点选择。有效给药途径是显效减毒重要措施,如汤剂起效快,而丸剂则慢,口服剂、外用剂较安全,副作用小,中药注射剂、水针剂则安全性低。如砒石不能作酒剂,违者毙命。
1.5 工艺标准不健全,滥用误用
中药作用机制复杂,部分成分不适合注射剂,且制备工艺及标准还不完善,个别技术还不成熟。如双黄注射液中,不同制备工艺的黄芩苷和汉黄芩苷的含量不同;黄芩苷与过敏反应有关,而汉黄芩苷与毒性反应有关。中药在人们心中存在无副作用的思想,且根基至深,目前患者擅自长期用药、偏信偏方、乱听信游医药贩而滥用中药导致中毒的事件逐年攀升。如听说苍耳子能治鼻炎,把苍耳子当花生仁做食疗用,导致服用过量而中毒。
2 中药使用对策
明确中药的毒性分类、强弱分级、中毒剂量、致死量、中毒机理并制定严格的临床用药指征、应用剂量和使用周期,真正做到趋利避害。
2.1 规范标准,辨证准确
明确正品和主流品种,力争达到一物一名,一名一物,规范市场地区习惯混乱现象,从源头上保证基源科属品种正确。使用有毒中药,更要辨准证侯,辨清发病机理,确定治疗原则,拟订相应方剂,随症加减,中病即止;如附子常用量为3~15 g,而在辨证大寒症中则为15~30 g。
2.2 规范炮制,限制用量
炮制时药材内部发生了相应的化学改变,使药性改变,有效成分含量增加,毒性成分含量降低,以及产生新的功效[10]。对有毒中药重视炮制,提倡“若有毒宜制”,加强炮制的统一性。执行炮制规范质量标准是保证有毒中药去毒存效的基石。
剂量是保证药效和避免中毒的重要因素,是中医辨证用药关键所在。中医素有“不传之秘在于量”之说,药物用量不同,主治也不同。毒性药物在临床应用中应严格控制用量,以免中毒。如明确规定了有毒中药的毒性限制量,砒石0.002~0.004 g,蟾酥0.015~0.03 g。
2.3 配伍合理,正确煎服
药有单行之专攻,方有合群之妙用;合理配伍,可以通过药物之间作用来中和或分解毒性成分,使方剂整体毒性降低或消除。如制川乌与白芍配伍,川乌总碱毒性明显降低;乌头与大黄配伍,乌头碱与大黄素1︰2比例配伍,具有减毒增效的作用[11]。
很多毒性药经过煎煮,毒性成分会挥发或水解,有效成份依然保存,如附子、乌头经久煎水解成毒性小的乌头次碱,因此,合理久煎可以减少毒性保存药效,是诸多医家应用有毒中药的可靠经验。毒性中药有特殊服用方法,如朱砂易水飞忌火煅,因遇火加热生成毒性更强的游离汞、氧化汞,应冲服禁汤服;雅胆子肉包裹吞服,乌头类中药应避免饮酒,洋金花可卷烟分次燃吸。服用毒性药物应以小剂量、多次服用,不宜在空腹、疲劳及心情低落时服用,以免增加胃肠道刺激。
2.4 剂型合理,地域季节
李东垣指出“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说明中药剂型与疗效密切相关[12],中药成分有不同理化特性,选择合理药物,合适剂型,要因人因病情而定,大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隔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宜用丸,又欲速用汤,稍缓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大概也[13]。
地域不同,服用方法不同,南北地域用量皆不相同。北方地外高寒,身体壮实,皮肤粗糙,气候干燥,用热性药较南方人用量可稍大些;夏天苦寒药用量宜重,冬天寒药用量宜轻。夏天发汗用量要轻,冬天发汗用量要重。
2.5 合理用中西药,安全评价管理
有些中西药配伍应用使药物疗效降低,毒副反应增强。中西药合用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合理配伍禁忌及其产生的损害,如含汞的中药及其制剂与具有还原性的西药如硫酸亚铁、亚硝酸异戊酯合用,可增加毒性。中西药联用导致的不良反应在逐年上升,主要原因是服药间隔时间太短,服药前未咨询医师与药师等。
正确贮存与养护管理是减少毒性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但人们为了使药材颜色鲜亮用硫磺熏蒸,致使硫磺含量超标;再者中药农药残留以及中药在栽培中残留的毒害也是导致中毒的原因,中药材成分不确定与农药残留、黄曲霉毒素、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存在,这种人为产生的毒性,增加了对有毒中药的安全性评价难度。对待中药安全性问题既要做到充分认识,又要做到理性对待,更要做到加强研究、合理应用。我们不但要有传统意识的纵向继承,而且要有现代研究的横向比较借鉴,更要汲取先进研究方法,以动态发展观评价安全性,将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与上市后评价结合起来,建立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强调对药效剂量、毒性剂量、毒副反应监测管理,确保用药安全。
3 结论
中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作用机制复杂,有无毒性,即是相对的,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任何事物都讲究量度,更何况中药是特殊商品,按中医辨证原理,依据中医理法方药组方原则,结合症状,随症加减才能显于较好疗效。有毒中药是一把双刃剑,它即具有卓越的临床疗效,使用得当可以起沉疴于顷刻;它又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使用不当又可毙性命于瞬间。正确对待中药的毒性,是安全用药的保障,既不能畏其毒而弃用,也不能持其无毒而滥用,只有规范操作行为,选择正确的基源品种药用部位,把握中药的药性,剂型炮制适宜,合理配伍,服法正确,中西药应用得法,对它有正确的安全评价,才能做到明其利而用之,知其弊而制之,充分发挥中药的治疗作用,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