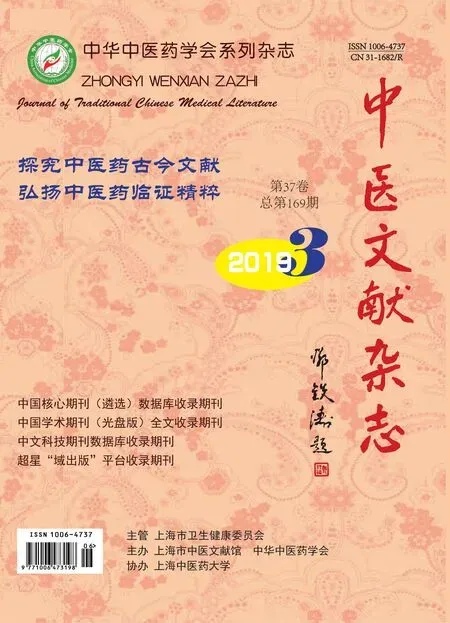开山采铜铸丰碑 笔耕不辍济岐黄*
——略述钱超尘四十余载治学方法及成就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杨兴亮 杨东方△ 王翠翠
钱超尘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医文献研究大家。自1972年奉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以来,他矢志不渝地坚守在中医文献第一线,迄今四十余年矣。钱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所涉及领域极广,几乎在中医文献学的每个领域都有建树,本文难以面面俱到,笔者择其要者,约略地将钱超尘先生治学四十余年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概括为“三文三求”。
治学方法
“三文”可以看作是钱先生治学方法的高度概括,即以文字训诂为工具,以历代文献为基础,以弘扬传播中医药文化为旨归。为发掘中医历代经典典籍,继承和发展中医医家学说做出了难以泯灭的功勋。
1.以文字训诂为工具
钱超尘教授1961年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又求学于文字训诂大家陆宗达先生,成为第一届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钱先生在此阶段习得的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传统小学知识和学习《说文》和古韵的方法,为将来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纵观钱先生一生治学之旅,虽然在不同时期学术侧重有所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语言学对于钱先生学术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先生以传统文字训诂为治学武器研究中医典籍,取得了许多突破前人启迪后学的不俗成就。
中国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小学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解释一字一词的“形”、“音”、“义”。古人有“小学为经学附庸”之语,前人认为研究小学的根本目的是“通经”,而“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钱先生善于将传统语言学当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医古籍训诂当中去,来解决中医面临的现实难题。比方说,在《伤寒论》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中记载的抵当汤,前人对于“抵当”的意义多半或流于字面意思,认为抵当汤可以抵挡病邪故称“抵当汤”、或随文释义认为“抵当”是“最恰当”之意,因命之曰“抵当汤”。但钱先生凭借对语言的敏感,认为这些解释统统有误。钱先生应用“古无舌上音”的音韵学原理,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证明“抵当”实为“至掌”的古音,而“至掌”也就是“水蛭”,则是抵当汤中的一味主药。因此,“抵当汤”是以方中主药为命名依据的,这符合张仲景命名医方的规律,因而成为学术定论。
真正的文字训诂大师绝非自湎于一词一句的研究,而是擅长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本学科的起源、发展与演进,钱先生亦是如此。钱先生不仅在中医经典中具体的字句训诂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更为难得的是,钱先生以深邃的智慧和长远的眼光将中医药训诂放在历史环境下考察研究,其关于训诂史的把握与论述尤为精到。这集中体现在钱超尘教授的《本草名物训诂发展简史》一书中。本草学“释名”发展历史悠久,但是缺乏总结性文献,先生《发展简史》一文从陶弘景奠定本草释名开始下至明清本草文献均有论述,其中对《本草纲目》释名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谬误给与了中肯评价,文末痛切指出了今人影印金陵本《本草纲目》误描误改以致错讹泛滥之现象,并举五十余例证明之。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至今仍是学术界学习研究本草训诂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2.以历代文献为基础
钱先生取得如此辉煌的治学成果很重要的基础是重视文献材料。在学术研究中,搜集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材料不全特别是重要材料的缺少,一定会导致结论的偏颇甚至错误。故史学大家陈垣一直强调搜集材料一定要“竭泽而渔”。钱先生在材料的搜集上就体现了这一点。以《黄帝内经》研究为例,众所周知,今传《黄帝内经》通行本是经过王冰重新分卷、迁移篇次、增润内容后形成的,早非《内经》原貌,今人要考察《内经》原貌就必然要了解唐以前《内经》的古传本。这样一来,19世纪在日本发现的《黄帝内经太素》就近乎是唯一的选择了。《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渊源和临床指导,自古至今研究论述《内经》者有几百家之多,而研究《太素》者则寥若晨星。这除了《太素》发现时间短,没有时间充分研究外,最大问题是中医界和文献界没有给予应有重视。钱先生有感于此,在仔细整理校注文本后,深研《黄帝内经太素》文本,出版专著《黄帝内经太素研究》一书,全书回顾了目前学界对于《太素》的研究概况,并从成书时代、所据底本及流传历史等方面研究《太素》。而该书也举例说明目前通行本(仁和寺本、萧延平本)存在的讹字误字,并创造性地运用音韵学方法进行《内经》、《太素》两书互校,改正了很多错讹之处。最后钱先生在书中讨论了杨上善的医学思想,总结了杨上善的几个重大医学思想,给人以深刻启发。该书条理清晰、论述精详,为目前研究《太素》之集大成者。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研究医经又并非单纯以医论医,往往结合大量文史类文献,广征博引,最终得出可靠结论。古人早就认识到“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1],钱先生先治小学,又治医学,对此语颇以为然。先生很多治学成果可以视为以文证医的经典范例。聊举一例,先生在研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时认为,文中“搏”字是俗体“摶(简化后作‘抟’)”字的讹字。为考证清楚这个问题,先生不仅引用了几乎所有我们能够见到的伤寒金匮类文献,而且从历代书法文献中搜罗例证,广征博引,从医籍和文籍两个方面来证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搏”字确系是俗体“摶”字的讹字。文中简明的语言、缜密的论证和丰富的实例让人读过之后不由信服。这个事例的意义并非只是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结论,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引我们重新思考中医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之间的关系。
3.以弘扬传播中医药文化为旨归
中医学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先生的很多学术结论已经被中医临床界所检验、接受和应用。这使埋没于故纸堆中的中医古籍重新焕发了生气,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医文献学,特别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价值。
“中医是在数千年文化发展中不断充实、不断壮大、不断吸收儒释道精神,把中国文化中积极内容吸收进来的科学文化。中医文化折射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积极最优秀的内容,中医所传承的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血脉”[2],钱先生如是说。中医历经数千年之演进,流传至今的各类中医典籍多如牛毛,如果漫无目的,仅凭自己喜好来研究中医文献,必定难有所成。钱教授认为研究中医文献要抓住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医经典。“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3]中医经典就是我们中医人的“六经”,先生一生治学领域虽然极为广阔,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但是都紧紧围绕着中医经典这条主线开展研究工作。
中医经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传统医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作为中医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我国传统医学的独特魅力展示出来,钱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深挖以中医经典为核心的中医文化底蕴,让人们有机会了解到中医学的优秀文化,钱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中医文化助推我国文化建设的行为,必将大大提高国民文化自信。
治学理念
“三求”是钱先生治学理念的高度概括,所谓“三求”,即“求深”、“求大”、“求新”。“求深”指不浅尝辄止,探求问题的根源;“求大”指格局大,探求的问题都是避不开的中医经典;“求新”指不炒冷饭,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
1.求深
先生为学不浅尝辄止,知其然更探其所以然。在传统语言学中音韵学是基础,“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4]。钱先生极为重视音韵学在中医文献学中的运用,不仅将音韵学运用到训诂学当中去,还擅长推而广之,将通过音韵学方法得出的可靠结论运用到其他学术领域。钱先生以上古音校勘《黄帝内经》一书,不仅改正了很多长久以来的错讹之处,而且还通过对某些代表字的古音转变历史考察判定了《黄帝内经》中的某些篇章的成书年代。例如:“明”、“行”二字在先秦古音里均属于阳部庚系开口字,东汉时期“明”、“行”二字逐渐转入耕部。钱教授通过考察发现在《黄帝内经》的某些条文中“明”字读古音作“谟郎反”(máng),属于阳部字,如《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中的“彰” 与“明”押韵同属阳部。而有些条文“明”字读今音作“武兵切”(míng),属于耕部字,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中 “平”、“宁”、“刑”、“清”四字与“明”押韵同为耕部字。“行”字古音转变与“明”相似,在此不再赘述,读者可以详参钱先生《内经语言研究》一书。根据这些代表字的韵部转变可以认定《黄帝内经》的某些篇章成书于东汉时期。这为《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提供了依据。
2.求大
钱先生常常以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3]自勉,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钱先生虽是一介书生,但是治学眼光独到,格局甚大。先生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是在静心地观察、冷峻地思考学科历史发展脉络之后,站在发展本学科的高度上统筹设计的。先生治学之旅看似纷繁,但是细细考察,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就是中医经典。钱先生常讲,中医如同厚重的三足鼎,《黄帝内经》、《伤寒论》(含金匮)和本草典籍即为鼎之三足。难得的是,钱先生在每个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黄帝内经》方面,钱先生着重研究《内经》语言现象,出版专著《内经语言研究》。在书中钱先生将《内经》中的训诂、音韵、语法等现象条分缕析,省却了学人习读《内经》之心力。在本草典籍方面,钱先生对古代本草巅峰之作《本草纲目》重新校正,改正“上图本”颇多错讹之处,以《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为名出版,此书后来获得中华中医药学术著作一等奖。这体现了学界对于钱先生学术成果的肯定。
当然先生用功最深的还当属《伤寒论》版本研究。在先生之前,《伤寒论》版本研究一直处于蒙蒙昧昧的状态。宋本《伤寒论》(实为明代赵开美本《仲景全书》)存世者几何?无人知晓。先生有感于此,将毕生心血用于宋本《伤寒论》的访寻工作,成果斐然。《伤寒论》版本之研究,当代无出其右者。先生历经坎坷,穷几十年之力,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四处求书,确定了宋本《伤寒论》目前共有五部。据钱先生考证:“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图书馆所藏为初刻本,有少许讹字,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及台湾故宫所藏为修刻本,改其讹字。徐矩庵题记,唯台湾本有之,他书皆无,尤为珍贵。”[5]至此国之重宝宋本《伤寒论》家底才算摸清。钱先生不满足于只是找到这些版本,还仔细梳理了《伤寒论》各个版本自古至今的传承历史。先生所著《伤寒论文献通考》一书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伤寒论》文献发展史之著作,曾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书中对于仲景事状及著作包括《金匮玉函经》以及在流传过程中分化演变出来的唐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高继冲本《伤寒论》、康治本、康平本《伤寒论》及敦煌出土《伤寒论》残卷均有考证,为人们研究《伤寒论》文献流传历史勾勒出清晰的图框。
先生研究《伤寒论》并非只把握版本流传等宏观方面,对于很多版本细节之处也有较好论述。例如《伤寒卒病论》之书名研究,钱先生引用郭雍《伤寒补亡论》之观点,认为卒(zá)为繁体杂(雜)之省文。《伤寒卒病论》即为《伤寒杂病论》。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正是因为先生细大不捐地研究,才建起一部无一缺憾、极为严密、传承有序的《伤寒论》传承史。“从来提倡学术者,但指示方向,使人不迷,开通道路,使人得入而已。转精转密,往往在其门下,与夫闻风私淑之人。”[6]先生半生心血建立了《伤寒论》传承史,为我们指示了学术门径,开通了学术道路,作为后学理应接过先生手中高擎的《伤寒论》文献研究大旗,使之“转精转密”。
3.求新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7]顾炎武将毫无自己创建的末流学者所著之书比喻为“废铜充铸”,以“采铜于山”比喻饱学之士所著之书。先生做学问最忌拾人牙慧,陈陈相因,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先生对于新材料的挖掘研究上。
上文已经提到先生治学的主线是围绕中医经典展开的,这一点在挖掘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上同样适用。钱先生讲究创新,不炒冷饭,对于新材料的研究眼光没有局限在国内,常常留心国外的有关文献,对于流传日本的文献颇有研究心得。对于流传日本的康平本《伤寒论》和康治本《伤寒论》都有研究,并有论文发表。近年来,先生花大力气将日本流传的《太平圣惠方》中卷八《伤寒论》部分以南朝秘本《伤寒论》为名影印出版,后半部分为敦煌文献中《伤寒论》内容。先生将上世纪由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盗掠出国长期流传海外的敦煌文献中有关《伤寒论》内容影印,并附上必要校正考证内容与前书合印,取名《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伤寒论〉校注考证》。本书出版为研究《伤寒论》提供了两个重要版本,此举无论对《伤寒论》文献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之作用。
对于域外学人确有创建的观点和结论,先生也往往多有采撷,这些观点与结论往往是建立在对于新材料的研究之上的。很值得关注的是先生关于汉方医学的研究。钱先生虽然没有专著来研究论述汉方医学,但是先生关于汉方医学的很多论述散见于各类著作。比如在《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一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日本江户时期的医籍训诂做了详尽介绍,文中重点对多纪父子、山田宗俊和伊藤子德等人的学术风格、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做了论述。通过简练的笔法、丰富的例证,梳理了中医古籍训诂在日本江户时期发展历史,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日本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训诂成就。
先生重新整理、发掘和研究了大量新文献,先生所发掘之新材料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拓宽中医文献学研究领域方面,先生确有开山采铜之功。
先生学识宏丰,笔者深知本文不能全面总结钱超尘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仅管窥蠡测。“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8],先生能取得今日之成就绝非偶然,必定是付出了艰苦卓绝、难以想象的磨难之后才到达此等境界。先生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如果本文能给读者以借鉴和启发,以先生的学术态度为榜样,以先生的学术方法为指导,推进中医文献专业整体进步,实为本文之最大目的,亦为当代中医最大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