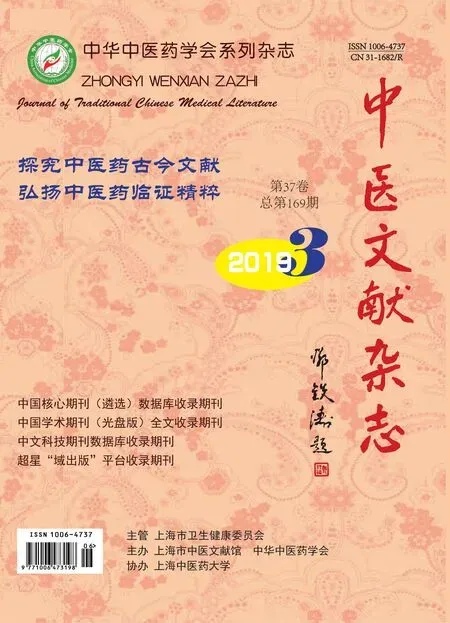张婷婷治疗痛经合并持续高热医案一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200437)
李爽爽 曹 阳 张婷婷△
张婷婷教授、主任医师,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妇科疾病,尤其在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等疾病诊治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临床方面,张教授注重辨证论治,善于用药,其提出的清瘀温通法能有效的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笔者有幸跟随张教授学习,现就张教授治疗痛经合并持续高热一则医案的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病因病机
痛经是指妇女正值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周期性小腹疼痛,或伴腰骶酸痛,甚至剧痛晕厥,影响正常工作及生活的疾病,西医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中医认为痛经病位在冲任与胞宫,多因生活所伤、情志不和、六淫为害,病因病机可概括为“不荣则痛”或“不通则痛”。《景岳全书·妇人规》就痛经分虚实提出:“经行腹痛,证与虚实。实者或因寒滞,或因血滞,或因气滞,或因热滞;虚者有因血虚,有因气虚。然实痛者,多痛于未行之前,经通而痛自减;虚痛者,于既行之后,血去而痛未止,或血去而痛益甚。大多可按可揉者为虚,拒按揉者为实。”[1]张教授认为[2],胞宫藏泄失司,冲任气血不畅,瘀血阻滞胞宫、冲任,是为本病的主要病机。
西医认为,发热是指机体在致热源作用下或各种原因下引起体温调节中枢的功能障碍时,体温升高超处正常范围[3]。中医将发热分为内伤发热和外感发热,前者以内伤为因,多为气血阴精、脏腑功能失调为病机,病程多较长,起病较缓,多以低热为主,但也有高热,伴头晕、神疲等不适;后者以感受外邪为因,多起病较急,病程较短,以高热为主,多伴有恶寒,兼有头痛、流涕等[4]。
经行发热是指每值经期或行经前后出现以发热为主的病证,称为“经行发热”或者“经来发热”[5]。段富津教授认为[6],经行发热的病因可分为外感和内伤,且以内伤发热更为常见,其认为由外感引起的发热,虽在经行之时,亦应按外感论治为主,兼顾经行之情,而由内伤引起的经行发热,则多以肝郁、血虚、血瘀、气虚引起。
临床医案
患者,女,14岁,2018年8月7日初诊。主诉“经行腹痛2年合并持续高热不退2年”。患者2016年8月下旬初潮,月经周期28~30天,经期10天,量多,色深红,有血块,伴痛经明显,痛经由经期第一天持续至第五天,VAS评分8- 9分,服芬必得等止痛药未见明显效果,须平卧休息,伴恶心、腰酸及腿酸,伴小腹冷加衣未减,偶有冷汗出。末次月经:2018年7月26日,历时10天。前次月经:2018年6月28日,历时10天。患者2016年10月24日起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高热不退,体温持续在39~40度,伴头晕头痛无力,余无明显不适。患者因高热持续不退,先后于江浙沪多家西医、中医医院就诊,曾行多项检查,包括骨穿、腰穿、PET-CT、头颅MRI、脑电图、血培养及病原学、基因检测等均未明确病因,予以多种抗生素等药物治疗无效。外院倾向于考虑“中枢性发热”。患者2017年4月1日体温忽然恢复正常,至2017年10月9日患者又再次高热持续不退,体温在39~40度。至就诊时患者刻下体温39度,伴头晕头痛,胃纳可,二便调,夜寐安,舌苔薄中腻舌红,脉细数。初问病史,患者及母亲并未提及高热病史,仅为痛经就诊,仔细询问才详述,患者目前因高热不退已休学在家。
西医诊断:持续高热待查(中枢性发热可能)、原发性痛经。四诊合参,中医辨病为内伤发热、少阳病、痛经病,治拟和解法,予小柴胡汤加减如下:柴胡5g,黄芩6g,制半夏6g,党参9g,生甘草3g,红藤15g,丹皮9g,川断9g,白芍15g,石膏30g,知母9g,炮姜2g,钩藤12g,紫苏梗6g,延胡索10g。上方7剂,日一剂,水煎200mL,饭后口服。
二诊:2018年8月16日。患者月经未至,于2018年8月9日查妇科腹部B超提示子宫及附件未见明显异常(内膜10mm)。刻下:体温39度,患者仍有头晕头痛,舌苔白腻,质暗红,脉细弦。考虑患者内膜偏厚可能,为月经将至,予以活血调经止痛之自拟方如下:炒当归12g,白芍12g,生熟地各12g,川芎6g,延胡索15g,炒川楝子5g,乌药9g,五灵脂12g,制乳香3g,制没药3g,生蒲黄15g,仙鹤草30g,砂仁3g,黄芩6g,巴戟天9g,败酱草9g,佛手6g。上方7剂,日一剂,水煎200mL,饭后口服。嘱患者经期停服。
三诊:2018年9月13日就诊。患者高热已退半月余,末次月经于2018年9月9日至,量中等,色较前红,持续5天,少腹痛明显缓解。刻下:体温37度,舌中白腻,质红,脉细弦。患者目前体温平,痛经较前缓解,分别予以2018年8月7日方7剂嘱患者经后口服,予以2018年8月16日方7剂嘱患者经前7日始服。后患者体温已平,痛经缓解,恢复正常学业生活。
医案分析讨论
《伤寒论》中提到“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本医案患者虽为高热,但历时较长,排除外邪因素,故考虑为内伤发热,而患者伴有头痛、脉细弦,故考虑为伤寒论所提及的少阳病。《伤寒论》载:“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指出了小柴胡汤的使用范围,适用于本病中的少阳病之发热。本病患者高热虽非经行发热,但考虑患者高热于初潮后2月出现,无法排除患者高热与月经来潮相关的可能性。国医大师段富津认为:“妇女行经期间,血海空虚,若再加情志不畅,易致肝胆疏泄不利,进而郁而化热,可用小柴胡汤化裁,以疏利肝胆、和解退热。”[6]
少阳病证,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当以和解法治之,不可用汗、吐、下法。一诊8月7日方以小柴胡汤加减。方中柴胡为君,性苦平,入肝胆经,透泄少阳之邪。黄芩为臣,性苦寒,清泄少阳半里之热。柴胡之升散,得黄芩之降泄,两者配伍为和解少阳之基本组合。胆气犯胃,胃失和降,佐以半夏、生姜和胃止呕,考虑炮姜有温经补虚之效,故而改生姜为炮姜。佐以党参补气健脾,白芍养血调经止痛,续断补肝肾,延胡索、苏梗理气止痛。取白虎汤中之石膏、知母清热生津之效。以丹皮、红藤、钩藤清热,又取丹皮、红藤活血止痛之效。以甘草为使,助参扶正,调和诸药。全方和解高热之同时,达调经止痛之效。
二诊考虑患者月经将至,8月16日方以活血调经止痛为主,以四物汤之炒当归、白芍、熟地、川芎补血调经,取补血要药之熟地滋阴补肾养血,加以活血良药之当归,配合白芍养血滋阴、缓急止痛,川芎活血行气。又以失笑散止痛,取生蒲黄、五灵脂化瘀散结之效,加以川楝子、延胡索活血行气止痛,制乳香、制没药活血定痛,败酱草祛瘀止痛,乌药温肾止痛,仙鹤草、生地黄止血,砂仁、佛手和胃,巴戟天补肾。全方诸药合用,达至活血调经止痛之效。
临床上用小柴胡汤、白虎汤治疗高热的病例屡见不鲜,但持续高热2年的病例确实少见。中医认为“妇女以肝为先天”。“素性抑郁或郁怒伤肝,肝失调达,冲任气血郁滞,瘀阻子宫、冲任,不通则痛,发为痛经,用小柴胡汤疏通三焦气机,疏肝解郁”[7]。而对于本病患者考虑高热与痛经同时存在,用小柴胡汤恰中其症。另外小柴胡汤用于调经,主要在于和解少阳、和调肝脾、疏利肝胆、调和气血,体现了“和”之意[7]。而对于临证治疗时,张教授注重运用中医经典理论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辨病与辨证结合,药味讲究用精不用多,药量讲究适宜。如本案中对于患者经前期与经后期侧重治疗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