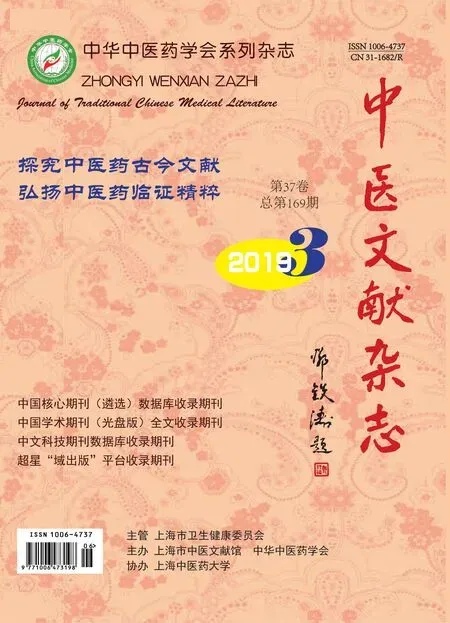陈建杰论治慢性乙型肝炎经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201203)
商斌仪 卓蕴慧 陈逸云 巩安宁 张 雯△ 指 导 陈建杰
慢性乙型肝炎是我国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之一,病情缠绵,治疗困难,与肝硬化、肝癌密切相关。2006年全国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我国1~59岁一般人群HBsAg携带率为7.18%[1],据此推算,我国现有的慢性HBV感染者约9300万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约2000万例。
陈建杰教授系上海市名中医,上海市领军人才,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工作,对于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有丰富的经验。现将陈建杰教授论治慢性乙型肝炎临证经验总结如下。
临证经验
1.顾护中州,扶正为主
由于脾胃素来被认为是后天之本和气血生化之源,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陈教授特别重视调摄脾胃功能,凡久病、重病的治疗和病后摄生都应该顾护脾胃。正如李东垣《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所言:“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陈教授认为脾主运化,其性喜燥而恶湿,而慢性乙型肝炎病机多为湿热缠绵,故常常导致脾胃气机困阻而运化功能失司,出现乏力、纳减、脘痞、便溏、苔腻等常见症候,临床遣方用药应紧紧围绕病机,尽量恢复脏腑正常生理功能,利用健脾化湿、芳香醒脾类的药物,开达中焦气机,促进脾胃健运,所谓“中州固而气机达,脾胃健则湿热化”。
此外,由于慢性乙型肝炎多属邪气留恋,通常治疗易偏于祛邪,重用、久用清热化湿之品,日久反伤及阴分,损及正气。陈教授认为:正气系人身之本,御邪之基,如《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正气之化生,无外乎先后天,对肝病而言,多湿热为患,湿重困脾,热重伤肾,一味祛邪,反伤正气,若正气不虚,则邪难久滞,故祛邪当先扶正。在临床用药上,健脾以六君化裁,补肾以院内自制补肾方为主,湿重者以苍术易白术,气滞者加川楝子、大腹皮,热重者加川连、黄芩,水泛者加猪苓、玉米须、陈葫芦瓢,黄疸者加茵陈、虎杖、三金汤等等,随证加减。
2.重视毒邪,清化为辅
陈教授认为,在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治疗实践中,毒邪致病是极其重要的病机理论[2]。传统上毒邪可分为外毒和内毒,前者包括疫疠之毒和六淫郁火化毒,后者则属气血脏腑运行失常所致病理代谢产物蓄积之毒。考虑到慢性乙型肝炎的疾病特点:乙型肝炎病毒当属外毒范畴,而乙肝病毒侵入人体后,病情缠绵难愈,引起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障碍等病理变化,代谢失常,病理产物蓄积日久蕴毒,是为内毒,故属内外毒兼而有之。所以陈教授认为,对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解毒排毒原则亦应贯穿始终。临床常用的清热解毒药有半枝莲、垂盆草、蛇舌草、虎杖、苦参、夏枯草、蒲公英、连翘等,这些药物既可有效改善肝脏炎症,又能对乙肝病毒复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临床实际应用中,陈教授提倡适时、短期的运用清热解毒药物,以尽可能祛邪不伤正。如在患者病情活动、肝功能不稳定时,配伍虎杖、蛇舌草、垂盆草、苦参等以清热祛湿解毒。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虎杖煎剂中的大黄素、大黄素葡萄糖甙、白藜芦醇甙、黄酮类、芪三酚甙等对多种病毒有抑制作用。近年来亦有研究认为垂盆草和苦参有保护肝细胞膜、改善炎症及抗病毒作用。但陈教授特别提出,清热解毒等苦寒之品,应“中病即止”,以防“伤中碍胃,徒损正气”。
3.剿抚并举,各因制宜
临床常见久病之人,湿热与伤阴并见,苔干厚腻,舌面少津,口干口苦,时有潮热。化湿则恐伤阴,养阴则虞邪恋,似为矛盾,但陈教授细析病机后认为:湿浊为邪盛,阴亏为正虚,总属正虚邪实。故临床上秉承“扶正与祛邪并举”的思想,采用化湿药与养阴药同用,剿抚兼施,有是证用是药,湿盛者虽舌红少津犹可投苍术、半夏,阴亏者虽苔腻肢困犹可用生地、石斛。同时注意养正存真,多用田基黄等利湿不伤阴的药物,在使用清热药时,常配炒谷芽顾护胃气。
此外,各人先天禀赋不同,故临床用药亦应随之变化,肝病患者若属阳虚体质,则虽有湿热内扰,仍可重投桂枝、巴戟,温阳益肾,祛湿外出。药性各异,当随令斟酌:春令风盛,慎投燥品;夏令暑湿,重用化湿;秋令属燥,慎投涩剂;冬令寒湿,补肾为先。
4.四诊合参,重视舌象
陈教授认为,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应该四诊合参,相互配合。而在四诊中首重望诊,即察神态、症状、舌象等整体情况,尤重舌象的变化。舌象与脏腑经络的功能状态与气血津液的盈亏、运行有着密切关系,舌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疾病的证型归属和病邪轻重,从而指导辨证施治。陈教授临床上观察大部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都表现为淡红舌白腻苔,说明体内多湿,乃脾胃湿浊之邪上泛所致,治当健运脾胃,化湿和中。
此外,若舌色淡红苔薄白,属脾虚为主,湿邪不甚,治宜健脾益气,多用党参、炒白术、茯苓等;若舌淡胖兼有齿痕苔白厚腻,属气虚湿盛,治宜益气健脾,燥湿祛邪,多重用苍术、茯苓,薏仁等;若舌偏红苔白腻欠润,属阴分不足,水湿内滞,治宜养阴祛湿并举,养阴多用玉竹、麦冬、生地等,祛湿多用半夏、陈皮、薏仁等;若舌色红苔白腻,属湿郁化热,治宜清热化湿,多用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若舌色红苔黄腻,属湿热并盛,治宜清热利湿,多用茵陈、虎杖、大黄等。
5.中西结合,病证互参
陈教授衷中而参西,尊古而创新,提倡利用现代医学的检测技术来拓展中医四诊的外沿,比如将实验室检查结果作为中医望诊的延伸,为临床辨证提供参考,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观察,发现若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升高,多为湿热并重,治疗当以清热利湿为主,多选茵陈、虎杖、金钱草、苦参等,若白蛋白降低、球蛋白增高、肝纤维化指标增高,多为气滞血瘀,治疗当以行气活血为主,多用川楝子、枳壳、鳖甲、桃仁等,收效甚著。此外,陈教授还提倡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应注重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中西医合理分工,各司其长,将中西医结合的疗效发挥到最大值。比如,目前慢性乙型肝炎的西医治疗主流方向是抗病毒治疗,但还面临着抗病毒药物疗效有限(尚不能完全清除病毒)、治疗周期长、不良反应多等等问题,此时联合中医中药不仅可以增加抗病毒疗效,缩短治疗周期,还可以减轻不良反应,大大增加患者治疗信心和依从性。陈教授以拉米夫定联合健脾清化方(炙黄芪、炒白术、苍术、陈皮、黄连、黄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以单独使用拉米夫定患者作对照,治疗周期1年,结果发现可提高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乙肝病毒定量(HBV-DNA)阴转率,同时降低了乙型肝炎病毒变异(耐药)的发生[3]。
验案举隅
蔡某,男,35岁。2005年6月14日初诊。主诉:右侧胁肋部隐痛4月余,加重1周。现病史:10余年前入职体检发现表面抗原阳性,未予重视。2005年2月,患者加班劳累后出现右侧胁肋部隐痛,休息后可缓解,因无其他明显不适,故未及时就诊。近1周来,右侧胁肋部时时胀痛,安静时尤为明显,故来就诊。刻下症见:全身乏力,右侧胁肋部胀痛,欲大透气,纳谷欠馨,口苦,脘腹痞胀,夜寐尚安,小溲偏黄,腑行日二次,质偏溏。舌色偏红,苔薄黄腻,脉小弦。
辅助检查:乙肝五项:HBsAg(+),HBeAg(+),HBcAb(+),HBsAb(-),HBeAb(-);乙肝病毒定量3.68×106copies/mL;肝功能:ALT 103 IU/L,AST 68 IU/L,γ-GT 83 IU/L,TBil 36.7umol/L,余均正常。上腹部B超提示:肝回声粗糙,胆囊炎,脾脏稍大,胰腺、双肾未见异常。中医诊断:胁痛病(肝郁脾虚,湿热内蕴证),西医诊断:慢性乙型肝炎。西医治疗:建议患者长期服用拉米夫定片抗乙肝病毒治疗,患者因有顾虑而不愿服用西药抗病毒,只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
中医治拟疏肝健脾,佐以清化。方药如下:柴胡9g,枳壳9g,制香附12g,苍术12g,炒白术30g,茵陈15g,金钱草15g,木香 9g,炒谷芽30g,玄胡12g,14剂。
二诊:2005年6月28日。患者服药后,肝区胀痛明显减轻,稍觉不耐劳,休息后可缓解,胃纳转馨,小溲晨起色黄,日间正常,腑行日一次0,成形。舌色偏红,苔薄白腻,脉细弦。上方加 炙黄芪12g,14剂。
三诊:2006年7月12日。近2周内肝区基本不觉胀痛,偶有隐痛亦能旋即缓解,因工作压力致睡眠欠酣,二便调畅。舌尖偏红,苔薄白,脉细数。复查乙肝五项:HBsAg(+),HBeAg(+),HBcAb(+),HBsAb(-),HBeAb(-);乙肝病毒定量2.53×104copies/ml;肝功能:ALT 50 IU/L,AST 38 IU/L,γ-GT 42 IU/L,TBil 26.1 umol/L。B超示:肝光点略粗,胆壁毛糙。上方加黄连3g,珍珠母30g(先煎),灵磁石30g(先煎), 14剂。
按:《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指出肝病“实脾”谓之上工之举。故陈教授临证中强调治病求本,注重人体内在因素,重视气血化生之源、运湿之枢纽的后天之本——脾胃功能,提出“清热祛湿为主,固护中州为要”的治则,以固“后天之本”。本案主症胁肋胀痛,属肝气郁结,不通则痛,以柴胡、枳壳、木香配伍制香附、玄胡,疏肝理气,行气止痛;乏力纳减,脘痞便溏,属脾胃虚弱,以苍术、白术配伍炒谷芽养胃益脾;口苦舌红,溲黄苔腻,属湿热郁结,以茵陈、金钱草为伍,清热化湿,利胆退黄。二诊、三诊随症斟酌,按需化裁,辨证准确,组方轻灵,药力精专,获效甚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