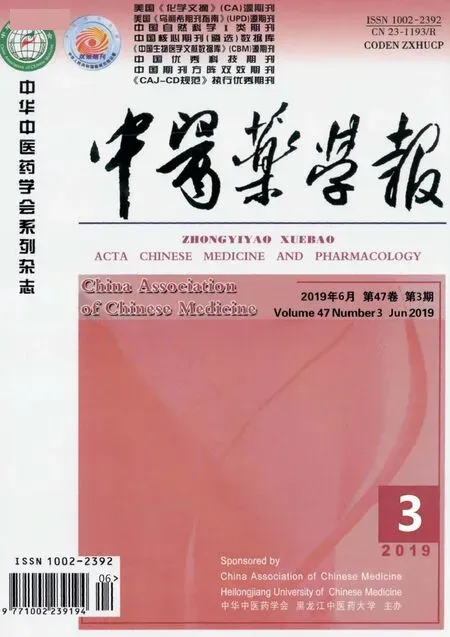陈士铎辨治燥证探究
曹雯,张肖敏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2.南通市中医院,江苏 南通 226001)
燥证是以鼻咽口眼、皮毛肌腠和脏腑出现干燥滞涩的一类疾病的统称。现代医学中发病率与日俱增的干眼症、干燥综合征等疾病,都可归结于中医“燥证”的范畴。由于这类疾病在西医治疗上主要以免疫抑制剂及激素治疗为主,常引发副作用,且取得临床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医则成为了患者寻求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清代医家陈士铎在他的《辨证录》《石室秘录》等著作中对治疗燥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临床治疗燥证有很大的价值,笔者进行整理,现初步总结如下。
1 “四燥”从脏腑论病因病机
陈士铎认可张子和关于燥证的分类,认为燥证应分四类:燥于外则皮毛皱揭,燥于内则精血枯涸,燥于上则咽鼻涸干,燥于下则便溺闭结[1]。他认为燥证的形成与脏腑功能的异常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强调并不是单单由某一脏腑所致,而是多脏腑共同致病。
1.1 外燥责之肺肝脾
陈士铎将皮肤不泽、皮毛拂抑、皮肤飞屑等归为外燥的特征性临床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种:①肺燥: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量少,动则气喘,皮肤失于润泽。《内经》中云:“夏伤于热,秋必病燥”。陈氏认为夏伤于热耗伤肺金,治疗之时不必大补肾水,当以润脾来解肺燥,稍予补肾之剂。他强调脾为肺之母,肾为肺之子,补脾可益肺气,补肾可润肺金,子母相治而相济,肺气更能润泽;②肝燥:因肝藏血,肝得血润而气舒,若肝中无血,则肝燥而气郁,肝气郁滞,犯逆脾胃,脾胃既伤,不可化精微传输于肺,则肺气不生。以两胁胀满,皮肤如虫咬,干呕不吐酸为主要临床表现;③脾燥:脾主四肢肌肉,脾燥的表现以肌肉消瘦,四肢如削,皮肤飞屑,口渴喜饮水等类风消之症候为特征。他认为脾燥的根本原因是胃热。胃热导致胃燥,同时胃热又移热于脾,脾热日久而成脾燥。或是胃热的同时,肝风内动,肝怒挟胃火逃窜,胃火入脾,木能克土,风火相合,脾燥乃成。
1.2 内燥责之心肾
陈氏认为内燥的概念主要是以精血耗竭为核心,他主要是通过男子阴精耗衰举例说明。一类以小便涩痛如淋、早泄为主要症状,他认为主要病因是由于心液耗伤,导致肾水暗耗。在一般生理情况下,心肾相交,心中之液与肾中之精相互浇灌,心静时寂然不动,动则相火代君行令,不敢僭越夺权。如若心火旺,相火也旺,一旦君火衰,相火就向上夺权,就会出现心火欲固,相火欲动;心火欲闭,相火欲开的情况。另一类则是由肾水亏虚所引起以阴器痿弱,见色不举,行房后出现大小便牵痛,甚至二便闭的症状。《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丈夫……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陈氏也认为人至六十之外,肾内水火两衰,不可妄动色心,以养天年。若色心不死,奋勇斗争,肾宫本不多精,又加畅泄,则精已涸竭,无阴以通大小肠,出现二便时牵痛[2]。一旦肾水亏燥到了极至,理论上阴阳两遗,水火两绝,魂魄不能自主,往往精脱而死。但是却出现了精遗后而出血,人未死,此乃阴脱阳未脱之征象,急救治法应大补肾中之水,以水生来留阳。
1.3 上燥
陈氏在描述上燥时,将其分为以口燥和眼燥为特征的两类。他认为口燥与肾、心、胃、三焦有关,眼燥主要与胆和心包有密切的联系。
他强调口干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肾水亏耗、心火燥烈、胃热炽盛、三焦火炽都可造成上燥,具体可阐述为以下四点:①心火燥烈:这一类型的上燥较为常见,多表现为口干、舌上起裂纹或疮点,干燥更甚者甚至夜不能寐。起因大多是因为心火为未济之火,火郁于内,各脏腑之气又不敢相通,煎熬心津,同时肾津不足,不能上交于心,形成既济之火;②肾水亏耗:这类上燥极具特征,患者多出现日间口燥,到夜里口中又复润泽。陈氏认为此类口燥之病,是阴阳两虚之症。日燥而夜不燥,是阴气之虚;夜燥而日不燥,是阳火之旺。口中津液乃是肾水所灌注,患者出现日燥夜不燥的表现,此时阳火大旺但是阴水又未出现大衰之象,能自保真阴,又不可相济其阳,阳火上越,于是出现日间口燥明显。治疗时不必泻阳火之旺,大补真阴即可;③胃火炽盛:胃火炽盛,胃阴耗竭,土成焦土,陈氏将其比喻成“大旱之土”,临床表现为口渴善饮,喜静不喜动,时发烦躁,“见水果则快,遇热汤则憎”[2];④三焦火炽:此类口燥时而渴甚,时而渴轻。他提出“下焦火动,而上、中二焦之火翕然相从,故渴甚;迨下焦火自熄,而中、上二焦之火浮游不定,故时而渴轻”[2]的观点,三焦火盛,多是由于肾中之水不相制约,肾旺而水静,肾虚而水动,无法资水相济三焦,故出现口渴时轻时重之象。
陈士铎认为眼燥一方面和胆燥相关,肝胆皆通于目,属木,木中有汁,则木得水而后养。肝胆互为表里,肝燥而胆燥,二者都主藏而不泻,胆汁藏而目明,胆汁泻而目暗。胆血一燥,就会出现“目痛、眼角刺触,羞明喜暗”的表现。另一方面,目系通于五脏,瞳神归属心肾之精,而心肾之精交于心包,心包属火,肾属水,若水火补相济,瞳神紧小,同时还会出现口干舌燥等表现。
1.4 下燥
下燥主要表现在前后二便。在大肠,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同时大肠濡润需要肾水浇灌,若肺肾皆燥,则大肠燥烈,大便干涩不行,因为肺金所伤,所以特别在秋后症状会更加明显;在膀胱,肾与膀胱唇齿相依,同时肺气的充沛对膀胱气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肺在水道上游,肺肾气足,水流下流顺畅,二者虚,水流多有阻滞;同理,肺肾阴液充足,化生下流才能源源不断,所以治疗时应当补益二脏之气阴;在小肠,陈氏提出大病之后,常会出现小便不出,患者自觉腹胀欲死,这是小肠燥的表现。小肠开合由肾与膀胱共同主宰,同时肾气又主膀胱之开闭,所以大补肾中之水,同时必须要补肺金之气,只有肺金清肃之令才能使水流顺畅,同时辅以利水之品。
2 治法治则
2.1 治燥以滋肾为要,治下燥以润肺为先
陈氏认为肾为水脏,脏腑的濡养都需要依赖肾水的浇灌。他强调“人身之逆,全在肾水之不足,故补逆必须补水,水足而逆者不逆也”[2]的观点。在《辨证录·燥证门》15则医案中13则运用补肾方药,喜用六味地黄丸方加减,以熟地黄的用法为其典型体现。在“水燥之极阴翘不倒案”例中补水以衰火,熟地黄用量达八两;水火两衰阴己痿弱见色不举案例中补水以长火,熟地黄用量只一两,重在知权达变[3]。在《石室秘录》中,关于双治法,他指出了治下燥要肺肾双治,这其中治肺更为重要,肺为清肃之官,肺气充足,肺金濡润,则下焦燥烈浊气才能清扫,肺气旺则水流。
2.2 重视五行生克乘侮
陈士铎治疗燥证时,特别注重脏腑之间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善于从他脏来治本脏。例如治疗外燥时,他提倡“润脾”和“滋肾”为大法,脾为肺之母,肾为肺之子,补脾以益肺气,补肾而不损肺气,子母相治而济,肺气才能更加润泽,拟用子母两濡汤:麦冬三钱,天花粉一钱,紫苑一钱,甘草三分,苏叶五分,天冬三钱,熟地五钱,玄参三钱,丹皮二钱,牛膝一钱[2]。如肝燥之病,肝中无血,则肝燥气郁,犯逆脾气,出现胀满、呕吐等表现,但是治疗时若仅仅通过润肝,则疗效欠佳,陈士铎评价这种做法为“可少润与目前,不能久润于长久”。其原因是肝燥是由于肾亏,滋肝必补肾,才能肾濡肝亦濡。
2.3 顾护脾胃
陈氏治疗燥症时,运用濡润之药时,特别注意顾护脾胃。脾喜燥恶湿,即便是脾燥也不过用濡润之剂,只有脾土健旺,才能易受润泽,单纯濡润,脾胃受损,内外交困,更不易治燥。
2.4 强调夏季养护
《内经》云:“夏伤于热,秋必病燥”。夏伤于热损耗肺金之气,根据肺的生理特性,肺主升发肃降,司呼吸,与大肠互为表里,能调畅周身气机,通调水道。肺金受损后,入秋时会出现咳嗽咳痰不已,皮肤不泽或大便秘结或小便不通,点滴不出等临床表现。所以在夏季,他特别强调不要过分受热,注意养生与防护相结合。
3 病案举隅
一患者燥证,舌干肿大,溺血,大便又便血不止。陈氏治之,方用兼润丸:熟地一两,元参二两,麦冬二两,沙参二两,车前子五钱,地榆三钱,生地五钱,当归一两,白芍一两,水煎服。服一剂后症状减轻,二剂血止,便有生机也[4]。
按:陈士铎认为此患者夏季因感暑热之毒,至秋则燥极,肺金损伤,大小便热极而出现便血。理论上应以治血为原则,但是他认为若治血,便血不止并不会改善。反而燥证会更加严重。从治燥的角度出发,以地榆清火,车前子利水,火清水利,再加补血妙品,不必治血而血自止。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论述陈士铎治疗燥证的学术思想总结,其对于燥证的辨证和用方用药别具特色,方药精简。从脏腑出发辨证“四燥”,治法上重视肺肾双治及巧妙利用五行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