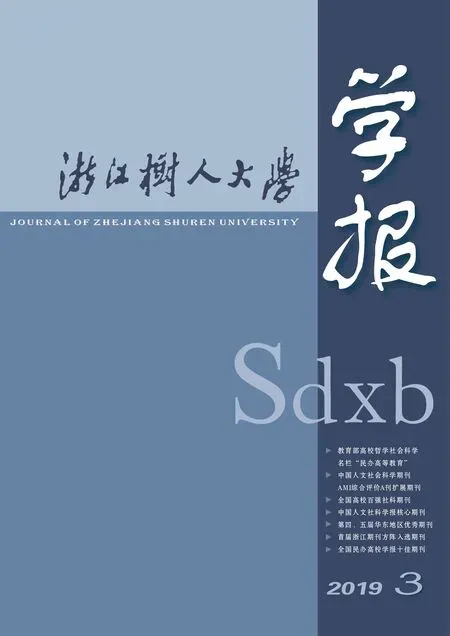盈盈的“力”:陈敬容《盈盈集》的生命意涵
徐建华 邵 红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陈敬容是“九叶派诗人”之一,但与“九叶诗派”整体上的现代主义诗风相区别,她的诗歌深深植根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并以此为立足点来把握世界和人生,由此呈现出鲜明的浪漫化个体风貌。《盈盈集》是陈敬容早期的作品,1948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935—1945年的诗作共71首,分为“哲人与猫”(1935—1939)、“横过夜”(1940—1945)和“向明天瞭望”(1945)三辑。关于“盈盈”一词的含义,可作如下说明:在同年出版的《中国新诗》第二集“黎明乐队”中,陈敬容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七章》的“按语”(引英译本序)中写道:“只有他才去倾听事物内部的生命,而突破浮嚣的近于疲乏的议论,用无比的爱与盈盈的力来抒说他自己的恐惧、警觉、担忧与抗拒,只有他才能在这个矛盾错乱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的完整,而从充实的人性里面提炼出了最高神性。”[注]陈敬容译:《里尔克·诗七章》,《中国新诗》第2集“黎明乐队”,森林出版社1948年版,第19-30页。这段文字可说是陈敬容整个生命历程与诗歌创作的夫子自道。值得珍视的是,《盈盈集》恰是里尔克式的生命过程另一种感性形态的微缩,表现出在一个特定阶段,诗人从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忧惧到生命的自我发现、进而走向对生命自由的渴望的过程。可以说:“盈盈”即“盈盈的力”。黑格尔说,人的生命是一个生命的内在之“力”持存流动、上升的回环式的发展过程,那么,《盈盈集》最终成为陈敬容个体生命形态的一个环节,是她始终以个体生命体验为立足点的诗歌创作以及自我扬弃的生命整体构成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生命的孤独体验
《盈盈集》的第一辑“哲人与猫”收录1935年至1939年作者创作的11首诗歌,其中前5首《十月》《夜客》《静夜》等创作于北平,后6首《断章》《哲人与猫》《窗》《遥祭——献给母亲》等写于成都。这段时间,陈敬容经历了感情的失败,备尝流浪的孤单。1932年春天,15岁的陈敬容遇到了她的代课老师曹葆华,两人相互吸引、互诉衷肠。1934年,他们一起离开四川乐山,来到北京。17岁的少女为了恋人和心中的梦想,背叛家人来到陌生的城市……两人感情的日渐平淡使陈敬容备感痛楚而无所适从。1935年春,即她来北平的第二年,写下《十月》:“纸窗外风竹切切:/峨眉,峨眉,古幽灵之穴……/是谁在竹筏上/抚着横笛,吹山头白雪如皓月?”[注]②③④⑤⑦⑧陈敬容:《盈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7页;第11页;第12页;第8页;第14页;第14页。诗中的“窗”“重帘”“晚风”“风竹”“峨眉”“横笛”和“白雪”等意象,仿佛少女青春生命的“力”的表征,“晚风幽咽”“风竹切切”……如故人一般纷至沓来,成为诗人表达思乡之情的镜像物。诗人的心无所依托,便在熟稔的乡情中寻找慰藉。
感情的变故使诗人心中的愁思更加深重。《静夜》写于1936年秋的北京:“一枕记忆,/白色的月色;/风无告地来去,/丝丝的,/草的叹息”,诗人无法忘怀家乡的一切,“丝丝的,草的叹息”中“草”比拟自己流浪在外就如同这个世界中的草:低等,不被在乎,没有存在感。诗的最后:“陌生人敲叩着陌生的门,在长巷里。/(听我的门上一声沉寂)”[注]②,除了自己以外,“他们”都是陌生人,有自己的热闹与归属,诗人什么也没有,她想象中的“夜客”,只是“一只猫,一个甲虫”,“一声沉寂”表现出心灵彻底的绝望。诗人主体内部生发出来的、不绝如缕的丝丝哀怨——生命内在之“力”,转化为客观物象“草”“静夜”等,诗人在认识和把握客观物象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促使其达成与自身相一致的经验状态,即客观物象成为诗人生命情感的承载物,“草”“静夜”和“长巷”等意象自身并不具有生命的独立性,而成为诗人生命镜像化的投射物,被赋予了主体强烈的情感色彩。
《窗》于1939年4月写于成都,是一个少女初恋的真实记录。陈敬容初遇才华出众的清华毕业生曹葆华时,被他深深吸引,完全沉浸在爱的世界里。当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平淡时,她写下了“我将怎样寻找/那些寂寞的足迹,/在你静静的窗前;/我将怎样寻找/我失落的叹息”[注]③这样的诗句。这种情感的伤痛只有靠诗人自己来抚慰:“空寞锁住你的窗,/锁住我的阳光,/重帘遮断了凝望;/留下晚风如故人/幽咽在屋上。”[注]④独特的意象蕴含着强烈的主观感受,无疾而终的初恋注定是痛苦的,感情失败的孤独感仿佛充斥着她的整个生命。
陈敬容与曹葆华的感情渐行渐远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迅速烧到北京。她再一次出走北京,回到大后方成都,与当时已去黄土高原的曹葆华分道扬镳。《断章》即于1937年秋写于成都:“我爱长长的静静的日子,/白昼的灯光,夜晚的灯;/我爱单色纸笔,单色衣履,/我爱单色的和寥落的生。”[注]⑤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注]杨朝军:《〈断章〉的衔接特征与艺术阐释》,《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8期,第147页。其重点不是“风景”,而是两个看风景的人之间戏剧性的关系。陈敬容的诗叙写的恰是两个“看风景的人”之一,另一个“看风景的人”已成为梦中人。“白昼”“灯光”“夜晚”等意象写尽了时光的漫长、人生的单调以及诗人内心的寒冷,“单色纸笔”“单色衣履”“单色的和寥落的生”中“单色”一词连续出现,灰暗的色调组合构成落寞的情绪世界,对应着诗人早年生活的迷茫感受,其中“我爱”一语更表现出她虽迷茫苦痛却不得不生活下去的悲哀。《盈盈集》第一辑中几乎每首诗都充斥着孤独、痛苦的意味。早年失母更是给陈敬容留下了深深的痛,她在《遥祭》中写道:“忧患同沉疴/抖着滞重的铁链,我的祭烛/寂寞地颤动,/泪和着濛濛的雾/向远山消融。”[注]⑦当年,陈敬容和曹葆华私奔被抓回来关在小屋子里时,家人都在训斥她,只有母亲给予了她真正的同情和理解,我们能从诗中“墓草青了黄了”和“我,一只孤鸟”[注]⑧这样的语句,看出她失去母亲的心痛和孤独。
从诗学意义上说,这一阶段诗人耽于自我的孤独体验,却无法从孤独与忧惧中解脱出来,去找寻生命的意义。她还不能意识到:主观情感的投射或外化所设定的“物性”,必然带有某种抽象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表面上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一瞬间。”[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由此可见,诗人通过主观情感的投射来把握事物、确证自我,只能是一瞬间的事,最终将归于空虚与沉寂。
二、生命的自我发现
《盈盈集》的第二辑“横过夜”收录陈敬容写于1940年至1945年的诗歌,共34首。其中《风夜》《给杏子》《横过夜》《紫色的毛羽》《骑士之恋》等18首写于兰州,《珠》《圈外》《在风砂夜》《薄暮》《归属》等10首写于临夏。这一时期诗人的创作与其不幸的婚姻是分不开的。1939年,陈敬容与回族诗人沙蕾结识,并很快进入热恋,数月后走到了一起。为了爱情,两人共赴沙蕾的老家兰州,一住就是5年。
《风夜》写于1942年:“你寻觅什么/在屋上疾疾地走?/你失落了什么,/向星群呼吼?//静静吧,静静吧,/黑猫去了,/它眼中的火/在颤抖。//你失落了什么,/在窗前疾疾地走;/你寻觅什么,/向暗角招手?//来呵,我的朋友,/将黄叶覆上我的脸,我的手;/听那呼唤……近了,那呼唤;/听呵,听呵,我要走!”[注]③④⑤⑥陈敬容:《盈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第32页;第23页;第23页;第30页。诗人无法挣脱痛苦的回忆,但仍在苦苦地找寻自我,“疾疾”和“呼吼”写出了诗人想要尽快摆脱过去、寻找新生命的急切心情。再如《在雾中穿行》:“我们在雾中穿行/在雾的深林。//那呼唤,/那井://一些远代的声音/远远地回应。//亲爱的,薄暮已栖息在/你迷失于雾的眼睛。”[注]③她像被雾迷住了一样,看不到方向,但仍在摸索着、追寻着。
再如《给杏子》:“菊花将开放,/菊花将萎去;/去时间的岸边/筑一道堤。”诗人想让时光停滞,探索其可能的方向,却再一次陷入迷茫:“我将伴着八月走向你,/我们静静地听/九月的黄昏的雨。//菊花将开放,/菊花将萎去;/去,去时间的岸边/筑一道堤。”[注]④美好的事物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摧残,诗人渴望着有什么可以抵挡住时光的流逝,让自己寻找到生命前行的方向,但是,等待她的依然是人生的困境。她只能对杏子说:“去我们的堤边哭泣,/为那青春,为那爱情;/去,去那遥远的海洋找寻……”[注]⑤青春和爱情随着时间去了,一切将不复返。
诗中大量问句的使用,是诗人寻找自我的一种表征。写于1942年6月13日夜里的《横过夜》是这一辑中重要的一首。诗人感觉到有什么在扰乱过去的“梦的足迹”,透过忧郁的夜的河流,她的生命露出些许微明:“夜草战栗,/夜风荡漾,/白的月光/在睡去的眼上。//什么忆想/滞涩着你的呼吸?/哪一种芳香/扰乱你梦的足迹?//……一些冰,一些冰,/下落的阴暗的云;/但你有一个环吗,/一个环,满缀着流星?//苍白的手/苍白的心——//月影横过/睡去的眼睛,/横过夜/与夜的寂静。”诗人倾听着“夜草”的“战栗”,“夜风”的“荡漾”,“白的月光”浸润了诗人的“眼”、诗人的梦。“白的月光”“阴暗的云”“苍白的手”“苍白的心”等都呈现出单一的色调,表现了诗人挥之不去的淡淡迷惘。但是,整首诗已不像第一辑里的诗歌那样,显现为同一情调下的意象的铺陈和变幻,即客观物象仅仅作为“抽象的确证物”,因诗人主体情感的变换而带上不同的色彩。在这首诗中,诗人在强调主体情绪的同时,自觉地运用了一组客观意象,通过意象的组合产生“力”的推进,由此升华出一种气氛,在情绪的流荡、低回里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寻找:客观物象的存在不是为了符合主观情感的需要,而是显出其独立的、鲜活的生命的“力”之本质。
当诗人深入客观物象生命的同时,会返回自身并激发出诗人主体新鲜的生命觉识——“无比的爱与盈盈的力”,进而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对生命的追问与思考。再如《紫色的毛羽》:“在暗夜里/静静地开/静静地落——//温柔的,温柔的絮语?//让年华流去,/让欢乐流去,/让风带着它的哀怨/向夜流去……//幽静的,幽静的爱侣!//营火辉耀着/你们的凝睇,/营火辉耀/如一条小溪。//为什么你们哭泣,/这样无声地哭泣?/什么在你们肩上抖动着呵,/在林头,在草野/紫色的,紫色的毛羽!”[注]⑥诗中疑问句的大量设置表明:她极力抛开早期独语式低沉的情绪状态,努力在倾听客观物象生命的基础上重新找回自我。在《创造》中,她这样写道:“有些微弱的低音骚扰在辽远的天空,/有些影像隔着日和夜翩翩舞蛹;/近了,这是那步声跫跫,在我心际,/一些云,一些树/一些拱桥……//伴和着我生命的浪潮/你们流来,你们流来!/……我在你们的哀乐中浸渍而抽芽,/而开出一树繁茂的花。”
《归属》(又名《水与海》)体现了诗人对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思考:“不息的流泉呵,可怜的心,/你寻觅着什么样的依归?/海,汹涌的大海,/我听见你召唤的涛声——//一切江河,一切溪流,/莫不向着你奔腾;/但它们仍将是水,/是水!它们属于/你,也属于自身。”诗人渴望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前提下,从群体中获得新的力量的支撑。生命视角的调整,促使诗人开始寻找具有突破性和冲击性的生命力量。《骑士之恋》写于1944年,那些日子陈敬容很少写诗,对爱情重拾信心的她并没有在这段婚姻里得到幸福,于是诗人有了这样的疑惑:“她可还能快乐地高飞,/我的骑士?她可依旧/在四月的阳光下歌唱?//不呵,她再也不高飞也不能歌唱,/只在我的园中默默地低翔。//那么,请你回到你的园中,/让我在这儿独自眺望,/看白云自在地飘航……”[注]②陈敬容:《盈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第67页。陈敬容的生活虽然不幸,但她并没有放弃重新寻回自己、开始新的生活的渴望。在《风暴》中,她不再表现出无奈的忧惧:“风暴正在卷来/正在卷来,/当月光下谁叩着船舷/说九月的海水太平静了。//梦中也有一片茫茫的水和天;/在遥远的水天一线/永系着对于无数的/陌生事物的焦渴的怀念。”
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任何人都无法停顿,陈敬容就是在经历过人生不停的折腾之后,静下心来,开始关照自己。自己是谁?难道就要这样一直孤独痛苦下去吗?这一阶段诗人发掘到一个与此前耽于孤独状态的自己形成很大反差的另一个自我,诗人已幡然醒悟并试图找寻真正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开始微微呈现它原本该有的色彩。
三、生命的自由律动
《盈盈集》的第三辑“向明天瞭望”收录1945年4月至10月的诗作共26首。对陈敬容来说,1945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离开了暴戾的“骑士”,从兰州的家里出走,于同年5月回到抗战胜利后的四川,投奔在重庆郊外小镇教书的本家兄弟,在小桥流水的磐溪担任小学代课教师。结束了不幸的婚姻生活,陈敬容如获新生,激情迸发。5月9日至5月13日,诗人写下了《自画像》《不开花的树枝》《漫游》《追寻》《假如你走来》《向明天瞭望》和《新鲜的焦渴》等诗作,开始发现自我,对自己和世界都有了新的认知。
经历前两个阶段的苦难后,陈敬容的诗歌从个人生命的迷惘和困顿的抒写开始转向对社会现实和宇宙人生的关注。这一时期,她的诗作充满突围式的、流动的力量感,以《律动》为例:“水波的起伏,/雨声的断续,/远钟的悠扬……//和灼热而温柔的/你心底的跳荡——//谁的意旨,谁的手呵/将律动安排在/每一个动作/每一声音响?……//谁的意旨,谁的手呵/将律动付与了/每一个‘动’的意象?//宇宙永在着,/生命永在着,/律动,永在着;//而我心灵的窗上/每夜颤动着/你,我的永恒的星光!” 诗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律动息息相通、浑融一体。从中可以看出,她拥有了对于社会现实和生命价值稳定的评判标准。
第三辑中的诗作,如《遗留》《烛火燃照之夜》《自画像》《向明天瞭望》《新鲜的焦渴》等,深深植根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充满了生命的“新鲜”与“焦渴”的意味。陈敬容的不平常遭遇,使其诗歌饱含着对坎坷命运的忧惧。可是,在重新认识生命之初,他的诗歌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对明天的向往,如《遗留》:“刚刚溜过的这一瞬间。/我也将它往后投掷了;/我还要抛掉/所有将成为过去的/极短暂的顷刻。//于是我立在/一只疾驶的船头/顺流而去——/看着每一个旧的我,/每一个属于‘过往’的我/缄默地被遗留给/一些终古屹立的岩石。”[注]②陈敬容认识到过去的不足,就连“上一秒的自己”,她也想丢弃。在《烛火燃照之夜》中,她希望“从纱帘内燃照的烛火”能“辉耀我心灵的幽室”,认识到只有真正投入现实世界,倾听生命的呼唤,才能真正确证自我、表现自我。
《自画像》描绘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或痛苦来锻炼——你需要火。带着感谢的叹息/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我爱生命,’你说/‘连痛苦也爱。’”[注]②③④⑤⑥⑦⑧陈敬容:《盈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第85页;第89页;第65页;第65页;第72页;第90页;第91页。诗人已经开始直视过去的痛苦经历,把它们当作是生命的一部分。诗中,她把自己比作很多事物:“一支温婉的烛火”,静静地燃烧,不卑不亢,希望平静地过生活;“一只小小的青虫”,虽然渺小,但能“张望碧蓝的海,碧蓝的天,惊讶于阳光的七色流彩”,“小小的青虫”“碧蓝的海”“碧蓝的天”等意象已不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单向投射物,正如《野火》中所说:“给我一只长长的竹管吧,/我要从宇宙的湖沼/汲取一个/最中心的波浪。”诗人意识到只有真正融入客观世界,在主客体生命的交替转化、融汇合一中,才能把握那个爱的世界,才能有盈盈的生命力。诗中写道:“让逸乐流来,/让痛苦流来。/红色的欢笑,灰色的眼泪,/都变成一些雪白的音符:/让它们流来,/向你流来。//……一切生命的浪潮在奔流,/伴和着你自己生命的潮浪;/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交织成绮丽的虹彩,/向着你飞扬。”这意味着,每个人与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宇宙生命之流的表现,诗人的“焦渴”在于如何才能真正汇入宇宙化的生命之流。
陈敬容在《追寻》中写道:“流云的情意,/流云的歌音,/和你,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的闪亮的生命。//……//永远地飞行,/永远的追寻,/你的翅膀日渐轻盈;/而你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更新。”[注]②她渴望着自己能告别过去,以“闪亮的生命”面对未来。在《向明天瞭望》中写道:“以最大的热力燃烧着,/人家说我很快就会死去;/但死亡能够带走什么,/当我甚至在坟墓里/也要用沉默继续我的歌唱?//是呵,朋友,沉默,是呵;/我有过沉默,我有过,/比死亡更可怕得多;/因为那些时候我是/被淹没在忧患的长河……//我用眼睛,用我的心/向每一个明天瞭望。”[注]③这些诗透露着一个明确的信息:陈敬容已跨越“第一辑”中忧郁的长河和“第二辑”中找寻的困惑,她要“用眼睛”“用心灵”,在“不断的燃烧中”向着明天瞭望。
在第一辑的《遥祭》一诗中,陈敬容还只是一只失去了母亲的“孤鸟”,在异乡孤独地生活着,生活的坎坷让她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在《横过夜》中,她是经历了爱情挫折的“倦飞”“倦鸣”的鸟,已厌倦了生活;在《骑士之恋》中,她变成了一只“再不能高飞也不能歌唱”的鸟,但仍渴望着“让我在这儿独自眺望,/看白云自在地漂航……”诗人开始重拾自我,试图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第三辑的第一首诗《飞鸟》写道:“负驮着太阳,/负驮着云彩/负驮着风…… //因此而更轻盈;/当你们轻盈的翔舞,/大地也记不起它的重负。”[注]④太阳意味着光明,诗人想“在高空里无忧地飞翔”,在阳光下获得光明和自由,这才是陈敬容所向往的,终于在“初霁的蓝天”中,她看到了自己:“你们带来心灵的春天,/在我寂寥的窗上/横一幅初霁的蓝天。”[注]⑤过去的陈敬容是寂寥孤独的,现在她确定了自己所想要的,必然会鼓足勇气去追求。“窗”是其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以前的“窗”是“寂寥”的,现在诗人通过“窗”看到了蓝天,“初霁”一词表达了诗人渴望抛弃过去、重活一次的热切心情。她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坎坷经历,而是向着更加广阔的世界进发。
在《野火》中,诗人写道:“新生的人类呵,/我热烈地祝福你/有更美丽的生长和变……”[注]⑥诗人祝福新的生命,诗句中的省略号表明她对新生命的无限遐想。再如《流溢》:“当生命的湖沼如此满注/时时要向外流溢”,却“带给我迫切的创造的热情”,诗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独地舔舐自己的伤口,她开始突破自己,准备着投入新的世界,这在《新鲜的焦渴》中也有很好地体现:“但是我更怀念/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希望中黄昏永远像黎明,/有太阳,有飞鸟,/有轻风拂树的微颤。”[注]⑦诗人虽然怀念过去的日子,但是她更愿意展望未来,用“怀念”一词来修饰“未来”,别有意味,因为诗人盼望着,未来这些不可知的日子可以变得明亮起来,变得令人怀念:“我焦渴着。通过了/多少欢乐,多少忧患,/我的灵魂不安地炽燃;/我厌倦今日,/厌倦刚刚逝去的瞬间——/甚至连我的焦渴我也要厌倦,/假若它已经不够新鲜。”[注]⑧陈敬容一直在渴望“比‘新鲜’变得‘更新鲜’”,渴望不断地超越自己。从《飞鸟》《烛火燃烧之夜》《野火》《追寻》《新鲜的饥渴》《铸炼》《风暴之后》等诗题中,读者可以看出:诗人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忧郁的小姑娘,她在寻找一种突破:既弹唱着个人的忧乐,又渴望着新的人生,这使其诗歌呈现矛盾所凝聚的坚韧与张力,如《边缘外的边缘》:“哪一个港岸/我将去投宿?/什么花将飘落在我温暖的水波?/风啊,雨啊,假若/你们向我发怒,/从你们发怒的琴弦上/也能弹奏出燃烧的颂歌。//……在黑夜的堤外/我有一片年青的草原,/在那儿露珠带着新鲜的战栗;/它铺展着有如/一个绿色的希望,/温柔地延伸/向边缘外的边缘。”
《盈盈集》是陈敬容第一部诗集。作为一个从不怀疑生命真实的浪漫主义者,她对个体生命所具有的力度和强度抱有充分的自信,诗人正是借助强有力的“创造力”来协调现实处境与自我“焦渴”之间的冲突,以一系列灌注着生命热情的鲜明意象,在快节奏的推进中,强化诗歌的力度,突破生活的表层而获得人生体验的升华。这种升华并非里尔克式的冷静的思考,而是用一连串激情的“力”之物象即通过诗人主体与客观物象之间生命力的交互转化来推动,在急速的奔涌和冲撞中捧出生命“盈盈”之水花。诗人正是凭借具有冲击性的生命的力量,超越时间和死亡,将个体生命的律动融入宇宙整体的无限中。《盈盈集》所显示出的新鲜的渴求与超越的精神,作为诗人生命的一个阶段,已成为诗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贯穿她整个生命旅程,成为诗人探索人生与艺术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