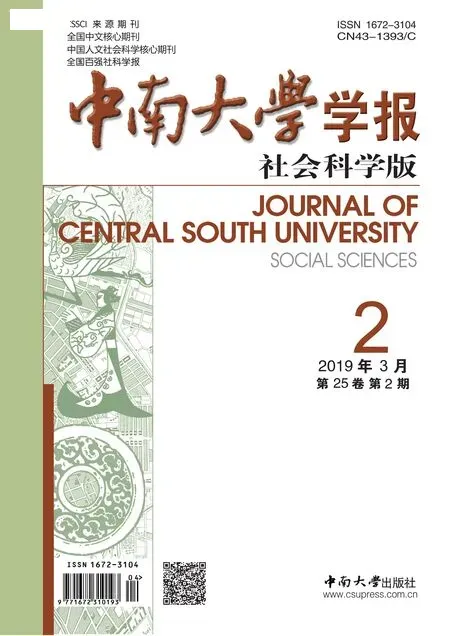贡布里希对柏拉图模仿说的诠释与批评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34)
艾布拉姆斯在其名著《镜与灯》中主张,西方现代艺术受浪漫主义美学传统的影响,并不想模仿自然,而是要表达情感。如果我们追问这位浪漫主义美学的研究者,以及追问现代艺术的诸位拥护者,西方古典艺术是否以模仿自然为鹄的,他们也许会表示同意,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希腊哲学家们有关艺术模仿现实的反思。“镜”与“灯”的比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在艾布拉姆斯看来,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美学观念其特征可喻之为“镜”,因为心灵和艺术是反映外部世界的镜面;而浪漫主义美学观念则应被喻为“灯”,因为心灵是发光体,外部世界只有通过心灵情感的照耀才能显现为艺术作品。[1](31-79)自此,“镜”与“灯”的比喻和对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关于西方艺术发展的经典表述。
也许在美学领域再没有哪一种观点比柏拉图的模仿说影响更加深远了。贡布里希称,模仿说出世之后,哲学家们就“一直忙于对这个定义加以肯定、否定或限定”[2](67)。而著名的艾布拉姆斯只不过占据模仿说这张大图的一个小角落而已。然而,贡布里希的研究却向我们表明,以模仿说为地图理解艺术,哪怕是理解以写真为目标的希腊和文艺复兴艺术,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无法窥见艺术和世界的真实关系。贡布里希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柏拉图模仿说的立论意图,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史家的敏锐眼光;而他对模仿说的批评则向我们揭示了艺术与现实双向生成的关系,体现了他对哲学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洞察。
一、柏拉图模仿说的内在问题
提及模仿说,几乎无人不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艺术模仿自然的经典诟病。借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把关乎事物的技艺分为三类:应用、制造和模仿。而画家、雕刻家以及诗人所擅长的技艺只有模仿这一项。所谓模仿就是“拿一面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3](66),以便得到各种事物的外形或虚像。由此可见,艾布拉姆斯的确是柏拉图传统的继承者,“镜”之喻的源头便在《理想国》。不过,艾布拉姆斯冷静陈述的古典美学特征却是柏拉图激烈反对的东西。柏拉图是反艺术的。虽然他写下的每篇对话都极富诗性,虽然他在字里行间向我们展现了他极高的艺术悟性和品味,但他确实主张应该把艺术家和诗人统统赶出理想国。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伦理诉求、教育理念、审美心理等多个方面来思索和探讨柏拉图反对艺术的理由,但所有这些理由将汇聚到一点,即柏拉图把艺术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看作是制造镜像幻境的不实之举。
对于诗人,柏拉图尚留三分情面。他只驱赶追随荷马专擅模仿的诗人,并留下话说,如果以后有人能证明这种诗的益处,他还是愿意迎接诗人们返回理想国。[3](83-84)但对于同时代的造型艺术家,柏拉图驱赶的信念却毫无松动的迹象,他们被逐出“理想国”的命运似乎无以转还。因为对柏拉图而言,以写真为目标的希腊画家和雕塑家是镜像的直接追随者,是虚幻影像的制造者。诗要以假乱真还需要调动听者的想象力,那些逼真图像则直接就具有混淆视听的能力。《理想国》里有著名的三种床:第一种是自然中本有的床,这种床最真实,是永存不变的,即“理念的床”;第二种是木匠根据床的理念制造的现实的床,“制造的床”虽达不到第一种床的完美和不朽,但分有了第一种床的真实性;最不真实却又极富欺骗性的床是画家根据现实的床画出来的“第三种床”,它仅是一个表观或者形相罢了。[3](67-69)
在贡布里希看来,柏拉图的模仿说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正是因为他的论述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写实艺术的第一感觉。为了表明柏拉图的这一论述与我们日常体验的直接关联,贡布里希特意撇开了柏拉图颇显玄妙又极富争议的词“理念”,转而使用日常语言重述了柏拉图有关三种床的论述。如果我们要向木工定购一张床,木工必须明白床这类东西是什么,即他要知道床的概念。但如果一个画家要画床,他就不需要知道他画的东西分属那类,他只要把现实的床描摹下来就成。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就是因为它与概念或柏拉图所称的“理念”相隔甚远。写实艺术一般来说要对景写生,图像模仿现实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境下,贡布里希争论说,柏拉图对三种床的排序不能成立,那就是我们不向木工定床,而向设计师定床,让木工照着设计师的图纸来制作。这样一来,画家就要被请回“理想国”了,因为是画家而不是木工在参照“理念”工作。[2](70)
先设计再制作的情境和艺术写生的情境一样自然和频繁,以至于柏拉图传统的某些继承者们声称艺术并不模仿现实,艺术直接模仿理念。艺术家由此获得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艺术家可不是普通人,他们是具有神圣禀赋的天才。声名远播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修正柏拉图的模仿说来维护艺术和艺术家的尊严的。然而,在贡布里希看来,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心心念念追寻的理念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原型或共相,而是艺术家借以分类和记录其视觉经验的图式。这些图式是艺术家们从前辈艺术家那里习得的,虽然它们是艺术创作必不可缺的起点,甚至在某个阶段会成为艺术家心目中的典范,但它们并非永恒不变。艺术家的创作始终遵循“图式加矫正”的节奏,因此,艺术直接模仿理念这个曾让无数艺术家为之激动和兴奋的学说,这个统治学院长达300年之久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其实是“以自我欺骗为基础的”,不过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哲学光环”罢了[2](113)。不仅如此,贡布里希还提醒我们,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永恒理念的主张正是后世艺术哲学和象征符号哲学陷入纷争的关键所在,因为只要我们承认事物的类别或概念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就不得不把艺术图像当作“虚像”[2](72)。然而,如果我们跟随贡布里希质疑的脚步继续前行,就会发现柏拉图所提出的“现实”与“虚像”、“制作”与“模仿”这些对立根本难以成立。
柏拉图为了贬低造型艺术家的成就为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即画缰辔的画家只能模仿缰辔的外观,他并不了解缰辔更不能制造缰辔。[3](74)但贡布里希却就此提出异议:画家一定不了解缰辔本就可疑,雕塑家为大理石马配上金属制缰辔就更谈不上是模仿缰辔的外观了。如果一个雕塑作品表现了一个躺在床上的人,那么这个床是现实的还是模拟的?这个雕塑家是床的模仿者还是制作者?一张放在商店橱窗的真床被视为床的符号,舞台上床的道具则被看作是真床。家具目录里的各种床既可表示此类产品被设计好了,准备接受订购,也可表示此类床有现货供应。而字典中床的图像则被视为图像符号,用以传达床这个名称的意义。[2](70-71)面对贡布里希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不禁感叹,柏拉图把床归为三种,理解起来倒还简单,怎么贡布里希反倒生出这许多的麻烦。然而,贡布里希的意图本就是为了解构柏拉图在制作与模仿、现实与形相之间所划出的那种鲜明而固定的界限。因为实际情况是“人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事物的世界;人的世界也是一个象征符号的世界”[2](71),制作和模仿之间、现实和虚像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甚至相互转化的情形。贡布里希的这些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层次的过渡和转化,并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生活世界并非坐落在制作与模仿、现实与虚像这两极之上,而是坐落在由这两极构成的谱系之中。
贡布里希对柏拉图的著作极为熟悉和看重。他的成名作《艺术与错觉》涉及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并且所及之处都极具眼光;他的长文《错觉与艺术》开篇就明确声称自己是遵照怀特海的教导,整篇文章就是想给柏拉图的一段文字做个注脚。[4](92)贡布里希曾谈到自己阅读柏拉图对话的体会,他说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够在场,好把与苏格拉底对话的那个托儿推到一旁。他讲这个体会的时候,谈的正是《克拉底鲁篇》中有关图像是真实事物的模仿还是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一问题。在贡布里希看来,虽然有时你会觉得苏格拉底的对谈者受骗上当实在太过容易,但若当真把自己放在对谈者的位置,却又发现想彻底驳倒苏格拉底并非易事。[2](263)柏拉图的模仿说当然是错误的,但这是有着睿智和极高洞察力的大哲的错误,是一个需要解释和说明的错误。贡布里希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柏拉图提出模仿说的缘由,也揭示了为什么对同时代的造型艺术家柏拉图竟会生出如此强烈的愤懑与不满。
二、模仿说与希腊艺术的革新
今天我们见惯了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以逼真为目标的绘画和雕刻,因而觉得艺术模仿自然是一个简单而显见的论断。然而,贡布里希却向我们指出,柏拉图谴责艺术的激烈态度恰恰提示我们写真这种艺术追求在希腊乃是一桩新鲜事儿。[2](84)和其他艺术创造一样,希腊艺术并非凭空而来,它起步于对埃及艺术图式的矫正和改造。然而,人们之所以称希腊是奇迹就是因为希腊人并不满足于发展其所继承的东西,他们使所有继承之物获得了崭新的样态。仅仅不过两百多年的努力,埃及的艺术图式在希腊艺术家手里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柏拉图强烈指责的“乱真之作”。
贡布里希恰切地把希腊艺术家对埃及图像的改制比做《睡美人》中王子的一吻,正是这一吻使图像艺术从埃及的概念化风格转变为我们所熟悉的叙事性写真图像。而触发这一吻的动力之源则是荷马史诗中独特的戏剧性唤起(dramatic evocation)①,戏剧性唤起促使图像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引发了图像形式的革新[2](93-94)。描绘于金字塔内部的那些埃及图像,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追求永恒,这些图像就是一些图画文字。艺术家从最富特征的角度描画人和物,以便它们获得永恒的存在。柏拉图对制作与模仿的区分无论如何都难以用来解释埃及的艺术图像。埃及的雕刻家则被称为“Ka”,是“代用之头”的制作者,因为埃及人深信图像是带有魔法的制作物,而不是什么现实事物的虚像。然而,这些图像传到希腊人手中就变成了要再现和匹配特定时刻、特定场景眼之所见的模真之作。
希腊艺术家希望在埃及古老的图式中发现叙事的戏剧性场景,于是开始不遗余力地对埃及图像进行矫正,直到图像能够取得栩栩如生、甚至欺骗眼睛的效果为止。从征服空间到表现光线,从塑造立体自然的人物外形到刻画人物的心灵,希腊艺术家们不断进行获取逼真视觉效果的探索和实验,终使物像获得审美自由,而不再受制于埃及艺术“实用的上下文”②。换言之,希腊人开始把绘画和雕塑作为美丽的物像来欣赏,而不是将其视为可畏的或灵验的现实替代物,因而也就第一次获得了柏拉图模仿说中所设定的艺术观念。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叙述就是从图像功能引起形式转变的角度入手,向我们阐述希腊艺术革新的一系列连锁反应。[2](93-102)而贡布里希反复提示我们,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恰好处于这场以写真为目标的狂飙突进运动的顶峰。
不过,身处这场艺术革命巅峰的柏拉图并未感到欢欣鼓舞,相反,他带着浓浓的怀旧情绪撰写了反对现代艺术的宣言。在《理想国》中,他通过模仿说对作为图像的第三种床极尽贬损,而在晚年撰写的《法律篇》中他更是明确声称:是永恒不变的埃及艺术而不是追求革新的希腊艺术才是艺术的典范。“很早以前埃及人好像就已认识到我们现在所谈的原则:……把样本陈列在神庙里展览,不准任何画家或艺术家对它们进行革新或是抛弃传统形式去创造新形式。一直到今天,无论在这些艺术还是在音乐里,丝毫的改动都在所不许。你会发现他们的艺术品还是按照一万年以前的老形式画出来或雕塑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绝非夸张——他们的古代绘画和雕刻和现代的作品比起来,丝毫不差,技巧也还是一样。”[5](279)那么柏拉图为什么推崇埃及艺术呢?他反对现代艺术仅仅是因为一种怀旧情绪吗?
在贡布里希看来,柏拉图提出模仿说是由于希腊艺术革新带来的图像描摹现实的新追求,而他对模真图像的谴责则体现了他对新图像所带来的新问题的敏感。柏拉图对这些逼真的图像可谓疑虑重重。首先,他担心采用短缩技巧的图像只能再现事物的某个侧面,因而会失去埃及艺术所具有的示意图式的完整性。“比如说床,可以直看,可以横看,可以从许多观点看。观点不同,它所现的外形也就不同,你以为这种不同是在床的本质,还是在床的外形呢?”[3](69)与希腊艺术不同,埃及艺术图像就不存在不同视点的问题,因而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或柏拉图心目中的理念。其次,柏拉图的第二个忧虑与第一个忧虑紧密相连,他认为希腊艺术家放弃或牺牲埃及物像永恒的功能而去描画一个飞逝的瞬间会引起物像的贬值,会把艺术家和观者引入琐碎的细节之中。最后,他的第三个忧虑又从前两个忧虑而来,但更偏重从观者的角度来谈。观看希腊图像让人们诉诸想象这种心灵的低级能力,而不是理性。因为希腊图像描画的是一个视点的眼之所见,看不见的地方就需要观者用想象力予以补助。
但这些还都不是让柏拉图最为忧心的问题。对柏拉图而言,最大的麻烦在于追拟自然的希腊艺术造就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让本来就难辨真假的懵懂心灵更加无所适从。贡布里希有意替柏拉图明述这一担忧:“他会申明,即便不插入一个亦此亦彼的朦胧领域,要我们把科学知识和神话区别开来,把现实和单纯的形象区别开来也够让我们为难的了。”③在贡布里希看来,柏拉图的这一担忧绝非庸人自扰,因为理解艺术之为虚构的观念对于不成熟的心灵并非易事,所以才有诸多把艺术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轶事。贡布里希多次提到的那段马蒂斯和一位妇人之间的对话便是对此观点的绝佳佐证。据说一位妇人参观马蒂斯的画室,向马蒂斯抱怨说某个女人的手臂太长了,马蒂斯却回答说:“夫人,您弄错了。这不是女人,这是一幅画。”[2](83)
事实上,柏拉图对写真图像的每一个担忧都值得斟酌玩味,而贡布里希的艺术史更是向我们表明,柏拉图的某些担忧在古典社会晚期已然变成了现实。在奥古斯都时代,写真图像的技法迅速传播,艺术与幻术的结合导致了物像的平庸化,于是有一些鉴赏家开始追随柏拉图推崇埃及的图像文字。不用等到基督教文化的入侵,古典时代晚期的艺术趣味已经开始回归。而基督教入主欧洲之后,图像又一次嵌入“实用的上下文”。这次不是为了追逐永恒,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宗教教义的回想,于是图像是否逼真的问题沉潜下去,直到文艺复兴才又浮出水面,并又一次得到热切的讨论。
尽管模仿自然的主张在后希腊时代一度隐匿,但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模仿现实的追求在西方艺术传统中再次生根,并奠定了我们解读西方艺术图像的“心理定向”④。我所谈及的“我们”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艺术的观者,也包括柏拉图同时代的希腊人。柏拉图著名的《会饮篇》恰好记录了耳濡目染写真图像的希腊人对埃及艺术图像的不适反应。“所以,我们得好自为之,要是对神们不规矩点,恐怕不免还会被切一次,结果就只得像墓石上的浮雕人似的四处走,鼻梁从中间被劈开,有如一块符片。”[5](53)不仅如此,贡布里希还提醒我们,就连崇尚埃及艺术的柏拉图也是带着希腊人的这种有色眼镜来解读埃及图像的,即“柏拉图认为埃及的浮雕是再现某些神圣的姿势”[2](83)。然而,如果说对于埃及图像而言,柏拉图的模仿说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么这副眼镜是否道出了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的实情呢?西方艺术为了匹配现实所做的努力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对现实的模仿、转录或复写呢?
三、艺术与现实谁模仿谁
众所周知,模仿说即便在希腊也不是柏拉图的一家之言,它是希腊哲学家们对艺术的一般看法。而当写真的诉求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被唤起时,更是有众多的画家和艺术理论家追随模仿说的脚步。比如伟大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有著名的“镜子说”,他认为艺术的标准在自然,能够准确地转录现实是衡量艺术佳作的尺度。西方艺术史中更是有大量的故事讲述绘画摹写自然的逼真程度足以欺骗眼睛,而这些故事参与塑造了西方艺术家的形象,即艺术家是复制现实的魔法师。[7](61-71)
由此看来,在追求逼真的道路上,西方艺术的确缀行甚远。贡布里希甚至说过一个大胆的论断:“在这个地球上,艺术家只在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做出过系统的代代相赓的努力,使他们的图像逐渐逼近可见世界并达到了可以乱人眼目的真实程度。”[8](11)在照相、摄影技术几乎覆盖全球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失掉了对这一论断的惊奇感,因为逼真图像不再难得,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往昔西方艺术家为此所做出的持续性努力,难以理解人们对写真图像的最初反应;另一方面正是全球化让我们能够比较各个民族的图像传统,让我们看到西方图像传统的独特性,理解贡布里希的这个貌似大胆的主张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
就拿我们中国自己的图像传统来比照。我们不谈不讲形似的文人山水,而把注意力放在肖像画领域。大概谁也不会认为我们传统的肖像画丝毫不以肖似为目的。肖像画被用来纪念先祖,也被用来缉拿要犯。前者不像倒还好说,后者不像麻烦就大了。《金瓶梅》中曾叙述过一个有关肖像画的故事。浪荡公子西门庆因爱妾李瓶儿之死,不顾礼法让韩画师观其遗体以画其肖像。画毕又送给家中女眷评判修改,最后得到邻居兼亲家乔大户的首肯,西门庆方才罢休。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想见韩画师的李瓶儿肖像画一定是肖似的佳作了。然而,我们也可以揣测,李瓶儿的肖像画不可能达到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的那些西方肖像画的逼真程度,否则国人初见郎世宁画作也不会因其太过逼真而感到不适了。中国绘画,哪怕是以肖似为目标的肖像画也从未在摹写现实的道路上不断推进,未曾对其所继承的图式进行大规模改制,因而比之西方肖像画,中国人物画有类型化的倾向。
也许正是由于西方艺术在摹写现实道路上的不断努力,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的主张才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然而,另外一些艺术现象则向我们提出了相反的模仿路径:不仅仅是艺术在模仿现实,有时现实也模仿艺术。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叙述经常提到这些相反路径的模仿。比如他曾提到自己观看鲁本斯那幅《画家之子》时的震惊,刚看到那幅画时,贡布里希觉得这个儿童的脸颊过于丰满,像是得了流行性腮腺炎。然而当他再去看现实中的儿童时,却发现这样脸颊丰满的儿童到处都有。[2](121)又如,克劳德·洛兰的风景画出现之后,英国人竟然按照这些画去寻找甚至建构优美的风景和建筑,而风景如画成了对自然之美的最高褒奖。又如,在我们看到梵高的星空和柏树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用线条组成的漩涡去解读星空和柏树。但看过梵高的绘画之后,我们再看星空下的柏树,梵高的画成了挥之不去的印象。最有趣的反向模仿则是漫画。一幅优秀的漫画根本不必肖似被描画者,这个被描画者倒要带着他的漫画进入人们的视野。艺术模仿自然的情况虽多,这些反向模仿的情况似乎也不少见。近代以来众人纷纷引称奥斯卡·王尔德的那个著名断言,“在惠斯勒没有画出雾之前,伦敦没有雾;在梵高画出普罗旺斯的柏树以前,普罗旺斯的柏树一定也少得多”[9](194)。在这些反向模仿的现象中,现实不再作为衡量图像的标准。相反,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因艺术图像而改观,图像好似把新的视觉印象强加在了现实身上。那么,艺术和现实到底是谁模仿了谁?
如果我们沿着柏拉图模仿说的思路,把模仿看作为获取相似性而进行的镜像式复制,那么这两类模仿现象就永远互相矛盾,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沿着贡布里希提供的思路,不把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辨认看作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模仿,而是看作主体在图像与现实之间不断交互解读以期产生等效认同,那么这两类现象的矛盾就被消解了。所谓图像逼真不是说图像复写了现实,而是说图像能让我们产生自然之物作用于我们心灵时的那种同一性反应。因而,贡布里希反复强调:“再现”也好,“模仿”也罢,图像解读“永远是一桩双向的事”[2](175)。我们在解读图像和解读现实之间不断往复,从而在图像与现实之间造成一种相互辨认、相互生成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彻底反驳了柏拉图的模仿说。“如果我们讲模仿自然,那就误解了这种技巧的特点。如果不是首先把自然分解开,再重新组合起来,自然就不能够被模仿或‘转录’。这不单单是观察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不断实验的事情。因为在这里,‘观察’一语也已倾向于使人误解而不是给人启发。”[2](10)因为西方再现艺术不是不断观察如何复制现实事物的外观或形相,而是不断实验如何改制图式以便产生一个构型,使我们面对这个构型能产生与我们面对自然之物时的同一性反应。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提倡艺术的模仿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当那些我们在生活中厌恶的东西作为艺术被逼真地再现时,我们却能产生一种辨认的快感。可见,同为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角度和柏拉图的角度其实非常不同,他不是把模仿看作现实之物外观的复制,而是看作主体辨认现实的手段。也正如贡布里希向我们表明的,亚里士多德是从等效认同的角度来看待造型艺术的,即“自然主义绘画能使我们从画布上安排的颜料构形中辨认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8](12)。从这一点入手,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是模仿现实、追求肖似,我们却觉得我们可以说西方肖像画比中国肖像画更逼真。那不过是由于西方传统的肖像画通常更容易引发我们对熟悉事物的辨认,更容易重建我们的现实感罢了。
因此,与其说写真艺术模仿现实,不如说这些艺术图像激发我们辨认现实的反应。事实上,所有的艺术都不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模仿现实,因为那种模仿意味着被模仿对象的现成性,意味着心灵归档类目的不变性。果真如此,现实模仿艺术的现象,或者用贡布里希的术语“反向辨认(inverted recognition)”[8](30)的现象就不可能发生。然而,正是由于我们观看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艺术才有可能提供新的角度,让我们对世界“重新分节”,我们才能通过艺术获得视觉的新发现。
四、图像带来的两重视觉发现
在西方艺术不断实验改造图式匹配可见世界的道路上,印象派接跑了最后一棒。在这之后,照相术等技术在探索写真的道路上取代了艺术,西方艺术的兴趣便转入其他领域。虽然今天我们早已学会退后两步,任色斑、色块自动组合引发投射,从而获得观看现实中光与影的效果,但在印象派绘画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些“乱涂之作”比传统的绘画更逼真,更容易引发辨认。贡布里希曾讲述过两个有关印象派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对我们理解他所说的反向辨认颇有助益。第一个故事简直可以称之为印象派绘画的理论先声、反向辨认的最佳实例。据说,早在1793年,歌德就观察到了有色阴影,并把他的相关论文寄给了德国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从此利希滕贝格就像小男孩追逐蝴蝶一样追寻这些有色阴影。[8](29)印象派绘画的早期支持者们就像利希滕贝格,他们努力跟随图像的指引,看到了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光线和色彩。而我们今天也已学会跟随他们,在人脸上辨认出各色阴影,而在没接触印象派绘画之前,我们一般都觉得人脸只有一种肉色。然而,在贡布里希所讲的第二个故事中,观画者可就不像利希滕贝格和今天的我们那样机智、那样配合了。第二个故事出自左拉的小说《杰作》。在这部小说中,左拉塑造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妻子,她批评自己的画家丈夫把白杨树画得太蓝了。画家循循善诱地教导妻子注意光线下白杨树微妙的蓝色,虽然妻子不得不承认这蓝色,但却责怪自然界不应该有蓝色的树。⑤左拉正是借画家妻子和公众对蓝色树木的不解甚至大惊失色来讽刺不接受印象派的无知庸众。
由此可见,反向辨认并不像从现实主义图画辨认现实那样毫不费力。虽然在第一个故事中,反向辨认迅速得到认可,但在第二个故事中,反向辨认却受到了巨大的阻力。然而,贡布里希反问:难道反向辨认的阻力仅仅是由于画家妻子或公众的愚蠢物质吗?把不变因素的知识带入绘画不恰恰是捕捉到了我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恒常性和稳定性吗?在贡布里希看来,我们感知世界并不是接受纷至沓来的刺激,而是按照刺激的相互关系对它们进行归档整理。⑥我们的那套归档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比如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是按照其大小、远近关系进行设想的,而传统的写真图像和照片之所以能够毫不费力地得到辨认,正是因为它们通过透视法等一系列摹写技巧重建了我们对现实感知的恒常性。难怪那么多人要追随柏拉图模仿说的脚步,只考虑艺术模仿自然这类在绘画中辨认现实的现象,而对在现实中辨认绘画这类自然模仿艺术的现象视而不见。
如果心灵归档系统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就将迷失在纷繁复杂的刺激中而不知所措。然而,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心灵的归档类目是固定不变的。在贡布里希看来,艺术大师毕加索把汽车的车灯改造成一张狒狒的脸,正是在尝试一种新颖的归档方法。他的这个雕塑作品为我们观看世界提供了一个新隐喻,它鼓励我们进行反向辨认,让我们在某种心境下,比如在一辆汽车堵住我们前行道路的时候,看到狒狒那呲牙咧嘴的样子。[2](74-75)而这种反向辨认高度提示着我们:视觉的稳定性并不排斥其可塑性,我们对图像的观看高度活跃地介入了我们对世界的观看。
正是因为艺术帮助我们以新的眼光观看世界,雕塑家罗丹所说的“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才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不过,贡布里希指出,这种新眼光,即艺术图像带给我们的视觉新发现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事物意义与价值理解的改变而引发的现实改观。去过农村的人都看到过农鞋,但一般不会对它们太在意。海德格尔说,如果农鞋没磨坏,连穿农鞋的农妇自己也不会在意。然而,当我们看了梵高画的农鞋,农鞋的意义就突然丰富起来,即“走进这个作品,我们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10](20)。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之所以与真理相关就是因为艺术作品让我们从最富意义的角度重新看待那些我们日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存在者。贡布里希所述的他观看罗伯特·劳申伯格招贴画的经验看似与海德格尔的表述迥然有异,但实质并无不同。贡布里希说他特别不喜欢劳申伯格制作的那些招贴画,但自从看了他的画之后,自己却开始情不自禁地注意到用来构造招贴画的那些破报纸和碎纸片了。贡布里希接着评论道:“情感的介入,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都有助于记忆和辨认。”[10](40)因此,第一层次通过艺术的视觉的新发现是由我们观看艺术图像时的情感和评价(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引发的,事物由此获得了我们的注意,而其意义的强弱也发生了改变。
在没看梵高画的农鞋之前,我们不能说自己从没见过农鞋;但在毕加索没制作出雕塑作品狒狒和幼子之前,我们也许真没想过可以把车灯看作狒狒脸。后者就是贡布里希所说的第二层次的反向辨认,即艺术图像尝试对世界重新分节。贡布里希以他观看劳伦斯·高英的画为例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在没看过劳伦斯·高英那幅《抛物线透视》之前,贡布里希从未发现自家地板的外形具有这幅绘画的图案。他对自家的地板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他自述“我几乎一点没注意到这些刺激,就像我没注意我在世界上走过时冲击着我的千百万其它刺激”[8](30)。如果我们同意贡布里希的看法,“观看”并不是接受千百万的刺激,也不是记录事物的外观,我们就知道贡布里希从高英绘画中得到的是观看地板外观的新方式,一种新的视觉分节方式。
在我看来,传统的西方再现性绘画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第一层次的视觉发现,它承认现有的视觉归档目录,着力于让我们从图像辨认现实,丰富我们对事物意义与价值的感知。而现代艺术则有意识地去尝试开展第二层次的反向辨认,即利用分离效果⑦和多义性⑧让我们注意到可见世界的不稳定性,从重新归档的角度丰富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象派既是传统艺术的终结者,也是现代艺术的先驱。一方面它跟随西方传统艺术的追求,探索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眼之所见,以图像能够辨识现实为目标;另一方面,正是印象派画家对户外光影关系的探索,开启了西方艺术大规模进行反向辨认的尝试,它使我们获得了为瞬间印象重新编码的契机,让我们能像利希滕贝格那样克服恒常性的干扰像看到有色阴影以及其他我们从未注意到的视觉效果。
以上谈及的任何一种视觉发现都与柏拉图模仿说所谈到的复写现实事物的外观毫不相干。传统的再现艺术一开始就指明意义而不是复现自然,而现代艺术则有意识地进行各种视觉编码的实验。然而,贡布里希提醒我们,柏拉图反对艺术的忧心仍然引人警醒,因为正是“理性,在坚持较窄的现实分类和较宽的隐喻分类之间的差异,在坚持外观和真实之间的界限”[2](74)。不过,我们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理性存在者,并且理性在心灵中的主导地位也不总是稳固的。“我们的双重本性,平衡于动物性和理性之间,在象征符号的双重性世界中找到了表现方法,在这个世界中已经自动地终止了怀疑之念。”[2](73)正是秉着柯勒律治“心甘情愿暂不怀疑的态度”[11](161),我们开辟了一个叫做艺术的领域。我们一方面有意追寻恐惧和怜悯的体验与光怪陆离的感官刺激,一方面又意识到它不是真的,不会产生现实的后果。不仅如此,艺术图像更以隐喻的方式、以象征符号的方式介入现实,让我们重新观看和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
注释:
① 在贡布里希看来,虽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但《荷马史诗》的独特之处是:诗人像一个目击者一样进行叙述。这样的叙述方式以及古典文化时期剧场布景的需要奠定了西方图像的写实主义特点。
② 所谓实用的上下文,是指物像被看作是能发挥效用的神秘之物,而非审美对象。比如埃及的神像主要是用来参拜的,因此效用是第一位的。希腊的神像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审美的对象。
③ 此处中文译本有误。参看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 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92,以及E.H.Gombrich:Art and Illusion, New York: Phaidon Press,2002: 109。
④ 心理定向(mental set)是贡布里希图像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我们对图像的预期。在贡布里希看来,我们把图像认作什么与我们对它的预期密切相关。比如我们就不会把一个半身像认作是整个身体被截掉了一半,因为我们对它有正确的心理预期,知道这是一种艺术表达程式。
⑤ 左拉在这部小说里曾两次提及人们对蓝色树木的不解。一次是人们对参展绘画中蓝色树木的不解,另一次就是他的妻子对其绘画中蓝色树木的不解。参看左拉《杰作》,冷杉, 冷枞,译,北京: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116, 141,以及E.H.贡布里希《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 32。
⑥ 贡布里希曾举心理学实验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不是对特定物上的反射光线进行反应,而是对光的格差或梯度进行反应。这个“我们”甚至包括许多动物,例如小鸡。参看 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 李本正, 范景中, 译,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36。
⑦ 在贡布里希看来,我们对图像之所是的认识受图像前后关系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分离图像的前后关系,就会使熟悉的图像解体。歌德和利希滕贝格对有色阴影的发现正是由于他们有意识地破坏各种相互暗示从而分离了我们对颜色的稳定感觉。参看E.H.贡布里希《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 32-33。
⑧ 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曾专门讨论过二维图像再现三维世界所带来的多义性问题。由于知觉的稳定性和对意义的追踪,对这种多义性我们一般难以察觉,除非通过特殊的实验才能使其显现。在《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中,贡布里希更是认为分离会导致我们更多地体会到我们眼见世界的多义性和不稳定性。参看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 李本正, 范景中, 译,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177-201,以及E.H.贡布里希《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范景中译,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 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