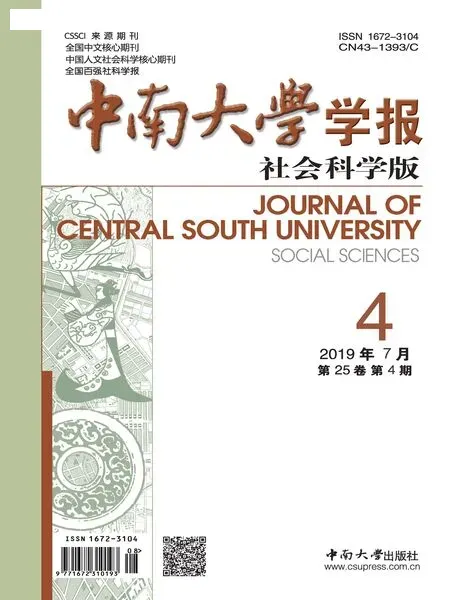传统目录学视域下《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文类涵义
温庆新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近今学者在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同时,往往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文体内涵、文体风格及文体意义等视角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言”的文体价值。如周秋良认为:“如果说,从古代小说创作史来看中国小说文体的独立表现为唐传奇的‘有意而为’;那么可以说,小说文体独立的理论论述则直到《总目》 的‘小说家言’之别是一家才初步完成。并且其标举荒诞,强调故事性,突出文采的认识,使得‘小说家言’之体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存在天然的相通性。”[1]这种“以西律中”的思路已成为学界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文体意义的主要手段。那么,此举对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文体意义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今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为探讨对象,从传统目录学分类的人伦秩序、政教意图及类名设定原则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所隐含的文类表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认知视角
纵观《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可知,“四库馆臣”往往多频次使用“小说体”“小说之体”及“小说之本色”等关键词对小说的内涵、特征进行论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有关《菽园杂记》提要言:“是编乃其(陆容)札录之文,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盖自唐宋以来,说部之体如是也。”[2](1204)此类关键话语在先于《四库全书总目》而成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六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朝野佥载》提要言:“其书记唐代轶事,多琐屑猥杂,然古来小说之体,大抵如此。”[3](377)又,《中朝故事》提要言:“上卷记君臣事迹、朝廷制度;下卷则杂陈神怪,纯为小说体矣。”[3](379)又,《张氏可书》提要言:“(张知甫)生北宋末年,犹及见汴都全盛,故于徽宗时朝廷故事,记载特详,往往意存劝戒。其杂以神怪诙谐,虽不出小说之体,要其大旨,固《东京梦华》之类也。”[3](387)又,《菽园杂记》提要言:“多记明代朝野故实,多可以参证史传。其杂以诙嘲鄙事,盖小说之体。惟考辨古义,或有偏驳,存而不论可矣。”[3](390)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既包含猥杂或神怪的内容,又包含考证之用的作品,就属于“小说体”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乐郊私语》提要曾指出:“(该书)所记轶闻琐语,多类小说;记赵孟坚事,尤失实。”[3](390)可知并不是由于作品中包含“轶闻琐语”之类的内容就可被认定属于“小说家言”,而是以相关作品中所写“轶闻琐语”的征信价值、书写方式与“小说家类”的源流衍变及文化特质是否存在相似之处而加以认定的。
据前所引,“四库馆臣”在表达“小说(之)体”时,往往强调要有“琐屑猥杂”的内容、“杂陈神怪”的言说方式,甚至带有“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等目录分类特征。傅荣贤曾指出:“古代书目类别结构的层次之分不仅是形态上的而且是意义上的。类别层次凝聚着汉族人的历史情感并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含义。”[4](223)上引诸多例证亦表明“四库馆臣”提出的“说部之体”或“小说(之)体”,不仅强调“小说家类”作品隐含“谈谐杂事”“轶闻琐语”等内容与“杂陈神怪”之类的书写方式、行文特征,而且强调相关小说作品隐含的“大旨”及文化涵义,意即批判相关作品“杂陈神怪诙谐”,而忽视了“意存劝诫”“参证史传”等价值。此类强调往往是基于“小说家类”的历史出处与“稗官”职责而引申出的源流叙述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提要叙述模式促使“四库馆臣”基于目录学部类设置的源流追溯,进一步从“小说家类”作品的产生缘起与衍变过程等角度加以分析。故而,“四库馆臣”对具体小说作品的提要进行表述时,紧紧围绕《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所谓“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2](1182)等“古制”,强调“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的认知视角,以此剖析后世小说作品在衍变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小说之体”的根源。比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开元天宝遗事》提要指出:“小说家言,得诸委巷,不能一一责以必实也。”[3](380)甚至“四库馆臣”不仅是从“得诸委巷”的文献出处来认定相关作品是否具有“小说家类”的品性,而且是从“委巷流传”的情况来认定相关作品在历代流传时的实际用途,以此决定是否归入“小说家类”中。比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穆天子传》提要就说:“(该书)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而与《列子·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当时委巷流传,有此杂记。旧史以其编纪月日,皆列起居录中,今改隶小说,以从其实。”[3](391)也就是说,“四库馆臣”从“稗官小说”的源流开始梳理,试图据此强调小说观念与小说文体特性具有超越时空的属性,并具有特殊学术流派的共性。
需要指出的是,从《汉书·艺文志》认为包括“小说家类”在内的“九流十家”属于“《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5]起,《汉书·艺文志》的类名命名处理往往从某一特定文治环境所形成的特有行为方式切入,归纳出“九流十家”(或诸子百家)为达到特定政教意图而形成的特定言说行为及其相应的言辞表达样式,并溯本追源;而后在“以类相从”原则的指导下总结相应言辞表达样式的文类形态,并统而命名[6]。而从《庄子·杂篇·外物》所谓“夫揭竿累,趋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7]起,“小说”作为一个“类名”的指称,不仅包含与诸如“道家”(《庄子》所指就是强调“小说”与“道家”的不同)等其他“大达”相对的学说,也强调了“小说”与其他“大达”本质有别的言论行为及其言辞方式,从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文体分类意识。到《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指明了“小说”是一种具有特定政教意图的行为方式的集合体,它与“街谈巷语”等品评政教得失的普遍化社会行为、“道听途说”的政教方式相联系。但“街谈巷语”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谈论“儒家”“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所涉及的内容,而不仅仅只是谈论“小说家”的小道内容,以至于时人混淆了“以类相从”背后言语的“所指”内容,并引发了言语“寓指”范围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讲,“以类相从”的命名原则,往往会产生“为例不纯”的矛盾,从而导致后世之人不断对此前的文类类名进行修正,或重新挑选其所认可的作品以归入其试图改变的部类中。据此而言,“四库馆臣”对“小说家类”出于“稗官”之“古制”的肯定,其实就是对“小说家类”所言“街谈巷语”等“涉及与朝政得失相关之庶人言论”[8]的认同,亦是“士传言”之“古制”的延续。《史记·周本纪》曾说:“百工谏,庶人传语。”同书“集解”引韦昭所言:“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言,传以语士。”“正义”亦曰:“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9]此处明确记载“士传言”的“古制”梗概。而在“古制”的约束下,由此形成了“稗官小说”采用杂以俳谐言语、口头调笑等难免带有夸张成分的表演手段进行“传言”的固定化言说特征与寓意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小说家类”的“改隶”或“退置”行为,就是一种依清代政教需求与传统书目类名分类原则对“为例不纯”进行修正的行为,最终带来重视“小说家类”书写“体例”的探讨。这种讨论就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主要认知视角。
二、“先道后器”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之体”的内涵及特质
在重视“小说家类”书写“体例”的推动下,“四库馆臣”对“小说之体”的“本色”及一般特征,做出了明确的形式认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大唐传载》提要指出:“其间及诙嘲琐语,则小说之本色也。”[3](378)《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则言:“间及于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2](1185)此类表述就是从“稗官小说”的形成与“俳优小说”紧密相关的认知展开评判,认为以“俳优”手法来进行言语思想的表述,是“小说家类”作品形成“诙嘲琐语”之“本色”的重要原因。在此类认知的推动下,“四库馆臣”在强调小说“本色”的同时也注意从“稗官之习”的角度展开针对具体小说作品的品评。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东斋记事》提要即言:“其中间涉语怪,不免稗官之习。”[3](382)可见,“稗官之习”与“诙嘲琐语”的表述,就成为“四库馆臣”基于“小说家类”源流衍变的认知视角而形成的对小说之本色及其一般特征的一种形式认定。
此举使得“四库馆臣”对于哪些作品能够著录于“小说家类”中,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比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南部新书》提要言:“所记皆唐时故实,兼及五代。多采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间。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3](381)这就明确了“轶闻琐语”与“朝章国典”等内容在“小说家类”作品中的重要区别。《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进一步指出:“是书乃其(钱易)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2](1189)这就明确了“录轶闻琐语”是“小说家类”作品的书写方式与内容特色。而“小说家类”所包含的“朝章国典”,虽然进一步强化了相关小说作品“资考证”的价值,却非“小说家类”作品常态化的主导性特征。因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南唐近事》提要中指出:“所记皆琐语碎事。疑(郑)文宝裒集遗文,以朝廷大政为《江表志》,以其余文为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而后“四库馆臣”加“谨案”,言:“偏霸事迹,例入载记。惟此书虽标南唐之名,而非其国记,故入之小说家。盖以书之体例为断,犹《明皇杂录》不可以入史部也。”[3](380)《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案语”内容大体同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处所谓“史体”与“小说体”的表述,明确了书写“朝章国典”等对国家政统有利及其可信程度,这应当成为“史体”的主要书写重点与言说方式;而“琐语碎事”的内容与“裒集遗文”的方式,是“小说家类”惯用的书写“体例”。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传统目录学“先道后器”的分类原则而定。
据研究,传统目录学的类名编排标准之一,往往是依“从大到小的带有演绎性质的排列,章学诚称为先道后器”[4](234)。章学诚曾于《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并说:“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岂有读著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10]也就是说,传统目录学往往将言“道”之书列于说“器”之书前,以此明确书籍“道”的功用与“器”的功用,最终实现“道器合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就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2](769)所谓“名品乃定”就指出不同类别书籍的内容、体例及意义有别。其将儒家列为第一,强化儒家之于治国之道的重要性;而后次以法家,强调治理国家之法则的重要性。由此,“四库馆臣”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归为“治世者所有事”,而将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归为“旁资参考”,其中显然蕴含了严格道器之分的思想,以便强调“器或寓道”的书籍价值及其意义层次,最终实现利于政教统治的意图。
据此,“四库馆臣”区分了“史体”与“小说体”的异同,这也是道器排列的分类思想作用的结果。《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小序指出:“(杂史类)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2](460)所谓“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云云,不仅是强调文献的内容与书写,也是对不同类别文献之意义与功能的强调。换句话讲,对“事系庙堂,语关军国”与“里巷琐言,稗官所述”的区分,就是贯彻先道后器的类名设定原则。前者可为治国之道服务,后者可为治国之道的效果进行验证与纠偏。可见,“四库馆臣”对“小说体”之“义例”的强调,应该是建立在对“小说体”之意义的认知上。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四库馆臣”对“小说家类”作品之“近正”意义的突出,并以“近正”作为对“小说体”进行价值等级划分的标准。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国史补》“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3](377)。即是此类。纵观《四库全书总目》可知,“四库馆臣”多次以“近正”展开对相关作品的名品定位。如《贾氏谈录》提要所言:“他如兴庆宫、华清宫、含元殿之制,淡墨题榜之始,以及院体书、百衲琴、澄泥研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较他小说固犹为切实近正也。”[2](1188)又,《司马法》提要:“然要其大旨,终为近正,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2](836)又,《东南纪闻》提要:“然大旨记述近实,持论近正,在说部之中犹为善本。”[2](1202)又,《席上腐谈》提要:“大旨皆不出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论独为近正。由其先明儒理,故不惑方士之诡说也。”[2](1253)等等。所谓“近”,《说文解字》言:“附也。从辵斤声。”[11]故与人之行走行为有关。《洪范》曾说:“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12]由此,“四库馆臣”所谓“近正”当是认为相关作品所写内容能够用于政统,且行文规范、言说方式征实而符合道统与政统所需,带有浓厚的人伦秩序意图。“小说家类”作品达此标准者少,实在是由于“里巷琐言,稗官所述”难免流于诙谐之论。
也就是说,“小说”与“载记”的区别仍在于猥杂诙谐的特点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归田录》提要所言“多记朝廷旧事,及士大夫谐谑之言。自序谓以李肇《国史补》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也”[3](382),即是典型之例。“谐谑之言”既不符合“近正”的特征,也不符合人心教化之正面意义。然而,“四库馆臣”也有将记录“朝章国典”的作品归入“小说家类”中的例子。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萍洲可谈》提要言:“是书多述其父所闻见。又(朱)彧初与苏轼兄弟游,后乃隙,末党附舒亶、吕惠卿,故与熙宁、元祐之际,颇有意抑扬。然所记朝章国典、土俗民风,皆颇足以资考证。”[3](386)关于此条提要的理解,应该把重点首先放在“四库馆臣”认为朱彧因党争而“有意抑扬”时人的做法,其次应该注意朱彧“多述其父所闻见”的资料来源。由此,虽然《萍洲可谈》含有“朝章国典、土俗民风”,但有关内容的来源与叙述笔法导致了该书所载唯有作为“资考证”的参考,而不能作为绝对凭据。故而,“四库馆臣”认为“小说家类”作品含有“朝章国典”之类的内容,并将其与“载记”、史志相区别,原因就在于认为“小说家类”的相关作品往往带有“诙嘲琐语”或抑扬太甚的“稗官之习”。比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桯史》“所载南北宋事,凡一百四十余条,多足补正史之遗。虽颇及诙嘲琐语,然大旨亦多寓劝惩”[3](388),这里虽然指出了《桯史》“多寓劝惩”,却“颇及诙嘲琐语”,难免带有“小说本色”。故而,于体例而论,《桯史》当入“小说家类”中。
由此可见,考察“四库馆臣”评判“小说家类”作品的考订价值时,应首先注意其是否从“稗官之习”或“小说本色”的角度对相关小说作品进行价值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四库馆臣”所言“小说家类”作品的“资考证”特征,往往指向可资参考且不能作为考辨的最主要依据、征信相对有限等方面。比如,《四库全书简明书目》有关《高斋漫录》提要指出:“是书虽卷帙寥寥,而所述朝廷典制及士大夫言行,往往可资法戒。其品诗文、供谐戏者,亦皆有理致可观。”[3](386)所谓“可资法戒”,不仅包含效法之意,也有劝诫之意。而《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提要亦言:“宋曾慥撰。慥有《类说》,已著录。《类说》自序,以为小道可观,而归之于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其撰述是书,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中如给舍之当服赪带,不历转运使之不得为知制诰,皆可补史志所未备。其征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于游谈无根者也。”[2](1197)所谓“随所见闻,咸登记录”,这就降低了此书文献来源的可靠程度,因此,虽其有助于“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但也是“可取者多”,而非皆可取。
这样看来,“稗官之习”与“诙嘲琐语”的关注内容与书写方式,就成为“四库馆臣”以“小说之体”的方式对相关作品书写提要的逻辑切入点与品评重点,从而对“小说家类”具体作品提要的意义表述形成明确导向。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关《先进遗风》提要言:“所录皆明代名臣言行,大抵严操守、砺品行、存忠厚者居多。又多居家行己之事,而朝政不及焉。其意似为当时士大夫讽也。”[3](390)就属此类。也就是说,“四库馆臣”区分“轶闻琐语”与“朝章国典”时,并不简单局限于上述两种内容的差异,而是强化文献区分背后的“纲纪”人伦秩序。因此,所谓“小说体”或“小说家言”的文体形态与文体价值表述,都要符合此类表述对于建构人伦秩序、政教统治秩序的需求。这是“四库馆臣”对类目及其涵义进行价值区分的延续。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大唐新语》提要言:“所记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凡分三十门,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前有《自序》,后有《总论》一篇,称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杂史类中。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2](1183)将《大唐新语》退置于“杂史类”中,不仅是此书与“史家之体例”的一般做法有别,也在于此书所包含的“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的内容,违背了“杂史类”小序所谓“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类目特征与功能要求。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小说之体”的内涵表述依旧是以政教思想为内核而展开的。“四库馆臣”对“小说之体”所作的“本色”说明,主要是从“小说家类”形成的历史传统与清代的文治需求两方面加以展开的,从而以是否带有诸如“琐屑猥杂”的内容、“杂陈神怪”的言说方式及“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的分类特征等“稗官之习”,作为界定“小说之体”内涵的标准。同时,“四库馆臣”以传统目录学“先道后器”的类名设定原则,对“小说家类”与“杂史”“载记”“杂家”等其他类别进行了本质区分与类别规范,甚至基于古人著书所普遍使用的“义例”原则及学术规范,来进一步界定“小说之本色”的特质。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13]虽然可以从“小说家类”作品中窥见其间的多种特征,但从部类“体制”就可以对具体小说作品进行辨别、归置,甚至淡化与“体制”主要特征不相干的其他特征。“四库馆臣”的相关归并,亦属此类。这种从传统目录学的部类体例来梳理“小说之体”文类内涵的方式,并不是对“小说之体”进行严格的思想、内容及形式限定,而是以一种“举其略”的示范作品加以说明。由此,在上述“小说之体”主要特征进行了规范的情况下,对于“小说家言”的虚构性、文辞华章等特征的评判,则非“小说家类”进行类别设定与作品归并的主要标准。也就是说,《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文类特征是一种确定性表述或概述性表述,而非限定性表述。
三、《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强调“小说之体”之“琐屑猥杂”内容、“杂陈神怪”言说方式,虽说带有一定的文体区分意味,但此类文体区分是建立在《四库全书总目》突出小说政教功用的基础上,以一种符合统治所需的知识结构将彼时所存形式多样的小说作品进行有效归并,从而为时人提供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典范作品。换句话讲,从清代特定政教需求出发,归纳、规范小说的知识内涵与价值导向,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此举以一种杂糅小说本体论、小说功用论及小说价值论的观念生成视角,且以官方权威来颁行天下,是以官学来限定、规范时人在官学知识体系之外的其他探索,最终以相应的知识谱系来展开对小说作品的内涵、价值及形式的限定与规范。这种认知完全不同于以西方历史语境与知识谱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以故事、虚构为主要元素的小说观念,更不可能产生以小说本体论的审美形式来建构相应小说观念的文化土壤。更何况,“四库馆臣”对“小说家类”所谓虚构的论述,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政统需求、风俗教化等基础上的。此类以官学约束体系而形成的小说观念及批评思想,能够与文人学子进行小说评点的文人化倾向,以及与彼时小说评点者的民间关照视角及其结论进行对比,以便从官学体系与民间视角等多方面建构清代小说批评史迹。
有鉴于此,我们探讨《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文类内涵与文体意义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受政教语境与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双重限制的“小说”文类观与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文类观,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应该说,传统目录学的学术批评范式,往往采用“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做法。它是一种类似于今人所谓“历史性文类”的做法。也就是说,从历代相关作品的衍变过程中,归纳、总结相关作品的共通特性及其在历史文化脉络中所起的共同作用,从中甄别出相关作品对该时期政教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将其作为正面启迪的典型或反面批判的对象。此举与借用规律的名义提炼相关文类之名的做法,即先圈定某些关键词,以此作为相关文类的形式、语言、内容及价值导向的主导性特征,最终促使所提炼的文类趋向显性化与定格化,二者有本质区别。探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向”或“现代转型”,无疑都存在着类似的思维矛盾。也就是说,以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小说观”的本质特征(如虚构、荒诞、形式、文采、故事及叙事等),来评判基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文治背景与政教传统下形成的隐含传统目录学特殊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的小说观念,无疑是隔靴搔痒的。据此,上文指出有学者认为“小说文体独立的理论论述则直到《总目》的‘小说家言’之别是一家才初步完成。并且其标举荒诞,强调故事性,突出文采的认识,使得‘小说家言’之体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存在天然的相通性”等观点,亦存在相似的认知误区。
那么,《四库全书总目》所言“荒诞”,是否就是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荒诞”之意呢?西方学者使用“荒诞”一词时,往往认为:“荒诞:1.〔音乐〕不和谐。2.不合乎理性或不恰当;现代用法中指明显地悖于情理,因而可笑愚蠢。”[14]他们甚至认为,“‘荒诞’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凸显,来源于人类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以及对生存价值的追寻”,从而在关注人之生存境遇的同时,“将丑怪和支离破碎的艺术形式搬上美学舞台,并用戏拟、反讽的手法来表现离奇的生活情境”,最终“彻底逃离了现实主义手法的束缚,以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世界的荒诞,从而使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考富有了象征意义”[15]。而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意图与成书语境看,其所言“荒诞”并非是对“人之生存境遇”与“荒诞的艺术手法”进行关注,而是从历代的文治教化需求与政统思想等角度,强调采录文献及其价值导向应与彼时政统思想合拍,以剔除采录文献中不利于政统需求的文本内容,并限定相关作品的意义导向。这种做法限制了对“人之生存境遇”的关注,否定了“悖于情理”的书写,强调的是历代政统需求与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对相关文献知识结构、意义导向的钳制。上引《四库全书总目》采用“先道后器”作为类名排序的做法,就体现了此类思想。同时,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所言“事件本身的虚妄,也即今天所说的虚构性”[16],亦存在不区分所使用话语在中西各自语境下的具体涵义等情况。显然,《四库全书总目》所使用的“虚妄”,并非等同于虚构,而是与“猥鄙荒诞”等词汇紧密相关,强调采录文献所隐含的荒诞、怪诞内容及其书写方式不利于民心“向善”的政统需求,从而带有强烈的褒贬色彩。而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虚构是被当作“小说(novel)”的“同义词”,它源于拉丁词“fingo”,意指“制造”或“赋予形式”,往往与想象、创造、非现实的、不可靠等词汇相联系,甚至被认为“可指任何与存在于我们心灵之外的无定形的变化相对立的心理结构”[17]。
可见,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乃至进行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翻译时由于便利而套用汉语中的相关词汇进行西方术语的翻译,使得今人有关“荒诞”的认知是一种源于西方文化语境的“荒诞”诠释;而对中国历代文治环境下使用“荒诞”一词的认知却不明确,从而导致今人使用“荒诞”一词与“荒诞”在古人笔下的意义指向,既相混淆又相包含。这种词汇使用方式,最终导致今人在进行中西文体比较研究时,认为“荒诞”的内涵与形式具有古今中外相通或一致的看法,而忽略了其中的差异性。对虚构一词的使用亦然。据此而言,不管是使用“荒诞”、虚构还是文采等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以之为“小说”文体主要特征的相关词汇,若是不能注意到具体语境下的使用方式与内涵指向,就无法得出“存在天然的相通性”或“现代转型”的论述过程及其结论,也无法有效进行古今中外小说批评的比较分析。由此看来,我们应基于中国古代的文治思想、知识体系、话语传统及使用情形等方面,综合分析古人使用诸如“戏曲小说”或“小说之体”等话语的意义区间,而后才能进行诸如“现代转型”之类的比较研究。因此,回归清代的政教语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分类体系,全面还原《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文类涵义及其意义导向,以古还古。此举将有助于深入探讨清人有关“小说”的认知意见及其时代必然性,进而纠正近今学界在古代小说的观念研究、文体分析及文化诠释过程中某些过于西化的研究思路,以及由此形成的认识偏差。但可以从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与政教背景看待小说作品的两种认知视角,深入比对中西有关小说概念内涵、认知视角及批评理念的异同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