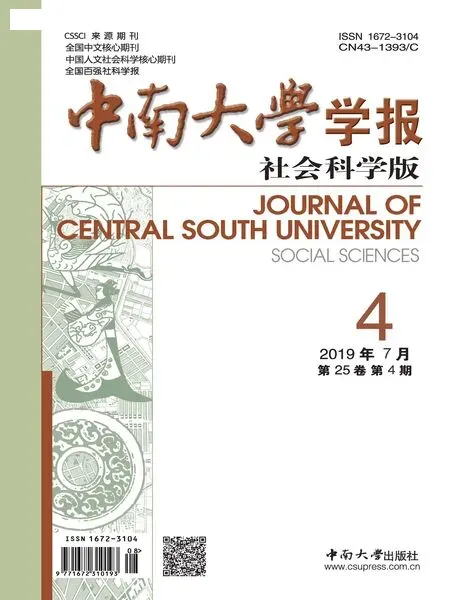齐桓公霸政形成新论
——以齐桓公权威身份的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熊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看来,合法统治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它们首要包含“合理的性质”“传统的性质”以及“魅力的性质”[1](241)。这些特点在聚合诸夏、首拓霸政的齐桓公身上,似乎都能追寻到踪迹:他以“尊王”的形式取得了周王的“合法授命”,同时阻断了东周初年的混乱局面,维持了多国共存的传统政治形态,更是凭借南伐北征、存邢救卫的英雄事迹成为后世传颂的“楷模”与“样板”。对此,钱穆认为霸政不亚于一个“变相的封建中心”,且“其事创始于齐,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2](60)。流行的看法认为,齐桓公的权威身份是以“尊王”的途径建构而成[3](162),且“尊王”策略的妥当运用造成了霸者在“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4]。但笔者认为,春秋诸多霸政模式间存在差异,齐桓公权威身份的合法性建构不以“尊王”为前提,反以侵蚀周姬王族权威,进而承接其政治文化身份为目标。东方霸政集团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对成周东部断裂的权威网络进行整合、连接,最后决意重塑的历史过程。
一、成周政治空间失序与东部权威网络的断裂
有关周王朝政治空间建构的特点,许倬云先生说它存有一个“点−线−面”式的权威网络:
重要的几个点,宗周(关中)是周人的根本之地,成周(洛阳附近)是东方发展的总基地。两个王畿之间,由虢与申维护,封晋在黄河以北,捍卫北面。……成周四围,有卫、蔡、管(后来又加上郑),监视商人后裔宋,东南面的汉水淮水上的诸侯,拉成南方的阵线。东面,齐鲁两个大邦既控制山东诸夷的故土,又扼住北面通辽的咽喉。在北方,则放下邢燕,掌握渤海平原。整个分割网络,形成一个大弧形,覆盖了今日陕、晋、豫、鲁、冀的黄河、汾水、济水、汉水、淮水,及渤海湾“九河”诸地区。环顾同时的古代文明,西周的布局,气魄宏大,罕见足以相比的例子。[5](11−12)
其中,丰镐之地不光是周人建构政治空间的起点,也是其积淀王者权威的文化本域。上帝在抛弃殷人后,选择了岐西作为新兴王者的受命之所,如《诗》曰:“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6](383)武王也于斯地继承了“文王之德”,随后挥师东进,力克大邑商。周族历代长老据此建构出了缜密的王者权威哲学,“宗周倚仗其与上帝与天的密切关系而握有政治与神话上的至上权威”[7](431)。因此,在宗周镐京与作为“东方发展总基地”的成周雒邑的关系界定上,“周王朝每代都会确认同一个事实——周是以陕西为大本营(中域),在此前提之下将其统治延伸至河南一带”[8](404)。
然宗周既失,直接导致了周姬长期宣扬的“骏命不易”的天命观变成了“天命靡常”,这对王者的权威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无论是当初与周室结盟、共同构筑政治管控网络的兄弟舅甥之国,还是其意图打压的先族遗民,都意识到这是“王族衰败以后重新争夺族姓地位”的绝佳时机[9](45)。因此,他们一方面唱衰“周德”:
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10](425)
另一方面,他们则宣扬天无常命,世无常主。楚人发问曰:“周幽谁诛,焉得夫襃姒?天命反侧,何罚何佑?”[11](111)齐人也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12](183)甚至连周民自己都对天命学说提出了质疑,“瞻卬昊天,则我不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6](456)。“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6](292)以至于在殷遗民中也兴起了“民族运动”①,“殷商亡国后,在那几百年中,人数是众多的,潜力是广大的,文化是继续存在的”[13](47)。
成周既无丰镐故地凭依,便迅速堕入骤然失序的政治空间中②。先是护卫两个王畿的申与虢:一者携犬戎破入宗周,弑幽王而立平王;另一者扶立周携王,与东迁的平王政权相对峙。清华简《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携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14],且有诸侯国出现了废弃携王、支持平王的政策转向历程[15]。两周由是撕裂。在北方,晋国肆意压迫周室的生存空间。对此,钱穆先生云:“晋文侯觊觎黄河西岸之土地,乃起兵杀携王,自为兼并。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2](48)无独有偶,原先监视宋人的郑国将战略重心由东方转移至西方,西灭东虢、郐,并与周室交恶,郑卿祝聃甚至射伤周王。《郑文公问太伯》中处处追赞郑国自始封以降历代郑君的功绩,但连“逐王于葛”这种事情都拿出来炫耀,可见彼时周室之窘况[16](118−122)。在南方,蛮楚冲破了汉阳诸姬拉成的阵线,“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17](1715)。在西部,秦人抓住时机,迅速填补了周室退出丰镐后的政治真空: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17](179)
这件事情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奠下了日后秦国崛起的基础。另一方面,秦襄公既得平王允地,便数代竭力伐戎。它导致的一个恶果是,部分不堪秦人打压的戎狄群落因此内迁,如“秦、晋迁陆浑戎于伊川”[10](394)。“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10](1005)更甚,平王轻易将岐西故地许给秦襄公的行为,直接让周室丢掉了其建构权威网络的地域凭依③。成周由此深陷封闭无望的政治空间中。
最为严重的是,身为周室远东代表的鲁国并未回护平王政权,这事实上造成了周姬权威网络的东部断裂。以周姬王族之权威身份论,“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17](1523)。以鲁与周室战略合作的结构性关系论,“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抱殷宋于肘掖间”[2](42)。然而鲁公对平王政权持不拥戴的态度,以至于平王崩时,鲁隐公亦未奔丧。后周桓王放低姿态,五聘于鲁。他竭意联欢于鲁的原因,乃是成周政权对外政策转向的切实需要。而鲁国则对成周极为冷淡,未见其有报聘之举,“隐十年之间,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鲁廷,而鲁朝聘之礼不行于王室,其罪大矣”[18](124)。对此,钱穆一针见血地指出:“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2](49)
二、“姜子携姬”:成周东部权威网络的重新整合
齐桓公的霸业可分为“创霸”“攘夷”与“尊王”三个时期[19](319−320):第一期自鲁庄公九年至十五年(前685—前679年)、第二期自鲁庄公三十年至鲁僖公四年(前664—前656年)④、第三期自鲁僖公四年至十七年(前656—前643年)。
齐桓公创霸之初,便着意灭掉谭、遂。鲁庄公十年(前684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10](182)。继而三年之后(前 681年),“夏六月,齐人灭遂”[10](193)。《左传》言用大师曰“灭”,而对于齐师灭谭的原因,其曰: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10](184−185)
与之相似,遂人被灭缘于其允诺参加北杏之盟而不至。不难看出,齐灭谭、遂的理由可谓牵强。齐桓公因谭人对自己不加礼遇而灭其国,那齐人灭他国社稷合乎礼乎?对此,后世学者疑惑说:“齐桓反国。以无礼灭谭。……伯者用心类如此。况望其以公灭私乎。”[20](213)齐国主持的北杏之盟意在团结诸夏,阻断成周政治的无序状态。若仅因一国不至便兴师剪灭,这岂不是陷诸夏于更大的混乱中?况且齐桓公是以北伐山戎、南拒蛮楚而扬名于后;以存邢救卫、扶助诸国而立信于诸侯。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他何以在号召建立正义的诸夏联盟时,会采用灭国的不义手段?
业师颜世安先生指出,齐桓公灭谭、遂两国看似不义,却符合东周初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强国兼并小国。如据学者测算,楚人在春秋时期共灭四五十国总是符合实际的[21](106)。但霸政建立以后,霸主不能轻易灭国,形成新的习惯。即便剪灭汉阳诸姬的楚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灭国行为。如楚庄王在破陈之后,意欲对陈室君臣“县之”,刚刚使齐归来的申叔斥责庄王的这种行为说:“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听此,“乃复国陈后”[17](1702)。
然而,齐灭谭、遂并非仅因时代局限。谭、遂地少民寡,于兴壮国力并无较大补益,反而让齐人徒背灭国的恶名。但若仔细辨析齐师所灭谭、遂两国的地域所在,其中有一个十分精妙的细节:它们均分布在济水南岸,紧邻东方强藩姬鲁。且遂国素为鲁之坚定附庸,司马迁言遂国被灭与鲁国紧密相关: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17](1487)
从这则史料不难看出,遂国之所以被鲁庄公“请献”,是在鲁师将败之下庄公急于献地媾和的无奈之举。所以,齐人看似用不义手段灭谭、遂的背后,实则隐伏着齐国“服鲁”的重要问题。这与齐人重整远东的谋霸计划有着结构性的关联。
实际上,灭谭、遂是齐桓公“服鲁”的曲线方针,其间颇为曲折。《春秋》言鲁庄公十年(前684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迁宿。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10](181)
材料中,齐宋联军数次不敌于鲁,且宋国一度遭鲁反侵,从中可见鲁国实力之雄厚。鉴于齐军被鲁国挫败于长勺与乘丘后的恶况,齐国开始调适其“服鲁”方针,由直接进攻鲁国转为孤立与包围之。齐桓公先是发起北杏之盟,利用多国会盟来孤立鲁国,“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10](193)。之后便灭谭、遂而戍之,将齐师开到了鲁国的家门口。
基于此,我们将齐桓公首次主持的北杏之盟与齐师灭谭、遂两国的战略布局结合来看,其巧妙之处在春秋争霸图上油然而现:以淮水支流沿岸的蔡国为起始点,东北向依次经过陈、宋,随后往北连接济水南岸的遂、谭,此为北线诸国;往南,经蔡、陈、宋之后连接邾国,此为南线各邦。南、北线诸国的汇合点就是盟主齐国,而被死死包围在南北两线中的正是鲁国。齐人会盟蔡、陈、宋、邾诸国,不但地理上打通了济水与淮水构筑的势力范围,而且还在战略上将鲁国严密围困。
至此,在成周王朝的政治版图上,出现了两个宏观的围困局面:第一处是在中原腹地。作为东方发展总基地的周都雒邑被秦、郑、晋、楚等非正义集团所围困。它事实上造成了成周政权与东部故有权威网络的深层断裂。与此相对应,身为周姬王族东方代表的鲁国,亦被齐桓公领导的东部创霸集团所围困。远东的政治格局由此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首先,齐国正式打破了周姬、齐姜同盟对殷商子姓遗族的围困局面,转向联络周边诸侯对鲁国进行反围困。西周时期,周姬王者以宗法分封体制确立了对诸夏的合法控制,“周姬及其兄弟之国在周代无疑享有政治与社会上的尊崇地位(虽未必为实力),而以诸侯为其舅国”[7](424)。其中,鲁姬与齐姜更是周室在东方的代表与最紧密的合作者,它们辅助周室震慑东方的反抗势力。管仲追忆齐国始建时就承担的职命是“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范围更是“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22](273)。而齐、鲁这两个东方大邦威慑的主要对象就是先代遗族,其中尤以宋为先朝圣国,势力最孤,“政治的势力都全在战胜的民族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包围在‘诸姬’重围里的宋国”[13](47)。及至齐桓公创霸,他一反西周遗制,主动解除了对子姓遗族的围困,并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服鲁”上,甚至一度产生过要灭鲁的想法。对此,殷人的复兴梦想与齐国的图霸事业不谋而合,“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2](60)。
而齐国帮助宋人破除困局的背后,隐伏着霸者权威累积的一个重要来源:三代古氏族之精神威权。 他们“虽政治实力多属微弱,但如宋郯鄫杞等国为古氏族之遗,或在精神上占有相当的崇高的地位”[7](424)。对此,颜世安先生说:“周初固然视殷为失败的敌国,同时却又视殷为同一个圈子中的前辈, 这是一个伟大的圈子,由历史上曾获王权的伟大姓族构成,周初人的观念似乎更多地是以进入这个圈子为荣耀,而不是以打败殷人为荣耀。”[23]这一点,中日两国学者看法相同。按照平势隆郎先生的“领域支配理论”⑤:“齐国非常希望能够把宋国的领域用于宣扬自己的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宋国是唯一作为殷商的一族而被周王朝封建的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和宋国扯上关系,就可以正当地通过宋国来占领殷商故地。”[8](263)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王者还是霸者,其权威的累积必须经由古代神圣氏族的共同认可。齐桓公不仅要以“服鲁”来确立其在东方的政治地位,还要凭借“联宋”来享有古代氏族的文化身份。因此,童书业先生说齐国在创霸时“只要征服了鲁和宋,霸业的基础便建筑完成了”[3](168)。
其次,远东格局的另一大改变是,齐国一改鲁国先前对成周政权的冷淡态度,主动联络周室,试图修补东部断裂的权威网络。在齐桓公创霸结束的前一年,曾有一次类似“尊王”的政治行为:
宋人背北杏之会。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22](245)
材料中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 680年) 。宋国违背先前的北杏盟约,齐因此“请师于周”。成周欣然派单伯会盟诸侯,与齐国一道迫使宋人请和。齐桓公此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不可思议,因为自周室衰微以来,诸侯间的征伐行为根本不用得到周室的批准。
实际上,这件事的重点在于成周与齐将会结成何种性质的统治关系。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成周王室对出兵东征欣然应允的初衷是,它“希望构筑起以‘小伯’为前提的‘王朝−卿士−霸主−诸侯’的等级式结构”[24](60)。换言之,成周政权希望齐国的东部整合战略是作为重建王者权威网络的一环而展开,霸政的推行必然不能以侵蚀王者权威为前提。但另一方面,齐桓公向成周王室请示这一特殊举动,意在取代鲁姬在东方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身份。齐国意图将旧有的“雒邑−曲阜”权威网络转型为“雒邑−营丘”。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王室的默许,双方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利益互惠。
综合来看,齐桓公在“服鲁”“联宋”以及首次尝试“尊王”的背后,隐伏着姜齐政权承接周姬王族政治文化身份的深层意图。我们不妨审视一下齐桓公在创霸时期主持的会盟,从中可以发现,先前的北杏之盟,大体上只是一群姬姓之外的二三流国家的会盟。齐虽为大国,但为姜姓,非周姬;蔡为周姬旁支之后,但为二流弱国;宋为殷族、陈为舜后、邾为鲁国附庸,它们均为外姓,且实力属于二三流之列。在一个无强姬宗邦参与的会盟中,很难言齐为霸国。齐桓公这个东方盟主更加名不符其实。
随后,齐国联合宋国,一意“服鲁”,并向西联系成周。至齐创霸的最后一年(前679年),齐、宋、陈、卫与郑共盟于鄄,《左传》言在这次会盟中“齐始伯也”。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参与这次会盟的诸侯国占据的文化地域与其氏族符号意义的层面考虑,即郑、卫为周姬之后,宋为子姓王族之后,陈相传为舜帝之后,再加之齐国力服的强鲁更是周姬王族在东土的代表。如是,我们又将看到一番别样的风景:大河南岸的齐都营丘取代了曲阜,成为新的东方政治中心。由这个中心向西南延伸,它在一线连接了卫、郑等周姬邦国;在另一线则贯通了宋、陈等先代遗族。它如同周初王室由西而东建构的“丰镐−雒邑−曲阜”权威网络,齐姜转而由东北向西南,反向伸出了一条同盟合作形式的政治文化轴。这条轴贯穿了姬姓王族、子姓王族以及先代圣后占据的文化地域,也是诸夏前两期结合的主要地域,“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自是霸业常在晋。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也”[2](60)。
而西周为震慑殷商子姓遗族等潜在反抗集团而结成的以“姬-姜”宗亲同盟关系,转型为齐国与以殷商子姓为代表的先代遗族势力紧密合作并裹挟周姬王族权威的新型权力格局。如果从氏族身份的角度看,这便是一种“姜子携姬”式的新型政治结构。无论是对于“尊王攘夷”的政治宣传,还是齐姜想继承周姬王者权威身份的意图,这种与神圣氏族的合作同盟以及地域链接,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神号召力量。
三、“攘夷”战略与霸政空间的拓展
齐桓公完成了“服鲁”与“联宋”等创霸计划后,下一步便开始“攘夷”(前679—前656年)。对此,《公羊传》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25](203)孔子亦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5](672)而管仲主导的攘夷事业,则首先放在了周朝北陲。鲁庄公三十年(前 664年),齐国正式伐山戎以救燕国。这次远征耗时日久,路途艰难,齐师“春往冬反,迷惑失道”[26](176)。返程之时,燕庄公又一路护送,不知不觉已入齐境。对此,齐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17](1488)于是齐国分割燕君所至之地予燕。此事传开,齐名始盛。
事实上,北伐山戎作为齐国第一次代表诸夏共同体远征的行动,它在缓解山戎对燕国侵扰的同时,还隐伏着齐国层累拓展霸政空间的重要问题。政治学学者认为,“如果一国实力不够,基本上不可能成为霸主,因为它终究过不了其他大国的反对这一关”[4]。纵观成周时局,西部的雒邑已被围困,南部的楚人亦活跃于江淮。齐桓公虽重整东方,但其在“联宋”的情况下,“服鲁”尚且周折艰难,更遑论直接针对西部强晋与南方大楚了,它唯有经营北部尚存空间。所以,齐桓公“攘夷”事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在于“如何以负面作用较小的方式扩展自己的权力,以免造成自我包围的效果”[4]。
而戎狄与诸夏杂处的局面一直就有,两者不光是以对抗为主。在东部地区,同盟与合作也是华夷关系的一大主题。如鲁国与楚丘戎就长期保持着会盟的关系:鲁隐公二年春(前721年),“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10](22−23)。以及鲁桓公二年(前710年),“公及戎盟于唐”[10](84)。楚丘之戎甚至曾西朝于周,想获得王室认可,“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22](200)。即便在华夷之辨前的东部族群冲突中,诸夏也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如鲁庄公十八年(前676年),“夏,公追戎于济西”[22](33)。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年),“夏,公至自伐戎”[22](38)。齐人虽因内乱暂时不敌于戎,但来自中部诸侯的支持十分强劲,鲁桓公六年(706年),“齐侯使乞师于郑……六月,大败戎师”[22](219)。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盛赞庄公的武功时便提及郑国“东伐齐酄之戎为彻”,这里的“齐酄之戎”便是远居于鲁西的济水之戎[27]。况且戎狄在与中原诸国的交战中,多是在寒冬时节乘虚而入,而交战结果,中原诸国是占据上风的。即便后来卫国被戎狄所灭,也是因为卫懿公好鹤以致国人离心所致,并不能直接说明戎狄之强,诸夏之弱。也就是说,至少在华夷之辨提出以前,戎狄的威胁尚不能过分言重。而且,齐桓公伐戎前曾知会过鲁国,双方“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22](260)。鲁廷群臣出于自己的政治军事考虑而未参与齐国的这次军事行动。等到齐国北伐胜利之后,齐桓公又向鲁国炫耀,“齐侯来献戎捷”。对此,《左传》言齐人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22](260)事实上,齐人此举背后或别有深意。彼时山戎虽多侵扰燕地,但山戎问题并非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且山戎跟中原他国也并无直接冲突。因此,齐若为燕而会盟征诸侯之师,千里犯险,未免私欲过重,与诸夏盟体之礼德信义文化亦有冲突。而齐在出征前知会鲁国的设想是,若齐鲁同盟伐戎,无非代表着周姬之东方代表与东方诸夏的盟主合手而平北,这对于霸政秩序的构建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即便齐鲁同盟不成,虢公尚能“败犬戎于渭汭”[22](264),以齐国多年聚集之力,伐戎必会取胜。取胜而再献戎于鲁,亦能彰显其东方霸主地位。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山戎距齐千里,路途远险。且《管子》说桓公在征戎路途中因见怪物而心生畏惧,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实质问题。反而,因为管仲力促此次远征,安定桓公前行,这恰恰说明这位齐桓霸政的设计者对于齐军败戎的能力是毫不怀疑的⑥。况且早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前 666年)时,齐军就已经秉承王命,奔伐卫国。所以,虽然北途坎坷,于齐而言也并非绝难之事。
更为重要的是,“攘夷”战略背后,实则还隐伏着齐国谋霸的宏观布局。姜齐在创霸阶段,已经完成了对周室东邦鲁国的压制,但他若想要进一步汲取成周王者的权威,就必须将势力的触角伸入到中原大国与南楚构筑的包围圈中。最巧妙的方法就是“攘夷”,原因是在成周的华夷版图上,与诸夏杂然相处的有三条戎狄生活带[28]:第一条是北方戎狄带,有北戎、无终戎以及狐氏戎等,它们大抵在晋国北境;还有一部分单独生活在更为偏远的地方,如齐桓公北伐的山戎。第二条是以蛮楚为首的南方戎狄带,其势最强,对诸夏多有觊觎之心。第三条则由东往西贯穿了整个周朝的大河核心地带,如位于大河下游的楚丘戎、戎州己氏之戎;位于中原腹地的阴戎、陆浑戎、伊洛戎、九州戎、茅戎、姜戎等;再一部则散落在宗周故地及以西地带,如犬戎、骊戎乃至西戎。流行的观点认为,齐伐山戎在地缘政治学上说不通。此前侵扰齐国的北戎和齐国征伐的山戎并非一支[29],双方素未结怨。但若以此来看,正是齐人征伐了与其未有瓜葛的山戎,才在“身份上”产生了对整个戎狄族群的地缘关系。只要齐国蓄力足够,它可以借夷祸染指任何地区。楚人曾对来伐的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22](273)事实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背后,隐伏的便是这种身份关系。齐人在远征了同样风马牛不相及的山戎后,才与南方的楚产生了同质的矛盾。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戎狄地带不光是齐国霸政成长的生命带,也是齐桓公构造新型权威身份的重要条件。
基于这个立论,齐国整个“攘夷”阶段的政策走向便都清晰了。“攘夷”是霸政走出东部进而渗入成周封锁圈乃至在中原展开的利器。齐桓公在创霸阶段结束时,尚能“服鲁”,但却不足以打败体系内的楚、晋大国。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管仲建议桓公北伐山戎,以地理空间换取齐国聚合诸侯的实力与威望。这个政策效果显著,诸夏地区因之产生了聚合的连锁效应。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东部攘夷集团迅速结成,并急速向西部、南部展开。鲁闵公元年(前 661年),齐国救邢, 管仲正式提出华夷之辨:“戎狄豺狼, 不可厌也,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22](262)随后,齐国援卫救郑,诸夏聚合的形势如火如荼。至管仲“攘夷”战略实施的最后一年(前656年), 齐国终于组成南伐联盟,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军队征讨楚人: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22](273−274)
材料中,齐国兴师南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征贡包茅,二是顺便责问三个世纪前的周昭王为何南征而不复?对于这种说辞,楚人深感无辜,因为彼时不按时纳贡的诸侯,绝非楚国一家。但在八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还是允诺要恢复对周室的贡茅,但对王者之死与楚相关这一点拒不承认。实际上,齐国以这两个理由而侵楚,可谓牵强。对此,周方银先生说:“显然,管仲责问楚国的两个罪名,其使用的时机和对象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可以说有十分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4]但正是基于这种情形,由齐桓公北伐开启的攘夷战略才能在七年间层层累积出可以与楚相较量的实力,齐桓公以“攘楚”保住诸夏文明的历史形象也由此塑成。
更具历史巧合的是,正是由于齐桓伐戎,存邢救卫,才导致戎人不敢再袭扰东方。后来戎人的进扰重心相继转移到了西部的成周、晋与郑等三国。晋国在与戎人的多次交锋中渐趋实现了军制的完善与实力的聚集,为接替齐桓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成周与郑则在戎狄的打击下更加衰弱。而且成周政权频繁请齐、晋霸者“平戎”或“戍周”:鲁僖公十二年(前648年),“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次年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22](290−291)。鲁僖公十六年(前 644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戍周”[22](300)。鲁昭公二十六年(前 516年),“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22](777)。次年秋,“会于扈,令戍周,且谋纳公也”[22](784)。以及鲁定公六年(前504年),“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22](823)。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霸政势力范围的西部拓展,为之后晋文公顺利承接霸业埋下了伏笔。齐国领导下的谋霸集团也因此冲脱东部藩篱,成功侵蚀了周姬王者的权威。
事实上,在齐国刚完成“攘夷”大业时,成周王族便察觉到霸政对周姬威权的侵蚀。前文提到,齐桓公“创霸”结束的前一年(前 680年),曾有一次请周师会盟伐宋的尊王行为。当时成周之所以欣然应允,是希望齐国能够重新连接成周在东方的权威网络。但后来的势态演进远远超出了周室当初的设想。成周政权意识到齐国并不仅仅在整合东部地区,它试图以“攘夷”的方式来拓展霸政的范围,进而重塑王朝的权威结构。所以,在齐国“攘夷”结束后的“尊王”阶段,周室反而一改先前的态度,暗中破坏齐人的霸政建设。在伐楚后的次年(前 655年),齐国发起了首止之会。周惠王阴使人劝告郑公不要赴会:
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22](278)
材料中,王室与郑伯对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表面观之,王室已经意识到了东部霸政集团对成周的威胁远比楚、晋、郑等国的围困更严重。更进一步,成周政权似乎并不认为戎狄之患能动摇王室的根基,因为其意欲所从的楚国,正是东周时代最庞大的夷狄势力。这与齐桓公靠“攘楚”来保留诸夏文明的观点似乎有所出入。对此,韩非说齐人伐楚乃是“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26](275)。
齐桓公“尊王”事业的顶峰发生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年)。此年,他号召诸夏共盟于葵丘。会盟之前,东部霸政集团已经正式拥立周襄王即位,这与钱穆先生所说的周平王乃西部非正义集团拥立、因此被东方诸侯所不齿的情形迥然相异。但成周使者宰孔却依然暗中破坏齐人霸业: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22](285)
材料中,齐国虽有“尊王攘夷”之功,但宰孔依然认为其“不务德”。这里的“德”与后来楚庄王问鼎时王孙满说的“在德不在鼎”实为同质,它指的便是周姬王者权威的合法性依据⑦。对此,颜世安先生的判断可谓卓识,他说:“东方的新权力体制建立过程中,尊周不具有根本意义……攘夷与尊王绝非一回事。”[30]“服鲁”和“尊王”都是霸者对周姬王族权威的汲取。
四、结语
齐桓公霸业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对成周旧有权威管控网络进行连接与重塑的产物。察其轨辙,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起初,西周王族建构了缜密的政治管控网络:宗周镐京为王者权威哲学的诞生地,“天命”与“周德”是维系它的两大支柱。成周雒邑是王室向东发展的总基地,而曲阜更是延伸王者权威的东方中心。由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在无形之中诞生,为西周国家配备了一种至关紧要的稳定性力量和因素”[31](104)。在此轴南北,错落分散着周姬王者的宗亲与盟友,如在《封许之命》的册文中,周王多次强调这个合作关系,“则惟汝吕丁,肇佑文王”,“ 扞辅武王”[32](118)。因此,“西周诸侯国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王室随意赐予其亲属和地方首领以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并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31](105)。而他们警戒、围困的中心正是先代王族余脉与外部夷狄。然周姬王者既失宗周,其权威哲学出现了崩塌迹象:“骏命不易”的天命观变成“天命靡常”,王者专享的“周德”已被上天厌弃。成周既无丰镐故地凭依,便迅速堕入骤然失序的政治空间中。更甚,身为远东宗邦的鲁国并未回护平王政权,这事实上造成了周姬权威网络的东部断裂。在这种情形下,诸侯间的混战便隐有诸国大族在王族衰败后重新争夺族姓地位的内涵。
齐桓公既然决意谋建霸业,那么如何重新连接东部地区同成周间的政治管控网络,便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齐国在最初的“创霸”时段,灭谭、遂不过为一表象,它有着精妙的地缘安排,其根本目的则是取代鲁国在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齐国一改西周时代姜姬合作的政治传统,主动联络宋、陈等先代遗族会盟。这事实上等于解除了西周时期周室针对殷商等潜在反抗势力设置的包围圈,而作为周室代表的鲁国却被东部创霸集团进行了反包围。远东政局由此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这些改变的背后,实则隐伏着姜齐集团承接周姬王族政治文化身份的深层意图。对于这一点,成周王室起初并未明显察觉。所以周王欣然派遣卿士参与东方的会盟,王室期待齐国能在取代鲁国后,重连成周政权的东部权威网络。
但随后的势态演进,逐渐超出了成周的设想。齐国在“创霸”之后进入了“攘夷”时段。事实上,无论是对内“尊王”还是对外“攘夷”,它们都对吸引诸侯参与霸政进而使之成为一种稳定的权力体制发挥了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给霸政的扩展提供了绝佳的时代契机。齐国能够北伐与齐素未有瓜葛的山戎,就能南征“风马牛不相及”的楚国,以至于借“平戎”与“戍周”来侵蚀成周的政治权威。至此,成周政权意识到,齐国不仅是在整合东部地区,它也以“尊王攘夷”的方式重塑了王朝的权威结构。所以,周室一改先前的态度,暗中破坏齐人的霸政建设,但此时霸者的合法性来源已经汇成,两个世纪的霸政时代由此开启。
注释:
①胡适在分析了《商颂》与《玄鸟》篇后指出,殷民族亡国之后的历史,似乎“曾有过一个民族复兴殷商的悬记,也曾有过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详见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 2013年版,第50页。)
②在宗周建构的政治空间中,东都雒邑是一个控驭多方的极佳据点,但也因此,它成为各支势力环伺的缓冲地带,此处的政治空间易被多方势力共同挤压、消解。时人对此已有察觉,如《国语•郑语》云:“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闲乎!’”
③许倬云先生曾疑惑说:“平王东迁后,宗周故地未尝全失……是以周人旧有畿辅之地,只少岐西一带。周人凭借旧业,再加上东都储积,有郑、虢大藩,左右提挈,王室恢复声威,应非不可能。”对此,许先生将成周之所以未能恢复旧业的原因归结于“东周二十五王,全不振作,内乱频仍,终于澌灭”。(详见许倬云:《周东迁始末》,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723页。)事实上,周室东迁与放弃故地的行为,也造成了其数百年来所建构的王者哲学失去了地域凭依,其统治的合理性严重受损。
④童书业先生将齐国霸政的“攘夷”期划定为鲁庄公十五年至鲁僖公四年(前679—前656年)。事实上,齐国北伐山戎是其“攘夷”战略的首要环节,它对齐国拓展霸政空间意义重大。对此,颜世安先生认为齐国之“攘夷”当从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开始。本文赞同并采用这种观点。(详见颜世安:《齐桓公霸政基础之探讨》,《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第114页。)
⑤平势隆郎认为,夏、商、周三代统治的疆土是一种“文化地域”,也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宣扬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母体地域”。据其观察,无论是姜齐还是田齐,它们在追溯历史、宣扬自己正统性以及领域支配正当性的时候,都很关注自身与夏、商(尤其是与商)之间的继承关系。如在“叔尸镈”铭中,“齐人通过继承血脉这一方法巧妙地论述了自己对于与夏王朝、商王朝相关领域具有正当的统治权”。(详见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周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31、262页。)
⑥《管子》传齐桓公在征伐北戎的途中,因遇到怪物而萌生惧惑曰:“事其不济乎!”但管仲却以此为祥瑞之兆,并言“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详见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0页。)从中可以看出,管仲将此次北伐视为霸者将兴的重要事件。
⑦“周德”的核心是“文王之德”,它是两周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概念。有几个解释值得注意。平势隆郎指出,“在西周时代(德是一种咒力、灵力)和战国时代(与现代意义的‘德’意思相近)的意思就大相径庭”。(参见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周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2页)。李泽厚先生认为周德代表的是一套行为,“主要是与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6−87页。)小仓芳彦的见解也值得重视,该氏以“省”与“德”在甲骨卜辞中十分相近的字形关系出发,指出“‘德’原来与王者所进行的‘省’事有关,是作为下述实际行动的概念而发挥作用的,即为征发谷物与兵赋而巡行,有时巡行转为征发,而当对方屈服时则饶恕”。(详见小仓芳彦:《á左传ñ中的霸与德——“德”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刘俊文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18页。)综此,可以看出,“周德”在两方面反复深化了一个认识:一方面,文王享德与天命,突出的是上天和神圣祖先的灵力色彩;第二,武王凭此进行的征伐,强调了周姬王者专享征伐权力的事实。两者构成了周室拓展王者政治空间的合法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