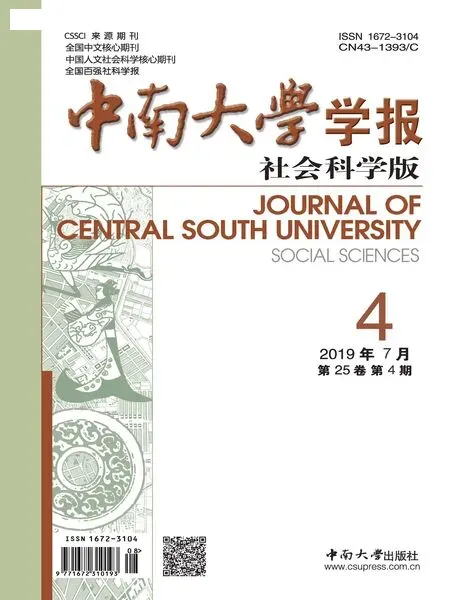论康德哲学中审美与幸福的关系
张齐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美与幸福是人生在世重要的价值体验,康德对二者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以往的康德哲学研究中,对幸福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梳理,大多是将幸福置于与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域中。然而对幸福与审美的关系,他们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偶有零星见解,也存在颇多误会。深受康德影响的诗人席勒曾说:“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1]今亦有人认为康德美学“实际上对幸福主义伦理学作了很大的让步”[2]。事实上,康德哲学中的幸福是在不同层次上探讨的,而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也不限于美,还涉及崇高。若要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需对它们各自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然后才能厘清二者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产生何种关系。笔者愿就前贤致思未尽处,对此作尽可能全面的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康德幸福论的层次
幸福(glückseligkeit)诚然是康德伦理学的重要话题,但学界一般认为,康德对幸福概念并没有做出十分明确的界定①。康德本人说过:“幸福的概念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以至于每一个人尽管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3](425)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之中,对于幸福的抉择首先是笼罩在道德境界的眷注之下的。“即便道德,真正说来也不是我们如何使得自己幸福的学说,而是我们应当如何配享幸福的学说。”[4](137)这里与道德对举的幸福只是“自然幸福”,仅仅限于感性欲求的满足——康德著作中的幸福绝大多数都指此而言。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认为“幸福是我们一切偏好(neigung)的满足(既在广度上就满足的杂多性而言,也在深度上就程度而言,还在绵延上就存续而言)”[5](514)。在康德哲学中,无论是幸福,还是道德,都是关联着人的意志(作为欲求能力)来探讨的。“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立法的原则。”[4](33)幸福原则是经验性的,涉及欲求能力的质料,与主体的愉快或不快的情感相关,偏重于主体的感受性(感性冲动、刺激),会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变化,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根本不能设想全体的一致性,故只可作为实践的准则,不可作为实践的法则。若依幸福原则而行,即使有合于义务的行为,也会因为缺少出于义务的动机,而使道德成为他律的道德;唯有按照那种只规定意志,不管是否能够达到结果的无条件的命令去行动,才是自律的道德。真正说来,这才是康德心有所属的道德。但他并未弃幸福于不顾。“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对幸福的要求,而是仅仅要求只要谈到义务,就根本不考虑幸福。”[4](99)依康德之见,甚至照顾自己的幸福在某种状态下也有可能是义务,这不仅因为幸福包含着更易履行义务的手段,也因为幸福的缺乏包含着更易逾越甚而践踏义务的诱惑。不过,康德着意要提醒人们留心的是,只促进自己的幸福,永远不可能是义务,更不可能是义务的原则。
可以看出,康德所作的这种分判,是对启蒙思想家霍尔巴哈、爱尔维修等人以道德为幸福手段的幸福主义伦理学的有力反拨,他使道德重新确立为人所当为的至高之善,而对幸福(自然幸福)有所贬抑。然而,毕竟康德对幸福还有另一种界定:“幸福是尘世中一个理性存在者的状态,对这个理性存在者来说,就他的实存的整体而言一切都按照愿望和意志进行。”[4](132)道德依纯粹意志而行,当然也涉及相应的欲求能力是否实现的问题,亦会引致幸福与否的感受。那么,是否存在“自然幸福”之外的“道德幸福”?
循道德律而行意味着对感性偏好的割舍,这需要自我强制,所以必将导致痛苦。但道德律也会唤起对它“敬重的情感”,这种情感并非道德律的根据,而是由道德律所引起的,它是对法则的服从,很难说是愉快的。因此“道德上的幸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康德又认为,对于那些认识到道德义务的崇高伟大的人来说,他们专注于道德修省,尽管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在善中进步,产生“满意和道德上的幸福”[6](75)。康德在有些场合又否定了该提法,认为“这种满意在其来源上就是对自己的人格的满意。自由本身以这样的方式将能够有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不能叫做幸福”[4](126)。他鲜明地表示:“某种不依据经验性的原因的道德上的幸福,而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荒唐说法。”[7](389)所以他反对“道德幸福”与“自然幸福”的区分,而宁愿将这种“对自己的人格及其特有的道德行为的满足”称之为“自己的完善”,而不是“自己的幸福”。康德所作的这种区分煞费苦心,他旨在尽力避免伊壁鸠鲁派将道德当作达致幸福手段的谬误以及斯多亚派将德性本身当作幸福的缺失。但康德在论及“他人的幸福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时,又认为除了促进他人“自然的福祉”之外,“他人道德上的福乐也属于其幸福,促成这种幸福对我们来说是义务”[7](406)。应该说,康德不同场合的表述多少有些自相抵牾,然揆其本心,无非是提醒人们勿以幸福为道德的根据,勿以道德为幸福的手段。但实践理性也毕竟有其欲求,当这种欲求得到满足时,也可以带来某种幸福感,这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②。故而,我们仍然有理由说,“道德上的幸福”是可能的,不过这幸福只是道德的一个附带的偶然结果(道德更有可能伴随着痛苦),而绝不能作为其必然的规定根据。鉴于此,我们认为“道德幸福”的说法可以保留,但要格外注意其使用限度。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一味地以“自然幸福”的实现为最高鹄的,是康德所极力摒弃的。但若不考虑“自然幸福”,只专注于道德践履,对于以“求达至善之术”作为自己学思追求的哲人来说,也失之偏颇。“仅仅幸福,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还远远不是完备的善。如果幸福不与配享幸福亦即道德上的善行结合起来,理性则并不赞同这样的幸福(无论偏好如何期望这种幸福)。但仅仅道德性,以及随之还有配享幸福,也远远不是完备的善。要完成这样的善,那不曾行事不配享幸福的人就必须能够希望分享幸福。”[5](519)所谓完备的善,即至善(或称圆善),必然要求幸福和道德的精确配称。德福一致的话题早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已经有深入探讨,但在康德看来,无论是伊壁鸠鲁派的“幸福就是整个至善,道德只是谋求幸福的手段”,还是斯多亚派的“道德就是整个至善,幸福只不过是对拥有道德的意识”,都是基于同一律来寻求道德和幸福的结合,实际上两者都失之偏颇。在康德所构想的新的至善格局中,道德仍是首要因素,只有道德才使至善具有了至上性。只有受道德制约,并作为道德修省的必要结果的幸福才构成了至善的第二要素,而两者的精确配称方使至善成为完备圆满的善。因此,至善的实现首先有待于受道德法则规定的意志的意向与道德法则完全适合,但这是作为一个感性存在者的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达到的,这便需要有人在时间上的无限存在作为保证,故欲使至善在实践上可能,必须悬设灵魂不死。只有在德性纯化的前提之下,幸福才成为至善中值得求取的另一要素。但幸福与道德价值的精确配称在世界的单纯自然进程当中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康德又认为,只有在一个道德的、全能的意志的主宰之下,至善才成为可能,所以必须悬设上帝存在。这就使得康德的道德哲学走向了宗教,成为道德神学。但在批判哲学的视野下,被重新赋义的至善绝不是对基督教上帝之国的简单摹写,而已然成为一种虚灵不昧的理念。诚然,这是永远不可能在实然的感性世界实现的,但作为一种应然的希望,它不限于地域、民族和时代,而具有终极意义,成为整个人类的至高向往。与之相应,其所蕴涵的幸福乃是“至善中的幸福”。在此至善格局下的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幸福”,也不限于“地上的幸福”“今生的幸福”,它指向所有人,指向天堂和永恒。所以康德也将其称作“永福”(seligkeit)③。
综上所述,基于感性欲求满足的“自然幸福”、基于道德完善而产生满足的“道德幸福”,基于“德福配称”的至善格局的“永福”,构成了康德以欲求能力为基石的幸福论在价值上的递进层次。与之相应,审美与幸福的关系便复杂起来,所以若要厘清此一问题,便需知晓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幸福,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审美,否则均会顾此失彼。
二、审美与自然幸福
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包括对美与崇高的分析。对象何以为美所需的条件,康德是从对鉴赏(geschmack)判断的分析来揭示的。康德将鉴赏分为“玄想性的鉴赏”和作为感官鉴赏的“经验性鉴赏”。前者的规则是先天地建立起来的,预示着必然性和对每个人的有效性;后者的规则是经验性的,不能要求普遍性、必然性[8](234)。在对美作分析时,康德所说的“鉴赏判断”一般是指前一种,他也称之为“纯粹鉴赏判断”或“真正的鉴赏判断”。
此鉴赏判断把对象的表象通过想象力与主体的愉快或不快的情感相联系。一般来讲,愉快或不快的情感总是与欲求能力相关,但鉴赏判断的这种情感却与欲求能力无关,它是不带任何利害(interesse)④的。正因为如此,它将自己与“快适”(angenehme)和善区别开来,因为这两者都具有与欲求能力的关系,都是和利害结合着的。两者当然也会产生愉悦或不愉悦,不过前者是以病理学上的东西为条件的,后者则是纯粹实践性的,它们均与对象的实存相关。鉴赏判断则是静观的,它对于对象的实存并不关心,只是将对象的表象形式关联于主体的愉快或不快的情感。鉴赏判断所引起的是一种愉悦的情感(gefühl),而快适则是一种愉悦的感觉(empfindung)。康德明确区分了感觉和情感,将感觉界定为“感官的一个客观的表象”,而将“任何时候都必定仅仅保持为主观的、绝对不可能构成一个对象的表象的那种东西”称为情感[9](213)。这就在愉悦的性质方面为鉴赏判断和快适作了确凿辨析。由于快适意味着感官欲望的满足,也属于“自然幸福”的一种,所以在此意义上,美超越了“自然幸福”。
此鉴赏判断中所感受到的美无须凭借概念而能使人普遍愉悦。就其不依赖于概念而使人愉快而言,它与快适相似。但是,快适的判断是建立在私人感觉之上的,其有效性仅适用于个人。感官的快适所适用的原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鉴赏(感官的鉴赏)。”[9](220)也就是说,人们的感官快适具有独特性,不能希求普遍性。康德也留意到,在对快适的评判中,人们也会发现普遍性的情况(如大家公认某一道菜为美食),也会称那些善于运用感官享受的快意为人助兴者为有鉴赏(有品味)的。但这种普遍性是通过比较而来的,只有大体上的规则,而美的鉴赏判断所采取或所要求的乃是全体性的规则。康德将鉴赏判断的普遍性归结为先验的理由——人的“心灵状态的普遍能传达性”,这作为鉴赏判断的主观条件,并为其奠定基础,这使得在此判断之中,美的判断总是先行于愉快感。假如在给予的对象上的愉快是先行的,那这一类愉快就只是感官的快意。通过判断愉快感的普遍与否以及发生次序,使得美与“自然幸福”区别开来。
此鉴赏判断既是无利害的,便没有从主体的利害关切所说起的“主观目的”,也没有从对象说起的“有用性”或“完善性”的“客观目的”。所以,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的,“惟有一个对象的表象中不带任何目的(无论是客观的目的还是主观的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因而惟有一个对象借以被给予我们的表象中的合目的性的纯然形式”[9](229)。康德所说的形式剔掉了一切可能引起感官享受的东西,他极力将纯粹鉴赏判断与“魅力(reiz)”和“感动(ruhrüng)”划清界限。后者是经验性的、质料的愉悦,属于感官判断,而不属于纯粹的、形式的愉悦,因而不是真正的鉴赏判断。针对有些人认为魅力(如颜色和音调)自身单独就足以称为美的论调,康德认为,只有就它们都是纯粹的而言,才有资格被视为美的,但这种纯粹性已经涉及形式的规定,所以它们之被算作美,仍然与其质料无关。这种基于形式与质料的谨慎区分,成为美有别于“自然幸福”的另一证明。
此外,在作纯粹鉴赏判断时,必然要涉及其客体的表象及主体的愉悦情感。感官享受的对象与愉悦的关系因其囿于经验的快适,系于偏爱而无法判断它对所有人具有必然性。审美对象对于愉悦的模态则有其必然性。“鉴赏判断所预先确定的必然性就是共感的理念。”[9](246)此共感原则只通过情感而非概念,却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何者令人喜欢、何者令人讨厌。只有预设了此共感为前提,才能作鉴赏判断,鉴赏判断的主观必然性才能被表现为客观的。康德所理解的共感并非偏滞于经验的感官知觉,而是先验的理念预设,故基于共感的美也不是经验性的,“属于幸福(按:自然幸福)概念的一切要素都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都必须借自经验”[3](425)。这也使得此“美”与 “自然幸福”迥异其趣。
康德通过对纯粹鉴赏判断的严格界定捕捉到美的虚灵气韵。这“美”无疑是超越了“自然幸福”的。然而据其分判,真正能够称得上美的事物实在少之又少。康德也仅仅举出了花、许多鸟类(鹦鹉、蜂鸟、极乐鸟)、大量海洋贝类、希腊式的素描、卷叶饰、音乐中的幻想曲等,作为他所心仪的美的例证。但人们在实际的审美体验中所感受到的美,并不完全合于纯粹鉴赏判断,而往往呈现出极为混杂的状态,以“不纯粹的鉴赏判断”为主。这种鉴赏判断有两类,一类依赖于完善性概念,一类则依赖于魅力和感动等经验性的感官愉悦。前者所体验的美等同于善,而后者所体验的美则混合了快适。在后者的意义上,不纯粹的鉴赏判断之美也可视作某种“自然幸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通常的自然美和艺术美鉴赏中,都混杂着色声香味等直接作用于感官的、经验性的成分,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感性欲求,所以绝非纯粹鉴赏判断的美。正因如此,纯粹鉴赏判断之美超越了“自然幸福”,而“不纯粹的鉴赏判断”之美则掺合了“自然幸福”。
审美判断力不仅包括美的分析论,也包括崇高的分析论。康德对崇高仍然采取的是“先验的解释”,他根据崇高的情感特征(内心激动)及其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的关系,将崇高划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
说到“数学的崇高”,康德认为崇高就是“与之相比别的一切都是小的”[9](259)、“绝对地大的东西”[9](257)。这种大并不是数学的实际量度,而是审美的单纯直观。在面对自然界或人工建造的壮阔庞大的景象时,人把对象之量纳入想象力,把握对象的各部分表象和总括对象的全部直观。但因其量实在太大,把握推进越远,总括就越困难,并将很快达到其最大值。于是,它所不能总括的“绝对大”的东西便会霍然呈露。想象力在此表现出对“最大的感性能力的不适合性”,但若仅有这“绝对大”, 将给人压抑与不愉快感。然而,恰恰是这种不足反而使我们感到自己有独立的纯粹的理性,凭借这种理性,将使我们穿透压抑与不愉悦感,获得另一种愉悦。显然,这是超越了感官享受的愉悦。
至于“力学的崇高”,则是人们在面对自然界极大的威力凌逼时产生的。被评判为崇高的自然界首先必须表现为激起畏惧之感的,但吊诡的是,“谁感到畏惧,他就根本不能对自然的崇高者作出判断”[9](271)。这是因为,虽然在这些自然威力面前,人试图用来与之相抗的肉体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但只要处于安全的地位,这些景象越是可畏惧,便越吸引人,因为它使我们的灵魂提升,并显露出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此即以道德理性为依据的人格性,从而意识到自己超越于自然之上的使命。借此,人可获得从重压下透出的愉悦之感。这便是“力学的崇高”的来由。在康德看来,能够超越自然威力评判崇高的人需要“道德理念的发展”,这也意味着他必然要超越于感性欲求的满足之上。
康德对美和崇高的分析舍弃了自己早年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那种经验性的描述方式,他也扬弃了博克的思路,而着力探讨美和崇高不为经验性原则所局囿的先天原则。在“美的分析论”中,尽管那些不纯粹的鉴赏判断可能会混同于经验性的“自然幸福”,但真正为康德所心仪的却是纯粹鉴赏判断所透显的美。无论是美,还是崇高,都被纳入先验哲学体系,这意味着它们对生理或心理感觉的超越,前者是以不沾染利害的方式超越,后者是以由抵抗而穿透利害的方式超越——实际上,这也正是审美对“自然幸福”的超越。
三、审美与道德幸福及永福
如前所述,配享“永福”的首要条件便是人类德性足够纯粹。所以要厘清审美与“永福”的关系,也就需先对审美与“道德幸福”的关系作一番考察。一般而言,人们向更加纯粹的道德趋近,更有可能伴随着感性上刻骨铭心的痛苦。因此“道德幸福”对人而言只具有可能性,并不具有必然性。此外,若要使道德幸福哪怕只是具有可能性,也要先有道德。这就先要探讨审美与道德的关系。众所周知,康德试图用判断力的批判来沟通自然概念的领地和自由概念的领地,而审美判断力又是“在根本上属于”判断力,故可作为通向道德的重要中介,这也是许多学者赞同并竭力论证的观点。然而,康德事实上是否真正达到这一目的,则是颇可质疑的。康德所论审美主要是对自然美、艺术美和崇高的评判,这三者与道德发生关系的进路并不相同,需要分别加以探讨。此外,他还专门讨论了作为“美的理想”的人,在我们看来,只有立足于此,才能真正洞彻康德哲学中审美与道德乃至“道德幸福”关联的閟机。
所谓自然美,顾名思义,就是对自然界的事物所作的认其为美的评判。据康德之见,这种评判不考虑自然事物的质料,排除其丰富多彩的作为魅力和感动的色声香味等因素,只针对其单纯形式,而无须对此事物是什么有某种概念,它没有任何利害而直接令人喜爱,虽然是主观的却具有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普遍性。自然美所唤起的是一种直接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基于道德情感的净化而产生的。但康德实际上并没有证明自然美何以可能作为通向道德的中介,而更多的是使用“亲缘关系”“类似性”“内在的亲和性”之类的表述来阐述两者的关联。但相似并不意味着必定相通,所以康德反而频频表达了这种意思:“对自然的美拥有一种直接的兴趣,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善的灵魂的特征。”[9](311)“谁对自然的美直接感兴趣,在他那里,人们就有理由至少猜测有一种对善的道德意向的禀赋。”[9](313)如此看来,倒是道德素质成了能够欣赏自然美的先决条件。由此,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便是:自然美的鉴赏无助于人“道德幸福”的提升。
再看艺术美。康德将艺术分作“机械的艺术”和“审美的(感性的)艺术”,“ 审美的(感性的)艺术”又可分作“快适的艺术”和“美的艺术”。机械的艺术只能通过概念来令人愉悦,把人引向认识或说教的目的;快适的艺术单纯以享受为目的,其意图与感官的愉悦相偕相随;而美的艺术表现为“无意图的意图”,这与自然美的无意图是趋近的。康德说:“美的艺术的产品中的合目的性虽然是有意的,但却毕竟不显得是有意的;也就是说,美的艺术必须被视为自然,虽然人们意识到它是艺术。”[9](320)显然,只有这种“美的艺术”才是康德最为推崇的,也只有在人们知道它是艺术但看起来却又像是自然时,才能被称为美的。这便决定了“美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不如自然美那么密切。康德还对诸种“美的艺术”的审美价值作了比较,这价值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他们与理念的关系。如果美的艺术不和道德理念或近或远地结合起来,那就只会被用作消遣,人们愈是利用这种消遣,便愈会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康德敏锐地观察到:“鉴赏的行家们不仅往往,而且甚至是习惯性地表现出爱慕虚荣、自以为是和败坏道德的热情,也许比其他人更不可能要求具有忠实于道德原理的优点。”[9](311)所以,对于艺术美的兴趣,“根本不能充当一种忠实于道德上的善,或者哪怕倾向于此的思维方式的证明”[9](311)。
总的来说,不论是对自然美还是艺术美的评判,都是鉴赏,“鉴赏包含着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性的趋势”[8](238)。但这只是“外在表现上的道德性”,而真正的道德性却是内在的、无待于外的。所以,鉴赏只能充当一种预备条件,而不能真正成为通向道德的桥梁。尽管康德想要证成审美的中介作用,却只是更加凸显了道德的至高地位。“对于建立鉴赏来说的真正预科就是发展道德理念和培养道德情感;因为只有当感性与道德情感达到一致时,纯正的鉴赏才能获得一种确定的、不变的形式。”[9](371)根据康德的表述,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都并不必然通向道德,亦无法导致道德上的幸福。
崇高虽然也属于审美评判,但却是有别于鉴赏的另一维度。在康德看来,美和崇高都不取决于某一确定的概念,却毕竟与概念相关。美涉及对象的形式和限制;而崇高则可以在无形式的对象及由此对象所诱发而表现出的无限制上发现。在对崇高进行分析时,康德更多的是借自然界的星空雷电、高山断崖、激流瀑布、荒郊原野等来加以阐释,但他的真正用意却不是让人在自然对象中发现崇高,他只是要说明,适用于以这种自然对象展现的崇高是“在心灵中发现的”。自然界的崇高不像自然美那样在其形式中就有某种合目的性,它对我们的判断力而言是违反目的的,但越是这样,便越是被判断为崇高。“因为真正的崇高者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是仅仅涉及理性的理念。”[9](255)不论是“力学的崇高”,还是“数学的崇高”,人们之所以能感受到它,就在于心灵能穿透感性的有限性,而领悟那超越一切感官尺度的东西,亦即无限的、理性的理念。在崇高的评判中,人们正是把对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替换到了自然客体上,因此,“对自然中的崇高者的情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9](267)。人们对这种人性理念(使命)的自觉先要经历感性上的陶冶,因此对于崇高的判断要比自然美更难以指望普遍认同,它需要更多的教养,需要心灵对于理念有相当的敏感度。“事实上,没有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通过文化的准备而称之为崇高的那种东西,对于未开化的人来说就将显得是吓人的。”[9](275)但崇高的判断并不因此就是从文化教养中产生出来的,相反,它是植根于人的“道德情感的禀赋”之中的。所以,依康德之见,对人而言,倒不是崇高的评判有助于道德的提升,反而是道德的提升更有助于崇高的评判。
可以看到,无论是对自然美、艺术美,还是对崇高的评判,它们作为审美判断力,都无法有效充当通向道德的中介。康德苦心孤诣地思辨,只是更加凸显了道德的至上性。那么,美善关联的真正桥梁何在?笔者认为,这在康德对美的理想的阐述中可以发现。康德根据鉴赏判断的纯粹与否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美:自由美和依附的美。按照康德的标准,纯粹的鉴赏判断非常严格,符合这种判断而能够被冠以自由美之名的对象也非常之少,但这不意味着依附的美的价值逊于自由美。康德在论及美的理想时提醒人们:“首先一定要注意:应当为之寻找一个理想的那种美,必须不是一种飘移的美,而是一种……固定下来的美。”[9](241)康德虽然在纯粹鉴赏判断的意义上对这种美略有微辞,但在整体的价值评判上,却给予了其更高的地位。他否定了其他事物能够拥有美的理想,而认为“惟有在自身中就有其实存的目的的东西,即能够通过理性自己规定自己的目的的人……才能够成为美的一个理想”[9](241−242)。鉴于康德以“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人”为创造的终极目的,所以他认为“在人的形象上,理想就在于道德的表达”[9](244)。这即是以道德价值在人的形象中的呈现作为美的理想。道德之善明证于人心,显现于人的外在形象,使人真正成为堪称美的理想的人。就此,康德终于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将审美与道德融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道德在康德整个美学体系中充当了定海神针,尽管他并没有实现以审美促进道德的预定目标,却以道德为审美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充分论证了人只有在人格美中才能成为美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美与善的统一。在康德那里,美善和谐境界的最终臻至,不是以前学者所普遍认为的由美而善,恰恰乃是由善而美(当然,这里的美非纯粹鉴赏判断意义上的美)。人不是因审美而趋近道德,而是因道德上的不断完善而使自己显现为美的,人亦因这种完善而有可能感到某种道德上的幸福,从而更有资格配称“至善”格局下的“永福”。
四、结语
综观康德的著述,他所谓的幸福实际涵盖了“自然幸福”“道德幸福”和“永福”等多重层次,这些幸福的来源、性质并不相同,与审美的关系也各各有别。在审美中,虽然不纯粹的鉴赏判断混杂着“自然幸福”,但为康德所推崇的纯粹鉴赏判断之美和崇高则超越了“自然幸福”。康德没有明确地承认纯粹鉴赏判断所产生的愉悦就是幸福,但如果我们将幸福视为一种满足感,那么它的确是可以作为幸福来看的。吊诡的是,这种满足就其表面来看,却是无关欲求的。不过,就其是人存在于世不可或缺的维度而言,仍可将其视作一种更深微之欲。纯粹鉴赏判断的幸福感,即基于此欲的满足而产生。这与基于感性欲求的满足以及基于实践理性完善的满足迥然不同,故作为一种幸福的性质亦与“自然幸福”和“道德幸福”殊异其趣。康德固然认为此鉴赏之美所提供的娱乐“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新颖的,而且人们不会对观看它感到厌倦”[9](252),然而,绝非 “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他未将幸福单一化到审美的向度上。在他那里,基于感性欲求的“自然幸福”毕竟还是幸福而未遭否弃。
此外,笔者不能认同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是“对幸福主义伦理学作了很大的让步”。康德虽未否弃幸福价值,但他对幸福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他没有直接点名批判霍尔巴哈、爱尔维修等人,但却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批判表现出来。他坚定地将自己的美学及道德哲学与他理解的伊壁鸠鲁划清界限,而丝毫未曾表现出与之相妥协的倾向。康德固然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探讨审美的,但他已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尽可能地将审美从感性欲求——也是身体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经验性纠葛中剥离出来,所以,即使将审美看作一种幸福,它也与经验论的幸福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了。
康德处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思潮为主导而感性欲望泛滥的时代,他对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性考察,厘清了一直以来纠缠不清的审美、道德与幸福的界域,确凿地肯认了心灵中不委落于尘寰的超越境界。这一思想体系直到现在仍不失其卓越价值。勿庸讳言,当前的时代精神,已然在利欲的征逐中陷溺太久。或许,我们仍可冀望从康德哲学中汲取智慧,洗濯心灵的尘垢,让生命焕发光彩。
注释:
① O’connor Daniel对此持异议.他认为康德对于幸福概念的思考一以贯之并经过了深思熟虑。参见 O’connor D.Kant’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Journal of Value Inquiry1982,16(3): 189.这种说法不合于康德著作事实。
② Wike注意到了康德在论及“道德幸福”时的这种矛盾,但他认为康德最终“拒绝了这种‘道德幸福’的概念”。参见Wike Victoria S.Kant on happiness in ethic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13−15.其实康德只是为保证其逻辑的一贯而不得不作出这种割舍,但他实际的道德践履则对此有真切体证。
③ Wike认为“永福可能是幸福的类似物……它与幸福的原因和来源不同”。参见Wike Victoria S.Kant on happiness in ethic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20.但这只是就其不同于“自然幸福”而言,就深层次的根源来说,它也是生命欲求的对象,仍可算作一种幸福。
④ Interesse,有“利益”“兴趣”义,或译作“利害”(宗白华、邓晓芒),或译作“兴趣”(李秋零),或译作“利害关心”(牟宗三)。此处取“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