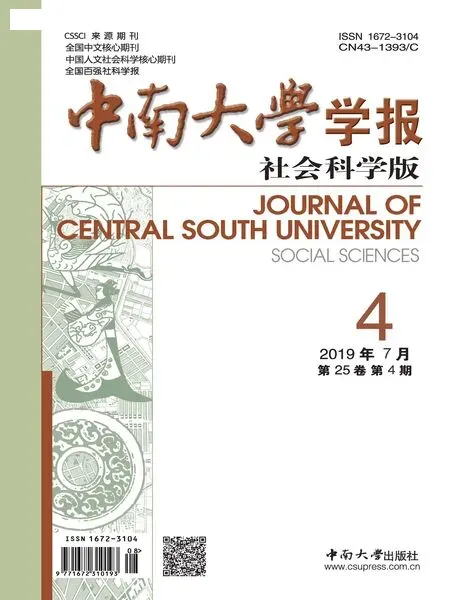“风景”抒写中人文精神与智性经验的构建
金春平
(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与艺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一、思想、审美与经验:学者散文的文体溯源
中国现代散文是在继承六朝文章、晚明小品、笔记小说,并汲取日本俳文和英国随笔的基础上创建,“最终发展出周氏‘小品’与鲁迅‘杂文’这现代中国散文的两大流派”[1],之后的“诗化写作”“哲理写作”“经验写作”等散文范式,基本上是由这两大散文类型演变发展而来。现代散文的文体属性使其在文学实践中成功地消弭了语言自律与文类创建、现代思维与古典审美、思想表述与文体趣味等方面的区隔,并且使“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2](574)。但与其他文类相比,无论是文体分化的多向性、语言的创造性,还是文化思维的融合性、美学追求的多样性,现代散文的发展和文类变革的步伐都要缓慢得多。形成这种散文发展史轨迹的重要原因,是现代散文可以吸纳一切文学元素的兼容属性,使其具有高度的文体自由。而文体的高度自由最终使散文成为缺乏文体边界和文类核心的“开放性文体”,并造成散文“文类规范”和“文类变革”的双重困境。因此,许多散文家和理论家都对散文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如朱自清说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3](243),郑明娳认为散文是“残留的文类”[4],梁锡华宣称散文“会衰退,甚至会消亡”[4]。
近一百年来散文的文类主体性虽然一直处于“未定型”的状态,但“未定型”所附带的可塑性和包容性,为散文新体式的建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在散文寻求自身变革的诸多方向中,“散文文体”与“他者话语”之间的融合,或者说散文“指涉内容”的延伸,是散文文类变革的重要现象,于是,中国散文先后出现过文化大散文、政治型散文、历史大散文、科普型散文等公共话题写作,也涌现过私语化、呓语化和口水化散文等个人写作,散文与“他者话语”的嫁接或联盟,无疑都拓展了散文自身的表意空间,丰富了其自身的言说姿态。但是,散文寻求其他话语形态作为自身文体变革的努力,也面临诸多创作困境——公共性话题散文的写作歧途在于真诚个人性和感官生活性的缺失,常表现为过度的形而上学的说教、缺乏深度体验的抒情、情感的虚伪矫情、思想的空洞无物以及语言的不及物等,这类散文虽然言辞考究、布局精心、意象高远,但却隐匿了一个完整、鲜活、丰盈的真性情的个体生命。个体化散文写作的病灶,在于普遍陷入无休止的小资呻吟、情感宣泄和自恋呓语当中无法自拔,这类散文仅仅定位于对生活表象及个人日常的“空间性”“物理性”“身体性”和“情绪性”进行直观呈现,放弃了唯有通过个体化写作才能对生活真实、心理体验、美学质素和思想潜流进行揭橥的言说优势,散文写作沦为个人隐私话语的表述工具,最终将个体化写作所擅长的理性反思和生活洞察的话语能力彻底背弃。
新世纪之交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对近一百年来的散文理念、散文文体、散文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并重新聚焦于散文的文体问题,即“散文写什么”和“散文怎么写”。知识分子试图将“个体性”(经验性)、“公共性”(思想性、哲理性和文化性)、“审美性”(文学诗性)进行创造性的融合构建,以此弥补单维度散文写作的诸多缺陷,并在文学实践中逐步确立知识分子散文或学者散文的文体共识。
一是对“真个人”的吁求。这里的“真个人”是具备文化现代性观念的个体之人,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真个人”具有启蒙与自我启蒙、批判与自我批判、文化反思与建构的能力,“真个人”还具备审视和有效言说历史、现实、生活、社会和人性的能力。“真个人”的“文化现代性观念”,体现在散文创作中就是作家“独立、真诚、理性和智慧”的“自由表述”方式,即通过对“个人精微的感觉,独特的心灵敏锐”的描述[5],对知识分子个体生命体验的理性自省,来发现被世俗生活世界所遮蔽的生命存在质地、精神嬗变细节和人文精神涌动。“真个人”的审美创造能力,主要表现为作家要警惕个人美学观念因臣服于某种外在流行性的美学意识形态而造就的审美虚伪,而必须将个体的天然性情、真诚情感和丰盈心灵进行艺术化表达。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知识分子 “自由”“敏锐”的“审美言说”转化为“精神叙述”,进而打造一个由知识分子的经验、情感、价值和审美所构建的“生活艺术世界”。这是知识分子散文以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张扬自我为核心的“诗性精神”的艺术表征。
二是知识分子散文文体的构建。散文的文体是由“文法的自由”“体验的深度”“审美的敏锐”“感知的丰厚”等标识所构成,因此,散文“变革创造性”的评判标尺,既包含文体结构的维度(如“语言的及物”“细节的准确”等的深化),也包含文体秩序的维度(如“散文经验”的开拓、“散文空间”的延宕等)。可以说,“艺术、思想和经验”共同构成散文语体必备的文类要素。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于对“政治理性”压抑“文学自律”的集体反叛,散文语体发生
了重要变化,那就是与寻根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结盟,当代散文整体回归“文学性”的“审美主义”传统。一方面,散文审美主义的语体具有“节制”“适度”“均衡”的美学优势,能够对当代文学观念中长期潜伏的政治化的“社会理性”与物质化的“工具理性”进行艺术消解,从而使当代散文能够从意识形态的钳制中获得语义解放。另一方面,当代散文过度依赖审美经验,也造成其内在思想性的整体贫乏,散文沉溺于审美物象、意象和想象的刻意经营,限制了个体化写作“哲学辩驳”与“话语构造”的能力,并削弱了散文对当代社会、思想观念、国人精神和生活肌理的介入效度。鉴于此,新世纪之交以来的知识分子散文写作或学者散文写作,力图在散文语体当中将审美、思想和经验进行融合,进而实现在生活美学的表述中彰显理性思考的叙述目的,或者建构源于个人思考而又通达公共经验的知识分子人文哲学叙述意图。学者丁帆的随笔散文因“澎湃着思辨的激情和启蒙的热诚”,“宽广的人文情怀和独有的知识结构”,“随笔见‘长句’,学问得‘赋格’”[6], 2018年获得中国散文界最高奖——“朱自清散文奖”。其代表作《人间风景》以现代知识分子对“风景哲学”的观照、经验构建与人文反思为创作主题,实践着对当代散文语体壁垒的聚合——一方面,作者续接起现代散文的“审美主义传统”,其自由节制的文体结构、古雅的语言、深远的意境、本真的叙述姿态,重塑了一位高洁士子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对风景话语进行的哲学思辨、文化追溯和记忆钩沉,既赋予其散文“美与诗”的外在形态,又融汇了“知识与学术”的认知,同时还有“思与理”的内在启悟,从而承接起现代散文的思想主义传统,构成人文知识分子新的“文化智识型”散文。
二、风景诗学:哲学思辨的文学表达
风景无论是作为人的原始视觉享受,还是作为人的意识形态呈现,其生成与发展都是人与自我审美世界关系的积极重建。但是,人与某类风景之间能否建立审美关系,往往存在感官享受与认知的差异。在农耕文明的静态型文化语境中,由于总体一致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摄,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历史美学意识及集体观感认知也基本趋于同质化,这种同质化的感官体验与美学经验,支配着人对风景的发现与表达,并逐步构建了具有民族性的“风景美学共同体”(如山水、田园、江河、草木等)。历代文人对这些风景意象的抒写都注入了具有民族性的审美认同、情感内涵和文化追慕。但是,当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交互叠加,既有的稳定的文化秩序碰撞重组,“风景”的“发现”已经升级为“文明形态冲突的战争”,游牧景观、田园景观、都市景观甚至人工智能景观共时并置,不同风景之间互为镜像,人与多元文明的对话关系开启。此时,在静态文化语境中人的美学共同体意识开始瓦解,“风景”成为一种“关系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存在,失去了被整体认同的可能。于是,在多维文明形态的交织中,人与景之间的“秩序关系重建”和“人文内涵开拓”就成为构建当代人“主体性”的重要方式。而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对“风景”的观感持续激发着自我思辨的激情,并以哲思、人性和审美为支点,构建出一种学者型散文的“风景诗学”,彰显了一位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独立而深刻的智性经验。
第一,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普遍的“文化认同”中洞悉内在的“文化悖论”的哲学内涵。作者在《瓦尔登湖旋舞曲》当中确认了梭罗所张扬的生态保护理念的前瞻性和远见性,但作者又在梭罗是坚定而前卫的生态主义者这一公共认知定论的表象背后,洞悉了梭罗其人其文其行隐藏的深刻哲学悖论及梭罗生态主义理念所面临的人文困境。梭罗回归自然时的文化决绝姿态,意味着他对现代文明的绝望。事实上,他的这种浪漫美学式的乌托邦想象,始终无法逾越身体性、物理性和空间性的制约,正如作者的质疑——为何梭罗两年后放弃了自然的孤独生活而重新回归现代都市?于是,梭罗作品中的生态主义指向与梭罗回归城市的生活行为之间就呈现出略带荒诞色彩的悖论。如何理解这种悖反就为作者提供了理念反思、理念增殖与理念思辨的巨大空间。在作者看来,梭罗的反资本工业文明的文化宣言是一种生态主义预警,而非提倡人类彻底回归前现代文明状态,梭罗仍然肯定“人类要发展”,但提醒人类必须认识到发展“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作者重新注解了被大众视为罪恶之源的“资本工业现代性”的内涵,指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悖论与实践困境。作者认为唯有通过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批判与理性实践,才能实现自救,这正是作者“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理念的文学演绎。《东京大学的树》同样是作者对大学地标树所隐喻的流行性认同思维的“悖论性”发现。大学地标树的高度往往被视为大学文化积淀厚度的物化表征,但作者却从这种风景审美的普遍常识当中,触及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悖论——以物的意象去臆想乃至判断物化表象下的内容,是极其狭隘甚至危险的认知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能遮蔽风景的复杂和局促,还可能借助审美暗示导致对物的象征意义的固化认知。源于对这种流行观念的警惕和质疑,作者直陈大学真正的文化风景是人文素养的高度,只有人的人文素养常青繁茂,物化的地标树才能承担起“文化之标”的象征身份。在这里,作者批判了“以物定性”的大众惯性思维,希冀人类构筑高洁的人文精神风景,来映照自然风景的圣洁。
第二,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感官审美中寻觅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人性内涵。《梭罗: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可视为作者与梭罗、与梭罗的文本、与爱默生,甚至与自我进行对话的产物,作者不断追问梭罗作为个体生命的哲学意义,并最终触摸到一位先锋性的“超验主义者”的生命质地。在作者看来,梭罗其文其行固然有明显的生态主义批判意味,但作为个体生命的梭罗更是一位“超验主义最前卫的践行者”,他对现代文明和社会群体的疏离,对自然万物和寰宇苍穹的亲近,正是其超验主义哲学的生活化实践。梭罗努力“返归”自然之母的积极姿态,是为了“寻找人性的原始与野性”,而梭罗之所以迷恋“原始与野性的人性”,是因为他一直试图构建“人性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他要对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神性,即人与超越经验之外的一切存在物的关系进行重构。“对于‘意义’的追寻,既可以指向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领悟,也可以指向对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思考”[7](10),从而完成对现代文明所依托的经验哲学和权威理性的颠覆,抵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至高境界,救赎被文明规训、被存在压抑的人。这是作者穿透梭罗个人“奇异”的日常生活表象,直抵梭罗的超验哲学世界和个体生命质地的全新诠释。在《寻找原始野性的风景线》当中,作者甘南之行的审美兴奋点是看到的最原始的自然风景。无论是作者对大自然野蛮生命力的欣赏,还是对大自然狂野蓬勃生命形态的玩味,以及对自然风景当中万物合一境界的向往,都使其散文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性美学,“一种浪漫的情感结构得以产生”[8](87)。《寻找原始野性的风景线》不仅是一位睿智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原始自然风景进行心灵参悟的艺术文本,也蕴藏着作者深沉的悲悯情怀。他审视着现代人深陷物质资本和都市文化囚禁的普遍处境,直陈现代人普遍丧失敏锐的审美能力和生命野性的生存境遇,以及当代人困于“文明生活”的囹圄而毫不自知的生命悲剧。如何化解当代人的生存困局?在作者看来,梭罗超验主义哲学所提倡的“人性自由精神”正是一种“新启蒙理念”,它包含了人类感性力量的重启、人类原始野性的恢复、人类启蒙理性精神的超越和对权威规训主义的反叛,以“大自然与人类平等”为最高的生命理想。可以说,作者寻觅“原始野性风景线”的目的是对当代文化语境中人性孱弱和感官愚钝的救治,旨在建构一种以自然至上、心灵解放和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
第三,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文学性的想象画面当中反观个体生命记忆图景的诗性内涵。作者在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解读中、对东京大学地标树的审美凝望中,赋予其散文的“风景诗学”以“哲学内涵”,希冀在多元文明冲突语境中开启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秩序重建;作者在对梭罗的超验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对西部原始风景的体味中,赋予其散文的“风景诗学”以“人性内涵”,传达对现代物化语境中人性异化的批判,希冀以“新启蒙主义精神”恢复人类的“生命元气”和“自然天性”。在《看风景的人》当中,作者一方面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文学史维度的评价,提炼出汪曾祺小说的风景美学内涵,即“浪漫主义的情怀诉求”“平静如水的生活真实”“理想主义的诗意感召”“生命悠然的生活趣味”。显然,作者指称的“风景”概念已经脱离了自然、人文的能指范畴,而将“风景”概念拓展到日常生活领域,这是作者对“风景诗学”的再次开掘。另一方面,《看风景的人》的诗性内涵还包括作者自己的心灵诗性,以及当作者进行自我对话时的情感诗性。在作者的审美感知中,之所以对汪曾祺小说的风景画面如此熟悉,是因为汪氏小说早已成为作者关于青春和故乡记忆的历史镜像。汪氏小说中的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既是打通作者与汪氏小说“诗性默契”的共识话题,也是作者开启记忆追寻和生命遐想的诗性通道。作者所要呈现的自我生命诗性,既蕴藏着作者曾蒙受历史苦难而终获解脱的精神慰藉,也有作者对青春岁月远去的心灵追寻,饱含着作者意欲逃离逼仄生活情境的企盼。汪曾祺的小说不仅为作者提供了一种诗意化的美学视界,而且作者从汪曾祺小说“悠然自得”的风景画和“平和冲淡”的风俗画里找到了隐匿的本然自我。这既是作者对自我“心灵风景”和“记忆风景”的咏怀,也是作者以艺术审美修辞的方式展开的一种精神遨游。
三、金陵精魂:人文风骨的文化寻踪
古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在历代文人的审美想象中,已经成为江南文化典型的美学意象,但它沧桑多舛的命运,又使其成为“帝王霸业”政治美学的意象载体。同时,现代南京城鳞次栉比的都市建筑物以极具感官化的消费美学宣示着这是一座充满现代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于是,“江南之魅”“王朝之刚”“都市声色”共同造就了南京城的“悖论性格”,而多重性格的奇妙并存,恰是古都南京的真实面相。对于古都南京这种复杂的“真实”,作者在《人间风景》的篇章当中,始终表现出对金陵人文精神、人文风骨和人文传统的抒写热情。在他看来,金陵所具有的坚韧而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才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基因。因此,一方面作者对古都金陵进行历史追问、古意访踪、现实观照和文化整理,探寻那些正被城市建设遗弃或改造的历史古物所蕴含的悲情和文化;另一方面,作者以史学家的考古意识、思想家的幽思、文学家的共情和哲学家的反思,将那些古迹所隐喻的“人”激活,触摸金陵的人文精神纹理,“文学的真理就记载在这些让无生命碎片说话的科学所开辟的康庄大道上……文学以这种方式向新的社会坦白它的真相”[9](21)。作者以极具知识性、思想性、抒情性和古典性的散文文笔,描述着金陵的“人文风景”“生命风景”和“自然风景”。“人群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景观”[10](61),探寻金陵历代知识分子的气节禀赋和价值追求,重估金陵士子的精神遗产对塑造金陵文化传统、对发展中国民族文化、对启示当代知识分子都极具价值。《人间风景》是作者与古人、作者与自我的“交互对话”,这种消弭了今人与古人、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的散文话语,构建出一个以士子风骨为主线的价值相通、精神相惜、人格相照的共时情景。作者与先贤进行的心灵对话,不仅是对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难题的回答,也确认着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独立品格、正义气节这一价值信念。
第一,作者对金陵先贤士子的追慕宣示着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启蒙精神和思想智慧。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以访古迹、抒幽思的叙议笔法,刻画了金陵“先贤士子群像”。这些先贤士子往往先知先觉、信念虔诚,他们所表现出的迥异于时代与世俗认知的另类形象也屡遭同时代人的误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坚持真理与苟安妥协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捍卫人的尊严与高贵、士的独立风骨,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成就金陵士子“启蒙精神”和“思想智慧”之时,也赋予金陵古都以“独立”“高洁”“坚韧”的恒久精魂和人文气质。在《豁蒙楼》当中,杨锐对信仰的执著使他遭遇“杀身之祸”,储安平对真理的坚持使他落得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但是他们的千古风度与独立人格却被历史所铭记,他们的生命抉择再次昭示:能否坚守“豁蒙”精神并付诸行动,才是评判古今知识分子真伪的重要标准。“豁蒙”精神在成就知识分子独特高贵品格的同时,也逐步内化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思想智慧。在这里,作者对“豁蒙”的解读、对“历代知识分子”人格风范和道义品格的宣扬,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宣示:这是一位有着坚定价值立场和思想智慧的当代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血脉的自觉传承,他以富有历史中间物色彩的理想坚守和信仰执著,来对现实世界、文化迷障和人格陨落进行倾力拯救,是作者对一生所坚守的理想信仰、价值立场、家国情怀和人生哲思的再次确认,“他必须恪守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底线……人性立场,是其传道授业的根本”[11](36)。但是,作者深知这种理想化人格的达成,充满了巨大的现实难度,因此在《豁蒙楼》叙述的草蛇灰线当中,始终萦绕着作者清醒的悲观主义情愫。
第二,作者在对先贤行踪的追思当中,宣示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在《扫叶楼》当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一向被视为消极遁世的龚贤在“独善其身”的表象之下,一直在坚守文人品格和士子气节。出于民族大义,龚贤“完全出于一个士子忠义的情怀”不仕后朝,但他的满腔热情和豪情壮志在前朝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在艺术世界里“道出了知识分子杜鹃啼血式的悲愤”。这是一种坚守人文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节义精神”的生命实践,龚贤“生活遁世”和“精神入世”的矛盾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作者对龚贤精神世界的洞悉让他无意中扮演了龚贤人格的当代代言者。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对知识分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人格期待,往往投射于以散文的思辨激情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学理臧否和品格评判中,最终得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道德勇气和人生智慧”的结论[12](205)。这种界定着眼于对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和良知的强调,与作者学术研究立场中的“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构成了内在的价值谱系。同时,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主体性的界定,也是将中国儒学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精神,与俄国知识分子“永远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知和是非感”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欧美知识分子“人性高于革命、高于一切制度”的启蒙精神,进行了比较和中国化构建。
第三,作者在对前朝士子命运的历史钩沉当中,宣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即风骨和抗争勇气。《桃花扇中的风景》描述了侯方域人格操守的沦陷过程,但作者却借助这一反面案例,进一步确认了对知识分子品格本质的论断,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由与独立。作者由昆剧《桃花扇》的重拍及十八年前的笔墨官司,引申出“文化复兴(消费)不能遗忘价值导向”的公共性命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叙述集中到对侯方域“文人士子”精神形态和灵魂的审视拷问上。一方面,作者梳理了侯方域 “中了副榜”、背叛东林复社党义、“反复于权奸阉党阮大铖之流的恩威之间”,以及降清后出谋划策剿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等历史事实,使侯方域与李香君等的捍卫气节、坚持操守等不屈品质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作者洞悉知识分子人格传统与城市人文精神之间的深刻互塑关系,即一座城市的人文精魂,不仅在于其精湛的物化美学遗产,也在于那些身处历史转折期的士子学人所表现出的人格修养、德性坚守、大义操守和民族气节。他们的智慧、信仰、良知和勇气,赋予一座城市以高贵的精神气质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而丧失了风骨、民族大义和抗争勇气的所谓的文化名士,早已成为以知识分子之名而行沽名钓誉之实的沉沦者。
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将审视和思考的触角深入到金陵这一充满历史传奇和艺术想象的城市中,并以其广博的史识、高超的智识、敏锐的情识,诠释着金陵精神的多元内涵。作者尤其关注知识分子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塑造关系,在他看来,古城金陵的文化命脉更多是由历朝历代“具有风骨的真正知识分子”和“一批批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文人”(《旧都感言》)所创造的,他们捍卫着人文信仰,传承着精神风骨,坚守着道德良知,金陵正是因为有这些知识分子的传奇,才葆有一种高贵、坚韧和高雅的人文品格,并拥有一种雍容的文化力量。当然,在历史与当下的对比当中,作者也清醒地洞察到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所遭遇的溃败,“秦淮烟水中的文化内容何时能够浊泾清渭、激浊扬清呢?”(《秦淮烟水》)对金陵人文传统日趋消散原因的追问,作者以一种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方式彰显出鲜明的思辨性、学理性和深邃性。同时,作者形构的既指向自我思想世界又指向大众精神世界的散文“复调”,能够廓清因多元文化秩序所导致的人文语境混乱,让读者经受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澄清,这成为作者审视金陵“人文风景”的总体叙述指向。
四、历史记忆:个体回望的生命重负
叙述历史的方法往往比历史本身更具话语能量。散文对历史的叙述要在时间线性维度当中折射叙事者与历史本身的对话。虽然散文不排斥叙述的历史志录功能与艺术想象功能,但散文对历史的介入,更多是以叙述者的情怀、史识、学养、思想等去呈现既有个人特性又有普世性的关于历史审视的人文思考,这是散文让历史重新出场的方式,并使学术性散文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
第一,作者以“史思”的方式复现金陵的历史记忆,在理性思辨和人性审视中捕捉历史更迭奥秘中不变的封建幽灵。在《南京十里长安街景》《幽径古丘》《斜阳下的明故宫》等作品中,一方面作者沉溺于金陵古都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广,另一方面作者又在每一处寻找着个体与历史进行对话的契机。无论是太平天国的昙花一现,还是明王朝的轰然倒塌,作者在对“残酷的历史”与“历史的残酷”的洞察中,触摸到中国国民性和文化传统意识中的普遍顽疾——缺乏现代理性精神的封建意识与文化人格。“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改不掉的陋习”,它也注定了封建王朝“由兴而亡”。在《墓碑风景》当中,明代开凿的巨型“阳山碑材”同样是历朝历代“帝王狷狂霸气”和“小人谄媚丑恶”的隐喻,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深处的封建幽灵总会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反复闪现,任何时代都难以逃离历史之神的掌控。在《陵寝风景》当中,一方面,作者表达了对前朝文化遗韵的想象与怀恋;另一方面,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市民大众对历史的集体遗忘,全民性的物化迷恋宣示着以物欲蒙昧为症候的消费主义幽灵的诞生。然而作者却坚定地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般的抗争,以金陵历史文化“守灵者”的虔诚与执著,在文字中复现着渐行渐远的历史。在《梦话扬州》《<闲话扬州>的闲话》当中,作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扬州“贤达”以道德化的“偏执”对知识分子“文人情怀”进行剿杀的文化事实,并洞悉这种“吃人般”的道德话语对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异化与扭曲。作者以故乡之子的疏离者身份,对造成“文化错位”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制约着扬州城的现代化变革。在这里,作者深知作为“扬州之子”的“忤逆之言”必然面临着道德危机和生活风险,但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直言,恰恰是知识分子风骨的表征。他为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权利屡遭大众和政治的双重围剿而辩护,作者在《人间风景》当中将时间寻踪、古迹复现、王朝兴衰、人文透视融为一体,描绘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想象图景。但在作者锐利的文字和绵密的叙述中,贯穿始终的是启蒙精神和人文话语,并以此直击造成历史悲剧的封建幽灵。
第二,作者以“共情”的方式复现着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还原了被公共书写遮蔽的“人的真实风景”。作者在其志人型的学术随笔当中,勾勒出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情感世界、生命追求,以亲历者的视角返归文学事件的历史现场,让平面化的学人历史立体化。这是作者对一代学人的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文字留存,以此防御时间之流与共识概念对前辈学人丰富性的遮蔽。《朝内大街166号的风景》记录了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的见闻感受。从追忆“茅编室”的人员队伍构成,到回忆张伯海、王仰晨、叶子铭、韦韬等学人前辈,再到抒写对张宇、邵振国、贾平凹等作家群体的印象。一方面,作者将个人置于历史图景的中心位置,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努力让抽象的历史叙事具备生活化的人性温度;另一方面,作者以回望的姿态,赋予历史生活最直接、最切实和最富有情感质地的呈现,让文学事件和文学史变得温润可触。可以说,作者对一代学人的记忆,是对宏大文学史图景的人文注解,是对学人的本真性情和生命微域的真实留存。《宠辱不惊 勘破风云》是作者对钱谷融生活印象的回忆素描,作者深情地追忆了这位学界前辈。无论是钱谷融在极左政治年代对“文学是人学”艺术真理的张扬,还是钱各融在经历反右风暴洗礼之后“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以及钱谷融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丝不苟、天真烂漫、童心未泯的本真情趣,作者都以诗意简白的语言诠释出钱谷融“学术信念的生活化”和“生活信念的学术化”的艺术人生态度与博雅生命情怀。这是作者对一代学人伟岸人格的仰望,也是作者以文学记忆的方式打通时空隧道、传承学人风骨的方式。
第三,作者以体验的方式复现了生命与青春的感怀彻悟,在存在哲思和历史追问当中,《人间风景》呈现出宏大历史对个体生命乃至代际命运的“塑形”与“改造”,彰显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话语进行“质疑”和“反抗”的勇气。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的“青春追忆”是对个体经历的宏大历史的“体验式”还原,其中既有自我意志与时间抗衡的疼痛和悲情,也有作者对青春、历史和生活体验的哲思追问,并以敬畏人性和彻悟生命为旨归。“生命高于任何其他东西的信念却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自明真理’的地位。”[13](251)在《沉疴之后读风景》和《观街景》当中,经历死亡体验的“我”重归人世凡尘,田园风景、城市风景和人文风景,都绽放出难以抵挡的生命力,“生与死”的跨界体验让作者从市井生活景观中,再次点燃了拥抱生命的热情之火。《河上的风景》《夜行客》《湖荡风景》《水田风俗画》《月下食》是对作者知青时期插队宝应县的青春历史再现。那段真切的人生记忆,定格为作者的生命驿站,并在不断的情感反刍和回望中,成为激发作者思考的生命之域。在《河上的风景》当中,十六岁的“我”在晦暗年代萌生的爱情向往和人生思考,是最真切最宝贵的生活体验。这段“青春”见证了当时的荒谬,也激发了一位少年超越时代与历史禁锢的生命渴望。在《湖荡风景》当中,“我们”是继续沉迷于激情历史之中,还是重新构建自我与历史的理性关系,这样的选择困惑恰恰是一代人难能可贵的觉醒,是他们对历史荒谬法则钳制个人命运的批判。在《水田风景画》当中,作者认识到没有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人“连畜生都不如”,这是作者对人类生存残酷真相的揭示,也是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更是作者对戕害人性、摧毁文明的反人道历史语境的尖锐批判。在《月下食》当中,作者对饥饿者的群像素描,揭示出人的理性自律在本能欲望面前孱弱无力。这是作者人道主义关怀的投射,他肯定人的生命欲望才是人类能够超越生活劫难、实现生命延续、激发未来想象的本真人性。
抽象的历史描述在《人间风景》当中被作者以真实的生活经验佐证,并时刻被作者的理性回望和历史反思升华。作者的随笔创作不仅是活色生香的个人体验的记忆整理,还是一位富有生命质感、真实性情和智慧的当代知识分子对历史、人生、自然以及自我的不断发现。《人间风景》当中学理化和思辨化的历史叙述,以见微知著的方式审视和介入宏大历史,其中不仅凝聚着作者对中国历史规律的判断,而且蕴含着作者对个体生命如何改造历史、反抗历史乃至超越历史的可能性的开掘。作者勾勒的一幕幕人间风景,祛除了关于历史记忆的种种或浪漫或悲情的偏狭,而在个体记忆的反观中,发掘人生的真谛,感受生命的悸动,思考命运的无常,反思历史的吊诡,为“风景”这一学术命题注入了知识性、历史性、思辨性和人文性的深邃内涵,从而建构出一种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人道主义的精神传统和现代学术的哲学思辨融为一体的人文智识型散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