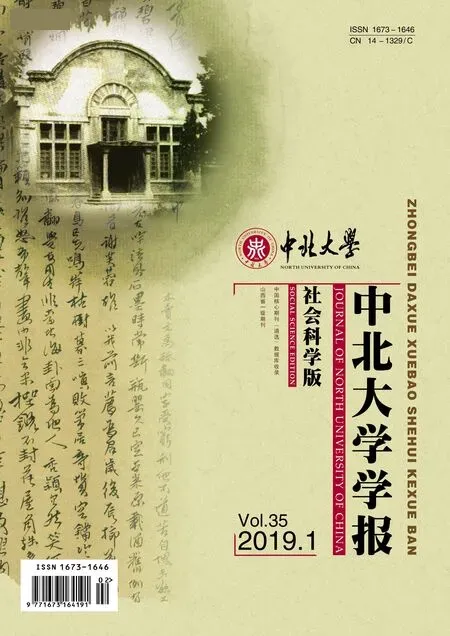论唐代太原尹与佛教
廖靖靖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在中古时期,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影响着国家的礼仪祭祀和百姓的日常劳作。佛教在唐代走向民间,被人们广泛信仰。对于唐代佛教的研究,前人著述甚丰,主要包括对宗教本身的分析,对文化传承的探究,以及史学领域的讨论。历史学的方法是要用丰富的史料深入分析佛教与历史事件、政治生活、社会经济多方面的互动关系。太原是李唐王室的龙兴之地,亦是安史之乱后护卫长安、洛阳的北都,国家的“北门”,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同时,佛教在此兴盛发展,佛寺林立、高僧辈出、信徒众多。即使历经晚唐藩镇割据之乱局和五代群雄相争之剧变,太原的佛教依旧持续传承。为什么会有如此局面?太原尹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太原尹是太原府的最高长官,引领地方行政制度的运转。太原尹的人选倍受朝廷重视,官员们以太原尹为迁任地方、中央的中转。裴宽、李光弼、范希朝、令狐楚、李克用等多位唐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实任于此。安史之乱后,北都地位不断上升,太原府成为唐代北方防御的支援基地,太原尹的委任也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太原尹、北都留守和河东节度使往往由同一位官员担任,三职合一镇守北都,可谓“镇北三独任”。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原尹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朝廷委派至太原的官员很多都崇佛、礼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并推动了河东地区佛教的发展,同时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在逐个梳理唐代太原尹的基础上,笔者拓展史料来源,从丰富的宋人笔记小说和唐诗中获取案例。
1 宋人笔记小说中的太原尹礼佛
在隋唐史学界,宋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根据宁欣的研究[1],首先,宋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唐五代的记载; 其次,宋人笔记小说述史、考史,有“史书化”的倾向,而且宋人笔记小说多采用谨慎态度对杂记、见闻进行纪实性的著述; 最后,宋人笔记小说里保留着关于生活、习俗、信仰的史料。史学领域对于宋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继续探索的空间。
我们可以从宋人的记述中看到很多关于唐代北都佛教情况的记载。唐代是太原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众多佛寺建立,出现了多位高僧大德,民间信仰佛教的人数也大为增长。《演繁露续集》记载:“安禄山反,杨国忠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2]185其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太原佛教信徒之多,杨国忠的度牒之计才能迅速获得大量资金。
元和十五年(820年),初任太原不久的裴度上报朝廷五台山的佛光现象。《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五台山佛光,其传旧矣。《唐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若金仙乘狻猊,领其徒千万,自巳至申乃灭。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3]257佛光现象是祥瑞之兆,且发生在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裴度上奏此事,既可知其对佛事的重视,也可见朝廷对佛教的推崇。
裴度之外,太原尹李暠、王缙、郑涓、裴休、卢钧、李克用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关联。开元十五年(727年),李暠任太原尹,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此职是天兵军改制而来。《新唐书》记载:“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4]3335崔岩在《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属性》[5]文中,首先分析太原周边的佛教环境,并对比佛教、祅教在教义上的差别,得出“黄坑”属于佛教方式。“黄坑”习俗之下成群饿狗食死人肉,影响恶劣。李暠到太原后以礼法教化民众,捕杀恶犬,最终革除此俗。虽然“黄坑”之事源于佛教僧徒习禅,能存在多年也是太原佛教兴盛的表现,李暠的举措更多是针对“黄坑”的现实影响,旨在改善现状,并非与佛教的对抗。
王缙曾在安史之乱时被选为太原少尹,协助李光弼镇守太原,并于大历三年(768年)至五年(770年)担任太原尹。据《旧唐书》记载:
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焉,度支具廪给。[6]3417
王缙兄弟信仰佛教,不食荤腥,到晚年尤甚。王缙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佛寺的修缮,如“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6]3417。他的行为对后世的庄宗崇佛产生影响,庄宗亦将大量的资财耗费在装饰寺院上。史书评价此事为“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6]3418。王缙在太原任职期间逐渐成为佛教信徒,他晚年致力于兴盛河东道的五台山金阁寺有此渊源。
大中九年(855年)至大中十年(856年)间,郑涓在太原任职太原尹。现今五台著名的古建筑佛光寺东大殿内有题字:“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7]801多位学者认为这里的“郑”就是郑涓,其派往河东的任期与大殿修筑的时间大致相符。[8]1667大中六年(852年)至大中九年(855年),卢钧到任北都后,《唐语林》称其“元公出赴行香”[9]31-32。行香,即上香行礼,严耀中在《从行香看礼制演变——兼析唐开成年间废行香风波》[10]157中指出这是“佛教向儒家礼仪制度与观念渗透的结果”。学者吴敏霞亦在《从唐墓志看唐代世俗佛教信仰》中阐述这是唐代社会普遍接受的佛教信仰方式之一。[11]结合现存遗迹和传世史料,虽然不能确切得出郑涓和卢钧二人在担任地方长官时信佛的程度,但是由此可以推知,唐中晚期佛教在河东地区得以继续传承,这与“大中之治”的相对稳定局面有一致性。
裴休于大中十三年(859年)任太原尹,他笃信佛教。陈艳玲的《论裴休的佛教信仰》[12]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回顾裴休的迁转经历,坐镇河东时期,是其从信佛到崇佛的重要阶段。《旧唐书》记载他家族世代奉佛,派往北都后,他在凤翔、太原的名山之中遍寻佛寺,向高僧求佛理。自身保持斋戒,焚香颂典,并以法号为字。面对时人的讥嘲,裴休坚持信仰,不抵触且不生怨。[6]4593《新唐书》亦记之:“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讲求其说,演绎附著数万言,习歌呗以为乐。与纥干閟素善,至为桑门号以相字,当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4]5368这一时期太原周边佛寺林立,佛教依旧盛行。裴休受到北都整体佛教氛围的影响,与僧人相交,并在治理太原的过程中奉行自己的佛教思想理念。漫索史料,与僧侣的频繁互动并非裴休一例,而是太原尹们的普遍情况,这在唐诗中多有体现。
2 唐诗中的太原尹与高僧交游
以诗证史是前人的经验之谈,也是吾辈需要承袭的传统。唐代诗的数量、质量、类别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文学史中可谓一绝。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它是极为独特的史料。一方面,它可补充正史之不载、不详,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多面镜; 另一方面,诗文中有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需要对照正史汲取背后的历史信息。太原尹们积极拜谒高僧在唐诗中多有涉及,其中有三首诗反映的事件大致相同,受到学界的关注。如:
何故谒司空,云山知几重。碛遥来雁尽,雪急去僧逢。清磬先寒角,禅灯彻晓烽。旧房闲片石,倚著最高松。[13]135
(贾岛《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 )
远去见双节,因行上五台。化楼侵晓出,雪路向春开。边寺连峰去,胡儿听法来。定知巡礼后,解夏始应回。[13]1879
(张籍《送僧游五台兼谒李司空》)
已共邻房别,应无更住心。中时过野店,后夜宿寒林。寺去人烟远,城连塞雪深。禅馀得新句,堪对上公吟。[13]1197
(朱庆馀《送僧往太原谒李司空》)
诗中受到拜谒的太原“李司空”为何人?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全唐诗》在三首诗的注释中都称此“李司空”为李听。齐文榜在《贾岛集校注》中指出《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中的李司空就是李载义,因为与贾岛生年相当的李姓检校司空兼太原尹只有载义一人。[14]215吴汝煜、胡可先先生认为《送僧往太原谒李司空》的李司空是李光颜,在《全唐诗人名考》[15]中分析:诗文中的事件发生于长庆至大和年间(821~835年),根据史料记载,这期间曾在太原担任要职的李姓官员有李载义、李听和李光颜,其中李载义任职于大和七年(833年)之后,但无司空之衔,而李听镇太原时检校的是兵部尚书,所以排除二人得出李光颜。蒋长栋于《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中直接指明三首诗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而张籍死于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或稍前,有明确的史料证明,从时间上看李载义不符合,李司空即李光颜。[16]151以上说法各有依据,根据任职时期和职官名称的演变,笔者更倾向于李光颜。虽然“李司空”的身份并无定论,但此次法师会见的无疑是北都最高地方官。诗文中,高僧前往北都的原因可能是去圣地五台山,也可能是去北边传扬佛法。其为何要与太原尹交游,耐人寻思。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太原尹普遍崇佛,与僧侣多有往来; 二是太原尹对北都,乃至整个河东地区的佛教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为远来高僧们重视。
3 晚唐至五代的太原尹与佛教
唐兴于太原,亦亡于太原:兴是指李渊从太原起兵,在这里建立王朝; 亡是指太原被李克用所据,唐王朝逐渐走向衰亡。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将太原尹制度延续到了五代。在这一时段,北都的重要性持续增强,成为兵家必争之权力中心。李克用父子对于佛教的态度可以说直接影响到河东地区佛寺与信众的命运。从现有史料中可以看到唐乾宁二年(895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竭河东之力,用工三十万,历时五年,兴建蒙山大佛阁,名为“庄严”。可见他们对佛教持有接纳的态度。
之后五代的太原尹也普遍信仰佛教,这是对隋唐的继承。文献记载:“后唐大同三年,魏王统军克蜀,孟先主尚庄宗妹福庆长公主,自太原节度驰赴西川。至明宗晏驾,宗室丧乱,朝士奔窜。有新罗僧携庄宗诸子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庆长公主犹子也。因为起院,以庄宗万寿节为名额,蜀人号为太子大师。”[17]73其中的太原节度使即太原尹由孟知祥担任。另有“石晋以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常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晋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劳。众心大悦”[18]52-58。刘知远为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他慰劳僧人之事,一方面是展示自己不计前嫌,另一方面也展现出自己对于佛教的认可和推崇。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晋阳的佛教势力,寺院有田产,僧人有处罚破坏寺院财产者的权力。
4 结 语
以上个案体现出唐代太原的宗教生活。概括起来有五个特点:第一,隋唐时期太原佛教盛行,佛寺林立,宗教文化遗存丰富,佛教长时期受到中央和地方长官的支持; 第二,太原尹受到北都佛教文化的影响,对于佛教的接受程度不同,太原为王缙、裴休等人提供了修佛的环境; 第三,佛教文化影响太原当地风俗; 第四,不同地区的高僧大德往来不同圣地,并与当地长官交游,为诗人所认同、记述; 第五,崇佛之风延续到五代,影响到了五代的太原尹。太原尹崇佛也促进了太原佛教的发展,从唐代到五代,北都佛教的兴盛程度达到一个高峰,而佛教正是太原稳定发展潜在的精神依托和社会各阶层沟通之途径,以佛教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古城市的变化将会是我们新的研究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