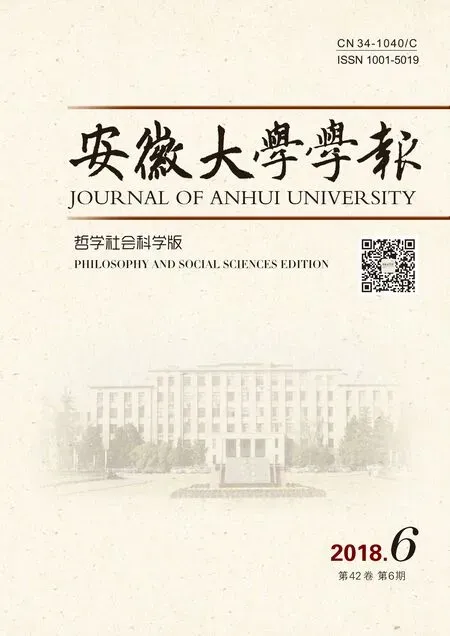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说”中的生态审美意识探讨
赵 凯,张 玲
引 言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相关史学、美学或者人学的原典解读和延伸阐释是充分的,也不乏创新的成果,但从生态审美的视角来“还原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并以此作为当代生态美学研究与生态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却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点的科学定位失准——这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与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的基本内涵,又使我们在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即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维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在当代中国俨然已成为显学,不可否认的是,其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却一直局限于西方当代美学与文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和学理上的借鉴与整合当然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又时常让人感觉到哲学科学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困惑。为此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必要的。寻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这一出发点,从马克思思想学说中汲取生态思想资源,对于中国语境下生态审美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一、劳动成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美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著名论断,科学地论证了艺术审美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学界将此界定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亦可简称为“劳动说”)。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感和艺术的起源问题,美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劳动”的本质是什么?作为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外部世界(自然)之间既自在而能动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美学史都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
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88页。在柏拉图看来,美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它不可能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而都根源于“美的理念”。这样,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的审美关系,只能成为脱离自然与实践活动的抽象物。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美在自然界和客观事物本身,但却认为美主要是在事物的“秩序、匀称与明确”等形式方面。由于亚里士多德对待事物往往采取静观的态度,所以他与柏拉图一样,把人的审美活动看作是只可观照的认识活动,而与物质实践活动无关。费尔巴哈虽然承认美的客观性,但他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感性的世界,而不可能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流动中去把握现实的、感性世界本身。黑格尔尽管意识到劳动的价值,但他也只是局限在“抽象的精神劳动”的层面。马克思在《手稿》中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人的劳动实践成就了世界历史,同时也改变了一切生命物种的生存状态。而“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内涵,正说明了在劳动实践的历史流动中去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出发点。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理解劳动的本质的,劳动造就了“自然的人化”与“人的对象化”,奠定了美和艺术起源的前提,马克思关于人类最初的美感与艺术起源的“劳动说”,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审美意识。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人类初民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量原始石壁上显示的人类祖先播种、狩猎的劳动画面,无不记录下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丰富历史,标尺出人与自然生态的不断进化。
“劳动创造了美”,这里的劳动,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2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全部活动——生命活动和生活活动,都与自然界密切联系;同时,自然界也是一种“属人”的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构成人与自然这种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正是人类的劳动实践。是劳动使人摆脱动物界,在自然面前站立起来;是劳动驱动着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自然成为人的现实,一方面形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是“人化的自然” 或“自然的人化”。劳动使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劳动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这是马克思自然观与生态思想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这一切又同时使人类最初的审美感受与艺术品的产生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劳动过程对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马克思认为,作为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最直接与最根本的方式——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基本过程和重要内容;离开了劳动,就失去了自然,同时也失去了人自身,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自身的自然”与“身外的自然”二者之间在劳动过程中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中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自身的自然”在最初表现为人对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但这却是人类介入自然、从事劳动实践的最根本的欲望和原动力。“自身的自然”与“身外的自然”都在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流动中,逐步形成了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之间的统一,并真正从“自然的人”走向“社会的人”。也就是说,一旦人自身的自然力自觉发挥出来后,他不仅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自然,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不断从功利走向审美。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375页。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的生理器官的作用,来阐明劳动给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质的变化与飞跃,从而为人的美感与艺术创造力的自觉提供基础。他谈到劳动怎样使人的手、发音器官和脑髓发展,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人的审美意识得以形成,艺术也就随之产生了。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最初更多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它不能完全以自然美的形式作为人类审美感知的对象,只有通过人类长期的劳动实践,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自由自觉的劳动,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劳动的形式,逐渐健全和发展自身的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和审美功能,并超越大自然本身,才能在审美观照中感受与表现大自然的奥秘与神奇。
马克思十分重视人的感性认识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重要价值。在他的思想中,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重要形式和基本内涵。“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4~325页。联系《手稿》中的上下文,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批判和扬弃了费尔巴哈的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观,而倡导“彻底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才开展这一番论述的。所以他首先指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一切本质皆来源于自然,来源于为人所认识的相对的自然。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既有能动的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受动的备受局限的一面,正在这种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中,人方能体现出作为“社会人”的本质与特征。马克思突出强调,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人与自然界既表现为互相独立又表现为互相依存,这种关系得以现实肯定的唯一方式便是人的感性的活动——人的历史的能动的社会劳动实践。只有“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才是人的感觉的全面性和感性活动生成的依据。
二、“自然美”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
马克思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探究劳动的本质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美”首先在于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同时,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应该看到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人类的审美欲望、审美趣味与审美创造,离不开人与自然互动中生态互补、生态平衡与生态创造;同样,艺术与审美创造中的“自然美”,也是人与自然能动与受动关系的结果。正如曾繁仁先生所说:“自然之美绝非实体之美,也非 ‘人化自然’之美,而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一种共同体之美。”[注]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5页。只有通过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才能够得到发展,才能开放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在获得物质产品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从而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即确证自己是具有艺术创造力和欣赏力的人。这样,劳动在创造“人化的自然”的同时,也实现“人的对象化”,也即“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页。。
在美学史上,诸多美学家都将艺术与美感起源问题作为其美学研究的起点,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生成又都是难以回避的话题。朱光潜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说”有着自己独到的领悟与见解,他从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视角,来谈劳动实践对人的感性、审美性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在他看来,劳动的结果导致“人也不复是单纯的抽象的人,而是与自然结成统一体的人了”。他在《西方美学史》中曾引用过黑格尔《美学》中那为人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例如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显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种需要(把内在的理念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从而实现自己——引者)贯串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很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是把艺术和人的改造世界从而改造自己的劳动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可看到美学的实践观点的萌芽。这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为神圣家族写的准备论文》里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看出了劳动的本质,他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现实的人,看作他自己劳动的产品。’”朱光潜同时指出,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在劳动问题上的局限性,因为他所承认的劳动“即抽象的心灵的劳动”[注]以上引文见《朱光潜全集》第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2~143页。。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介入与活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即类的特性体现在自然之中,使自然成为人的本质与特征的确证,成为人的现实性和人的创造物,这样一个辩证互动的过程,就自然而言,叫作“自然的人化”,就人而言,叫作“人的对象化”。黑格尔笔下的小男孩,恰恰是人类祖先的象征,他的举手投足,他的笑对自然,为我们勾勒出人类社会早期,人与自然密切接触的奇妙的生态图景。人面对自然,从模仿到创造,从对峙到互存,并一步一步从功利走向审美。人在自己所创造的自然中直观自身,也就是直观即欣赏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美的作品,因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快慰,激起感情上的冲动,于是,人类最初的审美感觉油然而生;人类最初的艺术品也悄然问世。
普列汉诺夫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生动而精辟地阐释了劳动实践对人类早期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原始狩猎者的心理本性决定着他一般地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但他的生产力状况,他的狩猎的生活方式则使他恰好有是这些而非别的审美趣味和概念。这个结论清楚地阐明了狩猎部落的艺术,同时又是另一个有利于唯物史观的论据。”[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一卷,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页。他并以考古中发现的数万年前狩猎的绘画为例:狩猎者善于以山中的巨石与灌木丛作为掩体,并选择形状尖利的石块作为武器,袭击正在飞奔的野兽,狩猎者敏锐的观察力与健壮灵活的身体,以及对劳动工具的熟练运用,在绘画中生动呈现。狩猎者在这种劳动场面的记忆与复现中,逐渐成为人类最早的舞蹈家。
对于人来说,大自然最初表现为一种对立和异己的力量,最初的自然界并不能成为人类审美的对象,是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在普列汉诺夫的描述中,原始部落的女人并不用鲜花来装饰自己,尽管他们居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正是人类劳动实践的过程,既改变了人自身,也改变了自然界,使人与自然之间互为因果,既有物质的影响,又有精神的影响;既有身体享受的愉悦与快感,又逐渐形成审美的感觉与兴趣。“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2页。“自然的人化”与“人的对象化”使自然烙刻下人的本质的印记,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自然界才会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对象,并成为意识创造活动的客体。
但是,那些并非“人化的自然”,为什么也同样对人具有审美意义,并在人类最初的艺术创作中成为表现对象呢?譬如火红的太阳、明亮的月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森林……这些自然现象虽然没有打上人的劳动的烙印,但由于他们客观影响着人与自然生态的能动联系,实际上是直接参与了人类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一般地都是用所有者的眼光去看自然,他觉得大地上的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的。太阳和日光之所以美得可爱,也就是因为它们是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源泉,同时也因为日光直接有益于人的生命机能,增进他体内器官的活动,因而有益于我们的精神状态。”[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页。所以,人在这些并没有与劳动过程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然现象身上,同样可以“直观自身”,产生审美感觉,并使它们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观点,并进而科学阐释了劳动创造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和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但应该看到,这里的“劳动”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前提下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异化” 状态下劳动的结果,就完全可能呈现出特殊的状态。即,“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4页。。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中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否定,正是为了使忧心忡忡的穷人从赤贫的、畸形的、野蛮的、愚蠢和痴呆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唤醒与恢复人作为人的感觉与人对自然感觉的全部真实性,使人类的社会劳动与生活实践自觉演绎为自然向人的审美生成。也诚如曾繁仁先生所说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劳动由人的本质表现(肯定)到异化(否定),再到异化劳动之扬弃重新使之成为人的本质(否定之否定),应该说是具有深刻哲学与政治学意义的。而在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恰也经过了这样一种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否定(自然与人异化),再到否定之否定(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之处。”[注]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第157页。“异化”劳动能否创造美?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领域一直存有争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异化”劳动导致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扭曲与变形,带来审美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与消解。“异化”劳动状态下的艺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否定美”,喜剧大师卓别林演绎的《摩登时代》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实现对“异化”劳动的摆脱与超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才能回归正常,艺术审美的自由创造性才能得以真正体现。
三、 “美的规律”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美的规律”的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思想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艺术与美感起源的问题,进一步发现“劳动说”中所蕴藏的生态审美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3~274页。马克思是在比较了人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生产劳动的区别后,提出“美的规律”学说的。在我们看来,“美的规律”学说有着这样几个层面的逻辑联系。
(一)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
正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才确证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即“族类的身份”,这样,“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3页。。劳动成为将人从被奴役的动物式的生活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力量,成为消除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唯一途径。其结果是人类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拥有自然界,并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二)“尺度”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种的尺度”“内在的尺度”以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既是对事物属性的标识性的概念界定,又是揭示事物之间普遍性联系的范畴分析。它不仅纵向梳理了人类自身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普遍性本质与特征,而且横向廓清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所以,“尺度”虽然主要指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尺度,但同时也是指“人化的自然”的尺度。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创造性活动不仅像动物那样只是遵循对象的外部可感的形态和模样进行生产,以满足自身的狭隘的肉体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够按照对象的“内在的尺度即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来把握和塑造物体,同时体现出主体的、内在的尺度,即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和满足自身的高级的精神需要”[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马克思“美的规律”学说中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强调作为社会主体(审美主体)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体,即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类存在物”的统一体。而实现人的社会理性精神与自然欲望的现实基础正是人的物质劳动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凸现出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焕发出审美与艺术创造的欲望和激情,人类最初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品才可能应运而生。
(三)“美的规律”的论述重点在于凸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3页。这里,马克思将人类特性概括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我们看来,这是马克思诸多关于人的特性(或本质)的学理阐释中最符合人类自身面貌因而最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论断。自由,是人对狭隘物欲的超越,是人既依附自然又能动升华的标志。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动物只能是自然的奴役对象,而人则能够能动地介入自然,并积极适应自然的变化。自觉,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志的,并能够在自然中观照自身。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依据。当人还处在非自由与非自觉状态时,他对自然界充其量只能是简单地、机械地模仿,不可能从事能动的、复杂的创造,更谈不上进行审美活动,创造艺术品。
“美的规律”凝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重要内涵的自然观念与生态意识。马尔库塞说:“马克思的思想,是把自然界看成这样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成为满足人的天生媒介物,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本身的悦人力量和性质也得以恢复和解放出来。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尖锐对立,这种对‘自然的人的占有将会是非暴力的、非破坏性的,其方向是旨在顺应自然中的生命的维系、感性、审美性质。因此,改造了的‘人化的自然’,将反过来推动人对完满的追求。”[注]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季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美的规律既是人的规律,也是自然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的规律。人的审美感觉的产生,艺术作品的产生,绝不是人与自然单方面的作用,对于人而言,人的感受美的器官——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一句话,人类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创造能力,只有在“自然的人化”中才能产生并获得发展。同样,人的感觉器官所能感受到的美——耳朵所感受到的音乐美,眼睛所感受到的形式美,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审美和艺术创作的对象,也只是由于存在着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
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前提,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以及“人化的自然”是艺术审美的源泉等观点阐释,无疑体现出重要的生态审美意识。当然,马克思不会离开人的主体生成的社会历史活动来认同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既不认同黑格尔脱离人的物质活动的抽象的精神劳动,同时批判费尔巴哈的抛弃“感性的活动”的“感性的对象”。“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这里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正是自由自觉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正是通过劳动实践而摆脱动物界,而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倡导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正是强调在“人的能动的、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价值平等”的理想境界。我们同时要指出的是,以往我们在探讨人类最初艺术与美感的起源问题时,对马克思“劳动创造美”的命题的理解,存在着简单而偏狭的思维与诠释,只是将“劳动”等同于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劳动,而忽略了“劳动”本身应有的丰富内涵,殊不知早期人类自身的“种的繁衍”对于人类最初美感与艺术起源的重要影响;更缺少自觉而明确地从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维度来探究这个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命题。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结 语
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以及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日益得到重视,西方当代美学与文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逐渐成为理论资源主流。但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也必然以人与自然的融合作为基本的价值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脱离人的主体生成与历史实践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与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意识是相悖的。我们今天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说”中的思想观念与学理阐释,并努力发掘其中的生态审美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丰富和拓展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起源于劳动”说的价值内涵,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中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创作和理论上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性联系,不断丰富与拓展当代生态审美观的价值内涵,从而为科学评价生态美学和文学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