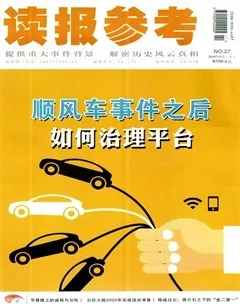亚非学生的吴桥杂技之梦
17岁的埃塞俄比亚姑娘黑克玛正在接近儿时的梦想——成为一个身怀绝技的人。
一年前,黑克玛成为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第14期留学生的一员时,只想着精进技术会带来更好的生活。而吴桥的招牌的确有这样的魔力,她还没回国,就被埃塞俄比亚国家杂技团“预定”了。
和她同期的35名外国学生,多数揣着类似的想法,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老挝和坦桑尼亚,年龄多在二十岁上下,多数在杂技上小有造诣,才获得了来中国“镀金”的机会。
8月8日,这批身怀吴桥杂技技艺的留学生踏上归途。和之前的13期学员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此可以凭借杂技安身立命,甚至过上优渥的生活。
为了最后的毕业演出,黑克玛已经排练了一个多月。
练功房里,塞拉利昂小伙儿手中翻飞着一顶顶草帽;埃塞俄比亚和老挝的女生在软垫上平躺,中国红鼓在她们双脚上轻巧翻跃;另一名老挝姑娘用手夹住一米多长、直径如铅笔的钎子,无论下腰、劈叉还是倒立,钎顶的14个红碟始终匀速旋转……
黑克玛则在三个项目中不停切换,除了滚环与吊环,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绸吊。
而刚刚来到中国的26名新留学生,每日重复着跑步、压腿、踢腿、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基本功。
塞拉利昂女孩贝特。一手扶杆,一手扶墙,左腿站立,右腿紧贴墙壁180度向上。
非洲西部国家塞拉利昂本没有杂技,2016年首次选派2名学员来吴桥学艺后,就开始筹办第一所公立杂技学校。而最好的机会仍然是到中国深造。
扎着五个蓬松发髻的贝特只有12岁,因舞蹈特长被选中。
吴桥素有“杂技之乡”之称,吴桥杂技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明末清初,吴桥杂技艺人走向世界,在50多个国家及地区留下足迹。
1950年代,中国国家杂技团里几乎一半都是吴桥籍演员。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欧14国,每每接见华侨代表,也总能看到吴桥杂技艺人的身影。
1984年,胡耀邦去江西考察时在吴桥短暂停留,当得知吴桥杂技仍靠家族式传承时,他提议:“你们应该办个学校。”次年,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创立,三十多年来在国内外杂技艺术节拿奖无数。
在这里,中国学生6年才能毕业,前3年练基本功,后3年学项目。但留学生交换时间通常只有1年,一入学直接练项目,辅以基础练习。第15期学生有一个多月专门夯实基础,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两名扎着脏辫的肯尼亚新生告诉记者:“一年太短,我们想尽可能多学技巧。”他俩一个20岁,一个22岁,在肯尼亚已当了两年杂技演员。他们十分珍惜在吴桥学习的机会,“这里的老师会纠正我们不标准的动作,在我们国家,只是叫我们做成动作而已”。
在吴桥杂技学校,留学生每天8点踏入练功房,上午练3.5小时,下午练3小时,晚上自由活动。而中国学生早上5点半起床做一个半小时的早课,之后才吃早饭。每天的专业课时间至少5小时,课后还要练功。
每位受访的专业课老师都感叹,中国学生听话、勤奋、遵守课堂纪律。而非洲学生每每集合,必有人迟到,常趿拉着拖鞋就来了;训练时段,还有人不声不响地径直回宿舍休息了。
自2002年起主管留学生教育的常务副校长齐志义告诉记者,非洲学生虽然“聪明,懒惰,没有时间观念”,但“身体条件都非常好,耐力、弹跳力、爆发力、平衡能力,比中国孩子都要优秀”。
当杂技在中国衰落,却在亚非国家成为收入颇丰的职业选择。
老挝留学生红姆巴斯9岁开始练杂技,20岁被国家杂技团录用,一个月能拿2000元基础工资,演出还有额外收入;在非洲,杂技和马戏都颇有前景。2015年,首届非洲杂技艺术节在埃塞俄比亚举行,85名年轻的表演者来自7个非洲国家的马戏团。活动组织方认为,马戏表演让非洲年轻人自信,一位吊架表演者坦陈,若没有马戏团,他可能会卷入帮派或毒品之中。
杂技也为许多女性提供了新的未来。乔恩毕业后进入了Mother Africa,一个总部位于德国、由非洲籍演员组成的艺术表演团体。5年来,她每天在不同的欧洲城市跳舞、变魔术,周薪达700欧元。
黑克玛不会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回国后,她将进入埃塞俄比亚国家杂技团,要是能到国外演出,收入将更可观。考虑到杂技表演存在年龄天花板,黑克玛打算同步念高中、考大学,日后当医生或服装设计师。“如果我的钱足够多,我还想开一个杂技学校。”
马尼最终选择长居中国。他毕业后加入一家德国经纪公司,奔波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表演柔术,每月基本工资2350欧元。他大概也是国人最熟悉的非洲杂技演员。那时,中国杂技市场行情好,马尼又是国际面孔,演出档期每天都是排满的,一场演出收入就有1至3万元。
在中国生活6年,马尼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常居沈阳,口头禅是“还行”,有一大票中国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马尼希望今后能转型为DJ或歌手。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