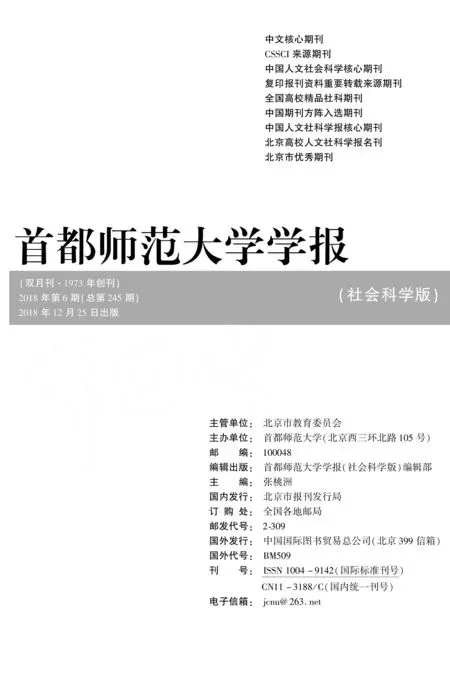谁在受欺凌?
——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研究
胡咏梅 李佳哲
一、 问题的提出
面对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现象,不少国家已经采取相关防治措施。例如,挪威建立了零容忍方案,发表了《反欺凌宣言》;澳大利亚成立专门的政府组织帮助学校解决欺凌问题,并将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命名为国家“反欺凌日”;美国和日本也相继颁布反欺凌法案,实施全面的反欺凌政策。我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校园欺凌问题: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2016 年 11 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等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2018 年3月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做客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部长之声”时,谈及老百姓对教育的十大期盼,“校园欺凌少一点”和“流动儿童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留守儿童得到关爱”并列成为十大期盼之一。校园欺凌问题已然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目前急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中国目前仍未有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缺乏准确、全面、权威、系统的数据,也缺乏深度专业的研究[注]储朝晖:《校园欺凌的中国问题与求解》,《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12期,第42-48页。。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4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中学生数据库,尝试回答:到底是谁在受欺凌?学生个体层面的哪些因素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城乡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差异有哪些?以期为中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精准防治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1)校园欺凌的概念及类型
全球范围内校园欺凌研究始于 20 世纪70 年代。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心理学家奥维尤斯(Olweus, D.)被誉为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之父,他在挪威和瑞典的中小学进行关于攻击行为的调查后发现,欺凌(bullying)行为是校园场域内青少年之间攻击行为的主要形式。他认为,校园欺凌是指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地、反复地、持续地做出负面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注]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long-term outcomes for the victims and an effective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L. R. Huesmann. Aggressive Behavior: Current Perspectives.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4: 97-130.我国学者张文新等也认为欺凌是儿童间尤其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目前针对校园欺凌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统一规范的概念,但关于校园欺凌的类型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主要包括关系欺凌(relational bullying)、言语欺凌(verbal bullying)、身体欺凌(physical bullying)[注]关系欺凌主要是欺凌者通过操纵人际关系,使得受欺凌者被孤立,感到不被群体认同,被排斥。言语欺凌指欺凌者对受欺凌者进行口头上的恐吓、责骂、羞辱、嘲弄或贬低等,从而对受欺凌者造成心理伤害,尽管肉眼看不到伤口,但它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比肢体伤害更严重,此行为通常伴随着关系欺凌,且两者属于欺凌发生刚开始阶段。身体或肢体欺凌是指受欺凌者遭受身体暴力,钱财物被勒索、抢夺或被偷,被强制做不想做的事情等,它是临床上最容易辨认的一种形态,是教育工作者最常关注的一种形态。等形式,近些年也出现网络欺凌(cyber bullying)新形式,即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如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对受害人实施恐吓、侮辱、威胁,甚至在网络上传播不实谣言、公开上传羞辱受害人的图片或者录像等。
(2)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
李明、郭瑞迎利用知识图谱等方法分析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两个子库(SCI-E,SSCI)收录的2007-2016 年有关校园欺凌研究的文献,发现国际学术期刊上校园欺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校园欺凌的本质及形式,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及危害、成因、对策等方面。[注]李明、郭瑞迎:《境外校园欺凌研究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9期,第103-109页。也有学者对我国近十年校园欺凌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各国校园欺凌表现”和“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对策”三大方面。[注]冯帮、李璇:《我国近十年校园欺凌问题研究述评》,《上海教育科研》2017年第4期,第10-15页。不少学者引介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的经验举措,如黄明涛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日本和韩国等七个发达国家校园欺凌治理体系进行梳理,认为其共同特点包括强化各方职责、注重过程监控、搭建各种防治校园欺凌的平台、注重网络欺凌的治理等。[注]黄明涛:《国外校园欺凌立法治理体系:现状、特点与借鉴——基于七个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55-63页。由此,“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的热点,对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3)防治校园欺凌现象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美国社会学家 C.W. Mills 提出的重要他人理论认为,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重要人物,如家长、教师和同伴,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重要他人的主导类型大体上呈家长——教师——同伴——无现实存在的重要他人这样的演变趋势。中学生人际交往是指其与周围人如家长、教师、同学的心理和行为的沟通过程,其主要人际关系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父母、教师、同伴往往是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有效帮助、并且可供学生依赖的对象。紧密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儿童减轻校园欺凌的困扰,而青少年感知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越融洽,其遭受欺凌的可能性越小。[注]Gage,N. A.,Prykanowski,D. A. & Larson, A. School climat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A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 analysi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2014,(29):256-271.黄亮基于 PISA2015 中国数据发现,父母情感支持、教师支持与学生经常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关系。[注]黄亮:《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6-42页。马雷军认为平时难以融入班集体、同伴关系水平较差的学生容易遭受欺凌。[注]马雷军:《让每个学生都安全:校园欺凌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小学管理》2016年第8期,第4-8页。纪林芹等人也发现儿童童年晚期同伴关系不利对儿童的欺凌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注]纪林芹、魏星、陈亮、张文新:《童年晚期同伴关系不利与儿童的攻击行为:自我概念与同伴信念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报》2012年第11期,第1479-1489页。一些社会交往能力较弱的儿童,在同龄人群体中容易被边缘化而遭受欺凌。[注]Faris, R., & Felmlee, D. Casualties of Social Combat School Network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 79(2): 228-257.因此,中学生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师生关系水平会对其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此外,相关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其人际关系水平相关,如亲社会行为能显著提高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注]Ferguson, K. M., & Xie, B. Adult support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homeless youths who attend high school.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2012,41(5): 427-445.从而更容易在学业和人际关系方面取得成功,被欺凌的可能性更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设1:亲子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2:同伴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3:师生关系越好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假设4: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的中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
(4)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个体特征
Hindelang 于 1978 年提出生活方式理论(Lifestyle Theory),认为个人自身的一些行为或生活特性会增加其被侵害的可能性。[注]张小华、项宗友:《浙江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实证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为视角》,《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第101-105页。。依据生活方式理论,学生自身特征及行为会对其遭受欺凌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男孩遭受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女孩。[注]Craig, W., et al. A Cross-national Profile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40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9, 54(2): 216-224.[注]Elgar, F. J., Pickett, K. E., & Pickett, W., et al.School bullying, homici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cross-national pooled time series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3, (58):237-245.黄亮基于PISA2015中国数据发现,男生群体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比例均大于女生群体。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容易成为遭受歧视和嘲讽的受欺凌对象。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关注中学生校园欺凌城乡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国内实证研究目前仅发现黄亮等人的两篇文章,他们的研究发现,校园欺凌无显著差异地存在于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城乡变量对学生经常遭受校园欺凌的预测效果不显著。[注]黄亮:《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6-42页。[注]黄亮、赵德成:《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关系的实证研究——家长支持和教师支持的中介作用》,《教育科学》2018年第1期,第7-13页。但此研究并未估计城乡变量对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城乡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是否来自城市对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无显著预测作用。
与城乡变量相关,滕洪昌、姚建龙基于对全国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发现,父母在外打工的男生、父母在外打工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被欺凌的现象较为严重。[注]滕洪昌、姚建龙:《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全国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教育科学研究》 2018年第3期,第5-11页,第23页。有学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单亲家庭的子女可能由于家庭关系的淡漠或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无法给予其足够的关照和爱护而容易遭受欺凌。[注]周逸先:《防治校园欺凌要从家庭教育抓起》,《中国教育报》2017年12月20日。此外,有研究发现,受欺凌者通常具有较低的自尊水平,且自尊水平影响其遭受欺凌的概率。[注]Malecki, C. K., Demaray, M. K. & Coyle,S.,et al. Frequency, power differential, and intention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for victims of bullying. Child Youth Care Forum, 2015, (44):115-131.[注]谷传华、张文新:《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心理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5页。马雷军认为学业不佳的学生可能因为不能得到教师的重视甚至受到教师嘲讽,进而很可能遭受同学的歧视和欺凌。[注]马雷军:《让每个学生都安全:校园欺凌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小学管理》2016年第8期,第4-8页。雷雳、黄亮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学生学业表现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关系,学生学业表现越好,其受欺凌的程度就越低。[注]雷雳、王燕、郭伯良等:《班级行为范式对个体行为与受欺负关系影响的多层分析》,《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
综上所述,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学生个体是否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是否来自单亲家庭以及自身自尊水平等人格特质、学业成就可能会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但仍缺乏从学生个体特征层面系统设计的实证研究的支持。此外,关于城乡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是否存在影响及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将针对学生个体层面可能会对其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以期探究影响中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关键因素。
现有研究尤其国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为主,采用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而且此类研究样本量以及样本代表性问题值得商榷。相关结论需要来自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高质量研究数据的进一步检验。此外,国外不少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如已有研究发现,女生更容易受到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注]Veenstra,R. et al.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 Comparison of Bullies, Victims and Uninvolved Pre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5, 41(4): 672-682.而男生群体更容易发生身体欺凌。[注]Peets, K. & Kikas, E. Aggressive strategies and victimiz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Grad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ross-informant agreement. Aggressive Behavior, 2006, 32(1): 68-79.国内此类研究相对欠缺,而对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将利于精准防治我国校园欺凌现象这一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本文将利用2014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中学生数据库,估计中学生是否来自城市,是否为流动、留守儿童,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其自身学业表现、人格品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变量对其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效应以及对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异质性展开分析,且检验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需要指出,本研究利用大规模中学生调查数据,与已有同类研究相比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既关注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差异,同时也对流动、留守、单亲儿童校园欺凌研究给予实证数据的支持;在计量方法选择上,克服传统 OLS估计的局限,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进行各类影响因素的效应估计。当然,由于数据库设计的局限,对于流动、留守儿童的界定并未严格按照学术定义,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另外,本研究对于校园欺凌的成因分析尚未进行计量上的因果推断,但本研究依然为探讨个体层面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以及校园欺凌行为的精准防治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4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大型教育测评项目“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该项目在锡盟、郑州、福田等地实施全测,在浙江、株洲、洛阳、深圳、石家庄等地采用分层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式(PPS)实施测试。具体来说,第一阶段,采用分层 PPS 方法抽取县、区;第二阶段采用分层 PPS 方法抽取学校;第三阶段采用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学生。在测试中,九年级学生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人文测试,[注]“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的所有测试工具均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全国的学科教育专家编写,测试工具质量均符合大规模测试的测量学要求。同时填写心理健康、品德行为、影响因素等相关调查问卷。共有 178606 名九年级学生参与了此项调查,其中男生 94525 人,占比 52.92%,比女生高出 5.84%。学校所在地为城市、县镇、农村的学生分别占比 67.64%、24.73%、7.63%。在农村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较低,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初中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初中学校数量逐渐下降、很多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中学就读有关。
基于已有文献研究[注]Fu, Q., Land, K. C & Lamb, V. L.Bullying victimiza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12th gr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9 to 2009: Repetitive trends and persistent risk differentials.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6):1-21.[注]Malecki, C. K., Demaray, M. K. & Coyle, S., et al. Frequency, power differential, and intention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for victims of bullying. Child Youth Care Forum, 2015, (44): 115-131.[注]黄亮:《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6-42页。[注]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0期,第31-41页。,本文主要考察中学生的学业成就、家庭特征、人格品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变量对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拟采用如下计量模型探究影响中学生受欺凌的关键因素。
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各类校园欺凌,包括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身体欺凌三类。Olweus 编制的欺凌问卷(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被公认为是较好的测量工具。国内学者张文新对 Olweus 的欺凌问卷做了翻译和修订。“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以张文新修订的欺凌问卷为基础进行改编,测查学生在学校遭受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频次。其中,关系欺凌包括“被人排斥”、“被人在背后说坏话”两个题项,言语欺凌包括“受到取笑或捉弄”、“受到威胁或恐吓”两个题项,身体欺凌包括“被人故意打、踢、推、撞”、“自己的东西被人故意损坏”、“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三个题项。与 PISA 项目中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测量的相关题项相比,“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中对校园欺凌的测量添加了“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这一题项。经过内部一致性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校园欺凌量表的信效度指标较好,达到了测量学对量表工具的质量要求。
模型中的自变量的取值说明详见表1。其中自尊(self - esteem)、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hip)、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等变量均涉及对应量表。

表1 变量说明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所持有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等总体的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自尊的测量,早期由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被广泛应用。1993年,季益富和于欣将该量表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成员对季益富和于欣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做进一步修订,最后量表由“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归根结底,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我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我时常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等10个题项组成,采用“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组曾对 Furman & Buhrmester 在 1992 年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NRI)量表进行了修订、改编,形成了 8 个维度、23 个题项的亲子关系量表,量表的信效度良好。综合考虑问卷长度及时间限制,“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对该量表进行题项删减,最终选取每个维度上载荷较高的题项,形成“你对你和父母的关系感到满意吗”、“你和父母相处感到愉快吗”、“你会和父母分享心里的秘密和个人感受吗”、“你和父母会意见不合或吵架吗”、“你和父母会互相争论或指责对方吗”、“你和父母在一起会感到烦恼吗”、“当你遇到问题时父母会帮助你解决吗”、“父母喜欢或称赞你做的事情吗”、“你和父母互相感到厌烦吗”、“父母爱你吗”、“你会和父母一起做一些开心的事吗”共11个题项的量表,量表采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四级计分。
同伴关系主要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注]邹泓、林崇德:《青少年的交往目标与同伴关系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年第2期,第2-7页。“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对中文版儿童孤独感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CLS)进行修订,以儿童孤独感状况反映其同伴关系。最终量表包括“我和同学在一起时很开心”、“我的同学经常欺负我”、“我很满意自己与同学的关系”、“我经常与同学发生争执”、“当我需要时我可以找到朋友”、“我有许多好朋友”、“班上同学很喜欢我”、“我在班里觉得孤单”、“我很难让别的孩子喜欢我”、“我觉得在有些活动中没人理我”共10道题目,采取“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
师生关系主要指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系。综合考虑问卷长度及时间限制,“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对屈智勇编制的《师生关系量表》进行修订,最后形成由“老师公平地对待我”、“老师对我很关注”、“老师和我是好朋友”、“老师关心每一位学生”、“老师允许我们有不同的见解”、“老师耐心听我的想法”、“老师不讽刺、挖苦我”、“当我犯错误时老师会主动询问原因”、“老师不要求我必须接受他(她)的观点”、“我非常敬佩我的老师”、“老师鼓励我、表扬我”、“我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当我遇到学习以外的困难时会想到寻求老师的帮助”、“我愿意在老师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点”、“老师很信任我”组成的 15 个题项的量表,采用“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
亲社会行为是指给别人带来某些好处的行为,做出这些行为能使交往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和谐。[注]寇彧、付艳、张庆鹏:《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一项焦点群体访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54-173页。“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Goodman.R 于 1997 年编制的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修订的中文版问卷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改,最终亲社会行为量表采用“不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三级计分,包括“我尽量对别人友善”、“我常与他人分享东西(如食物、游戏、笔等)”、“如果有人受伤、难过或不适,我都乐意帮忙”、“我会友善地对待比我年龄小的孩子”、“我常自愿帮助别人”5 道题目,量表为单一维度,反映了个体亲社会行为状况。
本研究涉及的校园欺凌、自尊、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社会行为等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具体指标参见表2。

表2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

图1 中学生遭受各种形式校园欺凌的分布比例
由图1可知,所有欺凌形式中,“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发生的频率最低(6.64%),且为便于与PISA结果比较,以下分析中删除此题。而“受到取笑或捉弄”发生的频率最高(58.28%),这一结果与陈纯槿、郅庭瑾利用PISA数据计算结果不同,他们发现我国四省市校园欺凌发生率最低的是威胁形式的言语欺凌,而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故意损毁私人财物。[注]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0期,第31-41页。但本研究结果与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的结果基本一致,即言语欺凌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欺凌行为,至少有30.85%、58.28%、43.34% 的中学生遭受过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注]张云:《〈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发布——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http:/ /www. chinanews. com/sh/2017/05-21/8229705. Shtml,2017年10月12日。这一结果略高于其他研究的结果,如周金燕、冯思澈以北京市的12 所高中、初中和小学为样本发现,40.7%的北京中小学生有被叫难听绰号的经历,18.6% 的学生有被同学联合起来孤立的经历。[注]周金燕、冯思澈:《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调查及分析》,见杨东平、杨旻、黄胜利:《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29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针对我国10个省市的5864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有32.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注]刘洪超、孙振:《住手! 校园欺凌(微调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二) 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为探究哪些学生更可能遭受欺凌,笔者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分别探究在控制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个人学业表现、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自尊水平以及其是否为流动、留守儿童,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其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考虑到中学生学业表现、人际关系、社会行为、自尊水平等变量对其遭受关系欺凌、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的影响,估计方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如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为提高估计效率并检验各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采用似不相关回归的方法。此外,考虑到自尊水平、亲社会行为以及同伴关系之间的高度相关,似不相关回归的过程中同样采用两个模型,模型一不包含自尊和亲社会行为变量,模型二不包括同伴关系变量。模型一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0.508-0.661之间,且BP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H0: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P=0.0000),模型二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0.552-0.688之间,且BP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H0: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P=0.0000),说明模型一和模型二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比较适切。

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并不会对其遭受各种类型的欺凌产生显著影响(P>0.1),这一结果否定了本研究假设4。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亲社会行为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是间接的,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可能由于影响其人际关系水平,进而影响其遭受欺凌的概率,如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可能会影响其同伴接纳水平。[注]Ferguson, K. M., & Xie, B. Adult support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homeless youths who attend high school.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2012,41(5): 427-445.
中学生的学业表现对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几乎无影响(β=0.000,P<0.01)。但性别对三类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虽然无论是关系欺凌、身体欺凌还是言语欺凌,男生相较于女生都更可能遭受欺凌,但这种差异更多表现在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上。此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注]Barboza, G. E. Schiamberg, L. B., Oehmke, J., Korzeniewski, S.J., Post, L. A., & Heraux, C. 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ultiple contexts of adolescent bullying: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9, 38(1):101-121.[注]黄亮:《我国15岁在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基于PISA2015我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6-42页。[注]周金燕、冯思澈:《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调查及分析》,见杨东平、杨旻、黄胜利:《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29页。我们推测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暴力行为在男生群体中可能受到欣赏乃至崇拜,如西方的古罗马斗兽场、中国的梁山好汉等。男生群体相对于女生群体更加容易躁动和爆发冲突,因此,男生更可能成为身体欺凌的受害者,而欺凌过程中多种欺凌行为捆绑组合出现也可能使得男生成为言语和关系欺凌的受害者。
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中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但对其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整体来看,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可能的原因在于单亲家庭的中学生由于与父母中的一方情感冷漠,容易产生孤僻心理,在校园里易被同学误以为孤傲,从而遭受关系欺凌。此外,来自非单亲家庭的学生也可能由于认知与情感发展尚不成熟,同理心水平较低,将单亲家庭成长的同伴理解为是与自己不同类型的特殊群体,从而产生排斥、嘲笑甚至侮辱等欺凌行为。[注]Chan,H. C. O. & Wong,D. S. W.The overla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Assessing the psychological,familial and school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5,(24): 3224-3234.
是否为流动儿童对中学生遭受各种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与其他类型校园欺凌相比,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但是否为留守儿童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几乎相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这与周金燕、冯思澈的结论基本一致,他们发现外地学生比北京本地学生会遭受更多欺凌。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可能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设计的不公平,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注]周金燕、冯思澈:《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调查及分析》,见杨东平、杨旻、黄胜利:《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29页。王玉香通过质性研究发现,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与父母缺位所造成的安全感降低、青春期同伴依恋的归属感以及青少年彰显自主性的存在感有关。[注]王玉香:《农村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的质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2期,第63-68页。
自尊对各种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已有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注]Malecki, C. K., Demaray,M. K. & Coyle,S.,et al. Frequency, power differential, and intention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for victims of bullying. Child Youth Care Forum, 2015, (44):115-131.[注]谷传华、张文新:《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心理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5页。本研究发现,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呈现U型关系。自尊水平过低,降低了个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可能使得中学生在面对可能的欺凌行为时不能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乃至人格尊严,而是一味地委曲求全,最终导致其不断遭受校园欺凌。而中学生自尊水平过高,自我评价过高,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可能导致他人不满或对他人评价过于“敏感”,从而遭受校园欺凌,尤其是受到关系欺凌。因此,中学生保持适度水平的自尊对其免于遭受校园欺凌是必要的。
为考察表3似不相关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改变函数形式进行似不相关biprobit回归,结果见附表1。大部分模型系数结果与表3回归结果一致,只是在是否遭受关系欺凌这一行为上,女生显著多于男生。这一结果与Jing Wang等人[注]Jing Wang, Ronald J. Iannotti, and Tonja R. Nansel,Ph.D.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4): 368-375.的结果一致。由此可知,表3中各模型的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三)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异质性分析
表4中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成绩、自尊、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但中学生亲社会行为对其遭受言语欺凌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0.014,P<0.1),即中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其遭受言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4。此外,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不再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
我们尤其关注表4中城乡变量及其与其它变量的交互项对中学生遭受各种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校园欺凌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城乡变量仅对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预测作用(β=-0.05,P<0.01),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相较于城市中学生,来自乡村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言语欺凌。这可能与乡村学校规模较小、受乡村文化的影响有关。乡村学生彼此间甚至家庭间较为熟悉,身处乡村文化中也更可能接触非礼貌用语,容易发生取笑、捉弄同学的现象。此外,城乡变量与同伴关系的交互项(β=-0.026,P<0.05)会显著影响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的频次,但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没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乡村中学生,在遭受关系欺凌方面,同伴关系对城市中学生的影响效应更大。因此我们既要关注乡村中学生群体间言语欺凌现象,也要注意引导城市中学生构建和谐的同伴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校园欺凌行为的治理路径需要由事后的危机处理走向早期介入与防治。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关系欺凌次之,身体欺凌最低。相较于“看得见”的身体欺凌,老师和家长“听不见”的言语欺凌、“感觉不到”的关系欺凌更难以被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觉察和监控,但它们足以对受欺凌的中学生身心产生长久危害。因此,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在校园公共领域安装“电子眼”进行实时监控,另一方面,教师要注重和学生之间的日常交流,通过学生反映的信息了解班级内是否有人遭受关系欺凌或言语欺凌,以便及早查明事实,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例如,对已经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及时中断欺凌行为,避免对受欺凌者造成更多的伤害以及影响欺凌者未来的个性、心理及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同时,要保护受欺凌者,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以防受欺凌者因受欺凌而产生心理阴影。
第二,男生相较于女生,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且男女生在遭受校园欺凌上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上。由于男生更加容易躁动和爆发冲突,因此,家长、教师要多关注男生的言语和行为。男生家长要多关注其日常生活表现,是否出现异常行为,如衣冠不整地回家、晚上睡觉做噩梦、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等。如果男孩有此类行为,家长应及时与孩子沟通,了解其是否在学校遭受欺凌。教师也要加强针对中学生尤其男生的规则意识教育,可以借鉴奥维斯欺凌防范项目(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OBPP)[注]Lazarus, P.J., Pfohl, W.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Information for Educators. Communiqué, 2012,(4):27-28.,清晰界定欺凌行为,对中学生尤其男生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同时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和睦的同伴互动关系,防范学生间尤其是男生群体的嬉戏打闹或者小矛盾发展为欺凌事件。


第三,乡村儿童以及单亲、流动、留守儿童较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尤其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关系欺凌,乡村儿童、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但是否为留守儿童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几乎相同。因此,针对乡村中学生或者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流动儿童家庭等“高风险家庭”的中学生,学校应尽快建立关爱档案,教师需要重点关注,尽量保证其在校期间的安全。此外,学校和家庭要加强反校园欺凌合作,通过开家长会等形式,普及欺凌与反欺凌的知识,为家长发放反校园欺凌手册,以及加强家长与班级教师的沟通,尤其班主任需要与“高风险家庭”家长保持联络,鼓励他们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经常与孩子保持亲密的联系,给予孩子多一点关爱,帮助孩子提升社交技能,恢复和重建自尊、自信及信任等。
第四,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间呈现 U 型关系,且这种影响更多表现在关系欺凌上。因此,为使中学生和同伴建立良好关系,免于遭受关系欺凌,保持适度的自尊水平是十分必要的。自尊水平过低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过于消极甚至自卑,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个别辅导等形式,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团体活动,主动参与人际交往,大胆展示自己。家长也要正确评价孩子,充分信任他们,鼓励他们在人群中表达自我,以帮助其建立自信。对于自尊水平过高甚至有些“自负”的中学生,学校应注意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帮助此类学生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人。学会悦纳、尊重他人,才会被同辈群体接纳和认可。
第五,中学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均会显著影响中学生遭受欺凌的频次,且同伴关系对城市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因此,要给予在社会交际方面表现相对“弱势”的学生更多的关怀和帮助。父母要增强与孩子的交流,及时询问孩子在学校的人际交往情况,倾听孩子在诉说过程中流露出的一些信息,及时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否受到欺凌,尽早发现欺凌行为并请老师介入予以制止。此外,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学会自我保护,采取适当的自卫举措,如教会孩子学会反抗,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同时,教师要公平地给予每个学生支持和关爱,也可以引导中学生尤其城市中学生建立同伴支持系统,形成反欺凌的班级氛围。例如,借鉴芬兰校园反欺凌计划,通过以人际关系、群体压力等为主题的反欺凌课程和移情训练,强化学生反欺凌的态度,增加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充分发挥旁观者的作用,[注]在欺凌事件发生时,如旁观者沉默、默许、赞许及加入欺凌等表现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而旁观者如果反对、制止欺凌者,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欺凌行为的进度。在校园欺凌现象发生时,通常受欺凌者的同伴会在场,他们作为旁观者如果能够发挥旁观者作用,形成反欺凌的班级文化和校园文化,将会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和欺凌的危害程度。以此减少整个校园学生的欺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