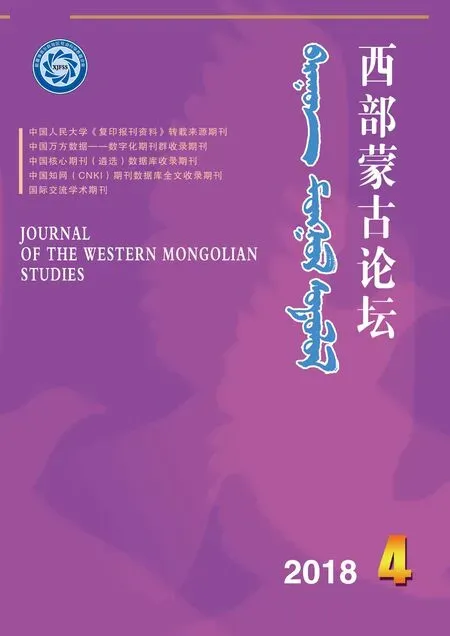圆梦之旅
——走马观花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
马大正 阿拉腾奥其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 2017年4月末,两位作者有幸赴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旅行考察,寻访18世纪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牙帐所在——马奴托海,畅游卡尔梅克草原以及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市,考察查干阿姆、扎木杨渡口、建于19世纪的和硕特庙遗址以及阿斯特拉罕克林姆林宫,并走访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人文科学研究所(原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与卡尔梅克学者进行交流。本文即为作者此次旅行考察的见闻及所思所想。另外,两位作者还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对土尔扈特蒙古历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有益考述。
开篇的话
远赴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追寻土尔扈特汗国的历史踪迹,是马大正多年的宿愿,自上世纪80年代萌发,至今已有近40年的岁月。马大正在记述自己寻访土尔扈特人历史的游记《天山问穹庐》中曾发出如下感叹:
“卫拉特蒙古是一个世界性民族,目前在蒙古、美国、法国等地都有他们的踪迹,最集中的还是在我们的邻邦俄罗斯。当年渥巴锡率领近17万部众踏上了东归故土之途,但在伏尔加河流域仍然留下了很多卫拉特蒙古人。本世纪的苏联时期,这部分卫拉特人曾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创造过辉煌。在1944年的一天又突遭厄运,一夜之间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居民被迫迁徒到西伯利亚,成为“被惩罚的民族”,直到1957年才得以平反,自治共和国重建,整个民族的名誉得以恢复。伏尔加河流域毕竞是卫拉特人曾经生活过一个半世纪的地方,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卫拉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曾在这里创立了土尔扈特汗国,他的牙帐所在地马奴托海,如今还能找到么?”[注]马大正:《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多少年过去,到卡尔梅克共和国寻访土尔扈特人的踪迹仍停留在计划而未有行动,一拖再拖,唯一原由是时间安排上身不由已。2014年再次提出,经中国边疆研究所阿拉腾奥其尔、新疆师范大学巴图巴雅尔联系,确定2015年5月成行,决定主访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顺访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还发来了邀请函。遗憾的是,成行前夕又生变故而作罢。好事多磨,心有不甘,加之马大正将至“奔八”之年,可以行动自如的岁月毕竟有限了。终于在2017年4月正式成行。只是原先计划的三人小组,成了马大正和阿拉腾奥其尔两人了,巴图巴雅尔因教务在身,未能同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此次为期10天访察的主题:
一是,尽可能寻访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的遗迹、遗址、遗物,并了解18世纪下半叶以降卡尔梅克人的历史与社会;
二是,与卡尔梅克历史研究者交往交流;
三是,体味埃里斯塔的文化氛围和卡尔梅克普通人的民风民俗。
考察的路线选择:
一是,2017年4月20日—4月21日,由北京飞莫斯科,当天转机伏尔加格勒,在伏尔加格勒寻访阿玉奇牙帐地马努托海遗址疑似地,以及当地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祖国母亲纪念碑;
二是,2017年4月22日—4月25日,由伏尔加格勒车行至埃里斯塔,以卡尔梅克首府埃里斯塔为中心,辐射周缘地区,特别是体味卡尔梅克草原特有的艳美;
三是,2017年4月26日—4月27日,由埃里斯塔车行至阿斯特拉罕,重点访察沿途的查干阿姆、伏尔加河渡口、和硕特庙和阿斯特拉罕的小克里姆林宫——沙俄时期阿斯特拉罕将军衙门所在地;
四是,2017年4月28日—5月1日,由阿斯特拉罕飞莫斯科,重点重访红场和俯首山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5月2日返抵北京。
时间有限,寻访内容丰富,加之主人们无比热情好客,留下十分亲切美好记忆。访察回来半年有余,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寻访中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文。思之再三,还是依访察之时间先后为序,分题记实。
马奴托海寻觅
马奴托海是土尔扈特汗国著名汗王阿玉奇汗的牙帐所在地。在记实寻觅见闻之前先追述一下17世纪30年代以降土尔扈特汗国(也就是卡尔梅克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历史轨迹。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人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徒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国,直至1771年渥巴锡率部重返故土。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建立的土尔扈特汗国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一)1632年至1669年,即和鄂勒克开拓局面,建立政权,是土尔扈特汗国的初创期;
(二)1670年—1724年,即著名汗王阿玉奇执政的年代,由于他卓有成效的施政,汗国势力不断发展与壮大,是土尔扈特国的鼎盛时期;
(三)1724年—1761年,即阿玉奇汗逝世后,由于王公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继承而造成汗国内乱频仍与汗位不断更迭,是汗国由兴盛向衰落的动乱时期;
(四)1761年—1771年,亦即渥巴锡执政时期,由于沙皇俄国控制空前加剧而造成汗国严重政治危机。土尔扈特人反抗压迫在渥巴锡领导下举族东归祖邦,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土尔扈特汗国走向瓦解。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杜尔伯特牧民和少量土尔扈特人、和硕特人大约4700余帐,全部归入阿斯特拉罕省长办公室下设的专门管理机构——“特别管理处”管辖,1797年俄国政府在阿斯特拉罕成立“卡尔梅克公署”,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已失去了政治独立,沦为俄国政府监督下的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20世纪以降是卡尔梅克人的历史也是曲折坎坷,1917年十月社会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1920年卡尔梅克人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自治共和国。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人活跃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游击战场,与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战斗。不幸的是,1943年底,全体卡尔梅克被扣上通敌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幼被强制迁到中亚、西伯利亚。直到50年代下半叶,这起冤案才得平反。1958后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改称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马奴托海的寻觅上。
1714年7月12日(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一),图理琛使团一行抵达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牙帐所在地马奴托海,次日,阿玉奇汗在其汗帐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
马奴托海在今之何地?马大正和马汝珩在《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11年第105页)记述“地点大致在阿斯特拉罕以北的伏尔加格勒到里亚尔之间的伏尔加河右岸一带”。此说只是指了一个大体方向,只有面而无点!近年,阿拉腾奥其尔在其专著《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了考证。
一是,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米勒、伯希和、加恩都认为马奴托海“位于伏尔加河以东、介于察里津和谢尔纳-雅尔之间”,而日本学者今西春秋认为当在“萨拉托夫向南或向东南方向的腹地”,具体言在“叶鲁斯兰河上游”,应在察里津(伏尔加格勒)以北,在萨拉托夫市对岸,今恩格斯市东南不太远的地方”。(均见该书第358—359页)
二是,从蒙古语马奴托海一词词义本身分析,此地应距察里津不远。蒙古语地名中经常出现“托海”(-toxai/-toqai)词尾,意为“河湾、湾”。假如我们看今日俄罗斯南部地图,就不难发现,伏尔加河由东北而来,在伏尔加格勒(即察里津)形成一道河湾,折而向东南,最后流入里海。因此,阿玉奇汗牙帐马努托海,应该就在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对岸不远的地方。循着这样的思路,阿拉腾奥其尔近日在英特网上浏览了维基百科(俄语版)对“伏尔加市(Волжский)”词条的解释。不出所料,我的这种推论完全得到印证。该词条释文:“伏尔加市位置:北纬48°47′00″,东经44°46′00″。……位于伏尔加格勒东北,阿克图巴河左岸,距离伏尔加格勒20公里。14世纪,在伏尔加市所在地方,曾有金帐汗国的一个或数个居民点。诺盖人、卡尔梅克和卡拉卡帕克人曾在这里游牧。1634年以后,卡尔梅克人经常把汗的牙帐设在马奴托海附近地区,即今Киляковки,当河水泛滥时,经惟一的多沙浅滩移到高处。察里津历任城防司令曾多次试图将卡尔梅克汗的牙帐移往阿克图巴河下游,但此事直到彼得一世去世后才做到。1729年以后,开始有俄罗斯人移住。”遗憾的是,这段文字没有注明出处,但并非毫无依据。伏尔加市就在伏尔加格勒东北方向,在伏尔加河对岸,在河湾的上方。由此看,马努托海位于今俄罗斯伏尔加市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该书第359—360页)
2017年4月21日,我们在乌兰巴义尔的带领下参观完令人震撼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和神往以久的祖国母亲纪念碑群后,驱车过伏尔加河来到30公里外的阿赫图巴河左岸,来到了前文所述伏尔加市基里亚科夫基(Киляковки)区。这里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当年图理琛曾造访过的阿玉奇汗牙帐所在地——马奴托海。
马奴托海实际上指的就是伏尔加河与阿赫图巴河之间的河滩地。当然,阿赫图巴河左岸高坡上的大片区域也都在马奴托海的范围之内。可以想象,到了夏日,河滩里一定是草木茂盛,河水丰沛,柳树成荫,郁郁葱葱。而我们到来的这个时节,正好是俄罗斯的春末,树木刚刚吐露春呀,尚未长出绿叶。河滩里,榆树和柳树相互参杂,枯枝残叶,黑压压一片。而这一天,天公也不作美,天气阴冷,乌云密布,而且云层很低。远处的伏尔加格勒市,隐隐约约,隐藏在春日伏尔加河河面弥漫的烟雾之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景象,正好映证了新疆一首土尔扈特民歌里所唱的情景:
Manu toxai-yin burγasun,

Urida-yin tabiγsan yöröl.
马奴托海的柳树呦,
雾气弥漫,烟雾缭绕。
你我能喜结连理呦,
是那上辈注定的缘分。
亲临向往已久的马奴托海,看到眼前的景象,马先生显得兴奋不已,喜悦或是惊喜,已经不能准确表达马先生此时的心情。老先生早已忘记了昨日的劳顿和疲惫,掏出昨夜我们离开后充好电的相机,开始不停地拍照,仿佛要把马奴托海全部装进相机里,带进永远的记忆里。
当我们驱车返回伏尔加格勒时,在离此处不远见到两块路碑:Киляковки和Ахтуба。马奴托海,当年阿玉奇汗汗帐所在地,即在今伏尔加格勒下属的伏尔加市,只是距离之后的卡尔梅克人政治、文化中心埃里斯塔市有百余公里之遥,也可想见当年游牧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疆域之遥宽!
奔驰在卡尔梅克大草原上遐思
卡尔梅克大草原是土尔扈特人赖以生活之地,到底有多大,是啥样子?
是像我们亲历过的风吹草底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是铺满白色珍珠(羊群)长满碧绿酥油草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从友人所摄的卡尔梅克大草原照片看:辽阔无际、碧绿一片中盛开鲜艳的郁金香花,又是一番美景。
卡尔梅克草原位于亚欧草原的西端,是我们熟知的南俄草原的一部分。东面,伏尔加河由北向南静静地流过,南面是欧亚大陆的内海——里海,但卡尔梅克草原丝毫也享受不到来自里海的水汽,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干旱,气温能达到+40多度。据说,五月是卡尔梅克最好的季节。
这次身临其境于卡尔梅克大草原有三次。一次是静态的,两次是动态的。
静态的一次是4月24日,我们造访埃里斯塔郊区的一棵树景区。景区所在地实是一片大草原,由于我们来的稍早,天气还带着早春的凉意,草原上盛开郁金香的美景不甚显著,但间或还可看到在刚泛绿的草地上红色、黄色的郁金香在风中摇曳!
我们一行顶着至少有六级的大风参观了景区中的两个景点:一是一棵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参天大树,树身挂满不同色彩的哈达和风马旗!二是一座放置酥油灯的小屋,酥油灯的火苗在我们眼前不停晃动。也许那天正好星期一,景区除我们一行四人外,未见游人踪迹。
静态的卡尔梅克大草原,艳丽依然,宁静温馨,除了风声就是寂静!
两次动态的。一次是4月22日由伏尔加格勒驱车南行约90余公里到伏尔加格勒州与卡尔梅克共和国交界处,在伏尔加格勒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两处很有特色的地标前稍做停留、照相后即进入卡尔梅克共和国境界,其时汽车奔驰在辽阔的卡尔梅克大草原,除了激动,还有期待!
另一次是4月26日,由埃里斯塔驱车东行,途经查干阿姆,赴里海畔的阿斯特拉罕,一路同样奔驰在辽阔的卡尔梅克大草原。
我们二次驱车奔驰在卡尔梅克大草原,草原景色依旧:极目远眺,天高云淡,一望无际,绿色一片,时有牛群、羊群散落其间。但当我们仰视东方日出的朝霞突然萌生联翩浮想:
1771年1月17日,就在这一天,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统一指挥下举族东返祖邦故土,整个民族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伏尔加河下游1月气候,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阵阵劲吹,当旭日的阳光酒向大雪覆盖的伏尔加河草原时,皑皑的白雪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就在此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撬,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保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是啊,246年后的此刻,我正同样面向日出东方的太阳,走在土尔扈特人东归祖邦的道路上!
这样感受,在书本的阅读中是体味不到的。
渥巴锡纪念碑雕像和渥巴锡画像
在埃里斯塔听说这里有一座渥巴锡纪念碑雕像感到十分兴奋,兴奋的是,今天的卡尔梅克人对渥巴锡当年举族东归之举从感情上到理智上是接受的,若非如此,尽管是蒙古国艺术家制作,也难得以置放在埃里斯塔。
4月24日下午,我们驱车至位于一处市郊居民区一侧的一块绿地,拜谒了渥巴锡纪念碑雕像。
渥巴锡纪念碑雕像于2012年11月9日在卡尔梅克首府埃利斯塔市树立,11月22日,埃利斯塔市民为雕像举办隆重的揭幕仪式。该雕像高4.39米,底座高3.4米,由蒙古国科布多省布尔根苏木赠送。
渥巴锡纪念碑雕像为青铜所铸,身著蒙古武士军服,骑马远眺,给人的印象是纪念有余,英姿不足,座骑雕塑更是缺乏动感。与耸立在新疆和静县城中心广场的汉石玉渥巴锡纪念雕像相比,后者的坐骑作奔驰状,大大提升了渥巴锡的英姿。
陪同我们参观的巴兹尔先生还讲了一段小掌故,当年蒙古国有关方面提出要赠捐渥巴锡纪念碑雕像给卡尔梅克共和国,希望安置在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几经讨论,最后市府同意安置在首府,但不是在市中心广场,而是选择较为偏僻的市郊一工业区的绿地上。
我们一行绕行雕像,向这位完成18世纪史诗式长征的英雄表达中华民族一员的尊敬与追思!
由渥巴锡的雕像不禁让我们又想到寻觅渥巴锡画像的往事与近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马大正在翻阅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英文版)时,看到有一幅渥巴锡画像的插图,印象极深。在马大正和马汝珩教授合著1984年出版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和1991年出版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书中均收选了这幅画像。但我们和读者一样,对这幅渥巴锡画像存在疑惑,画中人物颇显苍老,至少有50岁以上,需知渥巴锡逝世时才31岁呀!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一书中收了一幅蒙古族首领固始汗(即顾实汗),说明是“布达拉宫壁画”。两幅画像真有极大相似之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亨宁·哈士纶将顾实汗的画像错当成渥巴锡画像了。
尽管《蒙古的人和神》作者亨宁·哈士纶在20世纪30年代曾造访新疆和静县满汗王王府,书中收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但是大家心目中还是接受不了这么一幅渥巴锡画像。所以2010年7月在和静县召开的“东归历史与文化”研讨会上安排了一项渥巴锡画像征集活动。与会的好几位蒙古族画家提交了近10幅渥巴锡画像,还有好几幅素描像。画像中的渥巴锡是一位典型的蒙古汉子。宽阔脸膛、两眼炯炯有神,是的,人们心目中的渥巴锡应该这个样子,但毕竟是艺术的创作。
2012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故宫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在筹划这次展览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渥巴锡画像现收藏在德国汉斯博物馆”,原来,几年前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德国汉斯博物馆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无意中发现展馆内保存有中国清代的人物画像,感到有些意外,在仔细观看中,发现其中一幅画像的左上角写有蒙古文,右上角则用汉字写着“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没想到几年后,正是因为他们无意中的发现,“东归英雄”才得以回归故土。
据渥巴锡画像“回归”的当事人新疆博物馆道尔基同志介绍:在得知渥巴锡画像在国外这一重大线索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想尽一切办法,几经辗转,通过电子邮件与德国汉斯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完成了展览。1771年秋,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乾隆皇帝派清宫廷画师为渥巴锡画了这幅画像,并保存于皇宫之内。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这幅画流失海外。道尔基同志深感惋惜地说。
这幅渥巴锡画像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通过写真喷绘制作而成,规格为80x100厘米,共两幅。现一幅珍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而另一幅则赠送给了巴音郭楞博物馆,将被永久性展出。
画像中的渥巴锡头戴花翎、身著朝服,但面容憔悴、神情凝重、眼神忧伤……,这也许是1771年在承德时渥巴锡的真实写照!
1943—1957年大流放纪念碑
在埃里斯塔的郊区耸立着一座1996年为纪念1943—1957年卡尔梅克族被举族流放西伯利亚而建的被巨型纪念碑。熟悉卡尔梅克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纪念发生在二战期间对卡尔梅克人一次极不公正的、可以称之为政治迫害事件。
当年渥巴锡率领近十七万部众踏上了东归故土之途,在伏尔加河流域仍然留下很多卫拉特蒙古人。20世纪苏联时期,这部分卫拉特人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创造过辉煌,在1943年12月的一天(应是28日)又遭厄运,被以通敌(德国法西斯)一夜之间自治共和国被撤消,所有卡尔梅克居民被迁徙到西伯利亚,成为“被惩罚的民族”,直到1957年才得以平反,自治共和国重建,整个民族的名誉得以恢复。
2017年4月24日,我们在夕阳的余辉下瞻仰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是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1925—2016)的杰作。他还有一件更为引人注目的作品,那就是耸立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赫鲁晓夫黑白墓碑。它是用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体交叉组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铜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托座上。赫鲁晓夫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墓碑的基座由四块花岗石板拼成。一块镶嵌着赫鲁晓夫的姓名,另一块镶嵌着他的生卒年代。涅伊兹韦斯内在解释自己创作时说:
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具体含义,我力求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念,经过生与死两种力量的不断斗争,生命、人性才会得到升华和进化。生与死,白天与黑夜、善与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虽不规则,但又是一个整体。
赫鲁晓夫墓碑那黑白相间的几何体构思,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赫鲁晓夫复杂的性格和矛盾的一生。
在纪念碑群附近还陈列有当年流放卡尔梅克人用的火车车箱,在车箱里还布置有陈列室,置放着当年的实物和大流放的文字简介和图表。
造访卡尔梅克历史研究的圣地
2017年4月24日、25日,我们分别造访了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研中心和以帕里莫夫命名的国家博物馆。在我们心目中它们都是卡尔梅克历史研究的圣地,19世纪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卡尔梅克历史研究作品都与它们有关,并给予我们的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研究以极大的帮助,获益匪浅。
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研究土尔扈特史时有三本俄文著作引人注目并实践证明是三部学术精品,它们是:
一是,М.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圣彼得堡,1884年,作者利用了俄国设在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管理局档案资料,对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后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是俄国学者第一部系统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专著。此书是上世纪70年代马大正参加《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时从北京图书馆发现并复印,后请民族研究所李佩娟同志汉译,收入《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1集,2005年又编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第二册,可惜前者是内部打印本,后者是内部铅印本,尚未能正式出版。
二是,Н.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年,作者是跨俄罗斯、苏维埃两个时代的学者,本书广泛利用档案文献,是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专著。本书汉译本由许淑明译、徐滨校,马汝珩作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三是,《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76年。本书由苏联科学院与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语言文学历史科学研究所集体编著,全书系统地阐述了上自古代下迄十月革命时期卡尔梅克人居住地区的历史沿革,对十七世纪以来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活动的叙述尤为详尽。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广泛利用俄罗斯档案文献方面,这部专著确有自己优点,本书第三、四、五章叙述时段正好涵盖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人西迁和东归的历史。此书也是马大正上世纪70年代复印自北京图书馆藏书,后请闻铭、蔡曼华、武国璋同志汉译,收入《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2集,2005年又编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等编《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第二册,同样可惜的是至今只有内部打印本和铅印本。
上述三部书中第二、三部都与我们参访的两个学术机构有密切关系。
卡尔梅克共和国国家博物馆座落在爱里斯塔市郊。
2017年4月24日、25日,我们分别造访了卡尔梅克共和国帕里莫夫国家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研中心。
卡尔梅克共和国国家博物馆坐落在埃利斯塔市江格尔大街,成立于1921年3月25日,最早称卡尔梅克自治州历史-民族志博物馆,归当时的卡尔梅克州人民教育局档案、博物馆处管辖。著名卡尔梅克历史学家、卡尔梅克学奠基人Н.Н.帕里莫夫担任第一任馆长。博物馆自1931年起正式对外开放,供参观游览。
该博物馆可谓命运多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卡尔梅克被德军占领,博物馆遭到破坏,馆内藏品或遭到抢劫,或被德军运往德国。1943年12月,整个卡尔梅克民族以二战期间通敌为由被斯大林流放西伯利亚和苏联东部地区。到1959年底,博物馆才得以恢复重建,于1960年1月1日起开始对公众开放。2007年3月,原卡尔梅克国家美术馆与卡尔梅克共和国Н.Н.帕里莫夫民族志博物馆合并,成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国家博物馆(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узе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лмыкия им.Н.Н.Пальмова)。目前,该博物馆设有卡尔梅克民族历史、民族志、文化等展厅,还有佛教器物、卡尔梅克古老艺术以及当代卡尔梅克造型艺术的展厅。此外,在埃利斯塔市以及卡尔梅克部分城镇开设有多个分馆。
第一任馆长Н.Н.帕里莫夫,正是《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年)作者,是一位跨沙皇俄国和苏联两个时代的学者。本书广泛利用了俄国档案,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汉译本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卡尔梅克历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月24日是个星期一,参观者不多,但还是有好几队中、小学生的参观队伍在老师带领下安静有序地参观。博物馆展示内容除了卡尔梅克人社会、文化、民俗外,历史部分占了参观大厅一层一个大展厅,其中阿玉奇汗的业绩占了显要地位。对渥巴锡东归之举则是用平实的言词客观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始末,少有评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博物馆当代卡尔梅克造型艺术的展厅不仅看到了反映阿玉奇汗与彼得大帝会面场景的精美的油画,还看到了土尔扈特末代公主满琳的巨幅油画。
帕里莫夫在十月革命后曾担任过博物馆馆长之职,在他去世后为纪念他博物馆改名为以帕里莫夫命名卡尔梅克共和国博物馆。
4月25日,我们造访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即是前提到的第三种学术著作《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的主编者之一。马先生一直将这个研究所视作“卡尔梅克历史研究的圣地”。
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研中心成立于1941年,成立之初,叫作卡尔梅克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归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政府管辖(即所谓“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执行人民委员会”)。1988年,该研究所划归苏联科学院,并更名为“苏联科学院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后,一度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人文科学研究所”,现名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研中心。坐落在埃利斯塔市中心И.К.伊利什金大街,8号。
研究所成立以来,把研究卡尔梅克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向大众普及卡尔梅克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研究所的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一批诸如Ц-Д.诺明汉诺夫(Ц-Д.Номинханов)、Б.Б.巴德玛耶夫(Б.Б.Бадмаев)、И.К.伊利什金(И.К.Илишкин)、С.К.卡利亚耶夫(С.К.Каляев)、Д.А.帕夫洛夫(Д.А.Павлов)、У.Э.额尔德尼耶夫(У.Э.Эрдниев)、У.У.奥其罗夫(У.У.Очиров)等享誉世界的大师级学者。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科研中心现有工作人员76人,其中54人为科研工作者,有8名博士,31名副博士。所长是年轻的博士В.В.库坎诺娃(В.В.Куканова)女士。研究所下设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部、蒙古语文研究部、卡尔梅克咱雅班智达传统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部、编辑出版部等五个部门。该研究所是世界蒙古学、卫拉特-卡尔梅克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新一代的卡尔梅克学者们正努力把研究所打造成世界卫拉特-卡尔梅克学的学术组织中心。
我们受到所长В.В.库坎诺娃女士的热情欢迎,并在其亲自带领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卡尔梅克传统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及图书馆的善本室,还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图书馆虽然不大,但专业性很强,蒙古学、卫拉特-卡尔梅克学方面的图书资料丰富,特别是善本室所藏17—19世纪有关卡尔梅克历史、人文的俄文图书丰富,对研究者言无疑是一座资料宝库。最令人印象至深的是,图书馆里明亮,干净整洁,摆在书架上的一排排的书,一尘不染,没有呛鼻的尘埃和灰尘。
半天时间匆匆,但感悟获益却多多。
其一,了解了研究所正在开展的诸研究项目。
其二,实感到图书馆虽不大,但专业特色明显,特别是善本室里收藏的17—19世纪的有关卡尔梅克历史、人文的图书丰富,对研究者言无疑是一座资料宝库。
其三,研究所一些细节无不体现对传统尊重的优良所风,在大楼二层的走廊悬挂研究所历任所长的大幅照片,并配有生卒年和简历;在图书馆里设有专架陈列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赠书,并标上赠书者姓名和照片,真是值得我们研究机构学习和访效啊!
还需一提,2016年给我签发邀请函,现已退休的研究所前所长妮娜·奥其多娃女士,4月23日晚在埃里斯塔酒店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我们有幸认识了研究所已退休的专家,弗拉基米尔·桑奇罗夫(他是兹拉特金的学生),安德列·巴德玛耶夫(1939年出生)等。
这是一席俄式卡尔梅克宴,席间我们还先后接受了“卡尔梅克真理报”主编科涅耶夫、卡尔梅克国家电视台罗莎·格里莫科娃的采访。
欢宴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才尽兴而散。
我爱埃里斯塔
在埃里斯塔市中心广场有一座约有2米高的标碑,寓意是埃里斯塔在我心中,当地人则将其称之为“我爱埃里斯塔”标碑。
埃里斯塔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府,距莫斯科1836公里。是一个以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游走于埃里斯塔街间,给我们感触最深的是这是座多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的城市。
卡尔梅克人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的文化信息遍布城市四方,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和藏传佛教庙宇建筑华丽宏伟,在市中心广场还建有一座碑亭,内置有高近3米的转经筒。
卡尔梅克人是蒙古人一员,对蒙古文化的热爱是他们的民族本性,在埃里斯塔市街头可看到多座近现代当地的蒙古文化名人的塑像。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看到含有汉文化因素的碑,如老子雕像,汉人形象的老人雕像,在市中心广场还建有明显包含汉文化因素的长廊、牌楼,……
我们还发现一座普希金的雕像置于一幽静的街心花园之中。俄罗斯文化的基因也同样存在。
但是,在埃里斯塔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浸润着俄罗斯人特有的英勇主义传统的二战纪念碑群及碑前的长明灯火!这里的英雄纪念碑当然比不上莫斯科俯首山胜利广场上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柱,伏尔加格勒的祖国母亲纪念碑群,圣彼得堡的英勇保卫者纪念碑那样气势宏伟,显示着胜利者的豪情和霸气。但气势不凡,充满胜利者豪情和霸气,这一点是相通的。置身其间,让人震憾!
还有二则在埃里斯塔的见闻值得记述:
一是,4月22日,我们抵达的当天晚上,在当地学者巴兹尔陪同下先观看了一场自治共和国卫拉特艺术团的演出,又赶赴自治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参加纪念“世界读书日”活动(今天正好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读书日’)在国家图书馆一间不算大的会议里,穿着礼服的男女嘉宾有近百位,我和阿拉腾奥其尔作为异国客人,进入会场时还受到掌声欢迎。嘉宾围绕“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生命”的主题作了热情讲话,活动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包括小型合唱,民族乐器演奏,诗歌朗诵……,天公不作美,演出进行际,突然停电(据说是全市停电),在煤汽灯和无数手机灯光照射下演出照常,特别是一群孩子的诗歌朗诵,雅气的声音、庄重的神态,让马大正瞬间时空穿越,想起60余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学生时,曾参加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的现场情景,心际中一个纯、一个静我以为是共同的。这样场景在当今的中国已是十分陌生的了,可在埃里斯塔仍是生活的现实,真让人感慨!
另一是,4月24日中午,午餐后,我们在埃里斯塔市中心步行街散步观光,只见有披着披肩的一男一女青年肃立在一处房前,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宗教徒在募捐吧,问陪同我们的巴兹尔先生,“这不是宗教徒募捐行为,‘5·9’胜利日快到了,每年这个日子之前之后一个月当地中学生有一项活动,在卫国战争时获得英雄称号的战士旧居前站岗纪念,以示对英雄的怀念,对光荣传统的尊重,一次2人,一小时换岗一次。”巴兹尔还说:“当年我当中学生时也参加过这项活动!”听到此回答,我提议赶快返回照相留念。我在想不忘历史、永怀先烈的传统,真是值得学习,记住英雄、不忘历史,从娃娃抓起,多好啊!
陌生的查干阿姆
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4月26日,我们从埃里斯塔车行阿斯特拉罕途中第一站就在查干阿姆稍做停留。巴兹尔先生说,这里有阿玉奇汗纪念碑和加班沙拉勃纪念碑,值得一看。
是日上午11时余,车抵查干阿姆(Цаган Аман)。查干阿姆距离卡尔梅克首府300公里,城区不大,街上空旷无人,是卡尔梅克通伏尔加河的唯一通道。两座雕像相距不远。
阿玉奇汗的骑马雕像耸立在一街心花园中。
阿玉奇是土尔扈特汗国开创者书库岱青之孙、朋楚克之子,生于1642年,卒于1724年2月19日,享年81岁,执政50余年。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历史上著名的汗王,他执政期间,由于他卓越的统治才能、高超的外交策略,以及辉煌的武功战绩,不仅造就他本人一生的丰功伟业,使他成为当时遐迩闻名的游牧汗国领袖,同时也将土尔扈特国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托忒文历史文献《卡尔梅克诸简史》中曾对阿玉奇汗作过如下评述:他一生“帮助了许多国家和部落,没有让卡尔梅克人衰弱和受欺。让他强盛者尊重他,与他相衡者惧怕他。名义上是俄罗斯臣民,但一切事情均由自己做主,所以,他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中最有威望的一位”。
加班沙拉勃塑像则伫立在一居民楼前,塑像高近2米,塑像呈坐姿,加班沙拉勃面带忧郁,作沉思状。
凡是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有一部托忒文的历史著作《四卫拉特史》,我们眼前的这位加班沙拉勃就是《四卫拉特史》的作者。
据加班沙拉勃在《四卫拉特史》自述,他是土尔扈特诺颜和鄂尔勒克第六子博勒浑后代,其父和硕齐,是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的堂兄弟。本人是额木齐,即医生,准确说应是一位掌握医术的僧人。由于阿玉奇汗的要求,加班沙拉勃在1737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此时距离阿玉奇汗逝世已13个年头了。1724年阿玉奇汗逝世,导致汗国内讧不断,与准噶尔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周围一些部族也不断袭扰,掠夺土地和居民,俄罗斯也加紧对汗国的控制。《四卫拉特史》即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成书。加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成为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创作于18世纪中叶的“四卫拉特史”典籍。
现在,查干阿姆的居民是卡尔梅克巴嘎绰呼尔部族,据巴兹尔老师讲,当年他们是阿玉奇汗的属部。这就不难理解,阿玉奇汗的雕像为什么会立在与阿玉奇汗牙帐,极盛时期土尔扈特汗国政治中心马奴托海相距百余里的查干阿姆。
在伏尔加河渡口
4月26日,奔赴阿斯特拉罕途中第2个参观点是伏尔加河渡口。我们先后到离查干阿姆不足2—3公里的两个渡口走访。
一处是已被废弃的查干阿姆渡口,此处伏尔加河河面宽不足百米,我们漫步在已显荒芜的岸边,马大正偶然发现一块呈不规则圆形的砾石,拾起,拂去沾在上面的泥土,发现石块一侧是白色,据多年拾石经验,细观察也许能发现异样图案。待返回宾馆洗净后反复观察,此白色处竟呈现出一个明显女性图像,大喜之余,遂将此石命名为“伏尔加美女”!实是意外之收获。
另一处渡口,离查干阿姆渡口沿伏尔加河车行约20分钟,抵达嘉米央渡口,为等渡轮启航,我们在渡口餐厅美食了一顿伏尔加河鱼餐包,并漫步渡口周缘,河岸宽阔,杂树丛生,老树根遍地,我们喜言,这些老树根拉到国内加工后是可卖大价的木根雕工艺品啊!此处伏尔加河面宽百米以上,渡轮也就15分钟就到了河对岸。
据当地老一辈人传颂,嘉米央渡口正是当年土尔扈特人东返的一个主要渡口。渥巴锡所率东归队伍共三万三千三百六十余部,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渥巴锡所属约二万余户,十一万余人,是东归队伍中主要部分。其他各部在千户以上的有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舍楞等部。上述起义东归的队伍只限于伏尔加河东岸的土尔扈特部众,而居于伏尔加河西岸的部众并没有跟随渥巴锡一起东返,据汉文史料记载:“是岁(指乾隆三十五年——引者),冬温,河(指伏尔加河——引者)冰不冻,渥巴锡不能河此人户”(何秋涛《塑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附始末》)。也就是说伏尔加河河面未冰冻造成居于河西岸的部分土尔扈特部众未能加入东归队伍。今日我们置身于此处渡轮上,望着平静的伏尔加河河面。遥想246年前1月的历史往事,唯有感而慨之!
当然,经我们研究,伏尔加河河水未冰冻实非造成西岸部众未能参予东归的主要原因。当时游牧于西岸的是与渥巴锡政见不同的和硕特、杜尔伯特台吉扎木扬、扬德克,以及敦杜克夫家族所辖之部众,这部分王公贵族并不同意渥巴锡的东归主张,甚至还出现像扎木扬那样的告密者。因此,西岸各部王公不会起而响应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渥巴锡出于对这些人的疑虑,不把东归义举的准确信息向他们透露,也是正常的兵家之道。
扎木扬村及扎木扬其人
4月26日在奔赴阿斯特拉罕途中第三个点即是扎木扬村,在扎木扬渡口渡过伏尔加河,就可以来到建于19世纪的和硕特庙(Хошеутовский хурул)。
扎木扬村是当年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部贵族扎木扬的游牧地。
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以土尔扈特部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王公贵族(包括和硕特、杜伯尔特的一些家族),在俄国的日益加紧控制下,其内部早已发生分化。以敦杜克夫家族为代表的极少数封建王公,已完全东正教化,俯首听命于俄国政府的指挥;还有一些贵族,他们原不是渥巴锡家族的嫡系亲信,或者在争夺汗位斗争中与渥巴锡家族发生过矛盾冲突,因而他们支持俄国所采取的限制渥巴锡权力的措施,和硕特部的扎木扬就是这部分王公贵族的一个突出代表。扎木扬与渥巴锡父敦罗布喇什互娶对方姊妹而联姻,扎木扬在其妻达那拉(即敦罗布喇什之妹)死后,歧视达那拉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自己表兄渥巴锡寻求支援,因而引起扎木扬不满。早在1767年2月28日,扎木扬就写信给别克托夫,密告渥巴锡准备东返。接着在1768年至1769年间,4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领主已决定尽快渡过伏尔加河去中国”。[注]按扎木扬4次告密信的时间为1768年11月6日;12月2日,1769年2月3日;3月31日。见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0—42页。然而,扎木扬与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为人所共知,故别克托夫对扎木扬的密告并未予以重视。但是,在1769年3月间,别克托夫截获一封写给在阿斯特拉罕任职的土尔扈特籍法官的信。信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述说舍楞和其他台吉打算迁往准噶尔”[注]《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纲》,第215页。。这一信息自然要引起老谋深算的别克托夫惊恐与不安,但由于他于1767年即已被解除主管土尔扈特事务的职务而无法直接过问此事。他将此信送交给当时主管土尔扈特事务的基申斯科夫上校。此人是一个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军人,且与别克托夫一向不和,根本不相信别克托夫转来的情报。在他看来,别克托夫的这一做法,是为了排挤自己而有意制造混乱、扩大事态。基申斯科夫根本不相信在俄国强大压力和严密监视之下渥巴锡敢于组织其部众东迁,他曾用轻蔑的口吻对渥巴锡说:“你必须明白,你只是一头用链子拴着的熊,赶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不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注]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4页。
基申斯科夫骄横傲慢的态度,以及他与别克托夫的矛盾,恰好为聪明的汗国首领渥巴锡所利用。渥巴锡一方面巧妙地与基申斯科夫周旋,致使在渥巴锡身边呆了3年的基申斯科夫“什么也没有觉察到”[注]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2页。。同时渥巴锡又几次向俄国政府诉说:“尽人皆知,他和扎木扬不和,所以扎木扬如此中伤他。”[注]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1页。另方面,渥巴锡于1769年至1770年应沙俄政府之命,亲率士兵2万人,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借以麻痹沙俄当局。正由于渥巴锡运用一些巧妙计谋,致使俄国政府对渥巴锡的政治态度深信不疑。所以当别克托夫于1770年4月15日向政府报告,说土尔扈特人早于1767年即已准备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并要求把渥巴锡等汗国首领们“传至阿斯特拉罕,严加审讯”[注]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56页。时,俄国政府却于同年8月3日发出诏令中指出:“对他们(指土尔扈特人—引者)所持的一切猜疑都归罪于扎木扬领主的玩弄权术”[注]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57页。的结论。
和硕特庙
和硕特庙是参加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的英雄、和硕特兀鲁思首领色热卜扎布图门(Серебджаб Тюмень)倡议修建的,其设计者是著名僧人和历史学家巴图尔-乌巴什图门(Батур-Убуши Тюмень),该寺庙于1814年开始兴建,至1818年竣工。该庙于20世纪20年代被关闭,30年代被用作俱乐部,50年代却被当做仓库。1957年,卡尔梅克自制共和国得以恢复,但是和硕特庙以及和硕特庙所在整个地区被划归阿斯特拉罕州,和硕特庙也遭到破坏,只剩下主体建筑的中心殿宇。2004年,在卡尔梅克出现了恢复重建和硕特庙的呼声。
啊,阿斯特拉罕
经过一天车行,4月26日下午15时余抵达阿斯拉特罕,下榻在伏尔加河畔的路标酒店。
阿斯特拉罕市是伏尔加河三角洲上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州首府,是伏尔加河流经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她始建于13世纪,1460—1556年为阿斯特拉罕汗国都城。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的军队占领阿斯特拉罕,并将其纳入到莫斯科公国的版图,成为俄国南方的前哨。1722年,俄国出兵远征波斯期间,彼得大帝曾在阿斯特拉罕坐镇指挥,但兵败而归。今天,在阿斯特拉罕市的滨河大道上耸立着彼得大帝的巨型雕像。
我们来到阿斯特拉罕是基于这个城市与土尔扈特汗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的交集。
当我们散步在偌大的市中心广场上,仰望巨大的古罗马造型的塑像,耳际却响起了战马的嘶鸣,骑士的怒吼。啊,时光倒流到373年前的1644年。1643年,率领土尔扈特人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的创建人和鄂尔勒克将营地迁移到阿斯特拉罕附近。1644年和鄂尔勒克率领队伍,越过伏尔加河西岸向西南推进队伍,进逼阿斯特拉罕城,在围城战斗中土尔扈特人伤亡惨重,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可以说阿斯特拉罕是土尔扈特人的伤心之地。当年的古战场早已荡然无存,战斗场面的腥风血雨也仅留存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里,我们只是在沉思遥想回归现实:蔚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广场的喷泉和鲜花,远处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坐着小宝宝的童车款款而行……,和谐与宁静呀!
当我们走进金壁辉煌的有小克里姆林宫美称的当年阿斯特拉罕衙署所在地——小克里姆林宫。阿斯特拉罕克里姆林宫——是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建筑和军事工程艺术的杰出代表,是俄罗斯最南端的一座克里姆林宫。1980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是阿斯特拉罕州历史与民俗博物馆。
我们走过一栋已粉刷一新的白色大楼,虽只有一层,但楼正面有七个门洞,一字排开有将近20米之宽,此楼大门紧闭,不是开放参观点,在楼前左侧有一岗亭引起我们注意,岗亭显然是当年守卫此楼的门禁哨兵的值勤点。这栋曾发生过什么?没有留下史载,我们不知道,也无时间查,却引发出我们(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和巴兹尔)共同的联想:当年渥巴锡的仲兄萨赖作为人质居住在阿斯特拉罕,是否与此楼有关?研究者的我辈知道,18世纪40年代土尔扈特汗国王敦罗布喇什,曾多次交涉要求俄国政府释放作为人质,而幽禁于阿斯特拉罕的儿子萨赖,敦罗布喇什于1743年9月6日致信沙皇政府:萨赖“年幼孤身,而且以前的几任汗王从来不曾交过人质,因而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他要求沙皇下令放还他的儿子,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俄国)政府已确定向卡尔梅克汗要人质的制度,就认定无需加以改变了。”敦罗布喇什的要求遭到俄国政府拒绝后,他“企图从俄国的囚禁中把萨赖劫走”,但由于俄国看守严密,此举没有成功。(均参见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萨赖于1744年作为沙俄的人质,死于阿斯特拉罕的软禁生活中,萨赖之死,使敦罗布喇什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同时也促使他对俄态度由忍让急剧地转向对抗。到了18世纪60年代,由于俄国控制空前加强而造成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对渥巴锡来说,其重返祖邦的思想变得更加迫切与渴望,而恰在此时,俄国政府又“要求渥巴锡交出他的一个儿子作人质,同时还决定要求交出300名显贵名门的子弟”。俄国政府的这决定,不能不引起渥巴锡对往事的回忆,他的仲兄萨赖正是作为沙俄的人质,于23年前死于阿斯特拉罕的幽禁之中。新仇旧恨使他再也无法忍受沙俄的政府的“征兵求质之烦”!
渥巴锡之仲兄作为人质死于阿斯特拉罕,史载明确。具体拘禁之地、死亡之地,未留下史载,但人质不是普通的囚犯,将萨赖安置在作为当年阿斯特拉罕衙署所在地的小克里姆林宫、居住在这座白色大楼里,似也不失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若如此,小克里姆林宫也是土尔扈特人又一处伤心之地。
小克里姆林宫既然是沙俄时代阿斯特拉罕衙署所在地,这里同样也发生了诸多与留居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相关的政治大事,诸如:
1771年10月间,叶卡德琳娜二世颁布了“关于废除土尔扈特汗国的命令,同时取消了‘汗’和汗国总督的称号”。(参见《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由于这项命令的实施,建立于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汗国已不复存在;
1771年10月后,阿斯特拉罕省长办公厅下设了一个专门管理机构——特别管理处,1772年,在这个“特别管理处”内又设立了一个审理卡尔梅克人本民族案件的法院——扎尔固。到1786年,阿斯特拉罕省长波将金下令关闭了这个扎尔固,将其原来审理本民族案件的职能转交县级法院受理。
1797年,俄国政府在阿斯特拉罕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以上一系列措施使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彻底失去了政治独立地位,沦为俄国政府监督下的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以上的一道道政令、一项项举措,阿斯特拉罕省长即是执笔者,也是制定者!
当我们在之后参观阿斯特拉罕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历史陈列室时,在历届阿斯特拉罕省长的画像,政绩的说明前,可看到18世纪后卡尔梅克人社会的变迁,这应成为我国学者土尔扈特历史研究的一个个新的切入点,我们期待不久就有这方面新作面世。
我们在阿斯特拉罕二天三夜(4月26日—28日)在寻觅土尔扈特人历史遗痕之余,还让人感悟了当今阿斯特拉罕城市文化底蕴。
感悟之一,英雄主义的历史传统。
城市中心广场仍保留有耸立的列宁雕像,连同花岗岩底座据目测高达4米,同时小克里姆林宫一侧建有无名烈士纪念碑,碑前是永不熄灭的长明灯火!忘记历史意味背叛,战斗的俄罗斯民族的这一特性值得世人敬仰。
感悟之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当我们白天和夜间几次在河滨大道上散步,所见其景是初升的朝霞、落日的余辉;百年的古树、多姿的雕塑,所见其人是垂钓的老人、漫步的情侣、骑马的游客,……这里人们正在尽情享受着生活的美!
我们以为,对英勇历史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应成为每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基调,对此,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努力之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