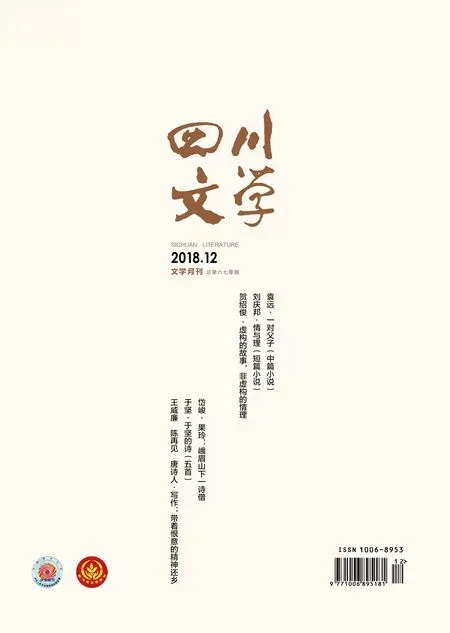人在山水间
身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巴蜀人,自生命呱呱坠地伊始,便注定要与自然山水结下不解之缘。我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严谨,存有某些偏失,严格的说法应当是能够同自然山水结下情缘的,并不仅仅只是巴蜀人,大凡生活在各种丘陵、山地、高原的人,只要是依山傍水,或者是距山水不远,都会自然而然地要与自然山水为伴,要与自然山水亲和,乃至与自然山水达成生命的体认和灵魂的共契。这是自然山水给予我的幸运,也是它给予人类共同的幸运。
一
在我的关于山的最初概念里,并不只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山体、山峦、山峰等这类形象符号的指称,同时也是对一座名叫山城的城市的情感蕴含,因为那是除了父母之外的我的另一个生命源头,是存储在自己身体内部某个角落里的一个怎么都无法消除的心相。在我年幼的时候,作为技术能力拔尖的父亲被单位选中,成为第一批积极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号令的一员,于是他带领着我们全家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地向北进发,最后落脚于川北的这座中等城市。
我们的住家被安排在一个四合院里,距离大院的两千米之外,就是一座座如波浪起伏的群山。因为那时年龄还小,生命能力不足以登上山巅,就只能站在一个高处远远地对它进行眺望和想象。历经几度春秋的洗礼,渐渐成长为一个愣头愣脑少年的我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欲意进入山中一探究竟,看它的内腹里到底装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一个深秋的午后,当我和一群小玩伴一路兴冲冲地爬上去,山里的景象令人很有些失望,因为除了一座寺庙、一间道观、一个读书台、一排摩崖石刻,就是满地枯黄的落叶和几块光秃的稻田,唯有那个从嘴里流出一股股清冽山泉的石蛙,才顿觉有了一点儿好玩的兴味。这便是一个没有生命积淀和人生内涵的少年之于山的初识。许多年后,当我慢慢知道这座山为川西北第一圣境,那座寺庙是鼎鼎大名的西蜀子云亭,那个读书台是汉代文豪杨雄当年读书时所用,那排摩崖石刻是大唐著名的雕刻艺术,就很为自己少年时代的无知而感到特别羞愧,如果一个人连他所在城市的这些著名历史都无从知晓,他怎能成为这个城市中的合格市民。
我的第一次富有生命意义的山行,品味到的并不是登山的身体快感和生活乐趣,也不是站在山巅领略群峰逶迤、大地苍茫的精神愉悦,而是一种直入心底的痛苦磨砺和艰难。那时刚刚从一名高中生变身为一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下乡的地点是一个蜗居在二十公里开外被一片丘陵环抱的村子。因为交通运输相当落后,根本没有直达的客车,只能步行前往,我与壮年的父亲便背着几包必需的生活用品早早地从家里出发,像两只负重前行的蚂蚁,步履缓慢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在距离那个村子的几公里处,我们必须翻越一座拔地而起,有三百多米高和近千个石阶的高山,站在山脚举目仰望,蜿蜒绵长、逐级上扬的石阶就仿佛是一架通往太空深处的天梯。历经了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年轻的身体本已十分疲惫,炽烈的夏日在没有一朵云彩的苍穹肆无忌惮地宣泄,被烘烤得全身汗水禁不住地汹涌外流,四肢更加软弱乏力,腰酸背痛更为强烈,所剩无几的心力和意志也正在一步步地消失殆尽,背负的东西似乎越来越沉重,拾级而上的每一步都异乎寻常的艰难,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法言表的超强重压,使整个生命几乎达到坍塌和崩溃的极限。很多年后,当我在批阅一个学生的散文习作,文中细述他上初中后便每周都要两度翻越三座壁立千仞、陡峭险峻的高山才能抵达那所乡镇中学,倾情诉说他时常迎着晚霞出发、摸着星月归家的求学历程时,才顿觉汗颜和惭怍,我的那次所谓的艰难山行,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每个人山行的艰难都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存在,你所亲历的和体验到的未必就是最艰难的。


二
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已经非常习惯地这样思维——将山水进行合称,尤其在绘画艺术领域。这样的话语表达说明:在人类的情感意向和文化认知里,山与水从来就是一种合一的存在,是一个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失去了山的水,或者失去了水的山,都将是一种不完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喜欢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既能欣赏到山的伟美,又可品味到水的柔美,且在山水的共契中生发人生憬悟。如果说山是水的骨骼,那么水就是山的灵魂。探寻和发现水的灵魂,便是人在山水间行走的另一个使命。
在已然相当模糊的童年记忆中,那条默默流淌了很久很久的世界闻名的大江,似乎就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只需穿过一条幽深狭长的小巷和那一间间十分简陋而低矮的民居便可抵达。不知是因为自己刚刚学会在大地上摇摇晃晃地跑动,还是被母亲时时刻刻逡巡的眼光所看住,抑或是从外面不断传来些许不知姓甚名谁的生命被湍急的江水卷走的消息的缘故,即便是在长姐长兄带领下一起玩耍,也是很难得随随便便地去走进和亲近那条大江的。所以对于那条声名赫赫的大江流的最初的印象和了解,大多是片言只语、一鳞半爪的,就像一个历史片段,根本无法形成一种完整的系统性的认知建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反倒是那个热闹非凡的码头,成天船来船往、上客下客、卸货装货,一派忙忙碌碌的样子,站在石堤上远远望去,就有如在看一场热闹又嘈杂的人间世态。只有当一艘艘装满乘客或是货物的船随着江流渐渐离去,又浑然不知它们欲意驶向哪一个远方抵达哪一个码头,小小的童心里才顿觉有些失落和茫然,如轻轻摇漾的涟漪一般。举家迁往川北后,在住家东边的千米之外也有一条流淌了很久很久的大河,只是它远没有那么大的名声,流水也不是浩浩汤汤的,更失之于一个热闹非凡的码头,唯有的是寂寞无主的水自流,流淌出或有波幅或成圆弧的非常细腻和富有动感美的曲线。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人的内心便被这种从容淡定又优雅美韵的水之曲线引领着,一步步地走进琳琅缤纷的水世界,也由是开启了我在江河湖海中行走的漫长旅程。
大概是因为江河就在身旁,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江河,同时也包括了溪流、池塘、水库等等,是一种赋予了多元水文化意义的界域。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我少年时代的水之旅程变得十分容易。能够拥有良好的水性,可以在江河里恣意地畅游,无疑是少年时代最大的快乐和最荣耀的事,因为这会令那些不会游泳的旱鸭子玩伴们尤为歆羡而又特别妒忌。除此而外,便是一些与水相戏的乐趣。虽然少年的时光已然有些久远,却仍能十分清晰地记得那时与水相戏的一些细节和场景:我们不是将做好的纸船一只只地停放在小溪的上面,定睛地注视着这些轻灵的小白帆在流水里不由自主地漂移、在水涡中无法自控地旋转;就是在河滩上找来一大堆扁圆形的卵石,有力地将它们一个个掷向平静的江面,看谁打出的水漂最多,谁扔出的线路最长,谁能击中水面的游鱼;或者是用一块宽大又厚实的木板,几个玩伴同时坐在上面划水前行,先落水的是一副惊慌失措的快乐,坐在木板上被不停摇晃的则有一种惊险刺激的愉悦。然而,当时间以其不可撼动的力量坚定地朝前奔走时,少年岁月里的那些畅游快乐和戏水乐趣,如一群随季节迁徙的鸟儿纷纷远去,忽然而至的青年时代再也不会被这些简单的充满童稚气、游戏性的娱乐和快慰所吸引,便将渴望的眼光纷纷投向远方。
第一次领略到迥异于一般江河并富于多元形态的水美和水的魂灵,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在被人们盛赞为人间瑶池的黄龙寺和童话世界的九寨沟。迈着滞重的脚步登上近四千多米高的黄龙之巅,人的气喘吁吁还没有消退,散发出冷意的展阔坦然的五彩池便夺眶而入,突兀而强烈的刺激不仅使人的眼睛一阵错愕,内心更是迸射出一声惊呼:它简直就是水美的绝唱,是最为璀璨的水的精魂。待稍稍淡定后才慢慢厘清,是因为它彻底颠覆了一个人对于水的色彩的惯性认知,以为水都不过是一种青色或绿色的存在。人几乎是被这种魂魄的魅力牵引着游完五彩池的,至于它究竟是由哪几种色彩构成,及至今日都有些迷糊不清,但它所凸显出的那种特别鲜明的异质性水美和水魂,却从此深深地烙在人的脑海里。九寨沟里的五彩池,显得没有那么冷艳,更多了些许柔美和梦幻的韵致,它静静地安卧在重重叠叠的山峦和起伏错落的松柏间,高原的阳光穿过浓密的树丛一束束地投射在由碧蓝、天蓝、橄榄绿、橙红合成的池中,从原始森林徐徐吹来的凉风轻轻地拂抚着池面,光影、水影、色影、树影融为一体,盈盈地闪烁出极为梦幻的水的美感,令人仿佛置身于水的仙境一般。
作为水的色彩美的一种经典存在,无论是黄龙寺的还是九寨沟的五彩池,无疑都是最吸引游人聚集和生发惊叹与赞美的所在,除此而外,就是这两个自然风景区所呈现出的那种由海子、瀑布、溪流、水滩共构的多样态的水美特质和水魂内涵,或是张扬出宽阔与深邃,或是挥洒出豪迈与激情,或者是流溢着宁静与温婉,或者是蕴含着庄重与冷傲。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人们将各种美妙词汇和美丽想象不断地倾注在它们的身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和丰厚了其水文化的内蕴。然而有一种水美或者水的灵魂,却在我们的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或漠视。在原始森林下面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水潭,一群身体几近透明的鱼在里面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将自己的手伸入到水中,试图同这些小生灵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彻骨的寒冷便迅疾地浸透了人的整条胳膊,那种手指的突然僵硬、血液的瞬间凝固,令常常自诩有较强生命热度、不惧任何寒冻的我终生难忘。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当地人说:只需再有几分钟,你的这只手就可能报废了。内心顿生出几分莫名的恐惧。虽然已先知道这是刚刚从原始森林流淌下来的雪水,却没有想到它竟然能够具有如此的寒冷,可以在短时间内威胁到人的生命,看来人是必须有所惧怕的,有惧怕的人才会慢慢生长出敬畏之心。注视着那个小水潭,脑海里禁不住闪出这样的生命憬悟:极寒是另一种水美的高度,也是其灵魂抵达的深度。
正是在那个瞬间,一种有关水美和水的灵魂的更为深沉的思索,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来来回回地萦绕和盘旋:当河流从一种徐缓的水平流动突然换变为一种急速的立体坠落,它在瞬时之间的这种惊世一跳,以彻底砸碎自己的方式来意图表达的,难道只是为了激起几朵浪花,或者仅仅是变换一下自己前行的方式?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如此,因为它并没有显示出自己在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但在我的理解和认知中,河流的这种纵身一跃,并不仅仅只是展示出了水的物态存在及其前行方式的变化,更是对于水美和水的灵魂的一种精神意义的重构。正是基于了这样的理解和认知,人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了一种更为充实也更加愉悦的东西,再细细回望黄果树瀑布对面那些构筑在峭壁上的一间间民房,感受到的已不再是几许的危险,而是由衷的羡慕:它们是多么的有福祉,能时时刻刻同黄果树瀑布遥相对望,能终日欣赏到伟岸的水美和高瞻的水的灵魂。
三
在人类已有的历史记忆和经验认知中,所有的江河无一例外的源自雪山和冰川,或者地表之下,或者苍天之上,也都可以表征为一种在大地的阶梯上逐级而下的流动,那些在行径途中偶然发生的拐弯和迂回,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并非左右得了水的前行脚步,于是水在流经高原、山地、平原的途中,源源不断地进入人类的生存视野。饮水而生是人类的第一选择,人类自其诞生以来就无法抗拒水的巨大诱惑,其他的生命种类也不会例外,所以人类只能臣服于水的定律和制约,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整个人类世界历史前行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有了水的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重要角色,以及有了同水的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本质关联,人类才具有了存活的可能及其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存在展示,才最终一步步地实现了人种的不断繁衍、人丁的愈发兴旺、族群的更加壮大,以及对于人类生命历史进程的文明缔造。逐水而居是人类的又一重大选择,大凡具有丰沛水资源的地方,常常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开始的所在,许许多多的古代城郭和古代村落,莫不是因为有了水的缘故才固定下来,并在漫长历史岁月的反复洗礼后成为现代意义的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那些在河流改道后因为彻底失去了水的供养和滋润的地方,则慢慢地演变成一座遗址或是一处废墟。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水的历史,人类的生命存在其实就是水的存在。
作为与水同在也与水同行的山,既是自然世界里的另一种生命形态,又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重要依附。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初的人类大多是一个个的山民,他们不仅选择山上的洞穴居身,而且以山里的林木果实为食,甚至还要与山中的各种猛兽进行殊死的较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这个立体符号标识显著的山里行走,不是在仔仔细细地寻找,就是在反反复复地勘探,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生活伴侣和生命依附,乃至于慢慢发展成为他们对于土地的开垦、对于稻麦的种植和对于生儿育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或许是为了彻底摆脱猛兽们的袭扰和威胁,也或许是因为山上有限的食物不足以供养生命的存在,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人类主动选择了对于山的群体性撤离,纷纷把自己的定居迁往草木茂盛的牧场、水源丰沛的河畔、土壤肥沃的平原。人类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山,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常常牵挂着山,并怀揣着不同的情感和心理重回山中,或者是探访那些隐藏在深山的自然秘境,或者是展开一段寻找内心宁静的旅程。
步山水而幽远,枕山水以抵达,这不啻是一个人的最大幸福之一。我缱绻这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