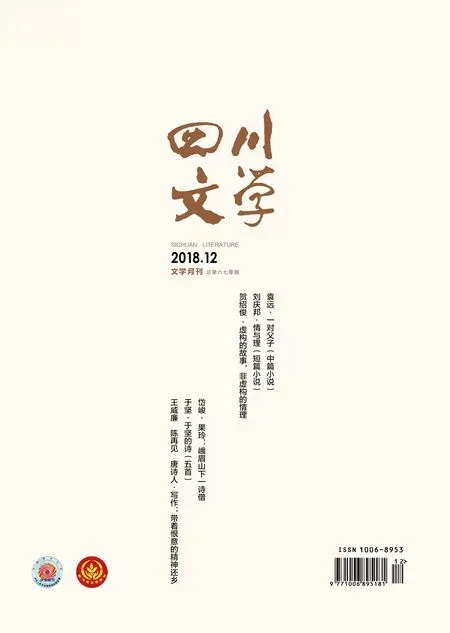虚构的故事,非虚构的情理
——读刘庆邦的《情与理——叔辈的故事之二》
刘庆邦打算写一批叔辈的故事,《情与理》是其中的第二篇。既然是写自己叔辈的故事,就有两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其一,他所写的对象都是自己的亲人,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与亲人们的交往是留在他心中最真切的记忆,显然这些真切的记忆是他写小说的基本资源。但他写的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他要以虚构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人物。其二,他所写的人物都是他的叔辈,是他的长辈,刘庆邦是一位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作家,他会以一种恭敬、认真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叔辈,他在小说中倾诉的是真情,遵循的是常理。虚构的故事,加上非虚构的情理,是刘庆邦成功的秘诀。
虽说小说家写小说是从现实生活中取的材料,虚构也能追溯出原型,正如鲁迅所言,他的人物也来自生活,但他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刘庆邦写小说多半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但这一回他要专门写写他的叔辈,每一篇小说明确就是写他的一位叔叔,比如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他唯一的一个亲叔叔。那么再采用鲁迅所言的“杂取种种人”的方法就不合适了,他要是给自己的亲叔叔找一张北京的脸他的亲叔叔也不会答应呀!这一回他要让人感觉到他写的就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可以断定,小说中不少细节都来自他的真切记忆,都是真实的。但如果百分之百的真实,那就不是写的小说,而是在写纪实作品了。但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来自真实,却能超越真实。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就是以超越真实为写作目标的,他要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方式创造一个文学的世界。刘庆邦就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因此他即使写自己的叔辈,他也要把人物置于虚构的文学世界之中。当然,这一次他不是以“杂取”的方式来虚构,而是以“发酵”的方式来虚构,即以他的真切记忆为引子,在记忆的逻辑基础上生发出符合人物性格的故事来。另一方面,他还要将虚构隐藏起来,给人感觉他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以自己娴熟的叙述能力做到了这一点。
刘庆邦是一位特别看重伦理道德的作家,因此当他写叔辈的故事时这一点肯定会凸显出来。乡村是一个伦理社会,亲人之间的关系都遵循着一定的伦理要求来规范其行为举止。伦理要求是固定的,但亲人们的性格脾气是各不相同的。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套用托翁的话来概括刘庆邦所写的叔辈故事,那就是:伦理要求都一样,但每一个叔叔的遭遇却各不相同。让刘庆邦难以忘怀的正是叔叔们因为各自性格脾气的差异而带来伦理方面的问题。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举止古怪的叔叔,他古怪就古怪在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得罪了众多的亲人和近邻,连他自己的父亲都感到颜面尽失。这样一个古怪的叔叔自然也是不把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放在眼里的。比如父亲去世了,叔叔先是偷吃了盖斗馍,而后又躲起来不参加父亲的下葬。叔叔的性格具有极强的叛逆性。叛逆性在作家的笔下往往被当成英雄人物的基本品格。可惜叔叔辜负了他身上这点能够成就为英雄的叛逆性。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有过当英雄的机会,比如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但他并没有干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见成就英雄光有叛逆性是不够的,因此叔叔的叛逆性使他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其结果就是破坏了本来平静、和睦的人际关系。刘庆邦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肯定不会仅仅停留在客观讲述叔叔的这些古怪故事上,他一定要以叔叔为基础,建构起一个文学世界来。那么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文学世界的呢?我以为,“情与理”便是这个文学世界的核心。所谓情,是说面对一个悖常情、逆常理的叔叔,仍然舍弃不了那一份亲情,仍然把他当长辈对待。刘庆邦在叙述中渗透了这种复杂的亲情,这是一种痛惜之情,也是一种无奈之情。所谓理,则是指维系着乡村人伦正常秩序的基本规矩,因此他将讲故事的重点放在写叔叔那些违背常理的行为是怎样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撕裂。叔叔的行为一再地伤害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但亲人们并没有采取与其强暴对抗的方式,而是在伦理规则上做适当的调整,试图以人伦亲情感化之。这种方式在传统社会里还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尽管叔叔的行为对正常秩序造成了破坏,但人们经过调整和妥协还能够将撕裂开的口子修补好。但最大的破坏来自社会系统。因此小说的最后写到了叔叔在“文革”中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使“我”一家遭到极大的伤害,而且也彻底扯断了“我”及其家人与叔叔之间的亲情纽带。小说的结尾很有意思,面对叔叔带来的恶果,“我”不禁嚎啕大哭。这种哭既包含着对叔叔的指责,更包含着对那个荒诞年代的指责。正如刘庆邦自己所说的,他写叔叔的目的就是要“写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